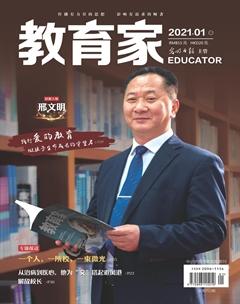暮色將至巢非巢
秦子瀚
巢非巢,雀鳥安可度此宵。
記得疫情暴發以前,對面的小區里大概是養了一群鴿子的,只是近幾日忽然覺得少了什么,這才發覺這群“鄰居”不見了,或是被撲殺了,或是被送走了,總之肯定是被處置了。但凡生活中常見之物有了丟失或者更變都易使人不安而焦慮。而今鴿子走了,我也漸漸不安而焦慮地懷念起來,總感覺少了什么,讓我染上了一種患得患失的煩躁,大抵就像口渴的時候順手去拿右手邊的茶杯,但摸索一陣之后發現桌上哪有什么茶杯。那是一種異常別扭的感覺。
對于那群鴿子最清晰的記憶莫過于暮色將至時候,或灰或白或花各色鴿子結成的鴿群,在邊上一兩個小區的上空打著旋子,一圈又一圈,像是水盆里放水時的漩渦,越來越小,慢慢靠近對面頂樓的家。雖然記憶里像是在放默片,但想起時卻好像可以聽見鴿群撲棱翅膀的聲音,牽動人心,在薄暮時刻勾動著人們回家的沖動。這聲音不是整齊劃一的,而是錯落有致、此起彼伏,像是海邊的浪花,一層疊著一層,將那歸鄉的、思家的情緒像蠶絲被一般疊成厚厚一床。好像聽到這聲音就像聞到女人們的飯菜香和男人們下班后皮鞋里悶了一天的腳臭。
薄暮是思家的時分。
傍晚時的城市總是無聲地預演著歸家的序曲,孩童們不等老師宣布下課便開始收拾起書包,只待鈴聲一響便擁擠著跑出校門,四處張望著來往的車輛,打量著車里的家長。老師們在辦公室里默契地收拾著桌子,談論著今晚家里的晚餐菜譜。馬路上也總是傳來不耐煩的車喇叭聲,尖銳的鳴笛蓋過了飛鳥撲棱翅膀的聲音。此起彼伏的歸心糾纏在一起,像一把藤制的癢癢撓,在每一個呼吸里搔動著。不管飛禽走獸抑或是人,大抵在黃昏迫近、夜幕將至之時都有著一種發自本能的回家的沖動,好像晁補之《行香子》中的“歸鳥翩翩,樓上黃昏”。說是躲避敵害也好,尋求歸宿也罷,終歸是想要回到那個曾經居住過的熟悉的故地,飲喉嚨熟悉的水,睡身體熟悉的巢室。所有的動物,包括人,害怕的都是那些不可知的、未知的,而已知的則帶著心安的魔力,帶來穩定與安全感。所謂歸家,大概就是在對未知的無力中恐懼地尋找那些能帶來熟悉的安定,讓漂泊在孤寂中的靈魂得以扎根在心靈的故土上。
可人似乎偏偏又是矛盾的。因為人也是動物,故而人是念舊的、思家的。“每逢佳節倍思親”“明月何時照我還”,思鄉想家可以說是人類普遍存在的情懷,它不是屬于個人的。但又仔細想想,人為何要離開那片生養自己、為自己所熟知的土地?背井離鄉,踏上漫漫征途,甚至不知前路是何方,有何兇險或機遇等待著自己。然而人總是義無反顧地離開,正如其義無反顧地歸來。每天北上廣深都會迎來大批的外來人口,車站、機場人頭攢動。而在全國的其他地方,每天也都有大量的人謀劃著離開家鄉,在深夜中無法合眼,思索著何去何從、如何在外面闖蕩出一番事業。也總有人站在大城市的高樓上俯瞰,看那萬家燈火卻沒有一盞為自己而點,炊煙裊裊卻無一縷自己最愛的味道。浪子,總是有著說服自己的理由,或者說是有著忍受眷戀的決絕。所謂思鄉詩情也大多是出于這些浪子之手——“低頭思故鄉”的李青蓮也曾是那個“仰天大笑出門去”的狂生;“寄書長不達”的杜少陵亦嘗懷“致君堯舜上”的宏愿進京。無數布衣書生躊躇滿志地上路,卻又失魂落魄地思鄉。
然而,與其說人的矛盾與反復,倒不如說人的“巢”與鳥獸的“巢”不一樣。巢不單單是家,更是那個一想起就心向往之的地方。心之所至,天涯咫尺,在故地與夢想間來回游蕩,但身卻限于交通、頓于車馬、阻于山河,所以身體永遠在羈旅中,在到達心靈的征程上。巢非巢,人生就在于這場奔波的旅程啊。
( 作者系寧波大學人文與傳媒學院學生)
責任編輯:周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