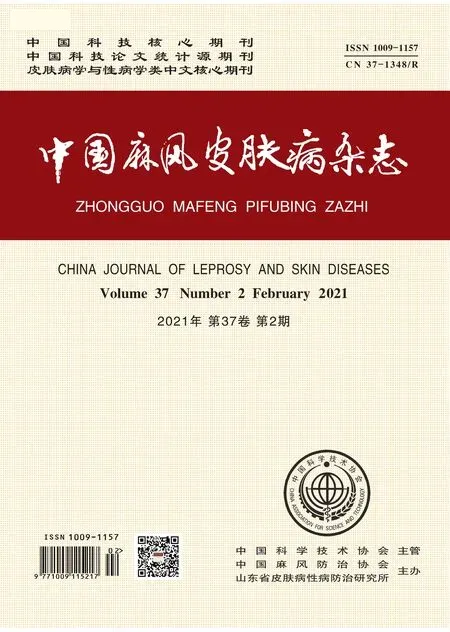Bart綜合征一例基因檢測
劉 靜 朱 靜
1淮北市人民醫院(徐州醫科大學淮北臨床學院)皮膚科,安徽淮北,235000;2淮北市人民醫院(徐州醫科大學淮北臨床學院)燒傷整形科,安徽淮北,235000
臨床資料患兒,男,于2020年2月7日經我院產科順產娩出。胎齡(40周+1),出生體重4.1 kg,產后即發現患兒雙下肢、足部、左手腕、面部皮膚缺失,于2月8日轉上級醫院進一步治療。入院查體:一般情況可,各系統未見異常。面部部分皮膚缺失伴少許滲出,口腔黏膜破潰,雙下肢及足部伸側皮膚大面積缺損、糜爛、滲出,右側足背過伸(圖1)。

圖1 1a:口腔黏膜受損;1b:雙下肢皮膚破損伴少量滲出,右下肢過伸
輔助檢查:2020年2月10日血常規示白細胞計數4.44×109/L,中性粒細胞百分比35.00%,紅細胞計數6.08×1012/L,血紅蛋白218 g/L;血生化:總膽紅素48.00 μmol/L,直接膽紅素16.00 μmol/L,間接膽紅素32.00 μmol/L,白蛋白33.2 g/L,C-反應蛋白69.80 mg/L;膿毒血癥二項(PCT/IL-6):降鈣素原0.630 ng/mL,白介素6181.50 pg/mL;免疫十一項:乙肝表面抗體陽性。2020年2月12日血常規:白細胞計數5.94×109/L,中性粒細胞百分比31.00%,紅細胞計數5.71×1012/L,血紅蛋白204 g/L;血生化:C-反應蛋白59.90 mg/L;膿毒血癥二項(PCT/IL-6):降鈣素原0.164 ng/mL,白介素6338.80 pg/mL。2020年2月11、12、14日在院期間先后3次取創面分泌物送檢普通細菌培養2天,均無細菌生長。
經詢問患兒父母雙方,均否認有相關家族史,家族成員在出生時無皮膚異常、指趾甲異常,非近親結婚。患兒為頭胎順產,既往無流產史。孕婦在孕期按期孕檢,孕中期行彩超檢查時提示:胎兒雙側腎竇分離,胎兒雙側足背過度前屈,NT、無創、OGTT等均未見明顯異常。
患兒家長拒絕皮膚組織病理有創性檢查。根據患兒的臨床表型可初步診斷其為大皰性表皮松解癥。為進一步明確診斷,經患兒父母同意,對患兒進行基因檢測。采集患兒2 mL外周血提取基因組DNA,通過二代測序對大皰性表皮松解癥已知的21個致病基因(KRT5、KRT14、PLEC、DST、KLHL24、TGM5、DSP、PKP1、JUP、EXPH5、COL7A1、LAMA3、LAMB3、LAMC2、ITGA6、ITGB4、COL17A1、CD151、ITGA3、PLCG2、FERMT1)的全部外顯子和外顯子側翼序列進行檢測。結果在先證者(患兒)COL7A1基因上檢測到2個致病性變異,即c.2005C>T:p.R669X和c.7922G>A:p.G2641E。而在另外20個基因上未檢測到致病性變異。進一步進行一代測序驗證,顯示先證者這2個變異分別來自其母親(c.2005C>T)和父親(c.7922G>A)(圖2)。COL7A1基因是常染色體大皰性表皮松解癥的明確致病基因,因此,根據患兒的臨床表型和基因檢測結果,可明確診斷隱性營養不良型大皰性表皮松解癥(recessive dystrophic epidermolysis bullosa, RDEB),即Bart綜合征(Bart’s syndrome, BS)。

圖2 一代測序驗證:先證者檢測到c.2005C>T和c.7922G>A突變;父親檢測到c.7922G>A突變;母親檢測到c.2005C>T突變
治療:患兒經換藥等支持對癥處理于一周后出院,雙下肢部分伸側面及其他區域的表皮缺損外滲出量減少,見新鮮表皮被覆(圖3)。

圖3 患兒出院后雙下肢及足部表皮缺損處滲出減少,見有新鮮表皮被覆
討論先天性皮膚缺損又名皮膚再生不良(aplasia cutis congenita, ACC)。先天性皮膚缺損呈現多部位發病,約有84%位于頭部[1],70%是單發皮損,20%為多發或伴有其他部位的皮損。缺損形狀呈塊狀、片狀或不規則形狀[2]。先天性大皰性表皮松解癥指患兒身體的某處表皮、真皮甚至皮下組織出現先天性缺損或發育不全,皮膚受壓或摩擦后即可引起大皰,多發生于四肢末端和關節伸側的機械損傷后出現水皰、大皰、愈后瘢痕、粟丘疹和指(趾)甲損害是共同特征。嚴重者水皰不僅局限于體表皮膚,而且可見于體內的軟組織(黏膜)[3]。注意到本例患兒的皮損集中分布在雙下肢、手腕部,且有口腔黏膜受累,與國外文獻多報道皮損多發在頭部存在差異,可以解釋為區域差異導致[4]。
1986年Frieden[5]根據皮損部位、臨床表現、是否合并其他異常將ACC分為9類。其中第6類:皮損位于四肢,伴有大皰性表皮松解癥,水皰多位于四肢,即ACC同時伴隨大皰性表皮松解癥(epidermolysis bullosa,EB)。
大皰性表皮松解癥是一種分型復雜的疾病,亞型較多,而且幾種亞型有時同時出現于同一患者,即使是同一患者也可能在不同時期表現為幾種亞型特征,因此多數臨床醫生難以做出準確診斷[6]。2013年國際EB會議審核了本病的整體數據,強調了不再僅僅依靠臨床特征進行亞型分類,即修改了EB患者的分型方法,更多地關注每種亞型在分子層面的發病原因,倡導在臨床上使用新的分型和診斷方法:剝洋蔥法[7]。這種方法采用漸進的方式,先根據靶蛋白和超微結構中不同皮膚裂隙位置劃分到四種主要類型開始,即分為表皮內是單純型EBS(EB simplex)、基底膜中是交界型JEB(junctional EB)、基底膜下是營養不良型DEB(dystrophic EB)和混合模式Kindler綜合征(KS)4個型別,且每個型別又有多種亞型。四種主要類型的區別:單純型EBS的裂隙在基底層角化細胞區,水皰位于表皮的中層或上層;交界型JEB的裂隙發生在透明板內;營養不良型DEB水皰發生在致密板下面的真皮上部;Kindler綜合征(KS)的裂隙可能發生在基底層角化細胞中,透明板層或致密板下面[8]。早期診斷多以透射電鏡確認患者水皰所在位置,然后再進一步明確診斷;近年逐漸轉變為使用免疫熒光或免疫組化定位[9],做相應基因測序以確定致病基因位點,對患者的 EB 類型、遺傳模式、臨床表現、免疫熒光抗原定位檢測結果及突變情況等因素進行綜合考慮。在可能致病基因位點上再進行基因定位診斷,最后確認EB分型[10]。
研究表明,EB的發病原因是角化細胞或皮膚基底膜區(表皮和真皮的交界)內的蛋白質突變引起皮膚超微結構異常,通常皮膚和皮外癥狀的嚴重程度反映了突變的類型和目標蛋白的超微結構位置。所有的營養不良型DEB(dystrophic EB)的突變都發生在VII型膠原基因[11]。
Bart綜合征是營養不良型大皰性表皮松解癥的一種,非常罕見,發病率大約在3.3/106,1966年由Bart首先報道[12]。1996年Chrlstiano等證實本病是VII型膠原基因(COL7A1)突變所致[13],目前已發現COL7A1基因的700多個突變。本例中在患兒COL7A1 上檢測到的c.2005C>T和c.7922G>A復合雜合變異,前者為無義突變,會導致肽鏈延伸至第669位氨基酸位置時提前終止,在ExAC(EAS)中的頻率為0.0001,在NCBI和ClinVar數據庫中均記錄為Pathogenic(rs780261665);后者為錯義突變,會導致肽鏈第2641位氨基酸由甘氨酸轉變為谷氨酸,在ExAC(EAS)中的頻率為0,在NCBI、Ensembl、ClinVar等數據庫中未見報道。基因突變導致pro-α1(VII)鏈蛋白的生產出現異常,從而影響VII型膠原蛋白的生產,繼而影響錨纖維的組成和功能[14],最終造成皮膚非常脆弱,摩擦或其他輕微外傷可能導致兩層皮膚分離,易起水皰。
Bart綜合征的臨床診斷需與其他疾病鑒別,如葡萄球菌性燙傷樣皮膚綜合征、新生兒膿皰瘡、先天性大皰性魚鱗病樣紅皮病、先天性梅毒、新生兒單純皰疹等。其中葡萄球菌皮膚燙傷樣綜合征(staphylococcal scalded skin syndrome, SSSS)是發生于新生兒的嚴重急性泛發性剝脫性膿皰病[15],是在全身泛發紅斑的基礎上,發生松弛性燙傷樣大皰及大片表皮剝脫為特征。多發生于出生后1~5周的嬰兒,發病突然,初在口周或眼瞼四周發生紅斑,其后迅速蔓延至軀干和四肢近端,甚至泛發全身,一般經過7~14天后痊愈。本例患兒除特異性皮損外,并無明顯的感染性中毒表現,故而可排除以上感染性疾病的可能性。
大皰性表皮松解癥的預后情況高度依賴于其疾病亞型,差異較大。其中單純型EBS(EB simplex)和顯性營養不良型(Dominant dystrophic epidermolysis bullosa,DDEB)預后較好,可存在正常的預期壽命。交界型JEB(junctional EB)因水皰全身泛發、廣泛剝脫,預后通常不好,可在出生后早期即死亡[16]。Bart綜合征通常出現手指和腳趾均被瘢痕包裹,隨年齡增長肌肉逐漸萎縮,最終形成棒狀手而致殘,同時可伴黏膜損害、甲營養不良、牙齒排列不規則,毛發稀疏等。嚴重病例因為大面積表皮剝脫、黏膜受累、伴發心肌病而死亡。少數RDEB患兒可出現惡性黑素瘤[17]。因此對EB的分型診斷應盡量、及早確定,以利于后期針對性治療。
目前對該病治療尚無有效方法,多采取提前干預,對可能發生嚴重的皮膚及口腔感染,局部滲出液增多引起的低蛋白血癥、電解質紊亂、肺部感染等制訂出護理計劃,并嚴格按照執行,糾正營養不良,防止細菌感染,保護表皮免受摩擦,減少身體殘疾和肌肉攣縮,以預防并發癥的發生,促進皮損早期愈合。本例在治療上予以頭孢美唑抗感染,患兒體表皮膚缺損面實施無菌換藥,使用優拓,系脂質水膠敷料,由100%聚酯網、水膠體(羧甲基纖維素鈉)、凡士林構成,創造出有益于傷口愈合的濕性環境,并及時祛除死皮和膿痂,再涂以抗生素類及重組人表皮生長因子凝膠,凡士林覆蓋,采取每日或隔日換藥一次。創面處保持干燥,盡可能避免長時間受壓,同時積極預防繼發細菌感染。
因BS目前仍缺乏有效治療手段,即使經過長期治療,依然嚴重影響患者的生活質量,則更加強調了分子生物學、遺傳學研究的重要性,因此產前診斷是有效的預防措施,除常規孕檢外,應積極開展針對性的遺傳咨詢和指導。預先盡可能明確父母或其他已患病親屬的致病性基因突變點,在妊娠第9~10周做羊膜腔穿刺,獲取絨毛膜絨毛或羊水細胞標本進行DNA產前檢測,從而促進優生優育。
志謝:感謝上海安百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技術部孔祥生老師在基因檢測方面所給予的指導及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