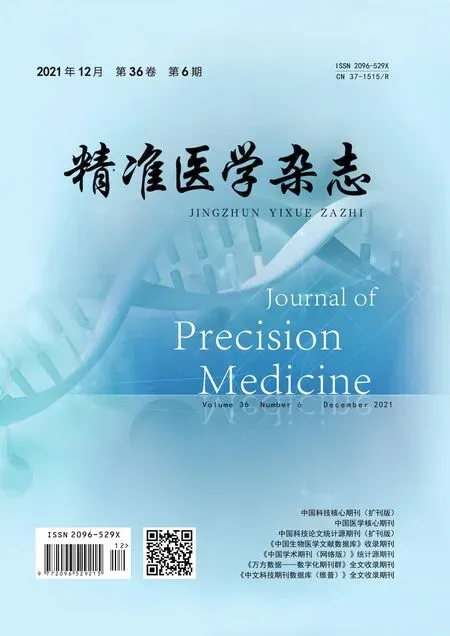多發性骨髓瘤患者腎損害預測模型的建立與驗證
劉瑩瑩 崔莉 卜泉東 郭丹丹 谷曉娟 胥雪玲 劉雪梅
(青島大學附屬醫院腎病科,山東 青島 266003)
多發性骨髓瘤(MM)是血液系統第二位常見惡性腫瘤[1-2],患者骨髓中異常增生的漿細胞分泌的單克隆免疫球蛋白或其片段,易對腎臟造成損害[3-4]。多達20%~50%的MM患者在初次確診時即伴有腎損害(RI),部分患者在治療過程中出現RI,大約5%~10%的患者需要進行透析治療[5]。研究顯示,在MM患者中腎功能的逆轉程度是比漿細胞對化療的反應能力更為重要的決定其預后的因素[6]。初診時伴有RI者經積極治療后可獲得與腎功能正常患者同樣的療效[7]。有研究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研究MM患者RI的危險因素,但有關MM患者RI預測模型的相關報道較少[8-9]。本研究通過對本院初診MM患者的臨床資料進行回顧性分析,建立并驗證針對MM患者并發RI的預測模型,為MM患者RI的早期防治提供重要的參考依據。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選取2012年6月1日—2019年10月31日于我院各科確診為MM患者作為研究對象。納入標準,符合MM診斷標準的初診患者[10]。排除標準:①已行化療患者;②近3個月有腎毒性藥物使用史者;③存在低血容量者;④近1月內合并感染性疾病者;⑤既往有腎臟病病史者;⑥存在尿路梗阻者;⑦基線資料不完整者。依據IMWG和NCCN指南標準將血肌酐≥176.8 μmol/L作為患者發生RI的依據[10-11]。將所有患者分為RI組和非RI組。本研究經過了青島大學附屬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核批準(QYFYWZLL 25967)。
1.2 研究方法
收集患者的一般資料,包括患者的性別、年齡;收集患者初診時的實驗檢測指標,包括血肌酐、血免疫球蛋白輕鏈κ/λ比值、尿隱血、尿蛋白、校正血清鈣、血紅蛋白、血尿酸、乳酸脫氫酶、β2-微球蛋白、尿密度、總膽固醇、三酰甘油、血球蛋白、血白蛋白。校正血清鈣由血清總鈣(mmol/L)-0.025×血清白蛋白濃度(g/L)+1.0(mmol/L)進行計算得到。建立數據庫。
1.3 統計學分析

2 結 果
2.1 MM患者基本資料
根據預測模型國際規范指南標準[12],將2012年6月1日—2017年12月31日確診的MM患者672例納入訓練組,將2018年1月1日—2019年10月31日確診的MM患者286例納入驗證組。參考相關文獻報道[13-14],并結合本研究可用數據,最終納入樣本量總計958例,男566例,女392例。訓練組與驗證組患者尿蛋白、血尿酸、乳酸脫氫酶水平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z=-3.890~-3.200,P<0.05),兩組其余指標進行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訓練組與驗證組MM患者臨床資料的比較
2.2 訓練組兩組臨床資料的比較
與訓練組中非RI組比較,RI組的男性、血免疫球蛋白輕鏈κ/λ比值異常、血尿、蛋白尿占比均比較高(P<0.01),校正血清鈣、血尿酸、乳酸脫氫酶、β2-微球蛋白、三酰甘油水平均高于非RI組(z=-10.612~-2.547,P<0.01),血紅蛋白、尿密度水平較低(z=-7.684、-5.289,P<0.01)。而兩組年齡、總膽固醇、血球蛋白、血白蛋白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訓練組RI患者與非RI患者臨床資料比較

續表(2)
2.3 MM患者并發RI預測模型的建立及其預測能力驗證
單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性別、年齡、血免疫球蛋白輕鏈κ/λ比值、尿隱血、尿蛋白、校正血清鈣、血紅蛋白、血尿酸、乳酸脫氫酶、β2-微球蛋白、血球蛋白以及血白蛋白為并發RI的危險因素(P<0.2)。各變量的共線性診斷方差膨脹因子均接近于1。將上述因素納入多因素Logistic回歸方程。根據AIC準則,最終將血尿酸、尿蛋白、血紅蛋白、球蛋白、血免疫球蛋白輕鏈κ/λ比值、校正血清鈣、尿隱血7項因素納入構建MM并發RI的預測模型。見表3。根據回歸系數分配自變量評分,并以列線圖的形式顯示(圖1)。訓練組MM并發RI預測模型的AUC為0.882(95%CI=0.849~0.914,P<0.01)(圖2a),ROC分析結果顯示,該模型的最佳診斷界值為0.232,診斷靈敏度為79.85%,診斷特異度為84.94%。將MM并發RI預測模型應用于驗證組進行驗證,MM并發RI預測模型的AUC為0.928(95%CI=0.896~0.960,P<0.01)(圖2b)。將訓練組的最佳預測界值應用于驗證組,顯示診斷的靈敏度為92.06%,診斷的特異度為78.03%。驗證組Hosmer-Lemeshow檢驗結果顯示P=0.374(P>0.05),MM并發RI預測模型在驗證組中預測概率與實際概率之間一致性較好,準確度較高。見圖3。

表3 MM患者發生RI的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

圖1 MM并發RI發生風險的列線圖

a、b分別為訓練組與驗證組ROC曲線

圖3 MM并發RI預測模型的校準曲線
2.4 臨床實用性評價
決策曲線分析的結果顯示,當閾概率在0.03~0.75時,患者的臨床凈獲益均較高;當閾概率為0.232時,可使15%的患者凈獲益,同時借助該模型進行MM并發RI的早期診斷,可降低55%的臨床干預措施。見圖4。

a:預測模型的凈獲益分析,b:干預措施凈減少分析
3 討 論
MM對患者的腎臟造成的損害較為嚴重。但MM患者在RI早期可以逆轉,使得生存時間得以延長[15-16]。因此,探討MM并發RI的相關預測因素,構建其預測模型,對于MM患者的預后具有重要的臨床意義。據英國一項大型研究報道顯示,在其對日本、歐洲、中國和韓國的MM患者隊列研究中,分別有16%、21%、24%以及33%的MM患者并發RI[17]。本研究MM患者RI的發生率為20.6%,發生率略低于上述此報道的中國MM患者隊列RI的發生率,考慮可能與納入的研究對象范圍大小不一致相關。
MM患者血清中存在大量的游離免疫球蛋白輕鏈(FLC)[18],其作為一種生物活性蛋白,可以激活細胞內的氧化還原反應,對腎小管上皮細胞產生直接毒性損傷[19]。而隨著FLC的增多,體內的正常血清球蛋白則會相應減少。從側面顯示了MM患者體內正常血清球蛋白越少,其并發RI的可能性越大。這與本研究中的結果相一致。血液中大量FLC被腎小球濾過后,當其量超過腎小管的重吸收能力時,就會形成骨髓瘤管型,阻塞和損傷腎小管,導致RI的發生[20]。因此FLC水平是預測MM患者是否會發生嚴重RI的良好指標。研究表明,當患者血清FLC水平高于800 mg/L時出現嚴重RI的風險增加[8]。在正常情況下,不會在尿液中檢測到FLC。當其超過腎臟的吸收能力時,就會形成溢出性蛋白尿,對腎小球系膜細胞、腎小管間質均具有毒性作用[21]。患者的尿蛋白越多,其越易并發RI。因此可通過早期發現MM患者尿蛋白的異常,對RI的發生進行及早識別。
本研究發現高尿酸血癥是MM患者并發RI的一項預測因素,在MM腫瘤細胞大量破壞時可導致核酸分解增加,致使尿酸升高,引起腎臟內皮細胞功能紊亂、氧化應激損傷和腎間質的炎癥反應,從而導致RI[22-23]。長期的高尿酸血癥還可以通過激活免疫反應引起尿酸性腎病[24],從而間接加重RI。這與SRIVASTAVA等[25]的結果相一致。
大量的骨髓瘤細胞浸潤骨髓使得骨髓的造血功能低下,紅細胞生成減少,導致機體貧血,而嚴重的貧血可引起腎組織缺血缺氧,并發一系列炎性反應,進而導致RI[26-28]。促紅細胞生成素(EPO)可促使體內紅細胞的生成,因其主要由腎臟間質中的特定細胞所分泌,當腎間質出現纖維化時,EPO的生成必然會相應的減少[29-30]。一項回顧性研究證明,如果MM患者存在貧血時,其血清中EPO水平可作為腎臟是否具有可逆性的獨立預測因素[31]。表明貧血是MM患者并發RI的獨立危險因素之一。血紅蛋白越低,并發RI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對于MM并發RI者建議積極改善患者的貧血狀態[32]。而血液系統的異常,不僅表現為貧血這一種癥狀,MM分泌的M蛋白黏附于血小板、一些凝血因子表面及與纖維蛋白單體結合,影響纖維蛋白多聚化和凝血酶時間,患者可出現血尿及凝血功能的異常。本研究顯示,MM患者的血尿程度越重,其并發RI的可能性越大,且有研究報道顯示,血尿可為MM的首發表現[33]。
MM可引起溶骨性破壞,使患者體內血鈣升高,加劇腎臟血管收縮,腎臟有效灌注減少,腎小球濾過率下降,使腎臟功能受損,甚至可導致腎前性氮質血癥的發生。高鈣血癥還可導致集合管對抗利尿激素的敏感性降低以及髓袢升支對氯化物的轉運異常,造成腎臟濃縮功能下降,從而導致腎小管、集合管的功能障礙[34]。研究表明,MM患者血清鈣水平與腎功能不全的發生具有一定的關系[35]。因此隨著患者體內血鈣水平的升高,MM患者罹患RI的風險顯著增加。
本研究的優點包括:①本研究首次通過臨床檢驗指標構建了MM患者并發RI的預測模型,可根據MM患者的情況個體化預測其發生RI的風險,可為臨床早期防治RI并改善MM患者的預后提供重要的參考依據。②該模型以列線圖的形式直觀地呈現預測結果,操作簡單,易于推廣。同時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①本研究是單中心、回顧性研究,患者的病史依靠病歷記錄和患者調查取得,可能存在一定的信息偏倚。②本研究的樣本量有限,證據級別不如多中心研究高。下一步將擴大樣本量,并進行多中心、前瞻性的驗證。
綜上所述,本研究首次建立了MM患者并發RI的預測模型,并從多方面評估其準確性和驗證的可靠性,基于該預測模型,臨床醫生可初步個體化地評估MM患者的預后,幫助臨床醫生制定進一步的預防及治療策略,從而有效改善MM患者的預后,使患者從臨床獲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