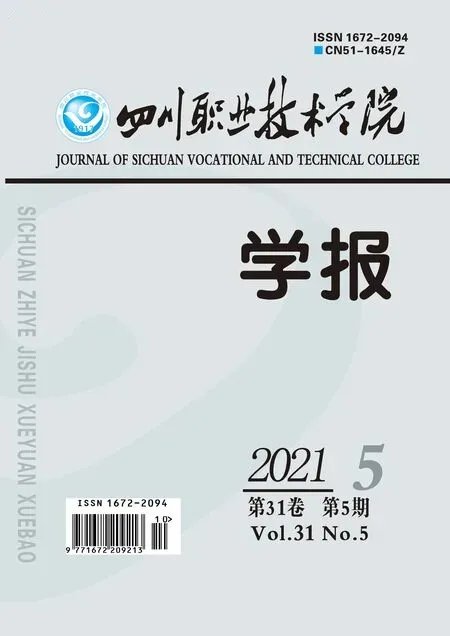四庫“周禮之屬”部分提要辨析
賈曼莉,李文勝
(山西師范大學 戲劇與影視學院,山西 臨汾 041000)
《四庫全書總目》與庫本之提要有差異。故筆者擬就經部禮類周禮之屬之部分提要進行辨析,望請方家指正。《總目》以影印浙本(1965中華書局)為底本,同時以《武英殿四庫全書總目》(2019國家圖書館出版社)為參照本。庫本提要文淵閣本選《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2012北京出版社),文溯閣本選《文溯閣四庫全書提要·經部》(2014中華書局),文津閣本為《文津閣四庫全書提要匯編》(2006商務印書館)。
一、《周禮注疏》四十二卷
雖不足以當《冬官》,然百工為九經之一,其工為九官之一。[1]149(《總目》)
按:“其工”,殿本、文淵閣本都作“共工”,文溯、文津無此部分。九官出自《尚書·舜典》,《尚書正義》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此處,孔傳認為“共謂供其職事。”而在《堯典》中,“孔傳云:‘共工,官稱。’”比較而觀,孔傳對“共工”的注解出現了不同。但《舜典》中孔穎達《正義》對“共工”的解釋為:“即彼以‘共工’二字為官名。今命此人云‘汝作共工’,明是帝謂此人堪供此職,非是呼此官名為‘共工’也。其官或以‘共工’為名,要帝意言‘共’謂供此職也。”[2]131很明顯孔安國與孔穎達都認為此處之“共”有“供職”之意。相較孔安國的注釋來說,孔穎達很堅定地認為“共工”非是官名。或做官名,“共”的供職之意也未發生變化。而《周禮注疏》載:“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鄭玄注:“百工,司空事官之屬,監百工者,唐虞以上曰共工。”賈公彥疏:“唐虞以上皆曰共工,堯時誓為司空。”[2]905故而可知,共工在上古為司空之代稱,其職務為監察百工。故而九官之一是共工,而不是其工,《總目》似為疏漏。
二、《周禮詳解》四十卷
①以國服為之息云:“各以其所服國事賈物為息。若農以粟米,工以器械,皆以其所有也。”[1]150(《總目》)
按:殿本同,文溯無“其”字,文津缺此部分,文淵閣本“其”作“共”。鄭司農云:“貸者,謂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賈之國所出為息也。假令其國出絲絮,則以絲絮償”,鄭司農提倡息應以各國所出口之貨物為準。而鄭玄則言:“以國服為之息,以其于國服事之稅為息也。”賈公彥亦云:“鄭玄不從鄭司農,凡言服者,服事為名,此經以民之服事,唯出稅是也。”[2]738鄭玄與賈公彥都認為息應是田稅,而不能以貨物代替。孫詒讓說:“必以所出為息者,取其易得,且官不失利也”[3],即王昭禹所言“農以粟米,工以器械”。只要以同等物品代替還清則已,而不是鄭玄所說之以田稅為差,如“萬泉出息五百,計當二十取一也”。前鄭、后鄭與孫詒讓之爭集中于“息”究竟以何物為標準,是同等貨物,亦是田稅,但毋庸置疑的是應以各自國家為準。而《周禮詳解》卷十四亦載:“以國服為之息,各以其所服國事賈物為息也。”[4]故應從《總目》作“其”,而不作“共”。
②元末朱申作《句解》,蓋從其例,究為一失。[4]198(《周禮詳解》之《文淵閣提要》)
按:殿本同,《總目》作“宋末”,文溯、文津無此部分。《周禮句解》之提要《總目》與閣本均載“宋朱申作《周禮句解》十二卷”。而后《總目》細言《江西通志》朱申為宋太學生,李心傳《道命錄》有淳祐十一年新安朱申《序》,其結銜題“朝散大夫知江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1]152。《總目》似乎認為《江西通志》太學生朱申與為李心傳作序之朱申不是一人,且不確定《周禮句解》到底為何人所著。反觀文津閣提要載“贛州人,宋太學生,不言時代。朱彝尊《經義考》載是書于南宋末,而別載其《論語辨》別于黃鍰之后,江奇之前。考閩書,鍰以政和五年登第,奇以宣和三年登第,則申又曾為北宋徽宗時人,莫之詳也。”[5]260文津提要亦無法確定太學生《江西通志》朱申是何時之人,《經義考》載朱申之《周禮句解》于南宋末黃鐘《周禮集解》之后;同時又載朱申之《論語辨》于徽宗之時,并認為人亦可能為徽宗之時人,但無法給出準確的結論。因此,對朱申之年代要進行考辨。
首先《總目》與文津閣本《江西通志》之朱申,《江西通志》載“字維宣,雩都人,皇祐(北宋仁宗1049—1054)年間有聲太學”,而朱申為李心傳作序是淳祐十一年(南宋理宗1251),此必定不是同一人;其次,按朱彝尊《經義考》所言,朱申之《周禮句解》于南宋末,而朱申之《論語辨》為北宋末徽宗時期,即本人應在1115年(政和五年)——1121年(宣和三年)期間登第,一人之書出現在不同時代,本就混亂。假設朱申為北宋末人,按照當時的人均壽命,距離朱申為李心傳作序還有大約一百三十多年。所以,朱申大概不是徽宗時期之人,或者不是《經義考》所言作《論語辨》之朱申,更不可能在政和五年至宣和三年期間登第,那最可能的便是朱申為南宋之人。據程敏政編《新安文獻志》載:“朱知軍(申)默齋權之從子紹熙六年進士,歷官知無為軍,嘗刻道命錄。”[6]此句之從子當為侄子,《朱子語類》載:“據禮,兄弟之子當稱從子為是,自曾祖而下三代稱從子,自高祖四世而上稱族子。”[7]《新安文獻志》之朱申為朱權之從子,朱權為南宋人,宋代程珌《洺水集》有《朱惠州行狀》,其載:“公始入太學……由是族之子弟益知向方,侄申從侄況相繼登科。”[8]此處之申應是為李心傳(1251年)作序之朱申,亦是《新安文獻志》之朱申。但朱申應不是紹熙六年進士,因為紹熙為南宋光宗之年號,并只有五年,而且從前后文看,朱申之前為“許環山,字衡甫休寧東閣人紹熙元年進士”;后為“汪太初,又字南老……紹熙元年進士”。同時據明弘治十五年刻本影印本《徽州府志》卷六載:“紹熙元年余復榜,朱申,休寧人,見人物志朱申傳。”[9]故朱申應為紹熙元年(1190)進士。保守估計此時他的年齡可能在二十至四十左右,此時距離元初1271年,相差整整九十年。所以,他也不是元末之人。因此,筆者認為朱申應為南宋之人,故其他文獻提到“元末朱申作句解”之語應是錯誤的。
三、《周禮復古編》一卷
宋俞庭椿撰。庭椿字壽翁,臨川人,乾通八年進士。[10](《文淵閣提要》)
按:“通”其余本作“道”。查閱《宋史》,無乾通之年號。《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所藏據明弘治十六年刻本影印本弘治《撫州府志》載“乾道八年壬辰黃定榜,俞庭椿與陸九淵并列同年進士。”[11]故而應作“乾道”,而不是“乾通”,《文淵閣提要》誤。
四、《鬳齋考工記解》二卷
于戈之長內則折前,謂援與胡句相并如磬之折。[1]152(《總目》)
按:殿本、文淵、文津作“于戈之長內則折謂前為援與胡相并如磬之折”,文溯作“于戈之長內則折前,謂為援與胡相并如磬之折。”查閱《鬳齋考工記解》原文為“胡之下曰戈鐏處也,太長則胡以上之援與胡句相并如磬之折,則不可以刺也”。此句是經文“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疾”之釋文,意在說明戈之所用關鍵在于胡。《周禮注疏》之鄭玄言:“內如果太長則會侵援,前為援,援短則易曲如磬折,曲如磬折則引之與胡并鉤。”[2]915意在說明治戈之時應避免的錯誤,故而應以《總目》為準。
五、《周官集傳》十六卷
又《甸祝》“禂牲禂馬”,鄭《注》:“禂讀如伏誅之誅,今侏大字也。”[1]153(《總目》)
按:殿本在鄭《注》前加了“掌祝號”三字,而去了“伏誅之”三字。而文淵閣本“《甸祝》”作“《喪祝》”,“禂牲禂馬”后加“亦如之”三字,其他如殿本,但無“掌祝號”三字,文溯、文津缺此一段。此句是“《甸祝》禂牲、禂馬,皆掌其祝號”之釋文,意在說明甸祝之職務為掌田獵祭祀祝禱。據阮元十三經注疏所據底本之宋十行本《周禮注疏》載:“玄謂,禂讀如伏誅之誅,今侏大字也,為牲祭,求肥充,為馬祭,求肥健。”[2]815故應以《總目》為準。
六、《周禮全經釋原》十四卷
書中訓解,其稱“釋”者,皆采輯古注。其曰“原”者,則尚遷推闡作《經》本意也。[1]155(《總目》)
按:殿本同。而閣本“訓解”作“解詁”,“釋”為“說”,“皆采輯古注”作“皆依古注集成”。《周禮全經釋原》之《凡例》作“故每篇訓釋之后必作原以發明之謂之曰原者,推原作經本意也,猶原道原性之原。一訓釋之中有采先儒之說書曰某氏,訓釋之后總解有采先儒論著,以代作原者,亦書某氏曰。敬以自漢以來先儒姓氏名字所著書目及地望總列于前,使觀者欲求其人有所考證云。故訓釋亦大書,與原曰同依正義。加釋曰,二字別于原曰故名釋原云。”[12]507因此“釋曰”為先儒論說與古注訓釋。如《周禮全經釋原》卷一之《內饔》載:“饔,割煎和調之稱。內饔所主在內,以其掌王及后世子及宗廟,皆是在內之事。”[12]513此句之訓釋分別采集了鄭玄注“饔,割亨煎和之稱。內饔所主在內”與賈公彥疏“又云‘所主在內’者,以其掌王及后世子及宗廟,皆是在內之事”的注疏[2]640。故而書名為全經釋原,《總目》更為合適。
七、《周禮訓纂》二十一卷
《續漢輿服志》曰:“乘輿重牙斑輪,升龍飛軨。”注引薛綜《東京賦注》“飛軨以緹油,廣八寸,長注地。系軸頭。”所云緹油……《續漢輿服志》注:“舊典傳車驂駕乘赤帷裳……敕去襜帷。”[1]156(《總目》)
按:文溯、文津無此部分。書名《周禮訓纂》,總目與殿本同,閣本作《周禮纂訓》。查閱《四庫采進書目》,福建省進呈第三次書目有李鐘倫《周禮訓纂》二十一卷,六本[13]169。可知《總目》正確。《續漢輿服志》,殿本、文淵閣多了一個“書”字,輿服志為《續漢書》八志之一。“緹油”,文淵閣、殿本作“油緹”。查閱宋白鷺洲書院本《后漢書補志》,原文為“飛軨以緹油,廣八寸,長注地,畫左蒼龍,右白虎,系軸頭,兩千石亦然,但無畫耳”[14],故應以《總目》為準。“舊典傳車驂駕乘赤帷裳”之“乘”字,文淵、殿本無此字。查閱原文為“案本傳舊典傳車驂駕乘赤帷裳,惟郭賀為冀州,敕去襜帷。”[14]故而可知,以《總目》為準。
八、《周官集注》十二卷
后苞別著《望溪集》,指《周官》之文為劉歆竄改以媚王莽。(閣本)
按:《總目》作“后苞別著《周官辨》十篇”,殿本作“《周官辨》十卷”。《總目》集部有方苞《望溪集》八卷,《望溪集》中亦無“周官辨論”之內容。而據清乾隆刻本影印本《周官辨》所載可知,其內容分兩篇《辨偽》,八篇《辨惑》,故應從《總目》。且自序亦言:“《周官》多失其本指,而莽與歆所竄入者實有數端,學者既無據以別其真偽,而反之于心,實有所難……而猶能察其心而不以為妄矣。”[15]故而應為《周官辨》,但卻不是十卷,而是一卷。《四庫采進書目》中有安徽省呈送書目《周官辨》一卷,一本,清方苞撰[13]142,故而知殿本、閣本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