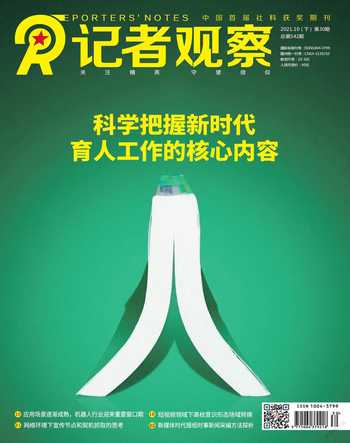“智媒時代”高職新聞傳播教育的改革
沈亞圓
傳媒技術和媒體產業格局不斷發展變化,重構著內容生產和信息傳播的過程,智媒時代到來對新聞傳播教育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與高層次的本科、碩士類新聞傳播教育相比,高職新聞傳播人才培養首當其沖地受到機器代替人工的危機,高職新聞傳播教育改革迫在眉睫。本文從問題視角出發,在“智媒”環境下,梳理智媒時代發展現狀,探討對高職傳媒人才培養面臨的挑戰,分析高職新聞傳播人才培養的不足與核心競爭力,最后為高職新聞傳播教育精準培養改革提出建設性的思路和建議。
隨著移動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5G通信以及人工智能等技術的迅猛發展,傳媒技術和方式不斷迭代升級,一個“萬物皆媒、人機共生、自我進化”的“智媒時代”已然到來。美國、英國、德國、法國等國自2012年就開始出現一批技術公司進行自動化寫作的軟件研發,主要應用在包括自然天氣、財經股市、體育競賽等方面比較“模式化”的快訊、消息寫作等。在國內,主流媒體及互聯網科技企業巨頭如新華社、人民日報社、騰訊、阿里巴巴以及今日頭條等,從2015年起先后推出“機器人寫作軟件”。如新華社的人工智能平臺“媒體大腦”在2018年“兩會”中僅用15秒就生產出全球第一條AI視頻新聞。2019年5月,人民日報社首款人工智能虛擬主播“果果”在“2019中國國際大數據產業博覽會”亮相,不管是機器主播的外形或聲音,還是臉部肌肉、嘴唇動作,與真人主播幾乎無異。這都標志著人工智能技術在傳媒應用領域的不斷突破,同時也使得業界人員與學者們不禁自我設問:未來我們需要怎樣的新聞傳播人才?未來需要進行怎樣的新聞傳播教育改革?
2020年12月7日,“國際人工智能與教育會議”開幕,以“培養新能力 迎接智能時代”為主題,形成共識:“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向我們展示了變革教育的巨大潛能,幫助每個人獲取駕馭新科技、創造美好生活的能力,正是教育的使命所在”。從傳統媒體到新媒體,再到融媒體、全媒體的“概念升級”,再到置身于“智媒體”時代的序幕中,傳媒技術的迭代發展從未停止過對傳媒業和新聞傳播教育的深刻影響。
本文通過在“中國知網”搜索與“智媒”或“智能媒體”相關的學術論文,發現國內大概是從 2016年開始對“智媒”的研究進入高峰期,這與“機器人寫作”“自動化新聞”“智能推薦”“個性化定制”等傳播新技術開始運用到信息生產、分發與運營領域的時間一脈相關。近幾年對于“智媒體”的研究成倍式增長,從研究對象來看,學者們主要是以“人工智能”為理論核心,“智媒時代”“新聞生產”“物聯網”是第一圈層核心關鍵詞,其它再擴展到“媒體時代”“受眾”“媒介融合”“媒介生態/形態”等第二圈層方向。
影響較大的是知名學者彭蘭、蘇濤、喻國明等分別在16-17年左右的公開發表的“新媒體發展趨勢報告(2016)”“2017年新媒體研究綜述”“人工智能驅動下的智能傳媒運作范式的考察”,高屋建瓴地描述了智媒生產運作范式及智媒時代特征。專門針對“智媒時代”的新聞傳播教育改革展開的學術研究也已經有數十篇,主要集中在兩大方面。一方面是闡述“智媒”帶來的影響與人才危機:如潘曉婷(2018)分析了智媒時代的新聞人才危機,并分析了四個不可替代的人才能力;楊妮(2019)主要分析了人工智能技術在新聞生產過程中的應用優勢與局限、變革與發展等。一方面是為應對“智媒”環境,探討新聞傳播教育如何變革發展:如李明德,王含陽等(2020)對目前新聞傳播人才能力培養的困境進行了思考,并提出了實現目標和調整路徑;陳小娟(2020)引入“美國SAMR模型——替代(Substitution)、增強(Augmentation)、修改(Modification)和Redefinition(重塑)四個技術運用層次”來探索智能時代新聞傳播人才培養路徑建設。
但這些學者全都是站在本科類院校的高度來進行分析和展望,對高職新聞傳播教育的特點缺乏分層分類研究,不能進行針對性地有效指導。高職新聞傳播教育在培養傳媒人才的作用與貢獻上不可忽視,但高職教育領域對于“智媒”發展環境下的新聞傳播教育變革研究卻幾乎為空白,對人工智能應如何融入高職新聞傳播類專業教育更沒有任何居安思危的思考與探索。因此,迫切需要高職新聞傳播教育領域有針對性地跟上媒介發展與學術研究的步伐。
信息內容生產與傳播全流程發生重構
傳媒行業的發展一直以來都與傳播技術的變革步步耦合,當下媒體智能化已然成為媒體發展的主流趨勢,“人工智能”通過“程序化內容生產、算法化內容分發、自動化內容監管和精準化媒體運營”,來重構傳媒信息內容生產與傳播的全過程。在信息生產領域,已經開始實現從圖文到音視頻的媒介智能貫通,比如:文字的智能化寫作;圖像、音視頻的智能化編輯;智能化音視頻內容生產;圖像、音視頻內容的智能識別與處理;智能配音與AI主播等。
在內容分發領域,過去靠“把關人”來進行人工篩選和分發。現在轉變為依賴人工智能技術來“斷物識人”,如互聯網媒體平臺通過內置算法,根據用戶觀看喜好、沉浸時長或定位區域人群搜索偏好等來個性化推送內容。
在內容監管領域,以往主要通過平臺人工日常審核、用戶“舉報制度”、以及政府監管等來凈化網絡內容與環境。現在結合人工智能算法技術,通過“AI智能違規內容風險識別”“關鍵詞屏蔽”“搜索過濾”“違規攔截”等實現省時省力的自動化內容監管。如2020年以“平臺治理”為主題的抖音開放日會上提到:“抖音安全中心團隊”每天攔截處理違法違規內容和行為,如違規注冊、刷粉絲、刷流量以及發布違規評論等,就超過10億條。
在媒體運營方面,以往主要通過大量的線上線下市場與用戶調研,制定運營策略和計劃,人力執行大量運營活動,實現用戶增長或付費轉化。現在企業基于產品不同階段特點,通過大數據搭建精準的用戶畫像和會員體系,有針對性地設計差異化、個性化的營銷推廣策略,精準化直擊用戶痛點。而活動執行的效果又實現智能實時采集與分析,反哺用戶服務,提升用戶使用體驗。
高職新聞傳播人才更易面臨“替代危機”
在人工智能技術快速發展勢頭下,從天馬行空的科幻小說到嚴謹辯證的科學研究,大家都不斷地在慎思:“未來,機器人是否會代替人類工作?”隨著信息傳播全過程的重構,傳媒生態邊界被一定程度上打破,編輯、記者、媒體運營人員等都面臨嚴峻挑戰。Freyand Osborne(2017)分析了勞動力市場702個職業被智能化替代的風險概率,認為“多數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的職業被認為很有可能被淘汰……那些不需要發揮創造力和想象力,機械、重復的工作更容易被機器人取代,例如公司的普通文員、打字員、流水線上的工人、司機、保安、建筑工人、快遞員、抄表員、收銀員等”。
因此,對于高職新聞傳播類專業來說,學生招生層次較低、專業建設起步較晚、技能培養不夠深入、政策資源優勢不明顯等,更容易首當其沖地產生“人機—替代危機”。比如一般水平層次的記者和編輯所具備的“數據搜集”“篩題選題”“新聞寫作”“運營推送”等技術技能便失去了用武之地,其專業性讓位給了編程設計并在背后操控人工智能的“程序員”或者“算法師”。
業界變革對新聞傳播人才培養提出挑戰
2021年國家教育部發布《高等職業教育專科新舊專業對照表》,“新聞傳播大類”下設兩個專業小類,共計22個專業。其中“新聞出版類”包括網絡新聞與傳播、出版策劃與編輯、數字媒體設備應用與管理等6個專業;“廣播影視類”包括播音與主持、影視編導、傳播與策劃、新增網絡直播與運營等共16個專業。在這些專業目錄下,根據學者彭愛萍調研,截至2019年,全國有超過250所高職院校共開辦了538個新聞傳播類專業點。這些高職院校新聞傳播類專業每年為國家和社會培養和輸送大量的新媒體人才。“智媒時代”為我們創生了嶄新的新聞傳播教育環境,也為新環境下的高職新聞傳播人才培養提出了新的挑戰和難題。
比如人才培養理念與行業發展的適應匹配、技術課程和基礎課程的協同并舉、理論型師資與技術型師資的配合與補充、智能化實訓資源配備與教育投入巨大壓力、技術動力牽引與技術倫理風險等困境和挑戰,都成為高職新聞傳播教育發展需要直面的改革現實疑難。高職新聞傳播類專業應該培養什么層次、什么類型的,能夠適應“智媒時代”要求的傳媒人才?高職新聞傳播教育未來要如何變革適應市場行業發展?這些都是學界和教育界迫切需要回應及探索的問題。
人工智能時代,隨著互聯網技術和大數據技術與運用日臻成熟,“技術邏輯以其強大的運算、模擬、存儲以及智慧功能重構了新聞生產與傳播流程的話語實踐……一定程度上倒逼教育變革”。傳統的新聞傳播學是基于大眾傳播時代的生產實踐和流程而形成的相關知識體系,與嬗變轉型的傳媒現實環境有著明顯的不適應。那哪些是高職新聞傳播教育需要堅守的基礎,哪些又是需要進一步融合升級的技能,哪些又是因過時需淘汰的理論?這些都需要我們先來厘清思路邏輯,才能精準高效地進行改革。
高職新聞傳播教育應堅守的核心競爭力
面對智媒時代傳播技術的沖擊,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新聞研究生院院長瓦瑟曼教授在采訪中表達:“我不認為機器人將取代專業記者。但是,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越來越多的機器人將參與新聞信息的收集、核實,讀者互動和簡單的新聞資訊撰寫工作……但新聞人在尋找新聞線索、深度采訪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性……機器人可以為新聞人所用,但新聞的最終完成還得靠人。”與機器人相比,人類必然有著人類不可替代的優勢;那么與機器人、與本科層次及以上人才相比,高職新聞傳播教育人才的培養上,也有著高職的核心競爭優勢,比如在培養理念上,以專業群建設為基礎,融通“崗課賽證”,人才培養質量標準化;課程設置上,更加注重技術技能及實操訓練培養;在師資要求上,更強調引進具有行業企業實戰經驗的“雙師型”教師;在資源的投入上,更注意校企產業合作,共培共育;在學生培養上,三年培養制的靈活性也能使專業教育更具彈性,專業學生離行業市場更近等。
因此,高職新聞傳播教育改革并不是“一刀切”地全面顛覆性改革,而應該是堅守高職人才培養的核心競爭力與優勢,分解出高職新聞傳播教育低-中-高階不同層次的能力,根據高職新聞傳播教育實踐需求,提出可應用化的精準培養解決策略和路徑。
高職新聞傳播教育改革路徑
在“智媒環境”下,高職新聞傳播教育必須圍繞智媒技術發展訴求,升級教育理念,充分發揮和利用人工智能技術優勢,對人才培養方案、實踐課程體系、師資團隊建設、校企產業合作、智能化實訓場地及設備、智能化教育輔助等進行迭代重構,以培養符合“人工智能”時代發展需要的優秀傳媒人才。
其一,革新教育理念,人才培養對接行業發展。智能技術重塑傳媒產業新格局,使得一些簡單操作性的勞動工種消失或減少,如自動化信息寫作、報紙分發投遞員、內容審核員、咨詢客服等,大量崗位設置均發生調整和變化。但另一方面也降低了行業準入與內容生產制作門檻,人人皆是發聲者,天生自帶“網絡基因”的新一代人才中開始涌現出大量的網絡直播、短視頻UP主、自媒體、網絡文學作者等各類內容生產者和智能媒體輔助操作業務者。
因此高職新聞傳播教育應該定位于為中小微企業培養“智媒人才”,人才培養方案瞄準“智媒+崗位”需求,對接行業職業標準和工作過程,及時融通“人工智能”領域的職業技能鑒定證書和職業資格證書,打通學歷教育與職業培訓相融通的技術技能人才成長渠道。
其二,開發和培養創新型師資,校企合作共育。技能型人才培養的關鍵在于“雙師型”師資,面對“智媒”變革環境,高職教師一方面既要懂得傳統的教學規范和手段,另一方面也要掌握“智媒時代”的數據思維和技能技術。傳媒生態復雜多變,傳媒產業日新月異,學校對專業建設和人才培養的理論本相對落后于市場變革。對技術應用型高職專業培養模式而言,就必須依托于與企業進行產業合作共建,探索校企“人才雙向流動”機制,選派優秀教師到智媒領域企業掛職學習和生產實踐;同時引進具有一線“智媒+”工作經驗的能工巧匠充實到高職學院教師隊伍。引培并舉打造“創新型”雙師團隊,校企合作共育專業人才,這是快速解決“技術型師資”短板的有效途徑。
其三,智能化實訓軟硬件升級,深化“人-機融合”。在高職新聞傳播教育改革領域,除了我們通常意義上說到的課程改革、師資提升、教材革新等手段外,“還有利用高新技術裝備起來的實驗教學中心、虛擬仿真實驗教學中心、專業實踐基地等,成為新聞傳播人才培養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這就需要依托智媒技術引進,建立仿真智媒實驗室,如廣州城建職業學院作為高職院校,在2020年與北大方正電子有限公司合作率先建設“媒體融合與傳播”重點實驗室、一體化4KUHD數字超高清全媒體演播室、數字編輯實訓室、智慧創意策劃實訓室、產教融合平臺等,通過虛擬仿真技術、智慧教育平臺等,將“策劃、采寫、播音、錄制、編輯、分發、存儲、分析、評論、監測”等信息生產與傳播流程融為一體,讓學生可以沉浸式實操、交互式體驗,深化“人-機融合”。
其四,擁抱智能化教育輔助平臺,實現精準培養。人工智能技術的運用和普及,在教學環境、教學方法以及教學形式等方面助力教育領域變革。與媒介發展同步的新聞傳播教育更應該全面擁抱“人工智能”,打造“智慧教室”與“智能化教育輔助平臺”。課前與學生進行跨時空互動,更好地對學生先修預習情況進行數據智能評定,實時對教學內容進行動態調整。在面對面的授課過程中,教師可以充分利用VR/AR等技術呈現豐富多彩的傳媒實踐案例,利用無人機、虛擬布景布光平臺、AI自動剪輯等軟硬件讓學生輕松掌握核心技能,通過存儲和算法技術,還可以輕松實現課程資源的共享和精準推薦,促使人工智能+教育實現新聞傳播規模化教育與個性化人才培養的有機結合。
智媒技術的變革推動傳媒產業市場的變化,市場需求的瞬息萬變使得企業崗位設置及標準的推陳出新,崗位的調整又導致對接崗位的專業人才培養模式必須革新。對高職新聞傳播教育而言,如何擁抱變化,積極革新?那就需要在堅守高職新聞傳播教育核心競爭力的基礎上,針對人才培養方案和實踐教學體系、校企產業合作與師資團隊建設、智媒軟硬實訓條件升級、“人工智能+教育”等方面進行全面改革,才能培養出對接國家戰略需求和適應“智媒時代”發展的創新型新聞傳播人才。人才培養質量的提升與創新,又將反哺推動行業“智媒技術”的繼續迭代發展,從而形成“技術-社會-學校-人才”等之間的良性循環系統。
參考文獻:
[1]彭蘭.智媒化:未來媒體浪潮——新媒體發展趨勢報告(2016)[J].國際新聞界,2016,38(11):6-24.DOI:10.13495/j.cnki.cjjc.2016.11.001.
[2]潘曉婷.未來已來:智媒時代需要怎樣的新聞傳播人才[J].中國編輯,2018(09):45-50.
[3]楊妮,孫華.變革與堅守:人工智能時代的新聞傳播教育[J].出版廣角,2019(01):40-42.
[4]李明德,王含陽,張敏,楊琳.智媒時代新聞傳播人才能力培養的目標、困境與出路[J].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40(02):123-130.
[5]陳小娟.人工智能時代新聞傳播人才培養模式變革研究[J].傳播與版權,2020(10):1-3+19.
[6]宋建武,黃淼.媒體智能化應用:現狀、趨勢及路徑構建[J].新聞與寫作,2018(04):5-10.
[7]Frey C B,Osborne M A. The future of employment:how susceptible arejobs to computerization?[J].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2017,114:254-280.
[8]趙紅勛,馮奕翡.人工智能時代新聞傳播教育的變革邏輯[J].中國編輯,2021(01):78-81.
[9]羅自文,張金龍,楊穎,董慶文.智媒時代傳播技術的沖擊與美國新聞教育的走向——專訪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新聞研究生院院長瓦瑟曼教授[J].新聞大學,2021(03):110-116+121.
[10]張昆.新聞傳播教育史體系芻議[J].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40(02):116-122.DOI:10.15896/j.xjtuskxb.202002013.
[基金項目:本文系2020年廣州城建職業學院校級科研項目-教育研究專項“替代危機與精準培養:‘智媒時代’高職新聞傳播類教育的變革”(課題編號:2020JYYJ02)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