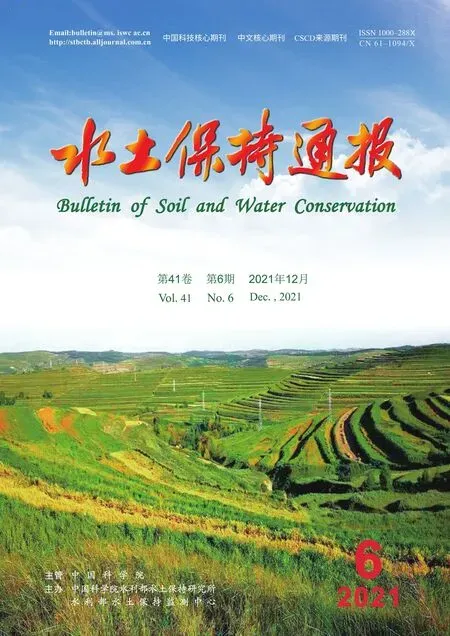基于三維生態足跡模型的山西省礦區2010-2019年自然資本存量動態評估
蔣毓琪, 楊怡康, 朱少英
(山西大同大學 商學院, 山西 大同 037009)
山西省作為黃河流域的煤炭資源型地區,工業化與城市化進程加快推進、資源高度損耗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使得環境污染嚴重與生態系統退化等嚴峻形勢加劇。基于“要素稟賦理論”,豐裕的自然資產成為資源型城市經濟增長的邏輯起點和路徑依賴[1]。煤炭資源開采推動經濟增長的同時,使得礦區環境污染嚴重與生態服務功能衰退,從而引致自然資本容量空間占用超載的負外部性加劇。自然資本存量主要通過測算生態足跡來體現。生態足跡概念是由Ree提出并建立一維模型,隨后Wackemagel[2]于1999年將其擴展到二維模型,側重自然資本的消費量與流量,而非維持區域生態系統平衡的自然資本存量。Niccolucci等[3]學者對模型改進,分別引入生態足跡深度和廣度,量化存量資本消耗與流量資本占用,構建三維立體模型。生態足跡方法具有架構清晰、易于操作的特點,為評估區域自然資本利用狀況與生態環境可持續發展提供理論依據。國內外學者圍繞自然資本,聚焦于三維生態足跡模型,從理論與實證方面進行了相關研究。在理論層面,由于地類的差異性導致其生態占用盈余與赤字不可替代、自然資本尚未耗竭使得足跡深度難以表征流量占用程度。針對生態足跡模型存在的缺陷,方愷等對其進行改進,建立了改進的三維生態足跡模型[4]。實證方面的成果集中于研究區域、研究方法、研究對象等。在研究區域方面,Niccolucci[5]基于40 a的數據從全球視角分析了生態足跡深度和廣度兩個維度的時空演化特征。方愷等[6]基于G20的環境監測數據,探究其自然資本的空間演化時序與格局分異,得出各國自然資本利用變化趨勢表現為資本流量占用減弱、資本存量消耗增強。秦超等[7]基于陜西省30 a數據對其自然資本動態變化進行研究,資本存量消耗是支撐區域資源需求的主要來源。在研究方法方面,自然資本測算主要包括能值法、空間分析法與生態足跡分析法,其中三維生態足跡模型被普遍應用到諸多領域[8]。在研究對象方面,程鈺等[9]對黃河三角洲地區自然資本動態評估并分析其動態演變特征,提出該區域資本流量不足,需引入外區域資本存量加以彌補。吳健生等[10]基于改進三維足跡模型,并引入足跡廣度基尼系數等指標,分別從產品、地類、區域3個維度評估關中地區土地自然資本利用狀況,結果表明中心城市的資本存量消耗嚴重,生態赤字嚴重,其他城市資本存量消耗處于低值區,生態環境壓力較小。礦區作為陸地生態系統的重要地理單元,是資源型城市經濟增長的核心要素,更是煤炭產業發展的空間載體。礦區具有生態環境空間的公共品性質和外部性特征,煤炭資源開采這一驅動因素使得在有限生態環境容量和資源承載力的約束條件下不同類型生態服務伴隨著生態過程發生變化。基于生態足跡理論,生態占用強調對生態空間的需求,生態承載力側重生態空間的供給側,且為經濟發展提供資源并凈化污染。生態占用超出生態承載力范圍導致生態系統失衡。針對礦區生態占用失衡,部分學者[11]提出解決思路:在定性方面,理清采礦權產權,明確責任主體,制定強制性制度與稅收、財政補貼相結合,倒逼其發展循環經濟使外部成本最小化;在定量方面,運用直接市場法、使用者成本法與影子工程法等測度負外部成本。薛建春[12]基于20 a時間序列數據,運用EMD和動力學預測法,探究礦區人均生態足跡的演化規律并利用系統動力學模型對礦區人均生態足跡進行預測。此外,基于市場價值與環境經濟學理論,煤炭開采導致礦區生態足跡赤字主要表現為大氣污染、水體污染、地表塌陷等,理應從這些方面測算其負外部效應帶來的環境經濟損失[13]。綜上所述,自然資本已有研究成果集中于理論與實證兩個方面,以研究區域、研究方法、研究對象等為視角對其進行動態評估。礦區生態環境的相關研究僅限于生態足跡的測算方法、生態占用與生態承載力之間的關系以及從市場價值、生態服務價值等視角定量測度負外部成本,但很少從礦區自然資本角度剖析,尚未在有限生態環境容量和資源承載力的約束條件下對礦區自然資本的足跡深度與廣度兩個維度進行定量研究,更未深入系統地解析煤炭開采對礦區自然資本存量產生的直接作用,這為本文提供了探討空間。
本研究以山西省礦區為例,以自然資本為視角,基于生態足跡與生態承載力核算結果,運用三維生態足跡模型,測算足跡深度與足跡廣度,旨在分析自然資本存量的動態演變特征并闡釋其作用機理,以期為山西省礦區生態修復、環境保護及生態補償提供理論依據。
1 研究區概況與數據來源
1.1 研究區概況
山西省作為典型的資源型地區,煤炭資源具有儲量大、煤質優、煤層厚、易開采的特點,保有儲量為3.00×1011t,主要分布于大同、寧武、河東、西山、霍西、沁水這6大煤田,其中,尚未利用資源量為1.70×1011t。在煤炭資源開發方面,山西省共有生產煤礦616座,合計產能9.63×108t/a,意味著山西煤炭生產以大型煤礦為主。煤炭工業大規模開采、利用對大氣環境產生影響,主要表現為煤礦抽放瓦斯利用率較低、煤矸石自燃易產生CO,SO2等有害氣體;對水資源影響,主要表現為礦井水排出引起地下水位嚴重下降,洗煤過程廢水排放具有重金屬離子以及降水沖刷煤矸石將其有害物質帶進地表水循環[14],通過大氣與地表、地下水體等介質流轉,對山西省礦區生態環境帶來負外部效應。
1.2 數據來源
確定具體的消費項目是測算生態足跡的前提,自然資本消費由生物資源消費和能源消費兩部分構成。山西省礦區資源消費主要來自煤炭開采,涉及到耕地、草地、林地、水域、建筑用地與工礦用地等不同地類(表1),其面積所用數據均來自2010—2019年《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國環境年鑒》《中國能源統計年鑒》《山西統計年鑒》以及山西省各城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等。由于山西省六大煤田不是完整的行政區域,獲取準確消費數據難度較大,本文依據不同煤田所在地市的消費情況整體分析,得到山西省礦區自然資本具體消費量。自然資本消耗量通常用生態足跡來衡量。生態足跡的核心是將研究區域發展所損耗的資源以及排放的廢棄物轉化為一定面積的生物生產性土地。基于不同地類生產能力不同,難以直接比較,生態足跡測算需要引入產量因子與均衡因子兩個參數。由于同一地類生物生產能力在不同地區具有顯著差異,需借助產量因子,比較不同區域間生物生產性土地面積。產量因子表征某區域生態系統的服務能力與全國范圍生態服務能力均值的差異。此外,不同地類的生物生產能力存在差異,難以直接比較,須借助均衡因子將其轉化為同一生產性質的土地面積進行核算。均衡因子表征某一生態系統的不同地類的生態服務能力與區域生態系統的服務能力均值的差異[15]。因此,本文選取了山西省的西山、大同、沁水、寧武、霍西與河東6大礦區為研究對象,不同地類的均衡因子和產量因子借鑒Wackernagel等[16]對中國生態足跡計算時的取值進行估算。

表1 山西省礦區2019年不同地類面積統計 104 hm2
2 研究方法
2.1 三維生態足跡模型
自然資本是指生態系統承載的自然資源與提供的生態服務,某區域經濟增長、社會進步需要消耗自然資本維系其可持續發展。生態足跡作為評估自然資源利用狀況的有效途徑,為衡量自然資本損耗提供了理論依據,而三維生態足跡模型較好地闡釋了其消耗與占用的狀態,揭示自然資本存量和流量的動態關系。基于人類對自然資本存量消耗與自然資本流量占用的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的思想,Niccolucci等[5]引入足跡深度和足跡廣度,用以表征人類對自然資本存量和流量的利用水平,構建三維生態足跡模型。足跡廣度閾值為[0,EC],意味著生態系統的資本供給側數量的上限是生態承載力;足跡深度閾值為[1,∞],表示其值越大,對自然資本需求量越大(圖1)。

圖1 自然資本廣度與深度的物理意義[17]
基礎三維生態足跡模型測算自然資本生態占用赤字是基于生態承載力與生態足跡的差值,忽視了赤字與盈余性質的差異,使兩者作用相互抵消,導致生態足跡廣度偏大而足跡深度被低估是該模型存在的缺陷。因此,本文借鑒方愷提出的改進三維生態足跡模型進行測算。
人均生態足跡深度與廣度,表示為:
(1)
(2)
EF3D,region=EFdepth,i·EFsize,i
(3)
式中:EF3D,region為山西省礦區人均生態足跡面積; EFdepth,region為人均生態足跡深度; EFsize,region為人均生態足跡廣度;i為不同地類面積; ECi,EFi分別為生態承載力與生態足跡。
2.2 模型補充指標
自然資本包括資本存量和資本流量,人類活動的生態足跡分別對地理空間自然資本存量消耗與流量實際占用程度產生影響。為了表征人均生態足跡處于自然深度時煤炭開采對礦區實際生態占用,引入自然資本流量占用率。自然資本存量消耗導致其存量發生變化,煤炭資源開采引致其存量動態變化。為了探究煤炭開采對煤炭存量的動態關系,引入自然資本存量流量利用比。
自然資本流量占用率(ORflow),表示為:
(4)
(5)
2.3 自然資本變化率
自然資本流量占用率與存量流量利用比表征生態足跡的動態關系。為了闡釋煤炭開采對礦區自然資本消耗的足跡深度與足跡廣度空間時序演變的趨勢與速度,引入自然資本變化率,借助多項式回歸模型,表示為:
EFdepth=EFdepth(t)=u0+u1t+u2t2+…+uttn
(6)
EFsize=EFsize(t)=v0+v1t+v2t2+…+vttn
(7)
式中:t為時間變量; EFdepth(t),EFsize(t)分別求導,即t年礦區生態足跡深度與廣度的變化率。此外,2010年起始,t=0; 2015年時,t=5,依此類推。
2.4 剪刀差
自然資本變化率反映了生態足跡深度與廣度的時空演變,自然資本在不同空間時序呈現出差異性。為了進一步探究煤炭開采對礦區自然資本存量消耗的足跡深度與足跡廣度空間時序演變趨勢與速度的差異,引入剪刀差模型,表示為:
(8)

3 研究結果與分析
3.1 生態足跡與生態承載力分析
依據生態足跡模型[18],測算山西省礦區生態足跡與生態承載力(圖2)。結果顯示,人均生態足跡由2010年的5.03 hm2/人增加到2016年為最大值的6.75 hm2/人,增幅為34.19%,年均增長5.70%,自2017年后,人均生態足跡在逐步減少,降低到2019年的5.49 hm2/人。人均生態承載力由2010—2016年逐年下降,2017年以后3 a略有小幅增加。人均生態赤字具有“先增后減”的特點,雖然2016年后,生態足跡與生態承載力的差距總體趨于縮小,但生態赤字現象仍然嚴重存在。

圖2 山西省礦區2010-2019年生態足跡與生態承載力變化趨勢
3.2 生態足跡深度與廣度動態變化分析
基于人均生態足跡與承載力的計算結果,利用公式(1)—(3),得到山西省礦區人均生態足跡深度與廣度(表2)。2010—2019年,人均生態足跡廣度大致呈遞減趨勢,由0.63 hm2/人降到0.47 hm2/人,其中2016—2019年由降低變為增長,但幅度較小且平穩。人均生態足跡深度呈現出“倒U”形特征,由7.98 hm2/人增加到15.34 hm2/人,隨之減少到11.68 hm2/人。人均生態足跡廣度與深度的變化趨勢在2017年后發生轉變,主要歸因于山西省加強生態文明建設,著重強調礦區生態環境修復、治理,減少煤炭資源開采、提升煤炭化工產品附加值,使得能源消耗賬戶中的工礦用地對礦區生態足跡赤字貢獻率降低。這與山西煤炭資源合理利用、布局,降低生態赤字、提升生態承載力的發展思路保持一致。

表2 山西省礦區2010-2019年人均足生態跡深度與廣度 hm2/人
3.3 資本存量消耗與流量占用的動態變化趨勢分析
基于改進的三維生態足跡模型,計算研究區域資本流量占用率是建立于生態承載力大于生態足跡的基礎上。在現實情況中,山西省礦區由于煤炭開采,使得礦井瓦斯、矸石自燃產生CO,SO2,CO2等有害氣體,尤其大量的NOX,形成化學污染與酸雨,對土壤、農林業與水體等造成破壞,給耕地、林地、草地、水域等不同地類帶來嚴重的負外部成本,與公式(4)矛盾,因此,資本流量占用率未能測算。依據公式(5),可得山西省礦區資本存量與流量之間的動態關系(表3)。

表3 山西省礦區2010-2019年資本流量占用率與存量流量利用比
2010—2019年,存量流量利用比呈現出先增后減的“倒U”形變化趨勢。2016年前,存量流量利用比逐年上升,煤炭資源過度開采是礦區化石能源用地存量消耗速度加快的主要原因。2017年,存量流量利用比開始下降,表明山西社會經濟發展對礦區煤炭資源流量的占用越來越小,意味著經濟增長對煤炭資源開采的依賴程度有所緩解。其原因歸結為2016年,山西實施煤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關閉多家煤礦,化解過剩產能,使得山西省礦區自然資本存量消耗逐年減少。
3.4 生態足跡廣度與深度剪刀差
依據公式(6)—(8),計算得到山西省礦區生態足跡深度與廣度的剪刀差(表4)。2010—2019年,礦區生態足跡深度與廣度差異由大變小,其中2010—2016年,剪刀差由1.13上升到1.56,其值處于[0,π/2],表明礦區生態足跡深度呈遞增趨勢,其與足跡廣度同向變動;2017—2019年,剪刀差由-1.53下降到-1.48,其值處于[-π/2, 0],表明礦區生態足跡深度呈遞減趨勢,其與足跡廣度同向變動。因此,礦區生態足跡深度與廣度的剪刀差主要取決于足跡深度的變化。

表4 山西省礦區2010-2019年足跡深度與足跡廣度剪刀差
基于“要素稟賦理論”,豐裕的煤炭資源成為山西經濟增長的邏輯起點,以損耗礦區生態環境、采用粗放式煤炭開采為路徑依賴。隨著煤炭“高污染、高能耗”的開采規模擴大,經濟實現快速發展的同時,礦區環境遭受嚴重污染、生態服務功能衰退,自然資本存量消耗逐年增加,生態占用需求遠遠超過生態承載供給側。人均生態赤字由2010年的4.40 hm2/人增加到2016年的6.31 hm2/人,增幅為43.41%,盡管2019年降為5.02 hm2/人,礦區自然資本存量的生態赤字所減緩,但依然嚴重。基于生態足跡理論,有限生態環境容量、資源承載力與煤炭開采引致生態系統失衡的矛盾突出。經濟處于高速發展時期,有限的生態存量與環境容量作為經濟增長的前提基礎,礦區自然資本存量赤字抑制了山西省經濟綠色健康發展。為了扭轉礦區生態赤字與經濟發展失衡,山西省制定環境規制政策、實行控煤政策,倒逼煤炭企業轉型升級,使得年煤炭產量有所下降,煤炭資源開采與礦區自然資本存量轉為良性互動。礦區生態資本存量與流量的消耗變動有所減緩,甚至出現下降趨勢,但礦區自然資本存量赤字仍然顯著存在。總之,山西礦區自然資本存量時空動態演變受資源稟賦、煤炭開采規模、礦區生態供給與需求、生態足跡與承載力以及資本流量、存量的深度、廣度等諸多因素共同作用(圖3)。

圖3 山西省礦區自然資本演化的作用機理
4 討論與結論
4.1 討 論
(1) 區域生態占用動態評估作為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三維生態足跡是衡量其可持續性的主要方法,諸多學者針對不同區域、研究對象開展研究[19]。從生態占用損耗程度看,山西省礦區生態赤字減小、足跡廣度、足跡深度對礦區生態占用的依賴性降低,與黃河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的生態赤字呈逐年擴大態勢、足跡廣度相對較大且足跡深度相對較高的研究結果存在差異[20]。原因在于山西省作為能源革命綜合改革試點,為了實現煤炭經濟綠色轉型,通過制定環境規制政策、調整煤炭產業結構與創新清潔能源技術等一系列措施,減緩礦區生態資本消耗增幅,這充分表明政策合理制定、產業合理布局、技術創新驅動為緩解生態超額占用、提升生態承載力提供有益思路。
(2) 自然資本供需動態均衡是區域綠色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障。礦區生態環境具有公共品性質和外部性特征,煤炭開采使得礦區在有限生態環境容量和資源承載力的約束條件下環境污染和生態服務功能衰退,表現為生態占用赤字引致負外部效應。為了有效解決煤炭開采帶來的負外部成本,依據“誰受益,誰付費”的原則,需要通過生態補償的方式修復、治理礦區生態環境。我國礦區生態補償依靠政府財政轉移支付很難實現,需要橫向轉移支付與之互相配合解決資金需求,包括征收生態補償稅費、設立生態補償基金、建立生態銀行與生態公益捐贈等多元化補償方式[21]。確定何種補償方式、精準測算補償標準、合理構建補償機制,以此實現降低煤炭資源的消耗程度、減少礦區生態占用赤字、提升生態承載力,確保礦區生態供需平衡,保障煤炭經濟增長與山西省礦區生態環境保護協同發展還有待進一步探討。
4.2 結 論
(1) 2010—2019年,山西省礦區人均生態足跡由2010年的5.03 hm2/人增加到2016年為最大值的6.75 hm2/人,增幅為34.19%,自2017年后,人均生態足跡在逐步減少,降低到2019年的5.49 hm2/人。人均生態承載力由2010—2016年逐漸下降,2017年以后3 a略有小幅增加。人均生態赤字具有“先增后減”的特點,表明生態足跡與生態承載力的差距總體趨于縮小。
(2) 2010—2019年,山西省礦區人均生態足跡廣度大致呈遞減趨勢,由0.63 hm2/人降到0.47 hm2/人,其中2016—2019年由降低變為增長,但幅度較小且平穩。人均生態足跡深度具有“倒U”形特征,作為其重要影響指標的存量流量利用比與之對應,也呈現出先增后減的“倒U”形變化趨勢。此外,生態足跡深度與廣度的剪刀差主要取決于足跡深度的變化。這充分表明山西省礦區人均生態足跡廣度與深度的變化趨勢趨于好轉,其原因歸結為山西省推進煤炭經濟綠色轉型,經濟增長對煤炭資源開采的依賴程度降低,使得能源消耗賬戶中的工礦用地對礦區生態環境的脅迫作用減小。
(3) 山西省礦區生態占用是一個復雜的自然—社會—經濟時空動態演變過程,是由資源稟賦、煤炭開采規模、礦區生態供給與需求、生態足跡與承載力以及資本流量、存量的深度、廣度等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