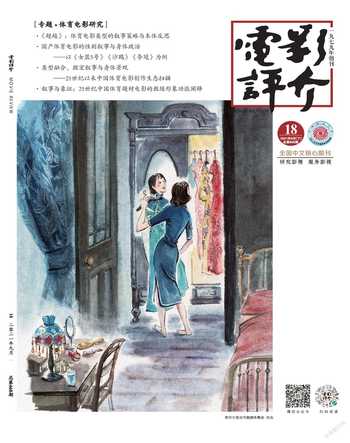生存?抗爭?超越:《人類星球》的紀錄片美學三題
《人類星球》是一部探討人與自然相處之道的紀錄片,以“環境坐標”和“故事集群”的模式講述地球上不同區域極端自然條件下人類頑強生存的故事和精神,全片八集視角獨特、扣人心弦,極具戲劇和視覺張力。除常規自然類紀錄片表現出奇偉瑰麗的自然風光、嚴酷的生存條件和人與自然的矛盾等內涵之外,更為難能可貴的是片中還昂揚著對人類自身的生存關照,頑強的抗爭精神以及超越人性的光輝。人與自然的關系一直是全人類共同關注的一個悠久命題,關系著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核心命脈,在世界不同區域、不同種族的神話傳說中幾乎都能找到相應的佐證。中國古代有“夸父逐日”“精衛填海”“女媧補天”等,古印度有“鹿角仙人”“吠陀諸神”等,古埃及有“原初之水”“太陽神”等,古希臘有“人類再生”“盜天火”等,凡此種種,不一而足。在這些神話故事中最重要的主題就是表現人類對自然的適應、抗爭與超越,人類在整個改造自然的過程中誕生的英雄故事,以及在抗爭自然過程中生發出的心靈和精神超越。從維系人類發展的維度看這種抗爭精神比實踐本身意義更為深遠和崇高。
紀錄片《人類星球》依然延續著人與自然相處之道的主題探討,以典型性地理環境特征為標識和坐標來完成敘事,選取同一個地理環境坐標系中數個人類與自然適應、利用和抗爭等最能反映人類本質力量的精彩故事,表現極致環境下人類對自然適應、實踐、抗爭以及過程中滋生的超越精神。《人類星球》被認為是工業化、標準化紀錄片制作的典型代表,全片共分為八集:海洋、沙漠、北極、叢林、山區、草原、河流和城市,每一集又采用“故事集群”模式由6-10個獨立故事組成,分別講述人類在特定環境中與大自然之間的故事,每個故事平均在6-8分鐘。逐集欣賞《人類星球》,觀眾猶如化身為上古神仙,一天之內上天入地神游世界,忽而從千里冰封的極地到高溫炙烤的沙漠,忽而從野性十足的草原到充滿神秘的雨林,又從無限風光的山巔到變幻莫測的海洋深處。人類一直都有探索未知的欲望和需求,只是這種愿景有時被忙碌的工作和生活的壓力所抑制。好的影視作品能夠讓人撫平浮躁,驅逐庸俗進入靈魂的凈土,給人帶來或震撼或靜謐或深思的視聽享受。《人類星球》這部紀錄片正是通過攝影機不斷延伸著觀眾的眼睛,引導人們遠離工業的喧囂回歸自然,在星光璀璨的夜晚和落日的余暉中探尋生存之美并思索存在真諦,為人類久已失衡的心靈天平找回丟失的砝碼。所有自然類紀錄片都不可避免會將奇幻的自然風貌、迥異的風土人情以及人與自然的矛盾作為主要表現內容,但《人類星球》在這些表現內容之外還高揚著濃濃的對人類本身生存的關照和生命的尊重,以及頑強的抗爭精神和超越人性的閃耀光輝。紀錄片人冷冶夫曾說:“紀錄片的生命在于透過生活觸及人的心靈,紀錄片對個人命運的關注會延伸到對社會的關注,對生活環境的關注,進而擴展到對整個人類生存的關照。”[1]《人類星球》正是通過緊緊圍繞一個個人物在嚴苛的自然環境中艱難求存的鮮活故事,將他們與自然和生命頑強抗爭的精神作為敘述主線,從而使整部紀錄片渾然一體,張力十足,扣人心弦。
一、強烈的生存關照
《人類星球》片名和序言早已直截了當表明主題,“人類為了生存直面險惡的自然,利用創造力努力存活。”生存是人類一切實踐活動的前提和動力,也是人類所有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起點。正如學者封孝倫所說:“人類生命的存在,才是一切最基本、最古老、最堅實、最有力的根源,也是一切活動的起點。”[2]紀錄片《人類星球》中既有不斷借助視聽手段來強化大自然和人類之間對抗矛盾關系來表現對“民生之多艱”的悲憫,又有對超越狹義生存之上的精神存在。《人類星球》中絕大多數人物故事其動因也正是謀求生存的最基本需求。第1集一共由7個獨立故事組成:哈維爾和安吉爾冒險采集鵝頸藤壺、本杰明獵殺鯨魚、夏威夷人沖浪、神秘的鯊魚召喚人布萊斯、約瑟芬壓縮機潛水捕魚、水下獵人瑟斌、攝影團隊潛水拍攝,有五個都是以生存作為人物行動的出發點,其中布萊斯召喚鯊魚的能力在歷史上也是為了獲取生存的基本食物,只是隨著時代發展逐漸演變為一種文化的堅守,除了這些之外只有夏威夷的沖浪和片尾花絮故事兩個部分是基于彰顯對大自然征服的勇氣和榮耀;第2集9個故事中有7個是基于生存;第3集7個故事中有4個是有關生存。這些故事中人物為了自己和家人的基本生活不惜冒著生命和健康的危險而與大自然進行抗爭。第1集中哈維爾與安吉爾冒險采集藤壺,稍有不慎就可能命喪大海的浪濤之下;第2集中馬佛迪也是頂著可能會隨時坍塌的土石帶人開掘地下水道;第3集中盧卡西和伙伴在隨時可能漲潮被封在冰縫的風險下撿拾貽貝;第5集夷真火山采集硫磺;第6集獅口奪食等不外如是。這些鮮活的故事從側面佐證了馬斯洛“需求層次說”,生理需求是人第一層次需求,只有第一層次需求得到滿足后,人們才會去尋求更高層次的需求。人首先是一個物質屬性的人,也是在依托、適應和改造自然的實踐過程中取得生存之本,然后才可能有更高維度的生存之義。不管是福柯的生存美學,雅思貝爾斯的生存與超越,亦或是海德格爾詩意的棲居,也都須在物質生存的基礎之上去建構,這也是眾多哲學家最終都將生存哲學歸結為實踐哲學的重要原因。
人類屬于自然的一部分,但是又超越自然。以上對生存的關照主要還是從生命的存在和物質的客觀性維度來展開,除此之外對生存的闡釋還可以從廣義這一更高維度來著手。廣義的生存還包括精神層面的生存,也就是超越狹義生存這一維度能夠體現人本質力量的“存在”。馬克思在論述這一觀點時使用了“人自由自覺的活動”這一表述,就是說“自由自覺”才是實踐活動的主體也就是人類最高的生存精神境界。
人是世界上最為特殊的一種生命存在形態,在所有生命體中只有人需要在各種各樣實踐活動中不斷確證著自己的存在意義,人的自由也首先體現為對自然的實踐自由。在《人類星球》中,人類自由自覺的實踐主要體現為三個層面:首先是對大自然有節制的索取。人類實踐的自由絕不是對大自然毫無節制的索取,更為可貴的自由應該體現為自控和節制。印度尼西亞蘭博塔小島的捕鯨幾個月才捕一頭,且僅僅是為了滿足村民的基本生存之需;因紐特人若米克萊被要求駕駛獨木舟使用傳統方法獵捕獨角鯨,也是基于保護獨角鯨群數量;蘇米爾駕馭大象采伐木頭既能滿足自己的生存所需,又不會給雨林帶來災難性的破壞;其次體現為對自然和生命的熱愛。欣賞影片的過程中,觀眾時時都能感受到片中人物雖身處極致環境生存艱難但是對大自然卻充滿強烈的尊重和敬畏之情。印度人希亞姆救養瞪羚;亞馬遜阿毋瓜嘉人恩維用母乳哺育猴子;都市養蜂人安德魯·科特在紐約的摩天大樓樓頂養蜂;終生居住在海上船屋的巴喬村人視大海為生命。特別是多貢人在干涸的安圖果湖捕魚這一段落尤其令人震撼,當捕魚的禱詞結束信號槍響起,數以千計的多貢人立刻亂作一團奔入干涸的湖中,導演此時適時的大遠景讓觀眾立刻感受到極為強烈的視覺和心理雙重刺激,洶涌的人群、騰起的水霧與嘈雜的歡呼聲交織在一起,一種原始的富有野性的生命律動隔著屏幕撲面而來,這既是豐收的喜悅狂歡也是感恩大自然饋贈的一種最高禮儀。再次體現為人類改造自然的偉大力量。這種力量并不單純指人類借助科技手段對自然的改造力度,還體現為人類借助和利用自然規律來改造自然的能力,更體現為一種與萬物共融共生的偉大力量。印度人哈利和侄女鑄造生命之橋;奧蘭多受仙人掌啟發張網集水;西巴布亞部落科羅威人建造樹屋;哈薩克族貝瑞克馴鷹狩獵;利用向蜜鳥引路尋找蜂蜜;桑布魯人利用大象尋找水源;大衛·斯塔德利用獵鷹驅逐鴿子;諾丁利用鴿子糞軟化皮革等。每一個故事都充分表明人與自然有機融合的力量,人類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馴化出一身順應自然規律解決生存問題的技能,也更能體現出人從自然的奴隸變為自然的主宰的自由。
此外,西非沃達貝人在有了充足的食物和水的滿足之后跳起的格瑞沃爾舞蹈;馬里人沙漠喜雨后的歡呼跳躍;天堂鳥捕手葛林參加盛裝派對曬曬大會;希哈里勇奪爭勇比賽冠軍。幾個具有強烈儀式感的故事是人類在長期處于生存壓力下得到滿足后深層生命力量的一種張揚和釋放。日本文學理論家廚川白村曾在《苦悶的象征》一書中對人生存本質提出深刻的見解:“稍微極端說起來,無壓抑,無生命的飛躍”。[3]西方多位哲學家如叔本華、尼采和伯格森等也都極為關注人生命深處的力量,(尼采稱其為權力意志),也正是這種深層力量成為人類沖破層層障礙的原力,帶領人們走向生命的遠方。
二、頑強的抗爭精神
縱觀整個人類發展歷史就是一部與自然不斷適應、抗爭和再平衡循環往復的級進過程。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大自然的運行從不會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公元前5世紀古希臘智者普羅泰戈拉提出“人是萬物的尺度”這一著名哲學命題,是為了闡釋人對世界的認識和實踐主要是從人的主觀出發,是對人的主體性的一種強化,與馬克思“人化的自然”具有相似意味。人與自然關系除了相互依存外,還有另一個重要命題就是抗爭,這本就是人類尋求生存之道的應有之義。人與自然抗爭的主題在很多文藝作品中都有涉及,如海明威的《老人與海》,斯皮爾伯格的電影《大白鯊》,災難片《后天》《2012》等。紀錄片《人類星球》除了表達出強烈的對人類自身的生存觀照外,導演還利用視聽語言對人與自然矛盾關系的不斷強化譜寫出一曲人類戰天斗地抗爭精神的生命贊歌,也是一種對狹義生存內涵更高維度的超越。這種抗爭精神在片中被分解為兩種看似對立但又統一的不同情感,一種是人類面對強大的自然力量時所表現出來的敬畏;另一種是與自然抗爭中所呈現出的大無畏精神。這兩種精神特質在人類發展和存續中不斷隨時代演進并代代相傳,一直滲透在人類的靈魂和血液里。這兩種精神在片中也是被導演所贊揚和推崇,從解說詞、鏡頭選擇、畫面構圖以及音樂等方面,觀眾都能明顯感受到。對大自然的敬畏和尊重是人類大無畏抗爭精神的前提,所有的抗爭都必須建立在對強大自然力量足夠的尊重基礎上,否則所有抗爭都會變為無謂的犧牲,非智者所為。
解說詞在紀錄片的敘事語言中具有拓展畫面信息內涵外延、升華主題和凝練哲理化思考的重要功能。“克服、主宰、設計、斗爭、勇士、制服、掌控、勝利、越挫越勇、重新設計星球的每塊表面……”這些都是在片中高頻出現的詞匯和語句,是導演對人類與大自然抗爭精神直抒胸臆式表達。此外,片中對人類與自然抗爭大無畏精神的贊揚重點還體現在對鏡頭選擇和畫面構圖兩個方面。為了突出人類和自然的矛盾關系和力量對比,導演在鏡頭選擇和使用上大量選擇能夠表征自然力量的景物空鏡頭來強化對大自然力量的渲染。以第1集《海洋》第1個故事為例,哈維爾和安格爾冒險采鵝頸藤壺這一段落共使用97個鏡頭,其中不同角度和景別洶涌澎湃的海浪空鏡頭使用了21個,直接表現人和海浪抗爭關系鏡頭有14個。在主人公出場之前就率先使用7個不同景別和視角的驚濤拍岸空鏡頭開場,起到交代故事發生地點環境信息的作用,但更重要的目的應該是為了充分渲染大自然洶涌澎湃的強大力量,強化人類與自然的力量對比關系,為人物出場以及高揚人與自然對抗的勇氣和精神做準備。再輔之以緊張跌宕的音樂,危險緊張的氣氛表現得淋漓盡致,人類勇敢抗爭的精神也實現了完美表達。在“山釀冒著湍急的河流過湄公河捕魚”“本杰明獵殺鯨魚”“圖布女人穿越沙海尋找水井”“馬丁制服阿爾卑斯雪崩”“約瑟法特兄弟維多利亞瀑布頂端冒險捕魚”等每一個故事中都采用了這種手法來強化人與自然的力量對比和矛盾沖突,強化了對人類改造和抗爭自然大無畏精神的表達。除了鏡頭數量上的突出之外,片中還利用大面積自然景物和渺小人類的面積對比的大遠景構圖來突出表現人類和自然力量的強弱關系,這是《人類星球》中較多采用的一種方法,時常結合兩極鏡頭和運動長鏡頭使用,效果倍加強烈。
《人類星球》創新性在每一集片尾都加上一個利用現代攝影技術拍攝典型故事的花絮段落,導演這樣處理有兩點作用:其一是為觀眾打開一扇窗,讓觀眾通過這扇窗了解唯美、夢幻、瑰麗的鏡頭背后艱辛的拍攝過程,滿足觀眾一定的窺視欲望。影視藝術本質上就具有滿足受眾探求、窺視外部世界審美心理的重要功能,片尾花絮的加入能夠讓這扇窗變得更有層次,讓觀眾在認知外部世界的同時還能更進一層,跟著攝影機參與拍攝的過程,帶來更強烈的心理體驗。其二,這些花絮本身就具有極強的矛盾沖突和故事性、觀賞性,攝制團隊雖然各種輔助設備和攝影技術都非常先進,但在大自然面前依然遇到很多障礙。這些花絮故事也正是在表現攝制團隊通過不懈努力逐漸破解難題和解決矛盾的過程,這從另一個維度對人類與自然抗爭精神這一主題表達進一步深化和升華。
三、人性的超越表達
大多文藝作品為了更加貼近生活貼近群眾,會盡可能讓所塑造人物回歸日常回歸人性,文藝批評也多有對《三國演義》中諸葛亮的角色塑造“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的批判。《人類星球》中對人物的塑造恰恰反其道而行,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視聽手段盡可能強化超越人性之上的表達與升華。這樣處理除了提高紀錄片的奇觀性和觀賞性,提升觀眾審美體驗外,更為重要的是反映導演對人類自身靈魂深處最高人格和人性的一種向往和追求,是對病態、墮落與世俗世界的一種拒絕和反撥。所謂“超越”是指人類靈魂深處的一種精神向度,是人對自我的一種理想追求與高級期待。馬斯洛將人的需求所分為的五個層次中最高需求也是“自我超越”或“自我實現”。在紀錄片《人類星球》中,導演主要通過以下三種方式完成“超越”的建構與表達。
(一)行“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
細品《人類星球》中人物,大部分身上都具有一種天然的“超越”。這些人雖身處極端之境,但又以大無畏的精神氣概與大自然進行頑強的抗爭,并在抗爭中鍛煉出超越常人的非常之能。夏威夷人湯姆挑戰人類極限八層樓高(約26米)的海浪;神秘的“喚鯊人”布萊斯具有從深海召喚鯊魚的能力;巴喬村水下獵人瑟斌在不使用任何呼吸輔助裝置的情況下能在水下狩獵5分鐘;在風沙肆虐的沙塵暴和非常饑渴的狀態下,16歲的男孩瑪瑪杜驅趕著維系全家生活的牛群去尋找水源,面對象群的阻擋,以瘦弱的身體擋在象群前,并勇敢的用樹枝驅散龐大的象群;薩米人艾莉埃萊尼·斯里出于責任帶領鹿群橫渡2.5公里亞挪海峽,完成極富挑戰的工作;哈利和侄女培植無花果樹用幾十年時間鑄造生命之橋;肯尼亞草原多羅博獵人拉基塔和同伴為了族人靠智慧和團隊精神以莫大的勇氣面對獅群。即使不考慮人物潛在的行為動機,這些行為和事件依然遠遠超越常人能力與認知。與影視劇中通過虛擬、敘事和影像所塑造的超越常態超級英雄不同[4],紀錄片中人物塑造的基點始終是現實世界的真實,環境、故事、人物雖然不一定與觀眾的生活特別接近,但觀眾觀看紀錄片初始心理定位和期待與觀看戲劇化電影還是有所區別的,也就是說對于紀錄片中的人物塑造哪怕是超越之態,觀眾在心理上更容易產生較高的接受和認同,特別是當塑造的人物本就是超越平凡的非常之人時。此外,特種攝影新技術新手段對《人類星球》“非常之人”塑造的成功可謂功不可沒,水下攝影、微型攝影機、航拍、飛貓、超長焦、紅外攝影等攝影新技術為觀眾提供了很多超常規陌生化視角來窺視人物行為,神秘感和奇幻感得到較大程度的加強。
(二)充滿神秘性的奇觀場景
“奇觀”是一個能夠既能描述審美對象又能評價審美主體視覺和心理感受的美學概念,近年來特別是隨著數字技術賦能影視藝術發展后愈發被頻繁提及或作為評價手段。“奇觀”顧名思義就是指不同尋常非常奇異罕見的視覺景象。《人類星球》中富有奇觀性的景象正是由于其陌生化和神秘性,才讓場景中的人與普通人具有了審美距離。從8集的片名中就可見一斑,導演用來區分故事版塊的地理環境標識如海洋、沙漠、北極、叢林等本身就是常人很少能夠觸達的區域,況且在這些區域中選擇的人物不管是從故事本身還是所發生具體區域都充滿了強烈的奇幻性和神秘性,再加之攝影師精心的構圖、特別的視角、神奇的光影設計以及令人驚嘆的運動技巧加持,這種超越人性的光輝就愈發突出。即使人們最熟悉的城市場景,導演選擇的依然是觀眾陌生并充滿神秘感的特殊區域和視角,比如迪拜大衛·斯塔德利用獵鷹驅逐鴿子、杰夫和朱尼爾地下捕鼠、城市邊緣垃圾堆撿拾食物的底層人群、紐約大樓頂上的養蜂人安德魯·科特等。將尋常的內容以不尋常的視角和形式呈現給觀眾,本就是一種創作人員的自我超越。在第1集《海洋》中,與自然和諧并存最具有靈感和創意的是拉瓜那地區的人們利用海豚捕魚,更為神奇的是捕魚人不但能叫出每一只海豚的名字而且還能通過其下潛動作和方向分辨魚群規模和數量,并確定撒網最佳時機,不得不令人驚嘆。特別是攝影師巧妙地利用夕陽的余暉逆光拍攝捕魚人群,給漁網和捕魚人勾上了一層金色的光芒,在波光粼粼的海面上,捕魚人勝似閑庭信步,平和、恬淡和溫馨的感覺躍然屏幕,好像不是在進行一場緊張的勞作,反倒像仙界一場充滿閑情逸致的休閑游戲。科羅威部落建造樹屋光怪陸離神秘異常的熱帶雨林;印度尼西亞人采集硫磺的地點是在巖漿飛濺煙霧繚繞如同“仙境”但卻危險異常的活火山中;山釀為了家人生活冒險渡過激流洶涌的湄公河,捕魚時所站立的浪濤肆虐的巖石堆;約瑟法特兄弟冒險捕魚的維多利亞瀑布之巔等不一而足,每一個環境、每一個場景對觀眾來說都堪稱極致之地,美則美矣,但也險到極致。這些場景對常人而言別說親至就算夢中都難得一見,只能“此景只應天上有,人間難得幾回觀”,非神仙不能居也。另外,攝影師精彩的用鏡也為場景賦能很多,每有神來之筆。如第3集《北極》中艾莉埃萊尼·斯里帶領馴鹿過河后一葉小舟飄蕩在水面,遠景中后景天空掛著一條瑰麗的七彩長虹,如同仙境;第7集《河流》中約瑟法特兄弟在維多利亞瀑布之巔捕魚時,鏡頭逐漸拉出,瀑布激流湍涌順勢而下,水霧騰空而起,落日的余暉中映出七彩的霞光,畫面唯美奇幻勝似仙境,類似案例在片中不勝枚舉。
(三)自我主宰,但兼濟天下
電影《英雄本色》中,周潤發飾演的小馬哥有句臺詞:“我就是神,神也是人,能掌握自己命運的就是神。”劇中小馬哥說這句臺詞時除了要主宰自己的命運外還為了所崇尚的更高一級精神追求“義”而幫助自己兄弟,連最后的死亡也是因為要保護他人。由是觀之,當人具有了超越常人或超越生存之上的“愛、良知、道義、信仰、光明”等人文關懷和理想精神之時,就是人性光輝最為閃耀之刻。人物具有行非常之事是“超越”的基礎和前提,當非常之能轉化為主宰自我命運和他人命運能力時,才是最高需求“自我實現”之核心要義。世俗之人往往為生活、前途或各種欲望等“他者”所主宰,猶如風中之草抑或水中浮萍顛沛搖擺,聲非出于己心,行非己所欲行。反觀《人類星球》片中諸人物,面對大自然的豐厚饋贈時只取個人所需絕不過量,視為“節制和適度”;面對激流險灘沙漠嚴寒等重重挑戰,為家人或部落而勇往直前,視為“無畏和勇氣”;面對失去父母的小猴、瞪羚以及失明老人伸出援助之手,視為“愛與感恩”;訓練老鷹驅逐鴿子和狩獵、借助海豚之力捕魚、利用向蜜鳥尋獲蜂蜜,視為“共融與和諧”。當人做事的出發點不是為己而是為了他人、集體和世界的時候,人物身上也就閃爍著超越的光芒。瘦弱的本杰明為了全村人幾個月的生存向巨大的抹香鯨發起致命一擊,慢鏡頭中當他從小小船頭擎著長矛高高躍起的那一刻,技術和勇氣賦予了他神一樣的光輝;30年來每當旱季來臨迪亞羅都會到干涸的安圖果湖捕魚,只是為了家人能夠熬過夏天的尾巴,當幸福之門為他和他的家人打開那一刻,在他身上也能看到超越的人性之光;奧蘭多受仙人掌啟發學會張網集水已然能夠滿足自家需要,但是他卻夢想著為整個部落從天上集水;亞馬遜阿毋瓜嘉人恩維用母乳喂養小猴;因紐特人若米克萊為了家人幾個星期的口糧駕獨木舟用傳統方法捕獨角鯨;希哈里為了部落榮譽而勇奪爭勇比賽冠軍;藏族父親斯坦金為送孩子上學而穿越危險的大披巾;建筑師諾曼·福斯特為全人類設計出零碳排放的建筑;希亞姆救養瞪羚等。一樁樁、一件件故事中的主人公無一不是為了他人、集體、世界而挑戰著極限,讓不可能完成的事情變成鮮活的現實,讓人性的超越和光輝普照大地。
【作者簡介】? 高賀勝,男,河北唐山人,北京師范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博士生,河北傳媒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影像文化傳播研究。
參考文獻:
[1]冷冶夫.關注人——紀錄片永遠的情結[ J ].當代傳播,2004(02):64.
[2]封孝倫.審美的根底在人的生命[ J ].學術月刊,2000(11):5-7.
[3][日]廚川白村,魯迅譯.苦悶的象征[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14.
[4]周星,雷雷.中國影像:超級英雄創造的思考[ J ].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02):77-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