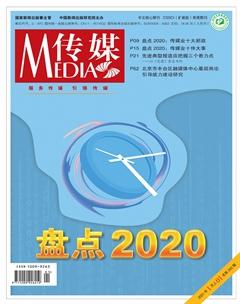閱讀研究的萬花鏡
徐麗芳
摘要:閱讀是一種個人化的認知行為,但也在很大程度上體現為人群和社會的文化活動和現象。閱讀首先是一種精神活動,但其所倚賴的生理基礎和其所伴生的消費活動都是物質維度的;閱讀是社會成員自組織的利器,但也是開展社會控制的有效手段。《閱讀社會學》一書從社會學視角研究閱讀,深入、系統地揭示了閱讀作為一種復雜人類活動所具有的豐富維度。
關鍵字:閱讀 閱讀社會學 認知 文化消費
閱讀是人類通往精神和意義世界必經的關隘,也是徘徊往來、縱橫馳騁于這個與物質世界平行的虛擬世界的輿馬舟楫。這個世界與人們身處的大千世界、紫陌紅塵一樣豐富多彩、變幻莫測,而閱讀作為其間的工具和手段,在多樣性、豐富性上不遑多讓。《閱讀社會學》一書讓讀者透過社會學的萬花鏡,看到閱讀作為一種錯綜復雜的人類社會現象,相反相成、對立統一的各種向度和表現。粗略地說,閱讀既是個人的也是社會的;既是物質的也是精神的;既是自組織的也是社會控制的。
一、閱讀:個人和社會的視角
閱讀是頗為個人化的行為。在中國其一直被視為文人墨客專屬的風雅之事,如倪文節公所言:“松聲、澗聲、山禽聲、夜蟲聲、鶴聲、琴聲、棋子落聲、雨滴階聲、雪灑窗聲、煎茶聲,皆聲之至清,而讀書聲為最。”而所謂“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這實際上是說不同讀者因為生活經歷、興趣愛好、受教育程度等的不同,對同一個文本的藝術形象會有不同解讀,強調的是閱讀感受的個人化問題。講到閱讀偏好,更常常有人援引西諺“談到趣味無爭辯”,而拒絕對讀書相關的高下、雅俗、有用無用的指指點點。
但無庸諱言,閱讀也在很大程度上體現為人類群體、社會的活動和現象。就像《閱讀社會學》指出的,閱讀是一種社會交往方式。19世紀中期,很多美國人閱讀雜志小說的動機是獲得談資以方便社交。就像科爾頓所言:“有些人為搜集談資而讀書,這些人占讀書人的大多數”。而成為讀者,是現代人的社會權利和責任。197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布的《圖書憲章》第1條就明確規定:“每個人都有閱讀的權利,社會有責任保障每個人都有機會享有閱讀的利益。”閱讀同時也是社會身份和社會地位的標志和象征。從公元前2000年前后巴比倫的達官顯貴、埃及的法老國王、古印度的高等級社會階層到17世紀法國的特權階層,讀寫能力和閱讀行為都是重要的社會分層和區隔標準。現代社會雖然逐漸普及閱讀,但是仍可通過閱讀相關的狀況大致判定不同讀者的社會地位、職業類別、家庭收入、自身修養等方面的差別。而從宏觀角度來看,閱讀是社會歷史文化積累與傳遞的非常通道,因為就像俄國作家赫爾岑所說“人類的全部生活都依次在書本中留下印記”。此外,閱讀也是提高人口質量的重要途徑,以色列、德國、日本國民都酷嗜讀書,其國民也相對地對人類做出了較大貢獻。同時,就像《閱讀社會學》指出的:一個社會閱讀的深度和廣度“既能體現該社會對人類文化的接受、吞吐能力,消化、創造知識的潛能,又是測量這個社會文化程度的重要標尺,還是社會進步的基礎”。
二、閱讀:物質和精神的維度
閱讀誠然是一種精神活動,是一種從書面語言和其他書面符號獲取意義的社會行為、實踐過程和心理過程。其本質是理解文本,學習文本,然后構建新文本。同時,閱讀亦是使精神生活豐盈、美好的必要條件之一。蘇軾《記黃魯直語》曰:“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義理不交于胸中,對鏡覺面目可憎,向人亦語言無味。”培根則說:“讀書足以怡情,足以傅彩,足以長才”。而且不同的閱讀活動有不同的功用,“讀史使人明智,讀詩使人聰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道德使人有修養,邏輯修辭使人善辯”。
同時,閱讀亦有其扎實的物質基礎和表現。首先,閱讀的發生均有其生理基礎,即先由眼睛感知文字等符號,然后將信息通過神經傳至大腦,再通過大腦視覺中樞、言語聽覺中樞等協同進行復雜的分析、綜合活動以理解當前信息,并根據特定方式進行大腦的編碼、儲存。美國埃默里大學的研究人員發現,讀完一本好書后,人的大腦會發生實際的、可監測的積極生理變化,并且這一變化會持續至少5天。而非智力原因的閱讀障礙往往是大腦結構異于常人,或神經與器質性損傷等原因造成的。其次,閱讀作為一種文本消費過程,不僅涉及文化、精神內涵的消化、吸收,同時也涉及對作為“物”的文本的消費。而正是由于閱讀涉及的物質消費,許多國家和地區通過法律規制等為國民閱讀提供切實的物質保障和制度支持,如將國民閱讀經費納入財政預算,免費提供讀物,提供公共閱讀場所、閱讀設施和閱讀資源,等等。而在經濟和產業發展的意義上,閱讀的這個維度拉動了滿足人們文本需要的產品和服務的生產、分配和交換,從而形成閱讀的社會產業。這個產業在全世界的許多國家日益成為國民經濟重要的組成部分。
三、閱讀:自組織和社會控制的手段
閱讀還是一個社會自組織的利器和主要手段。其主要表現形式之一,是各種以閱讀為紐帶的詩社、文社、讀書會等。一般認為1902年瑞典奧斯卡·奧爾森創立的“學習圈”是世界上最早的現代讀書會。但就閱讀自組織實為志趣相投者以書籍和閱讀為紐帶的集會、交流而言,其在世界各國的發展有著更為久遠的歷史。我國早在《禮記·學記》中即言:“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陶淵明亦謂:“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中國文人向來有志同道合、意氣相投者集會結社的傳統。這種文人階層或吟風弄月、賦詩作文,或揣摩時文、交流心得,或結伴出游、宴飲賞樂的自組織活動自魏晉南北朝開始萌芽,經歷宋元的發展在明代達到頂峰,至清朝開始衰落。而近代隨著圖書館、閱報所、民眾教育館、民眾學校等公共文化機構興起并紛紛舉辦各種讀書會,如1931年江蘇宜興縣圖書館成立宜興縣立圖書館讀書會、1934年浙江流通圖書館成立均益讀書會等,遂使對閱讀有興趣的普通民眾亦有機會加入各種讀書社團和閱讀活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隨著社會經濟文化發展水平的提高,各種依特定讀物、特定主題、特定讀者群體、特定機構、特定地區而生的讀書會如“日本《紅樓夢》讀書會”“音樂晚茶讀書會”“紅領巾讀書會”“金融博物館書院讀書會”“華夏醫學讀書會”等蓬勃興起。它們在政府機構和政府職能鞭長莫及的地方,發揮著文化認同、社會整合和公共域構建等功能。
而與此同時,由于社會閱讀活動對個體思想和行為具有特殊的影響和作用,因此,這往往也是開展社會控制的有效途徑和手段。《閱讀社會學》認為,閱讀社會控制的內涵是社會通過直接或間接的方式、以強制或非強制的手段對其成員的閱讀活動加以規定或影響,目的是使閱讀活動系統規范化,從而維護社會的正常秩序——這也是閱讀社會控制的必要性和正當性之所在。此外,筆者梳理了閱讀社會控制的內容和類型,包括:對讀者閱讀活動權能的社會控制;對閱讀內容和閱讀資源的社會控制;對閱讀文本生產、傳播、消費各環節和各領域的控制,等等。其中,筆者特別探討了閱讀領域的“反控制”,如古今中外官方越是查禁某些讀物,其越能在地下流行乃至出現洛陽紙貴、一書難求的狀況。更深一層則是,書籍本身就代表秩序——不管其為創作者、生產者所預設,或為權威人士、機構所強加,或出于認知和闡釋的需要,并表現為一套限制、義務、規矩或名分。但是,總有讀者試圖打破甚至顛覆其中的秩序,從而達成“反控制”的目的。
閱讀是一種迷人的活動,其可以作用于個人的情感、理智、修養;也可以形成、形塑一時甚或一代的文化、精神偏好和趣味;還可以影響國家和社會的文化、經濟、政治面貌與走向。而《閱讀社會學》的問世,為所有對閱讀感興趣的讀者和研究者提供了一副“新眼鏡”,可用之靈動而不失嚴謹、科學地觀察和領略閱讀的萬千氣象。
作者系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數字出版研究所所長、教授
參考文獻
[1][新西蘭]史蒂文·羅杰·費希爾.閱讀的歷史[M].李瑞林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
[2]蔣萌.全民閱讀中的社會自組織研究[D].南京:南京大學,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