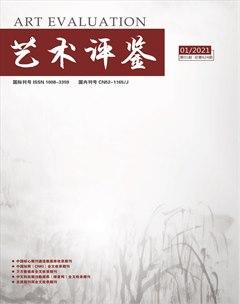克里姆特和席勒作品的時代背景和人文環境分析
史霞霞
摘要:克里姆特和席勒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偉大的表現主義畫家,兩者的作品使我們產生的不止是對藝術哲理性的思考,更多的是對生命“本真”的理解。克里姆特的作品哲理性強,而席勒的作品更多展現的是對自我的一種解放。本文通過比較研究法,總結、歸納兩者作品形成的時代背景、人文環境以及師承關系影響因素,讓我們更好地思考和感悟他們藝術作品的內涵,從對比作品中受到藝術的啟發。
關鍵詞:克里姆特? 席勒? 分析
中圖分類號:J60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3359(2021)01-0020-04
任何一位藝術家作品風格的形成都與他本人的成長經歷和所處的歷史背景、社會因素及藝術思潮息息相關。所以,要想更深刻地理解藝術家的作品就必須分析時代背景和人文環境。克里姆特和席勒生活在世紀之交的維也納,當時的時代背景及人們思想觀念的變革為“新藝術”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克里姆特和席勒是師徒關系,也是朋友關系。兩個人的個人生活經歷、所處的時代背景和受到的文化思潮等層面均有相似之處。
一、個人成長經歷對作品的影響
古斯塔夫·克里姆特出生于維也納的一個金銀雕刻手工藝匠的家庭,接受學習傳統的學院派風格繪畫。1888年和1889年,他繪畫了大量戲劇史壁畫和美術史博物館的壁畫。1897年以后,他的畫風大變:第一次突變是因為父親的死亡,讓克里姆特親眼目睹了死神的鐮刀如何從他耳邊經過,令他終身難忘。另一重大“挫折”是由于他以象征主義手法創作了《哲學》《醫學》《法學》三幅壁畫遭拒,成為當時飽受流言蜚語攻擊中傷的維也納藝術大丑聞。壁畫被拒的原因,是因為他反叛以往的學院派風格,運用了在當時比較前衛的象征手法,明確表達了對自己過去遵循的學院派“歷史傳統主義”的離經叛道和分離的跡象。著名美術史學家維克霍夫(Wickhoff)認為:“在人們指責作品充滿色情的背后,隱藏著人們對其思想內涵的排斥。作品流露著叔本華和尼采哲學的悲劇主義,帶著很強的未來主義色彩”。如同印象派的前輩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被當時的沙龍藝術團體被拒一樣,克里姆特的繪畫風格不被當時主流藝術承認,他認識到腐朽的學院派藝術再這樣下去,繪畫將會陷入停滯狀態,追求新的表達形式,表達自己對繪畫的認識對于克里姆特來說更重要。45歲時克里姆特結識了另一位新藝術運動的中堅柯克西卡,接受了表現主義思想,自此,他在思想上開始尋找屬于自己的表達手法,表現出他的哲理性和對世界的重新認識,畫面具有平面化、裝飾化以及哲理性的特點,幾何化的構圖形式給他的繪畫作品注入了強大的活力。1918年2月6日,克里姆特逝世,享年55歲。
1890年,席勒出生于奧地利圖倫的小鎮,時年克里姆特正好28歲。席勒曾去由克洛斯特新堡修道院所開設的學校學習繪畫。1905年1月1日,席勒父親去世,造成了席勒死神籠罩的童年。在1918年席勒的妻子埃迪特因一次流行感冒死亡,席勒茫然地凝視著埃迪特臨終前的痛苦模樣,被自己也許立即會死去的恐怖所纏繞;他關緊家中所有的窗戶和門,還加上了鎖,試圖阻止所有的感冒病魔的侵入。那時,與其說他是被妻子的死所震撼的男人,不如說他是因恐懼疾病而渾身顫抖的二十八歲“小孩”。可以說死亡籠罩了席勒短暫的一生。他曾經說:“是死亡將我塑造成藝術家,死亡是我作品的主題”。他的恐懼體現在他的藝術作品上,就像尼采在《悲劇的誕生》中說到希臘人對于生命的態度,認為“這一類人的生命之強健已經到了這一地步,以至于他們對于丑的渴望超過了對美的渴望,他們對可怕的、邪惡的、神秘的、毀滅性的、危險邪惡、痛苦的東西著迷遠遠超過了對優雅的、輕松的、善良的、了然的、安全的、快樂的東西的喜愛,著迷于這些東西并戰勝它們成為這一群強健者實現自己的權利意志的最高方式”。同樣的,席勒通過自我對生命本真的理解,從他生活的恐懼當中解脫出來,實現了自我的救贖,同時也給予世人以精神上的慰藉。
1918年10月31日席勒去世。在寫到席勒時,格奧爾格·特拉克爾說“在充滿腐朽氣息的阿諛奉承之中,他閉上了他的雙眼”。與此同時,席勒也意識到作為人的痛苦:“我只能說,因為我要……犧牲我自己,像殉道者一樣生活”。
克里姆特和席勒作品的第一次重大轉變是在命運開始都遭受了失去父親的經歷,造成他們心靈的巨大創傷。第二次重大轉變是對傳統學院派的反叛和分離,作品因此從象征走向表現的轉變。
二、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意識形態、藝術思潮因素對作品的影響
“新藝術運動”在歐洲和美國產生并發展成熟,這一運動源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社會意識形態和藝術思潮的影響。“新藝術運動”在各個國家都有不同的稱謂,其中法國稱為“新藝術”,奧地利稱為“分離派”,出現了以克里姆特等為代表的“裝飾畫”藝術家。新藝術運動從意識形態上看,它的興起說明了舊時代的結束和一個新的時代來臨,是一次“革命”的藝術運動,它僅僅屬于那個時代的語境,很快這一運動就消沉了。“為藝術而藝術”的思想是19世紀下半葉提出的,對后來“新藝術運動”在思想上奠定了理論基礎,認為美是改造客觀世界的偉大力量,告誡藝術家要回到大自然中去,發現拯救心靈的藝術表現形式。工藝美術運動強調的簡單、樸實的中世紀風格,為“維也納分離派”及其他團體或畫派奠定了美學基礎。另外,19世紀末法國的象征主義以及后印象派繪畫藝術對新藝術運動也有很大影響。象征主義表現主要體現在曲線風格的運用上。日本的浮世繪也隨著當時的經濟交流,流入歐洲,被歐洲印象畫派所發現并汲取其中“單純”的元素,浮世繪以干凈、明麗的畫面,特有的平面裝飾感,影響了眾多的畫家。
新藝術運動為克里姆特的藝術思想帶來一次次的突破和轉變,充分發揮自身的藝術思想。但克里姆特所處時代的主流意識還是古典主義學院派寫實藝術的年代,繪畫因刻意模仿古代風格,因此缺乏生氣。克里姆特所能接受到的教育范本,只是奢華眩目的歷史畫,或是當時紅得發紫的學院派大腕自命高雅的歷史畫。克里姆特28歲之前的繪畫作品受到學院派基本功寫訓練的影響,這一時期的作品(包含28歲的作品)有《男人體習作》作于1877-79年間(15-17歲)、《青年時代》素描稿1882年(20歲)、《寓言》1883年(21歲)、《田園詩》 1884年(22歲)、《倫敦環球劇院》 羅密歐與朱麗葉1886-88年(24-26歲)、《Taormina古代劇院》1886-1888年(24-26歲)、《盧森堡街頭演出的喜劇演員》1884-1892年(22-30歲)《金衣婦女像》1886-87年(24-25歲)、《維也納老城市劇院觀眾席》1887-88年(25-26歲)、《少女與夾竹桃》1890(28歲)、《鋼琴家Josef Pembaur像》1890(28歲)。從《金衣婦女像》開始,其作品的風格開始具有明顯的裝飾性,但仍未擺脫古典風影響。從他的三組畫:《哲學》《醫學》《法學》被當時沙龍藝術團拒絕之后,他作品的風格大變。之后的作品《婦女的三個階段》《吻》《生命之樹》《生與死》和《處女》等可以看出他風格的變化,同時受曲線風格、簡單樸實的工藝美術的中世紀風格、印象派等藝術運動的影響。
19世紀初20世紀末的歐洲藝術思潮涌入,打破了傳統藝術美的典雅氣息,以內心的沖突、矛盾激發強烈的情感,藝術家“隨著美的寶座地位逐漸被丑、變形、怪誕、空虛、斷裂等范疇所取代,隨著哲學對人深層意識中種種隱蔽力量和對人之巨大創造潛能的揭示和鼓勵,藝術也進入了一個充滿變革、標新立異、風格多元和個性突出的時期”。顯然,維亞納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藝術氣氛顯得陳腐不堪,反對新興的藝術,處于自身的藝術又不能再繼續發展下去的矛盾當中。當時埃貢·席勒也是分離派的一員,作品同樣受到當時藝術主流畫風的排斥和詆毀,由蒂姆和貝克爾編輯的德國藝術百科把席勒劃分到色情文藝家的行列,因為席勒的藝術就是對人體赤裸裸的描繪和表現。他的男女模特表現出難以置信的直率、夸張變形。席勒自己說:“對他而言,沒有什么‘現代性,存在的只有‘永恒”,他對新藝術家的定義是能在根本上發揮自己、建立自己的基礎,并且不信賴過去和傳統才是新藝術家。
三、藝術觀念的傳承
克里姆特和席勒在藝術觀念上既有相似之處,也有相背離之處。相似之處:一是克里姆特和席勒早期都接受了正規正統的繪畫技巧及基礎訓練;二是都參與了維也納“新藝術”運動,使得二者的作品風格有相似之處,即富有強烈的裝飾色彩;三是反叛當時保守的藝術主義,成立并加入“維也納分離派”;但是隨著二者在藝術表達方式、個人風格上表現出迥然不同的追求,克里姆特繪畫藝術發展為典型的表現主義,個人風格主要以“裝飾性”為主;而席勒在藝術上追求純粹的藝術表達;克里姆特注重作品商業性和表現性,席勒則注重自我的解放。
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維也納陷入了一種對死亡和浪漫的“美麗尸體”的追求。尼采的“上帝死了”,人們頓時失去信仰,思想和精神處于極度的混亂和焦灼狀態。畫家們通過他們的畫表現自己對這個世界的認識,力圖找回自我、尋找信仰。克里姆特是“分離派”的發起人,起到了中堅的重要作用,他的作品給當時的人們一種積極向上的活力,試圖擺脫沒有信仰的混亂思想的影響,實現他理想化的、哲理性的世界;席勒出生的時代較老師克里姆特的時代更不堪,因為歐洲當時處于一戰之前,社會一片混亂,貧富差距造成了很嚴重的社會問題,人們思想上處于無信仰狀態。席勒的時代造就了他走向自己的內心,表現出純粹的繪畫本體語言。從克里姆特的《生與死》,席勒的《死神與少女》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們對繪畫藝術的追求不同。
克里姆特的《生與死》用繪畫的方式展示了生命的輪回,畫面中有剛出生的嬰孩,婦女,老嫗,男子和骷髏頭,這些擠成一團的形象組成了“人肉盛宴”,預示死亡寓意的骷顱頭,都展現了他在尋找一種心靈的安頓。人物層層疊加,使空間增加、層次豐富,使人在有限的空間背后感知到生命的意義,不斷超越死亡的界線,是一種生存欲望的延續。畫家拋棄對傳統題材的表現,而是用一種悲觀主義的眼看待這個世界。
席勒的《死神與少女》取之于希臘神話,畫家是以自己和妻子埃迪特的形象創作的。畫面中心少女緊緊地摟抱住死神,少女紅黃相間的連衣裙與死神黑褐色的衣服,呈現熱烈與寧靜的對比。席勒從題材的選擇,到內心追求“基督式”的憐憫情懷,他的精神訴諸于純粹的繪畫作品中,脫離了哲理性和理想的追求,回到他的內心世界,實現單純的表達自己。
兩者作品背后都對“永恒輪回”和死亡進行思考,克里姆特用畫面金銀輝煌的裝飾性手法和平面特征上表達對生命的哲理性思考。席勒更加注重的是自己內心的表現,繪畫回到畫家自己的生命體驗。克里姆特其一生仍然沒有擺脫“權威的光環”,始終享受這世俗社會的名聲和財富。1912年席勒的作品《隱士》暗示了席勒和克里姆特分道揚鑣。畫面中兩位藝術家都穿著黑色長袍。為了突出畫中自己的落難狀態,席勒把自己和老師克里姆特看作是游走于社會邊緣的人,著重凸顯了作品中的人物痛苦、無助、困惑。
四、結語
縱觀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維也納,正處于時代動蕩不安、社會思潮發生重大變革的歷史時期。在這樣一個社會、思潮轉型的背景下,克里姆和席勒勇于突破腐朽的傳統思想觀念。在充滿詆毀和恐懼的時代氣息下,克里姆特和席勒并沒有失去對生活的信念,也沒有自暴自棄,而是掙脫思想和生活的束縛,沒有辜負藝術對藝術家的教養,始終保持對繪畫藝術的純粹性。席勒學習老師克里姆特的繪畫方式從他大學時期就已開始,克里姆特一度成為席勒繪畫藝術上崇拜的偶像,包括藝術風格、繪畫題材的選擇等等都追隨老師。他們的作品風格和面貌在一定時期具有相似性和共同性,但是隨著他們的審美情趣不同各自也都進行了不同的嘗試。
在今天,處于世紀之交的兩位藝術家克里姆特和席勒,我們可以看出他們藝術觀念和藝術形式所展現出來的超前性以及對于自身存在、價值得以永存、體現的強烈意識。“生”與“死”伴隨著一個人的一生,由此衍生出來的恐懼、焦慮、痛苦、危險感意識,不得不讓我們去思考自身如何應對和重新評估,過去和未來亦是如此。真正的藝術或多或少蘊含著生命和死亡意識,蘊藏著對有限生命的無限超越。
參考文獻:
[1][5]劉振.關于克里姆特《哲學》《醫學》和《法學》作品的分析[J].青年文學家,2014(30).
[2]滕守堯.藝術社會學描述[M].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92.
[3][英]塞爾斯登,[德]茨溫格伯格編.埃貢·席勒[M].劉媛譯.濟南:山東美術出版社,2008.
[4]龔建光.不僅只關乎“色情”——埃貢·席勒繪畫藝術簡評[J].佳木斯職業學院學報,2016(03).
[5]劉振.關于克里姆特《哲學》《醫學》和《法學》作品的分析[J].青年文學家,2014(30).
[6]馮驥才.維也納情感[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
[7]王穎.淺析克里姆特作品背后的隱性世界[D].福州:福建師范大學,2010年.
[8]馬健昕.精神分析美學與藝術創作心理[J].藝術教育,200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