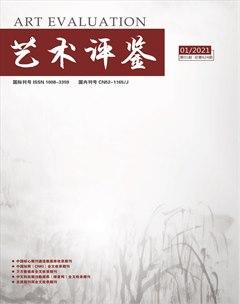田野:舞蹈文化的講述者
張璇
摘要:針對現階段舞蹈作品平面化、邊緣化和失語癥三個現象,筆者提出深扎田野的重要性,重訪在社會轉型當口下民間舞者的工作走向。田野將舞蹈事項放置于既定語境中,用身體語言表達地方性的符號意義,在此基礎上以包容的態度理解跨文化的舞蹈發展問題,客觀地看待舞蹈文化自覺性和多樣性的問題。
關鍵詞:舞蹈? 文化? 田野? 語境? 符號
中圖分類號:J70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3359(2021)01-0050-03
最近“深扎”一詞在關于舞蹈的論述中多次出現。什么是深扎,為什么要深扎,深扎的意義是什么等問題成為討論的中心。簡而言之,“深扎”即為職業舞者回到民間當中進行民間調查,從民間生活和民間舞蹈形態中感受民族舞蹈文化、激發創作靈感、提取原汁原味的舞蹈要素。
此外,相對于社會制度、組織機構和經濟的因素,文化、價值觀和自然在社會轉型時變化較慢,“快餐文化”使舞蹈得了“失語癥”,走向“扁平化”和“邊緣化”。失語癥讓舞蹈的語法結構混亂、語義不明;扁平化來自于個性舞者的獨我作品,不在乎觀眾是否能看懂,風格性、民族性不明確;邊緣則是指舞蹈成為大眾的伴酒菜,歌伴舞、酒廳舞越來越成為大眾接受舞蹈的方式,舞蹈是否只有在做配角時才能被接受?“深扎”為從事舞蹈事業的人解決失語癥、扁平化和邊緣化等問題提供了方向。
一、田野調查與舞蹈的認知
田野調查法越來越來多地被運用于舞蹈學科中,成為研究舞蹈的重要方法之一。田野調查從不同角度可分為多種類型,從調查內容分:綜合調查、專題調查、典型調查和個案調查。對舞蹈而言,根據不同的調查目的可以選擇與之相對應的類型,舞蹈本身具備多樣性和風格性的特點,田野調查具有其他方法不可代替的功能。
(一)田野:為了探求舞蹈語言的交流功能
當遇到“舞蹈是什么”的問題時,總擔心在定義生成時不自覺地陷入到本質化的窘境中。舞蹈是一個隨著時代變化不斷被建構的概念,不同的學者在不同時期會動態地提出自己對舞蹈的理解。本質意味著靜止,但如果我們將其放置在一個相對變化的時空中提出觀點,也是一種多維的共享。舞蹈是藝術、是語言、是宗教、是符號,歸根到底來說,舞蹈是一種文化,是一種用于交流的文化,至于藝術、宗教、符號只是因為表達的方式和存在的空間不同,形成了多種表現形式。
舞蹈作為交流的手段是以人體為載體,動作為主要表現手段,所以對于“動作”文本的呈現成為舞蹈文化分析的首要對象。按照一定的文化準則、意涵、邏輯、價值判斷展開舞蹈動作文本的實施。例如:日常生活中晚輩見到長輩需要“鞠躬”行禮,長輩和晚輩之間的行為規范不能顛倒。換句話說,“鞠躬”的動作表達了“尊敬”的意涵,舞蹈是以有節律、典型的、美化的動作表現特定的文化意涵和象征意義。
(二)田野:幫助理解舞蹈的存在語境
舞蹈的交流以合乎本民族規范的語言說著本民族的文化,舞蹈動作是表象,將動作放置于不同語境當中表達著迥然相異的文化內涵。根據馬林諾夫斯基的文化功能主義,將語境分為語言性語境、情境性語境、社會性語境。語言性語境強調上下文的提示關系:例如串翻身動作本身毫無意義,但放置于紅軍上雪山的情境中便賦予了“沒站穩滾了下來”的語義,此時將原本抽象的舞蹈動作變成了具象的表達。如果將串翻身沒站穩的涵義放在整個舞蹈作品的語境中,則體現出“艱難萬分”的內涵。在語言性語境中,注重語境大和小、局部和整體之間的層次關系。情境性語境意在說明共試下的發生,例如餐桌上的玫瑰花指向裝飾的美感,當情境變為男生送女生的禮物時就暗含了愛情的寓意。藏族舞蹈作品《紅河谷·序》利用演員開場時胳膊和腿的棱角分明的靜態姿勢描繪了一幅雪域高原上的軍民魚水情。
值得注意的是社會性語境:即表述人的文化背景,語義的產生與“人”的關系密切,注重交流雙方文化背景的差異,社會語境變化,對同一事物的認知往往不同。田野調查是深層次并且全方面了解舞蹈文化事項的主要方法,將舞蹈事項放置在社會語境中進行了解,運用多角色訪談的方式探求舞蹈的形成和背后的深層價值觀以及當地的宇宙觀。例如:民間小戲《大頭和尚戲柳翠》分布于我國十五個省市,講述的是出家之人和尚與民間寡婦柳翠之間的你來我往。這樣神圣與世俗的對話或者說屬于不倫之戀的小戲內容為什么會受到百姓們的喜愛,是否在當地的社火語境中只有一個訴說人欲的節目?
社火成為平時不可談論話題的釋放,也是一場演繹本能的狂歡。那么如此戲謔的表演為什么會在中國語境下存在?將此討論放置在社會性語境中分析,了解到其與歷史中滅人欲,存天理的思想有關。它強調:“盡管人欲并非都是惡或者不好,但它所蘊含的假、惡、丑的傾向是嚴重的,是屬于居敬、誠心的存養工夫需要消除之列的東西”。所以,是此種內斂節欲的思想用以化解社會矛盾,企圖從控制個人到社會以求達到整個宋朝的穩定,建立起為統治者服務的倫理規范。
二、通過田野調查解決舞蹈實踐中的問題
(一)不同的舞蹈是否有統一的審美
中國民間舞蹈文化根據民族的多樣性呈現出相同的特點:風格性、民族性、地域性,這是民間舞蹈的魅力所在。有些舞臺實踐是在田野調查過程中,院校的舞者自居于話語權的高位者,他們往往將自身的知識體系作為衡量一切文化現象的標準,在院校與民間劃上一條分界線彼此區隔,使得深扎田野變得毫無意義,更有甚者會影響到田野本身的文化生態。因此,舞蹈是否應該有統一的審美標準成為深扎田野前值得思考的問題。
不可否認的是任何一個社會都有表達意義和審美價值判斷的藝術活動,可能沒有“美”的術語,但一定會有美的評價,并且關乎美的評價都是二元對立的組成,介于美與丑之間。美和丑的評判又表現出多元的特點,每一種文化對美的認識、表現和判斷尺度都有所不同,例如:佤族的獵頭在其文化尺度中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但在我們的文化中卻不能認可和接受。那么,“美”的觀念是否有一個相對統一的價值尺度去衡量?從文化相對論的角度來看,絕對的文化相對論認為全人類沒有共同、統一的東西;而相對的文化相對論則認為全人類應該遵守一些共同的東西。絕對的文化相對論強調不同,相對的文化相對論主張在不同的基礎上,以包容的態度提示了共同。現今,在舞蹈實踐中出現嚴重的西方中心主義的現象,想要以西方審美標準判斷和衡量一切舞蹈的審美價值并以此來區分美與丑。芭蕾在某種程度上成為欣賞的標準,凡是符合芭蕾動作走向和節奏的表達才是美的作品,否則被認為是粗俗和野蠻的代名詞。這里的粗俗和野蠻存在文化進化論式的表達傾向,歐美為代表的文明社會才是藝術形式,是人類藝術的最高成果,認為原始人的社會結構簡單,所以他們的藝術文明也處于原始的階段。
根據美的統一性審美問題的討論,我們既不能用一種相同的文化標準去思考,也不能放大文化的特殊性。在討論審美標準的問題上,我們過多地將注意力集中在標準之上的相同與差異,忽略了審美主體之間的對話。而美的判斷恰恰地需要創作主體的情感性表達和欣賞主體主動地感受和體悟,是多種不同知識體系的交匯和協商、交流和對話。例如:我們所說的文化表征應該是互動的、主體間性的內涵,然而往往在民間藝術發展的過程中,會以自己文化核心為基準的基礎上不斷吸收其他文化的東西,這里說明的是“吸收”并不是批判和貶義的態度,“吸收”只是文化相遇、相融的現象,同時成為文化自身發展的特定要素。如何吸收,吸收什么,誰是主動,誰是被動的問題是關乎主體間性權力施展的重要話題。當以研究者的身份進入田野時,有時會被當地的村民公認為“權威”,并以我們為中心展開田野調查,在調查過程中不斷向所謂的權威學習民間舞蹈。在熱情的歡迎儀式過后,研究者不自覺地將自己放在話語權的高處,在向下對話的過程中忽略主體間的對話,當地的本土文化被所謂的權威抹殺。再如:在我國的一些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舞蹈大賽中,評委試圖用西方的理論和表演方法對民間藝術進行考察,認為想要成為優秀的民間藝術必須接受西方的訓練體系。這種說法無疑陷入到西方中心主義的思想中,并且抹殺了創作主體的話語權,單方面地強調欣賞者的知識體系,此時我們應該去詢問和理解創作主體對作品的文化意義。
(二)“變化”與“概念化”的認識
對于舞蹈而言,用文字記錄是件較為困難的事情,在1993年《中國民族民間舞蹈集成》針對全國舞蹈形態作出較為全面的描述,對于現在舞蹈研究工作者起著較為重要的地方民間舞蹈志的作用。但舞蹈文化是一個不斷建構的過程,從1993年至今,在近30年中,地方的民間舞蹈發生了如何的變化?筆者認為,只有重訪民間才能認知文化的建構特點。田野調查不僅是一種表象式的研究,而是一種事物表象與本質的結合,作為方法論和認識論,遵循了事物發展變化的一般規律。“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認識和實踐之每一循環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在舞蹈文化中,這種辯證唯物論的觀點同樣發揮著指導性的作用。
與“變化”相對的是“靜止”的看問題。有時候我們在講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實則是建立在犧牲一部分文化的基礎上得來的,是保護也是破壞,忽略了文化內部多樣性的特征。例如:在很多旅游場景中,為了吸引游客會刻意強調少數民族的某個習俗,例如壯族就要唱山歌,佤族就要拿著尖銳的刺刀跳舞殺牛,不自覺在展示的過程中被概念化表征,其實在當地的年輕人已經在墻上掛著各種歌星的海報,穿著同齡人的服裝。少數民族的特征在一些所謂保護的舉動中變得靜止、被概念化定型,豐富的文化動態變得表面化,我們應該以動態的演進角度看待文化的生產和再生產,沒有一種文化是一塵不變、甚至可以用簡單的符號去表述,應該將文化符號的關注點放在結構與能動性的問題上,放在族群內部與外部力量的互動中。
在這里,并不是不能對漸漸消失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做出任何重構性的舉動,而是如何看待非物質文化保護的問題。概念化總是在強調統一的時候忘記民族本身多樣的特征,概念本身就是追求本質的一種傾向,當定義一個民族文化的時候已經失敗,定義意味著標準,標準就要淘汰不符合要求的文化現象,到底什么是標準,在舞蹈發展的時候,我們是否過多地將紛繁復雜的舞蹈文化變得一致和簡單,在擁有“標準”時,是否失去民間文化的獨特魅力?秀山花燈,原屬于四川,現歸為重慶,在秀山花燈被推廣后,當地政府專門邀請外地的專家寫戲本,并結合了當今的主旋律。其中,當地老百姓流傳下來的段子不被重視,原本是文化瑰寶的東西被棄之不顧,請來所謂的專家編寫,并用外來的“標準”替換了傳統,花燈的戲班子不復存在,戲班子間的相互較勁變為統一的標準形態。
三、結語
深扎于田野,不斷地重訪民間才能認識舞蹈文化的邏輯和結構,每一個動作形態就是一個表現意義的符號,民族的多樣性使得民族舞蹈呈現百花綻放的態勢。在民族舞蹈文化中,有時會以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說法更多地引進外來的先進代替傳統,并且建立統一的標準,是規定般的束縛和捆綁,扼殺了文化多樣性的特點,忽視了當地的文化特點和理念,自上而下的話語權使得動態的文化變得靜止且統一。民族學中田野調查法以他者的身份進入田野,安靜地觀察文化生態,以包容的態度看待每一種文化的樣式,不去干涉和阻礙,讓民族之間在不同多樣中認識彼此、看待彼此、包容彼此。
參考文獻:
[1]劉建.轉型期當口下的中國民間舞——深扎的理論思考[J].舞蹈,2017(01):2.
[2][美]約翰·杜威.藝術即經驗[M].商務印書館,2010.
[3]楊堃.民族學調查方法[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23.
[4]張立文.宋明理學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5.
[5]樸永光.舞蹈文化概論[M].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9.
[6]毛澤東.實踐論[N].人民日報,1950-1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