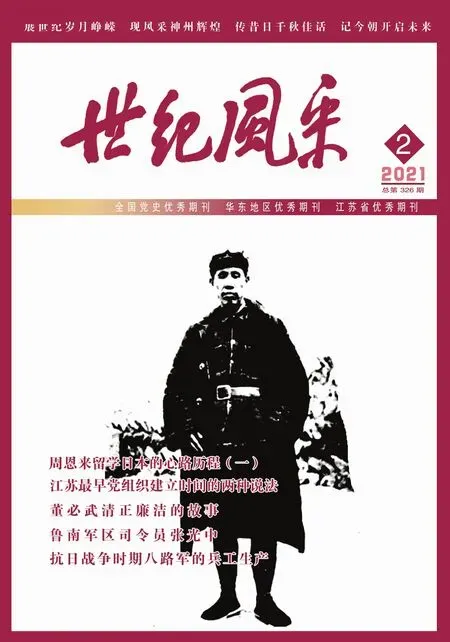江蘇最早黨組織建立時間的兩種說法

銅山站(今徐州北站)八號門
關于江蘇最早黨組織建立時間,目前學界多引用1921年6月張太雷在致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的書面報告中的表述:“截至今年5月1日止,中國共產黨已經有了七個省級地方黨組織”,“南京組織,它雖是最年輕的組織,但已經同周圍工人建立了牢固的聯系。”許多材料據此認為,在中共一大召開之前,南京已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組織,亦即是在江蘇境內建立的最早黨組織。事實是否如此,本文擬對此作一探究,以期厘清相關史實。需要說明的是,江蘇自建省以來,行政區劃時有變動,尤其是在民國時期,這種變動更為頻繁。例如,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建立以前,上海市隸屬于江蘇省,南京市為江蘇省省會。而1927年4月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南京成為中華民國的首都,并從江蘇省行政區劃中劃出,設立了南京特別市,同時上海市也從江蘇省行政區劃中劃出,設立了上海特別市,由國民政府行政院管轄。本文是按照現行的行政區劃來界定江蘇省的地理范圍。
張太雷向共產國際提交的報告最早以《共產國際第三次大會上的中國共產黨》(中國代表的報告——作者注)為題,刊登在伊爾庫茨克發行的《遠東人民》第三期(1921年8月)上。1928年,舒米亞茨基在為悼念張太雷而寫的文章中引用了其中的一部分,后來就再也無人提及。1971年,當時的蘇聯學者佩爾西茨在莫斯科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中央黨檔案館所藏的“俄共(布)中央委員會遠東局”的文件中,發現了內容幾乎完全相同的、題為《給共產國際第三次大會中國共產黨代表張太雷同志的報告》的俄語打印稿,并與《遠東人民》刊登的報告比較研究后發表,這才為世人所知。再到后來,中國的中央檔案館也發現了內容相同的俄語打印稿,并被翻譯成漢語。
總體來看,張太雷的報告中,介紹中國社會概況較多,而具體的記述則較少(比如,黨員人數就沒有提及)。但是,該報告涉及中國共產黨創建過程的幾個重要情況,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一章。在此章中,除了提到1921年3月召開各組織的代表會議,還這樣提到了中國共產黨的地方組織:
截至今年5月1日止,中國共產黨已經有七個省級地方黨組織,它們是:1.北京組織……2.天津組織及其唐山站分部……3.漢口組織……4.上海組織……5.廣東組織……6.香港組織……7.南京組織……
而目前掌握的檔案史料與此表述差距較大。2014年,由中共嘉興市委宣傳部、嘉興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嘉興學院紅船精神研究中心聯合撰寫的《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及其研究》一書,經過三年實地調研和詳細考證,認定中國共產黨早期成員共有58名,并對以往的“59名”“53名”等說法進行甄別分析,書中還詳細列出58名黨員所屬的黨組織,分別是上海14人,北京16人,武漢8人,長沙6人,廣州4人,濟南3人,旅法5人,旅日2人。2016年,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著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采納了58人之說,并詳細列出了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名錄。2002年,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著出版的另一本權威著作《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1921—1949)》雖然對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人數未定論,只籠統地說50多名,但對于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分布狀況與《中國共產黨九十年》的表述是一致的。可以看出,其時,天津、香港、南京三地并不存在黨組織,而長沙、濟南兩地已經成立早期黨組織,張太雷的報告中卻又未提到。何以會出現這種情況?日本學者石川禎浩在其廣受贊譽的《中國共產黨成立史》一書中經過認真考證,得出的可能情況是:報告執筆人為了給人以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深入發展的印象,作為權宜之計,杜撰了事實上從未召開和并不存在的會議和地方組織。其認為,在1920年至1921年的中國,打著“共產主義旗號的組織和人物并不少見,后來發展成中共的共產主義組織,當時還并不是代表中國的惟一的共產黨。”鑒于這種背景,不能排除如下的可能性,即張太雷在報告中提及“三月會議”和詳細記述地方組織,是為了提高他自己所屬的共產黨組織的地位,從而在與其他諸多共產主義組織爭奪正統地位的競爭中取勝。
此說法從其時參加共產國際三大會議并也號稱是來自中國的“共產黨”代表江亢虎寫的《江亢虎新俄游記》中也可得到證實。江亢虎,是辛亥革命期間曾經名噪一時的中國社會黨黨魁。在游記中,江亢虎說,其曾作為“社會黨員”列席共產國際第三次大會,并得到了發言權,但是在會議的第四天,江亢虎的代表資格又奇怪地被取消。為此,江亢虎曾經向共產國際主席季諾維也夫寫信表示抗議:
第三次大會開幕當天,我領到了具有議決權的代表證。可是,在出席大會四天之后,在沒有任何解釋的情況下,卡巴斯基(Kabasky)同志要我交還代表證,并剝奪了我作為來賓的權利。我認為這是一種侮辱,表示抗議。
收繳了江亢虎代表證的卡巴斯基,就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科別茨基(M.Kobetsky)。關于這次收繳代表證事件,江亢虎在另外的地方進一步地這樣記述道:
(我)本以社會黨代表名義出席第三國際會,已就緒矣。聞某團代表張某(張太雷)為中國共產黨代表,系由東方管理部(遠東書記處)部長舒氏(舒米亞茨基)所介紹而來者,因往訪之。……不意相晤之下,張閃爍其詞,不自承為代表。余方異之,及出席時,見張與舒氏在座。因詢之曰:“君代表券乎,來賓券乎?請相示。”張不可,而轉索余券。余立示之,張乃以其券相示,則亦代表券也。出席二、三日,不意國際會竟將余券收去。……至終事后細訪其故,始知張某等竟設為種種證據,致書于國際會,以中政府偵探目余。
顯然,江亢虎之所以被取消代表資格,是張太雷向共產國際主席季諾維也夫抗議的結果。據《江亢虎新俄游記》中《紀中國五共產黨事》的一節記載,1921年竟有五個自稱為中國正統的“共產黨”組織來到莫斯科,除張太雷、俞秀松代表的中國共產黨外,其余四個分別是:姚作賓代表的“東方共產黨”;社會主義青年團留學生成立的“少年共產黨”;黑龍江黑河的原中國社會黨支部“龔君、于君”改組的“中國共產黨”;只身赴俄的杭州的“張君(張民權)”自稱代表的“支那”共產黨。其中以“少年共產黨”人數最多。
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張軍鋒曾專門撰文分析中國早期“共產黨”組織,其認為,盡管我們今天已經很難查證追究這些都標榜正統的“共產黨”組織的詳細情況,但這個現象已經足以說明當時形形色色的共產主義組織的存在。僅從它們紛紛來到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大會的情形看,它們可能都與共產國際多多少少都有一定的聯系。而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也的確是俄共和共產國際在中國多渠道開展工作造成的。由于他們對中國革命者的真實情況不太了解,而中國各地形形色色的團體又缺乏相互聯絡,結果形成了多頭聯絡、山頭林立、錯綜復雜的現象。
多個中國“共產黨”組織一起在莫斯科出現,毫無疑問對還沒有正式成立的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建立牢固的關系并在共產國際開展工作都是一種極大的干擾。因此張太雷和俞秀松毫不猶豫地與他們展開了斗爭,并向共產國際提出抗議。俞秀松在1921年9月27日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書記處遞交的聲明中這樣說:
不久前來到莫斯科并自稱是中國共產黨代表的中國公民姚作賓不是中國共產黨黨員,因此沒有任何資格同共產國際進行聯系,凡是共產國際同他一起討論甚至決定的東西(根據姚作賓的建議,共產國際撥給款項等),中國共產黨都不承認,因為眾所周知,姚作賓在第二次全國學生大罷課期已成為中國學生唾棄的卑鄙叛徒。

隴海鐵路使用的蒸汽機車
共產國際認真對待這個問題,在取消了江亢虎的代表資格以后,也中斷了與姚作賓所代表的中國“共產黨”的正式聯系。
綜上所述,可以推斷,張太雷在報告中提到的天津、香港、南京早期黨組織的建立情況與實際情況并不吻合,其可能是出于與其他所謂“共產黨”組織斗爭的需要而杜撰出來的,事實并非如此。
目前學界普遍認可的江蘇最早黨組織,當為1922年春建立的中共隴海鐵路徐州(銅山)站支部。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后,中央局把發展黨團工會組織作為重要任務。1921年秋,北京地委、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北京分部在隴海鐵路指導開展工人運動。1921年10月20日,隴海鐵路徐州(銅山)站全體機務工人,為反對路局法國人的虐待,在隴海路大罷工中率先行動,罷工委員會負責人為姚佐唐。罷工勝利后,姚佐唐被選為徐州站工會會長,后又當選為中國勞動組織書記部北京分部委員。1922年春,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干事、共產黨員李震瀛在銅山車站發展姚佐唐、程圣賢、黃鈺成等人入黨,建立了中共隴海鐵路徐州(銅山)站支部,屬中共北京地委領導。同時,又發展一批團員,建立團的支部。1923年二七慘案后,反動軍閥當局封閉了隴海、津浦鐵路工會,搜捕工人領袖。徐州鐵路工運倍受摧殘,姚佐唐等人被迫先后離開徐州。5月,該站黨支部即停止活動。盡管隴海鐵路徐州(銅山)站支部活動的時間并不長,但其確是徐州地區的最早黨組織,也是江蘇最早建立的黨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