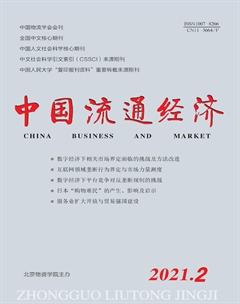數字經濟下相關市場界定面臨的挑戰及方法改進
摘要:信息通信技術和數字技術的深度融合與廣泛適用,推動著數字經濟高速發展,催生各類新業態、新產業、新模式不斷涌現,給市場競爭模式、產業組織結構以及經營者具體商業行為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數字經濟下以平臺為中心的商業模式擴展了相關市場上以商品基礎功能為主的商品功能疊加競爭,雙邊或多邊市場下的跨市場競爭與融合以及非對稱性定價結構等情況越來越復雜,給現行的以單邊市場上商品單一功能及其價格變化為主的相關市場界定方法帶來諸多挑戰,現有相關市場界定方法的局限性凸顯。為及時回應數字經濟下相關市場界定問題,應在厘清相關市場界定基本邏輯的基礎上,回歸對用戶需求替代變量的檢視,在價格變量逐漸弱化的同時,將用戶注意力、數據及商品質量視為相關市場界定中的重要變量,并結合用戶需求替代發生的具體場景,重視個案中相關市場界定的精準化分析。數字經濟領域市場競爭方式逐漸由傳統價格競爭轉向用戶注意力競爭和數據競爭,對用戶需求的精準把握和持續爭奪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經營者在相關市場的競爭優勢及其維持,經營者為了在注意力競爭中獲取競爭優勢,必須高度關注用戶需求,不斷優化升級商品質量,增值疊加商品功能,因此相關市場的界定必須考慮以用戶需求替代為基礎的用戶可轉向范圍和數據轉移成本,以體現數字經濟下個性化、定制化、精細化特征對反壟斷法適用的影響,同時凸顯用戶偏好在需求替代分析中的重要性。
關鍵詞:數字經濟;反壟斷法;相關市場界定;需求替代;非價格要素
中圖分類號:F123.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7-8266(2021)02-0003-10
一、引言
隨著信息通信技術和數字技術的融合創新發展,人類經濟社會組織形態和日常生活消費方式發生了深刻的改變,數字技術及基礎設施已經深嵌于人類經濟社會結構和治理之中,數據已成為全球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要素和核心原料[ 1 ]。在數字經濟促進市場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也給反壟斷法適用帶來巨大挑戰,尤其是用戶多歸屬、網絡外部性、平臺多邊性及跨界動態競爭等特征的出現,增加了界定數字經濟領域相關市場的難度。
譬如,在被譽為國內互聯網反壟斷第一案的“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訴騰訊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等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糾紛案”(以下簡稱“奇虎訴騰訊案”)中,一審法院①和二審法院②在相關市場界定要素的選擇上產生分歧,引發各界對互聯網反壟斷案件相關市場界定熱烈且持久的討論[ 2 ]。同時,域外的谷歌收購雙擊案[ 3 ]、美國運通卡案③等經典案件也反映了對互聯網領域反壟斷法適用中相關市場界定及其方法選擇的討論。
這些案件引發了國內外專家學者對數字經濟領域相關市場界定問題的激烈討論。為解決數字經濟領域相關市場界定的難題,首先需辨識當前數字經濟領域相關市場界定面臨的主要挑戰,其次要解析現有相關市場界定方法在數字經濟場景下的適用困難及現有對策,最后圍繞數字經濟自身發展特征及相關市場界定方法應用情況,以效果分析為導向,改進數字經濟領域相關市場的界定方法。
二、當前數字經濟領域相關市場界定面臨的主要挑戰
現實中任何市場競爭行為均發生在一定的場域內,在適用反壟斷法規制競爭行為時,通常需要界定發生爭議行為的具體相關市場,以此明確與行為人具有競爭關系的經營者范圍,并根據具有競爭關系的經營者在相關市場上的份額,判斷行為人的市場地位。具體言,相關機構經由對相關市場的界定,評估涉案經營者的市場力量,對涉嫌限制、排除競爭之具體行為做出效果評估。然而,由于數字經濟的高速發展,作為反壟斷法適用起點的相關市場界定受到了顛覆性影響,面臨諸多挑戰。
(一)功能替代性視域下界定相關商品市場的窘困
在界定相關商品市場過程中,商品功能是重要的考慮因素。與工業經濟下商品主要功能相對單一和固定的情況不同,數字經濟下商品可通過更新或升級的方式在原有功能上智能增加新功能,形成多種功能聚合的復合性商品,從而脫離原有開發設計者的初衷在其他市場上實現優勢功能擴展,使所謂“無心插柳柳成蔭”“歪打正著”的跨界競爭成為常態。在這一過程中,經營者的成本與收益并非必然為正相關關系,流量和數據成為商品功能開發與實現的關鍵,在傳導效應的加持下動態競爭更為明顯,這給現行的依據商品功能——主要指某單一功能界定相關商品市場的方法帶來很大挑戰,具體表現在基準功能確定與替代性分析兩個環節[ 4 ]。
基準功能的確定主要是為厘定具有需求/供給替代關系的商品提供參照。在傳統工業經濟場景下,商品功能相對單一且存在相對穩定的物理形態,較容易明確商品的基準功能,并以此劃定相關商品的范圍。在數字經濟場景下,除傳統商品和服務的線上化外,其他以數據為內容的商品和服務都具有很強的功能復合性特征,基于需求方的不同偏好,復合性商品的不同功能體驗可以分別構成相對獨立的商品或者共同構成組合商品[ 5 ]。譬如以平臺作為整體提供服務內容的情形,就是由多個商品的不同功能構成一個組合商品,并由此形成一個商品的相關市場。當然,這種認識和解釋能否被廣泛接受還需做更詳細的研究,即互聯網平臺及服務能否構成一個相對獨立的相關市場目前還未達成共識。在很多情況下,大多數學者和實務工作者傾向于具體到發生競爭爭議的某一邊商品市場,如在對“奇虎訴騰訊案”的研討中,有學者認為需要結合實際發生競爭關系的事實,將案件界定為三個市場,包括即時通信軟件及服務市場、殺毒軟件及服務市場以及互聯網廣告市場[ 2 ],而最高人民法院的判決則是將相關市場界定為即時通信軟件及服務市場。由此可以看出,對平臺作為一個整體提供服務,并由此構成一個相對獨立市場的判斷目前尚未成熟。數字經濟領域相關市場的界定應以現行反壟斷法適用框架和方法為基準,以具體某一商品功能的分析為前提,以此回應數字經濟下商品復合性特征對相關市場界定帶來的挑戰。
在實踐中圍繞如何對功能復合性商品進行合理且適當的定位,在深圳微源碼軟件開發有限公司與騰訊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市騰訊計算機系統有限公司壟斷糾紛一案中,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進行了嘗試。原告訴稱被告濫用微信在即時通信軟件及服務市場上的支配地位封鎖原告公眾號的行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權益,法院認為原被告雙方爭議行為直接指向的“產品”是微信軟件所提供的公眾號服務,涉及的產品是“微信公眾號”而不是“微信”④,通過聚焦原被告雙方爭議的商品的具體功能來反向分析實現這一基礎功能的商品載體或者說商品形態,以此準確劃定相關商品市場。
替代性分析環節的主要目的在于明確與假定壟斷者所提供商品功能具有緊密替代關系商品的范圍,面臨的挑戰主要源于平臺經營者跨界競爭所引發的商品功能疊加,導致商品的替代性分析難度加大。如微信作為主打免費在線社交的商品,基于龐大的用戶規模和在線社交內容的不斷發展,增加了在線支付功能以滿足用戶在線支付的需求,由此與同樣具備在線支付功能的支付寶產生了可替代性。若直接將支付寶與微信視為同一相關市場上的商品,會發現微信的其他替代品,譬如微博、陌陌等社交軟件與支付寶之間并不存在緊密的可替代性,因此是否將微信與支付寶劃入同一相關市場就存在疑問,主要原因在于具有復合性功能的微信商品存在與多個領域的商品具有可替代性的競爭關系,僅以某單一功能判斷互聯網數字經濟下復合性商品的可替代性在實踐中面臨著挑戰,分析結論并不準確。值得注意的是,替代性分析環節與商品界定環節存在緊密聯系,倘若能夠將微信支付與微信拆分為兩個商品,則在一定程度上就能夠明晰在線支付類商品的市場邊界。然而,由于當前較成熟的商品往往聚合多種功能,且對如何就復合性商品進行合理的拆分尚缺少統一標準,致使現有的替代性分析方法在面對具有復合性功能的商品時存在著明顯的局限。
(二)多邊(平臺)市場結構下相關市場界定的困難
在數字經濟市場環境下,互聯網企業間的競爭一般表現為多邊平臺市場的競爭,參與經濟活動的主體不再局限于簡單的買賣雙方,而是表現為平臺、供需雙方、第三方等,且各主體間存在某種動態匹配的可能與需要,市場整體呈現出雙邊乃至多邊化的結構特征,其中平臺作為鏈接各邊市場的重要基礎設施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平臺往往具備以下三個條件:擁有兩個或者兩個以上不同的客戶群體;因為某種外部性的存在,不同的客戶群體之間得以連接和協作;必須有某種介質(通常以數據的形式存在)來內化某一客戶群體對另一客戶群體所產生的外部性[ 6 ]。多邊(平臺)市場結構與普通的雙邊市場結構存在的根本區別在于多邊市場之間的網絡效應通常是間接的,存在于不同類型的客戶之間而不是直接針對相同類型的客戶。當一方參與的規模和強度影響另一方的福利時,就會發生間接網絡效應或跨群體效應[ 7 ]。
在間接網絡效應的作用下,多邊平臺通過獨特的運行方式同時連接兩邊或多邊不同類型的用戶,解決了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多組群用戶間相互依存,同時又形成各自的市場[ 8 ]。由于任意一邊市場的用戶規模和發展情況都會對另一邊市場產生影響,在分析多邊平臺市場競爭行為的效果時,必須綜合考量對市場兩邊甚或多邊的影響。雖然多邊市場結構下存在的網絡效應,特別是間接網絡效應已被各界認可,但在法律實踐中如何認定多邊市場及其競爭效果仍存在分歧。如在美國運通案中,美國地方法院選擇對雙邊市場進行拆分,即將運通卡的業務視為由兩個市場組成,一個涉及美國運通與商戶,另一個涉及美國運通與消費者。然而,聯邦第二巡回法院推翻了地方法院的判定,認為美國運通經營著一個交易平臺,在兩個方向上都有間接的網絡效應,同時向參與交易的雙方提供一個聯合的產品,所以應當將美國運通雙邊市場定義為單一的相關市場,而不是為商戶服務和消費者服務兩個不同的市場[ 9 ]。這種情況在我國互聯網數字經濟中也是難點,特別是在各類型平臺市場如電商平臺、社交平臺、支付平臺、搜索平臺、內容平臺等不斷興起的背景下,如何識別跨市場競爭所引發的市場效應變化及其規制已成為當前亟待回應的難題。
(三)多維競爭要素的凸顯削弱了價格要素對界定相關市場的作用
市場份額亦稱市場占有率,是指某企業某一產品(或品類)的銷售量(或銷售額)在市場同類產品(或品類)中所占比例,是判斷經營者市場力量的重要指標。我國《反壟斷法》第十八條市場支配地位認定條款和第十九條市場支配地位推定條款均體現了在規制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案件中市場份額的重要性。值得注意的是,在現行市場份額計算和識別中,商品價格要素占據重要地位,無論是假定壟斷者測試法(Small but Significant No transitory In? crease in Price,SSNIP)還是臨界損失分析法(Criti? cal Loss Analysis),都依賴商品價格的變化[ 10 ]。然而,數字經濟時代市場競爭的模式和要素發生了重大變化,動態競爭與跨界競爭、流量(注意力)競爭與(大)數據競爭等成為競爭的主要特征,免費端市場加收費端市場的多邊市場結構成為市場競爭發生的主要場景,市場競爭不再局限于價格要素,現有的以價格為主的市場份額計算方法很難客觀真實地反映數字經濟下經營者在多邊市場上的整體市場力量。因此,在評價平臺經營者市場力量時必須關注創新、用戶(注意力)以及數據等非價格要素。
1.創新要素
高頻次顛覆性的創新或競爭在數字經濟市場中表現得尤為明顯,“一些企業雖然依賴某些技術優勢可能會迅速占領某一相關市場且擁有市場支配地位,但是這種依靠高技術形成的市場壟斷具有很大的不穩定性,因為一旦一項創新性的技術或者產品問世,在位企業的市場壟斷地位就會被取代”[ 11 ]。因此,當相關市場上出現市場份額或市場占有率較高的企業時,并不意味著該企業具有相當的市場支配力量,因為其憑借數字技術創新所獲得的競爭優勢很可能是暫時的。在顛覆性創新競爭的市場環境下,市場占有率僅代表該企業通過以往或目前的努力在相關市場上獲得的競爭效果,并不能代表其實際擁有對相關市場的控制力,更無法推斷該企業在未來較長一段時間內會在相關市場具有支配地位,因為在高頻次的顛覆性創新競爭的市場環境下,基于特定時間段計算的市場份額很難準確地反映該經營者真實的市場力量[ 12 ]。在動態競爭場景下,特定時間內獲得的壟斷地位很可能只是基于技術創新的必然結果,并非是基于經營者市場力量長期存在的結果。創新與壟斷是數字經濟發展中的常態,但很難維持較長的時間,經常被新一輪更為激烈的顛覆性創新打破。因此,必須關注的是創新型壟斷是否能夠長時間地得到維持或強化,且這種維持或強化是源于經營者對既有市場力量之濫用。
2.用戶(注意力)要素
通過吸引并長期鎖定大量用戶的注意力以獲取利潤被認為是數字經濟增長的基本方式,數字經濟在很大程度上亦被稱為注意力經濟。注意力經濟并不是一個嚴格的經濟學概念,而是孕育于互聯網產業發展中的新興概念。最早提出注意力經濟的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指出,隨著時代的發展,信息的含義發生了變化,不再是稀缺的資源,而是豐富甚至過剩的,真正稀缺的是信息接收者的注意力,這種注意力體現為接收者為接收信息所消耗的時間[ 13 ]。因此,在數字經濟下市場競爭的核心之一即為用戶停留在某一企業平臺之上的有效時間,亦可稱為用戶注意力。
然而,對用戶注意力或者說用戶停留在某一企業上的有效時間的評價卻很難用現有的價格要素衡量。用戶注意力缺乏一個適當的估值標準,也很難通過對用戶注意力的通用性評價直接得出用戶注意力可以構成一個獨立相關市場的結論。即使在理論上可以將用戶注意力作為一個相關市場,但由于用戶注意力的多面向或者多歸屬,用戶可以依據自身的不同需求將其注意力分配至不同的企業,且分配的差異也不影響實質性的最終購買或不購買某類商品的決定。然而,從供給端的運營看,用戶的注意力卻可以產生對平臺企業獲利和供給端商家爭奪交易機會的實質性影響。由此可見,在數字經濟下多邊市場的結構對用戶注意力之于相關市場界定時的作用產生了不同理解,特別是對不同端市場的評價會產生不同的意義,這就對準確客觀地運用用戶注意力標準界定相關市場提出了挑戰。同時,由于缺乏客觀有效的用戶注意力衡量標準,將其轉化為現行價格要素予以分析的可能性非常小,這也使現行的相關市場界定方法受到實質性挑戰。
3.數據要素
在數字經濟下,基于數據展開的競爭已成為市場競爭的常態和必要形式,特別是將數據作為一種新型的生產要素后,數據要素市場上的競爭狀態及其對由數據引發的其他市場上競爭效果的評價已成為當前反壟斷法適用過程中亟待回應的難題。從數據到大數據(Big Data)再到厚數據(Thick Data)進而實現兩者的融合,在這一過程中數據的競爭法屬性不斷凸顯,由此引發的競爭與反競爭的爭議亦不斷涌現[ 14 ],其中由數據特別是大數據可能導致的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問題引起了廣泛關注[ 15 ]。正是基于此種考慮,《<反壟斷法>修訂草案(公開征求意見稿)》在認定互聯網領域經營者市場支配地位的過程中,也特別強調經營者“掌握和處理相關數據的能力”。
經營者對海量用戶數據的收集與分析能力越強,其從收費端市場,如廣告宣傳市場、商品銷售市場、內容服務市場上獲得的收益亦可能越多。同時,基于數據的累積和算法的優化,經營者可根據用戶數據實現用戶與第三方商家或其他用戶的精準匹配,從而提升商品或服務的質量,進一步增強對用戶的鎖定效應,且借助網絡外部交叉性效應,在鎖定和擴大一端用戶群體的同時,影響和維持另一端用戶的規模,鞏固甚或創造更大的利益空間,由此形成了基于數據的用戶反饋回路(循環)。此時,對優勢經營者市場地位的判斷已不能再簡單聚焦于該經營者所提供商品或服務的市場價格要素。基于此,現行的以商品或服務的價格為基準的相關市場界定方法亦失去了實踐的基礎,特別是當數據的瞬時性、可獲得性、復用性等特征不斷挑戰對數據的市場定價時,價格要素對數據相關市場及其傳導的其他相關市場的界定就失去了現實意義。
三、數字經濟下相關市場界定方法的適用困境與改進
(一)現有相關市場界定方法的適用困境
界定相關市場需借助一定的分析工具或者方法來識別存在競爭關系的商品范圍,在各國和地區的反壟斷實踐中,界定相關市場的方法主要采用定性分析法和定量分析法來判斷不同商品之間是否具有替代性[ 16 ]。隨著數字經濟向縱深發展,現有分析方法的局限逐漸顯露,且隨著數字經濟下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的不斷涌現,其適用也面臨愈來愈明顯的困境。
1.定性分析法失準——“好用但不好使”
定性分析是與定量分析相對應的概念,是對事物進行質的層面上的分析與認定,即主要依靠分析者的經驗,運用歸納與演繹、分析與綜合、抽象與概括等邏輯分析方法,對所掌握的各種材料進行分析加工,以此認識事物的本質。因為質的分析方法對海量精確的數據要求相對較低,因此運用此種分析法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17 ]。然而,定性分析容易受到分析者(在反壟斷實踐中主要指司法和執法人員)認知水平的限制,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主觀性。特別是數字經濟下的雙邊或多邊市場結構以及在這類市場結構之上大量存在的復合性商品,使需求替代分析法和供給替代分析法等在實踐中面臨較大的操作困難。
究其原因,一方面,很難客觀判斷后入經營者在進入市場時的難易度。雖然隨著信息通信技術和數字計算技術的發展以及軟硬件的不斷成熟與完善,市場準入門檻不斷降低,進入市場后的沉沒成本變得十分彈性——主要取決于后入經營者采取何種進入方式以及合作對象是誰,產業之間的轉換顯得更為容易,商品或服務的更新換代速度越來越快,但對于網絡效應以及數據競爭等因素是否能夠形成市場壁壘以及其強度如何識別,目前在理論界和實務界中尚未形成普遍認可的結論[ 18 ],市場進入難易度缺乏客觀統一的判斷標準,現行的定性分析方法難以奏效。另一方面,由于數字平臺商品本身具有很強的可延展性,經營者基于軟件平臺可以根據市場的情況以及消費者需要及時添加商品功能,如果對目標商品采用替代分析法,則會把屬性和用途存在極大差別的商品劃歸同一相關市場,導致相關市場范圍無限擴大[ 19 ]。這也導致現行需求/供給替代定性分析方法在面臨平臺所提供的商品功能不斷增項時難以準確適用的尷尬。
2.定量分析法失效——“好使但不好用”
定量分析法主要是借助數學模型、統計數據等技術手段對事物的數量特征、數量關系與數量變化進行分析,從而降低結果的不確定性。但是,定量分析法需以數量龐大而且精確度極高的數據信息為基礎,加以復雜的數學模型和公式應用,從而極大地增加了執法難度[ 17 ]。實踐中所采用的定量分析法主要為假定壟斷者測試分析法(SS? NIP)。該方法主要通過價格的增減和收益的變化來界定相關市場。然而,當SSNIP法面臨數字經濟市場競爭的諸多特點時,建立在工業經濟市場特征之上的數學模型和公式尚未及時有效地做出調整,使得SSNIP法在適用上面臨巨大挑戰。
一方面,具有多邊市場結構特征的平臺企業大量出現。SSNIP分析法主要建立在單邊市場基礎上[ 20 ],無法直接用于多邊市場結構的分析,因為SSNIP分析法沒有將多邊市場結構下的交叉網絡外部性對假定壟斷者提高價格的實際獲利的影響考慮在內,導致在界定相關市場時出現偏差。即SSNIP分析法僅考慮單邊市場的劃定,而忽視雙邊或多邊市場間的聯動現實對相關市場范圍的影響及其實際市場力量的評價。
另一方面,免費商品市場的出現。在互聯網多邊市場結構上價格具有非對稱性,在交叉網絡外部效應影響下,產生了一種復雜的價格結構。為實現多邊市場上利益的最大化,平臺企業往往基于不同市場端用戶的需求彈性,在總收益不變的情況下,向不同市場端的用戶收取不同的價格,其中最典型的是免費或零定價模式,即向價格比較敏感的普通消費者免費或零定價提供商品或者服務,而免費或零定價用戶端所產生的成本將由另一邊或其他多邊市場用戶(廣告商、第三方運營商等)予以承擔或直接給予補貼。零定價模式使SSNIP分析法所依據的價格變量失去了意義。
(二)相關市場界定方法之新探索
為解決在數字經濟領域傳統相關市場界定方法的不適用問題,國內外司法機構嘗試了多種方法,下面將對其中三種在司法實踐中得到實際運用的方法進行介紹和評析。
1.假定壟斷者測試法(SSNDQ)
由于SSNIP法在數字經濟中面臨較大的困難,在司法實踐中有部分法院選擇采用該方法的變通形式,即基于質量下降的假定壟斷者測試法SSNDQ(Small but Significant and Non-transitory De? crease in Quality)。該方法與SSNIP法的分析框架相似,只是以質量替代價格變量進行測試,探討在一段合理的時期內,經營者小幅降低質量時用戶的流失情況及經營者的盈利情況。有學者進一步對SSNDQ法的具體步驟進行了描述:當與該被調查的商品具有供給替代關系的商品質量特別是關鍵效能提升25%時,用戶會不會轉向該商品,或者當該被調查的商品關鍵效能下降25%時,用戶是否轉向其他可替代商品;或者當該被調查的商品——在互聯網領域通常表現為零定價商品上所引入的廣告量增長時,用戶是否有意愿且能夠轉向該商品等。如果前述情形存在可替代商品,那么在界定相關市場時,都需將這類商品劃入相關商品市場,通過這類可量化的指標來反向驗證質量變化這類難以量化的情形[ 21 ]。同時,SSNDQ法也可作為一種定性分析法。如在“奇虎訴騰訊案”二審中,最高人民法院認為,假定壟斷者測試作為一種分析思路或者方法既可以通過定性分析的方法進行,也可以通過定量分析的方法進行。
值得注意的是,SSNDQ法不論是作為一種定量分析法還是定性分析法,其在數字經濟下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當作為定量分析法時, SSNDQ法面臨著量化困難問題,質量的參數與變化幅度的調整方式與價格的上下調節存在較大差異;若將SSNDQ法作為定性分析法,則面臨著實操性的問題。在選取質量參數時存在很強的主觀性與不確定性,不同用戶對質量的偏好不相同甚至大相徑庭,不像價格具有相對統一的標準。特別是對多功能復合性商品,選取何種功能的質量進行調整、調整程度是否合理,以及調整質量是否能夠為企業帶來收益或者不會導致用戶(流量)規模性流失等,都有待結合個案進行具體分析。
2.盈利模式測試法
顧名思義,盈利模式測試法是以盈利模式為基準來界定相關商品市場的方法。舉例來說,在“Bertlesmann訴Mondadori案”中,歐盟委員會嘗試以盈利模式測試法來界定互聯網領域相關商品市場,重點考慮了實體市場難以對“遠程在線銷售”實現替代的現實情況,認為在線銷售的盈利模式具有其獨特之處,認定采用網絡遠程銷售方式進行商品銷售的市場為一個獨立市場[ 16 ]。
盈利模式測試法作為回應相關市場界定困難的對策之一,雖然在理論上可以解決傳統方法難以解決的免費/零定價商品市場的界定問題,且簡單易行,但其有效性仍有待檢驗[ 22 ]。因為盈利模式測試法與傳統界定相關市場的方法存在較大的區別,該方法著眼于平臺主要利潤的來源,缺乏對該市場上商品需求/供給是否具有可替代性的考察。盈利模式僅是一種商業模式,相對成熟且成功的商業模式往往會被不同領域的平臺效仿,若僅以商業模式作為界定相關市場的依據,往往不能真實反映不同商品存在的需求/供給替代關系,容易導致相關市場界定范圍過寬。
以數字經濟下平臺所采用的免費/零定價商業模式為例,倘若僅依據“免費/零定價+廣告”模式認定經營者之間是否存在競爭關系,則絕大多數的平臺皆可被認定為存在競爭關系,彼此間具有替代性,從而擴大了相關商品市場的范圍。如作為搜索引擎的百度和作為社交工具的微博都以廣告收入為主,盈利模式測試法將會把兩個并不存在緊密替代關系的商品視為具有競爭關系的商品,導致界定相關市場范圍的擴大。
3.直接證據法
由于在數字經濟下界定相關市場的方法在實踐中面臨的困境日益凸顯,主要各國和地區嘗試越過相關市場界定,以直接證據證明經營者的市場力量。如美國部分法院采用直接證據法,認為通過市場壁壘、超高定價、限制數量等直接證據就可以證明企業是否具有市場力量[ 11 ]。歐盟委員會競爭局競爭政策經濟咨詢組也曾提出采用直接證據法判定企業市場支配地位,即若行為后果被證實產生了重大的競爭損害,該行為本身就可以作為存在市場支配地位的證據[ 11 ]。直接證據法在我國反壟斷實踐中也有體現。在“奇虎訴騰訊案”的二審過程中,最高人民法院曾指出,“界定相關市場是評估經營者的市場力量及被訴壟斷行為對競爭的影響的工具,其本身并非目的。即使不明確界定相關市場,也可以通過排除或者妨礙競爭的直接證據對被訴經營者的市場地位及被訴壟斷行為可能的市場影響進行評估。”可見,直接證據法在反壟斷實踐中的運用正在挑戰界定相關市場的意義與價值。
然而,在實踐中直接證據法并不能有效解決相關市場界定的困境。如收取過高的價格或存在難以突破的市場壁壘等往往是假定壟斷者所具備的前提條件或實施的具體行為,但這些要素不能成為充分的證據來證明該經營者具備反壟斷法所規定的在某一相關市場上的支配地位。正如美國司法部2008年發布的研究報告《競爭與壟斷:謝爾曼法第2條意義上的單邊行為》中所指出的,高利潤率不一定反映企業具備壟斷力,因為會計成本一般只是依據會計規則,很少反映企業的真實成本,即便商品的價格超過短期邊際成本,也不能簡單推斷企業擁有壟斷力[ 11 ]。
綜上,數字經濟下相關市場界定方法的改進仍面臨巨大的現實挑戰,雖然從SSNIP法到SSNDQ法再到盈利模式測試法,甚至跨越相關市場界定的直接證據法的運用,對消解界定相關市場時的困難有一定幫助,且在個別案件中其適用性得到了證明,但數字經濟下相關市場界定的根本問題未得到徹底解決,界定相關市場的目標與實現該目標的具體方法之間的內在邏輯需要進一步厘清,其中需求/供給替代的分析思路與演繹邏輯仍需堅持,同時引入數字經濟下非價格要素和多邊市場結構的整體評價不失為下一步改進的基本方向。
四、數字經濟相關市場界定方法調整的方向
當前,在數字經濟中,免費/零定價市場邊與其他多邊市場密不可分,網絡效應、冒尖效應/鎖定效應、傳導效應等越來越明顯,新業態和新模式頻繁出現,建立于工業經濟場景下的以市場價格要素為核心變量、以用戶需求為主輔以經營者供給的替代分析法及其具體量化方法,對有效界定相關市場顯得乏力。解決數字經濟下相關市場界定面臨的問題與挑戰,有必要回歸相關市場界定的基本定位與功能,以此為出發點和落腳點,重述相關市場界定方法在數字經濟下改進的基本方向。
(一)厘清相關市場界定的基本邏輯
相關市場界定的概念及實踐源于美國,在1956年“美國訴杜邦公司案”中出現。在該案中聯邦最高院認為,市場是由具有合理可互換性的商品組成,涉及價格、用途和質量⑤。隨后,1968年美國出臺的《橫向合并指南(1968)》中對“相關商品市場”的概念進行了明確規定,“相關商品市場是由在價格、質量以及用途上具有合理替代性的商品組成的市場”。在《關于為歐洲共同體競爭法界定相關市場的委員會通知》第7段中,歐盟委員會將相關商品市場界定為“依據商品之特性、價格以及用途,在消費者看來是可以滿足交互替換之商品或服務”。隨后,在2004年發布的《關于執行<第139/2004號并購條例>的第802/2004號理事會條例》的第六部分,歐盟委員會對相關商品市場賦予了更為豐富且具體的內涵:對消費者而言,相關商品市場所涉及之商品或服務,在其相關物理或技術特性層面上,應呈現彼此間的可互換性和可替代性[ 23 ]。2009年,我國發布《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關于相關市場界定的指南》(以下簡稱《相關市場界定指南》),對相關市場的概念及界定方式做出了說明,其中對相關商品市場和相關地域市場的界定均強調需求者角度的“緊密替代關系”。
綜上可知,相關市場界定的基本邏輯在于通過需求替代分析識別商品之間是否存在現實合理且有效的競爭替代/約束關系,依我國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的表述即“較為緊密替代關系”(以下簡稱“替代關系”)。當某一相關市場上的競爭秩序受限制時,消費者若沒有其他可替代的商品以供選擇或者選擇商品時需要付出的成本超過合理水平,則可以推定該經營者所在相關市場上有效競爭約束出現了問題,據此可以在與之具有可替代性關系之商品范圍內判斷該經營者的市場地位。由此,相關市場界定的基本邏輯大致明確。申言之,前述多種界定相關市場的方法雖然在分析要素和具體工具選擇上有差異,但在本質上皆依循了相關市場界定的基本邏輯,即通過定性或定量的分析方法識別消費者需求可替代的范圍,進而判斷競爭約束存在的程度。如在北京銳邦涌和科貿有限公司訴強生(上海)醫療器材有限公司、強生(中國)醫療器材有限公司案中,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對《相關市場界定指南》第七條進行了如下闡釋:假定壟斷者測試方法是在替代分析原理基礎上的定量測度,本質仍然是替代分析⑥。簡言之,相關市場界定的基本邏輯是運用定性或定量的分析方法劃定消費者需求替代的范圍,從而盡可能準確合理地識別競爭約束發生的范圍和程度,完成從相關市場界定到該市場上經營者市場支配地位判定的法律分析過程。
(二)明確基于需求替代識別相關市場上競爭約束的意義
隨著相關市場界定理論和實踐的不斷發展,相關市場上競爭約束的識別方法也有了發展,在需求替代之外,還綜合考慮了供給替代和潛在的競爭等因素[ 24 ]。換言之,需求替代標準并非分析相關市場上競爭約束的唯一基準,供給替代能對經營者產生有效的競爭約束時,也應予以考慮,如產出能力的填補等。即使如此,在數字經濟下需求替代分析仍然居于主導地位甚至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因為在數字經濟下經營者的生產能力或者說供給能力在理論或實踐中都可以無限擴大,其供給量規模性增長的邊際成本趨于零。數字經濟下相關市場界定方法的選擇必須更多依靠用戶端包括消費者和商家的需求替代性分析。
用戶的需求替代是判斷數字經濟下相關市場上競爭約束存在與否的關鍵指標,也是界定相關市場范圍的核心要件。隨著市場競爭方式逐漸由傳統價格競爭轉向注意力競爭和數據競爭,對用戶需求的精準把握和持續爭奪已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經營者在相關市場上的競爭優勢及其維持。經營者必須高度關注用戶需求,并基于用戶需求不斷推出升級商品和服務[ 25 ],以最大限度增加用戶使用該商品和服務的時間,提高用戶的黏性。同時,在不斷滿足用戶需求甚至培育用戶需求的過程中,經營者必將擁有更多的用戶數據,在海量的多樣化用戶數據支撐下,能夠更準確地把握用戶的實際需求,提高市場競爭的預測能力。在這種情況下,亦可能產生新的更高的市場進入壁壘,阻礙數字創新型企業進入[ 26 ],此時的用戶需求替代標準已經轉變為經營者所在相關市場界定的標尺及市場力量評價的基準。
(三)轉向以非價格要素為重心的需求替代分析方法
在數字經濟下基于用戶需求替代標準來識別競爭約束的做法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和操作價值,故在調整和改進現行相關市場界定方法時,仍應以用戶需求替代為中心展開探索。與實體經濟場景下用戶需求替代標準適用不同的是,數字經濟領域市場競爭方式已由傳統價格競爭轉向用戶注意力競爭和數據競爭,對用戶需求的精準把握和持續爭奪已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經營者在相關市場上的競爭優勢及其穩定性,經營者必須高度關注用戶需求,并基于用戶需求不斷優化升級商品質量,增值疊加商品功能。數字經濟下平臺商業模式產生了以商品基礎功能為主的商品功能疊加競爭,推動了雙邊或多邊市場結構下跨市場競爭,出現了非對稱性定價結構,促使著用戶需求替代標準的具體變量發生重大變化。
在價格仍是重要變量的同時,用戶注意力、數據及商品質量都成為相關市場界定中的必要變量,考察范圍包括可量化的價格要素和難量化的非價格要素,涵蓋具有統一性標識的價格信號和極具個性化特征的用戶體驗反饋,這對現行的需求替代分析方法的適用帶來了很大的不穩定性和模糊性。因此,必須結合用戶需求替代發生的具體場景,重視個案中相關市場界定的精準分析。
以數字經濟下“免費/零定價端+收費端”市場結構為例,多邊市場平臺和靈活定價結構成為創新商業模式的基礎,大多數經營者采取前端讓利加后端收費的方式整合多邊市場上的商品,充分利用網絡交叉外部性效應,將多邊市場的各類商品的價格與收益綜合考慮,使單一市場上的商品定價有了更多的彈性空間,商品價格已不再是用戶選擇替代品的唯一考慮要素,諸多非價格要素成為用戶需求替代考量的重要指標,傳統的基于價格需求彈性的替代性關系受到巨大挑戰。因此,在互聯網數字經濟下準確把握用戶需求替代考核標準是科學調整相關市場界定方法的前提和基礎。
此外,互聯網數字經濟的技術創新速度和商品功能疊加升級速度都非常快,用戶需求的內涵與形態也在快速變化,對需求變量的觀察和選擇必須結合具體場景展開。如用戶更多地是根據搜索的內容和類型選擇不同的搜索平臺,而非根據平臺性質進行選擇,搜索平臺相對于用戶需求的生成和維持而言處于被動地位。然而,用戶對在線社交軟件及服務的選擇則更多依據平臺的性質,社交平臺相對于用戶需求的生成和維持居于主導地位。這就使得在選擇在線搜索服務市場與在線社交服務市場上的用戶需求替代的實際變量時需要細致區分,復雜程度越來越高。
綜上,用戶需求替代分析方法在數字經濟下并沒有因為競爭行為和商業模式的改變而無法適應新的市場競爭環境,只是需要將用戶需求替代分析中的變量結合個案予以動態調整,推動具體個案中相關市場界定的精準化,綜合考慮數字經濟的個性化、定制化特征在反壟斷法適用中的影響,同時凸顯用戶偏好在需求替代分析變量選擇上的重要性。
五、結語
隨著信息通信技術和數字技術的深度融合,互聯網數字經濟得到了飛速發展,產生了諸多新型市場競爭現象,如預防性收購、封鎖屏蔽、二選一等反競爭行為頻現,對市場競爭秩序構成威脅,亟待通過科學合理地適用反壟斷法予以解決,其中關鍵在于準確界定相關市場。通過對現有相關市場界定方法的檢視,本文認為需求替代分析方法仍然適用于數字經濟下的相關市場界定,只是在具體變量選擇上需要結合具體案件予以調整,實現數字經濟下相關市場界定的精準分析,結合數字經濟運行的具體場景來識別用戶的需求替代性,其中的基本原則是提高用戶對商品的體驗感,加大對非價格要素的考察,以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結合的方法界定相關市場的合理范圍。
注釋:
①參見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11)粵高法民三初字第2號.
②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13)民三終字第4號.
③參見Ohio v. Am. Express Co.,138 S. Ct. 2274(2018).
④參見深圳微源碼軟件開發有限公司與騰訊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市騰訊計算機系統有限公司壟斷糾紛一審民事判決書(2017)粵03民初250號.
⑤參見United States v. E. I. du Pont de Nemours & Co.,351 U.S. 377(1956).
⑥參見北京銳邦涌和科貿有限公司訴強生(上海)醫療器材有限公司、強生(中國)醫療器材有限公司縱向壟斷協議糾紛上訴案判決書(2012)滬高民三(知)終字第63號.
參考文獻:
[1]陳兵.數據時代開啟消費者保護多元共治新格局[J/OL].(2019-11-13)[2021-01-03].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http://kns.cnki.net/kcms/detail/22.1062.C.20191113.10 36.002.html.
[2]許光耀.互聯網產業中雙邊市場情形下支配地位濫用行為的反壟斷法調整——兼評奇虎訴騰訊案[J].法學評論,2018(1):108-119.
[3]RATLIFF J D,RUBINFELD D L.Online advertising:defin? ing relevant markets[J].Journal of competition law and eco? nomics,2010(6):653-686.
[4]張江莉.論相關產品市場界定中的“產品界定”——多邊平臺反壟斷案件的新難題[J].法學評論,2019(1):184-196.
[5]張江莉.多邊平臺的產品市場界定——兼論搜索引擎的產品市場[J].競爭政策研究,2018(1):5-19.
[6]EVANS,DAVID S.The antitrust economics of multi-sided platform markets[J].Yale journal on regulation,2003(2):331-333.
[7]WONG- ERVIN,KOREN.Assessing monopoly power or dominance in platform markets[EB/OL].(2020-01-26)[2021-01-04].https://ssrn.com/abstract=3525727.
[8]寧立志,王少南.雙邊市場條件下相關市場界定的困境和出路[J].政法論叢,2016(6):121-132.
[9]EVANS DAVID S,SCHMALENSEE RICHARD.The role of market definition in assessing anti- competitive harm in Ohio v. American express[EB/OL].(2019- 06- 08)[2021-01-04].https://ssrn.com/abstract=3401325.
[10]陳兵.因應超級平臺對反壟斷法規制的挑戰[J].法學,2020(2):103-128.
[11]王曉曄.論相關市場界定在濫用行為案件中的地位和作用[J].現代法學,2018(3):57-69.
[12]陳兵.網絡經濟下相關市場支配地位認定探析——以“3Q”案為例[J].價格理論與實踐,2015(9):16-20.
[13]曾田.網絡內容平臺競爭與反壟斷問題研究[J].知識產權,2019(1):45-60.
[14]陳兵.如何看待“數據壟斷”[N].第一財經日報,2020-07-28(A11).
[15]殷繼國.大數據經營者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法律規制[J].法商研究,2020(4):73-87.
[16]葉明.互聯網對相關產品市場界定的挑戰及解決思路[J].社會科學研究,2014(1):9-16.
[17]殷繼國.反壟斷執法思路辨析:定性分析抑或定量分析[J].價格理論與實踐,2014(12):27-29.
[18]殷繼國.大數據市場反壟斷規制的理論邏輯與基本路徑[J].政治與法律,2019(10):134-148.
[19]胡麗.互聯網經營者相關商品市場界定方法的反思與重構[J].法學雜志,2014(6):60-66.
[20]蔣巖波.互聯網行業反壟斷問題研究[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9:85-86.
[21]張小強,卓光俊.論網絡經濟中相關市場及市場支配地位的界定——評《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相關規定[J].重慶大學學報(社科版),2009(5):91-97.
[22]林平,劉豐波.雙邊市場中相關市場界定研究最新進展與判例評析[J].財經問題研究,2014(6):22-30.
[23]龍柯宇.論反壟斷法中知識產權相關市場界定的產品維度[J].求索,2013(2):183-185.
[24]王曉曄.反壟斷的相關市場界定及其技術方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9:3-4.
[25]朱理.互聯網領域競爭行為的法律邊界:挑戰與司法回應[J].競爭政策研究,2015(1):11-19.
[26]陳兵.大數據的競爭法屬性及規制意義[J].法學,2018(8):107-123.
責任編輯:方程
Challenges and Method Improvement of Relevant Market Definition in Digital Economy
CHEN Bing
(School of law,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350,China)
Abstract:The deep integration and wid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digital data technologypromote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cultivates various new industries and new models,and brings earth-shaking changes to the market competition mode,industrial organization structure and the specific business behavior of operators.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economy,the platform-centered business model leads to the enhanced competition,and the more complicated cross-market competition and integr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asymmetric pricing structure in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market,which brings many challenges to the current market definition method based on the commodity function and price in the unilateral market. The limitation of the existing related market definition is highlighted. In order to respond to the related market definition problems in the digital economy,it is suggested to return to the substitution analysis of user demand. While the price variable is gradually weakening,user attention,data and commodity quality constitute the important variables to be investigated in the relevant market definition.Based on this,it is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accurate analysis of the relevant market definition in the case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specific scenarios of user demand substitution.Specifically,with the market competition mode in the field of digital economy gradually changing from traditional price competition to user attention competition and data competition,the accurate grasp and continuous competition of user demand have largely determined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and maintenance of operators in relevant markets.Therefore,in order to gain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the attention competition,operators must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users needs,and constantly optimize and upgrade the quality of goods,and add commodity functions. So,the definition of relevant market should consider the users diversion scope and data transfer cost based on the users demand substitution,so as to reflectthe impact of personalized,customized and refined characteristics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anti-trust law in the digital economy,and highlights the increase of the weight of user preferences in the demand substitution analysis.
Key words:digital economy;anti-trust law;relevant market definition;demand substitution;non-price facto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