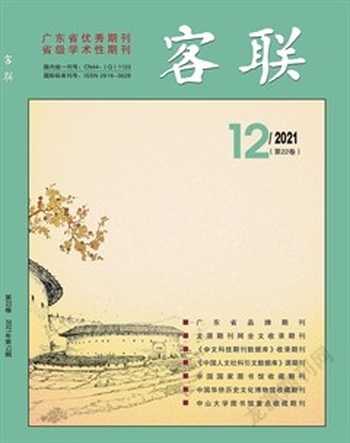懲罰性賠償制度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的現狀與完善
林燕
摘 要:受逐利因素影響,部分經營者在經營過程中侵害消費者合法權益的現象時有發生。懲罰性賠償制度作為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的一種特殊的懲罰制度,在日趨復雜的經濟環境下發揮了重要的震懾作用。文章基于懲罰性賠償的概念提出其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的必要性,并根據懲罰性賠償制度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的實施現狀提出相應的完善策略。
關鍵詞:懲罰性賠償制度;消費者權益保護法
一、懲罰性賠償的概念界定
關于懲罰性賠償的概念學術界多有探討,主要存在以下幾種觀點:一種認為懲罰性賠償同時兼具懲罰性和補償性兩種屬性,主要作用于精神損害賠償;另一種則認為懲罰性和補償性兩種屬性屬于對立關系,不存在包含關系,當受害人因加害人的惡意或欺詐行為而遭受損失時,受害人可要求實際損失以外的補償性賠償。筆者認為,懲罰性賠償既具有懲罰性、同時兼具法定性和威懾性,所以其概念為:受害方在遭受損害時可以向加害方請求超過實際損失的一種賠償,兼具懲罰性和補償性。補償性的一面體現在侵權行為造成的全部損失都需要不法侵害者承擔責任,彌補受害人全部的損失;懲罰性方面體現在,為了震懾不法侵害者,警示潛在的不法侵害者,除了要求不法侵害者賠償受害人的損失外,還必須對因其侵權而遭受損失的受害人給予更多的賠償。
二、懲罰性賠償制度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的必要性
(一)彌補了侵權責任中的救濟缺陷。侵權責任雖然對潛在的侵權行為具有一定的懲罰和威懾作用,但受到傳統民法理念的制約,它是以損失填平原則為基準,實現補償功能。受這一觀念指引,無論是針對違約行為的賠償還是侵權行為的賠償,給受害人的補償金數額不得少于其受到的實際損失,否則受害人將無法獲得全部救濟;消費者在正常的市場交易中,通常購買的生活用品或接受的服務都是數額較小,加之消費者在訴求救濟時還會面臨訴訟中的種種困難。更何況對于生產者來說,獲得的收益遠高于需要支付的賠償,這種懲罰的威懾作用微乎其微。因此,《消法》的這一規定借用了公法中罰金的懲罰功能,起到了威懾的作用,從而彌補了侵權責任中產品責任救濟上的缺陷。
(二)符合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立法目的。首先對經營者的不法行為進行有力威懾。如果嚴重侵犯消費者權利的違法行為不能受到與之匹配的處罰,則助長了商品或服務提供者的逐利心理,懲罰性賠償使得經營者增加其不法經營的成本,其威懾作用可有效減少經營者的不法行為;其次可平衡經營者和消費者的地位。懲罰性賠償制度約束強勢主體,使得強勢方承擔更重的責任,增加了他們的責任感。在商品交易的過程中,加重經營者利用其在商品信息上的優勢侵害消費者利益的責任,保護消費者在交易中的弱勢地位,賦予消費者可以要求多于商品價格的賠償的權利,以平衡兩者的地位。第三是調動消費者維權的積極性。懲罰性賠償制度本身突破了民法的損失填平原則,給予受害人多于所受損失的經濟補償,激勵受害人利用法律手段維護權益。這種私人提起的救濟方式,“額外獲益”降低了消費者關于訴訟成本的顧慮,提高了利用法律手段維護自己權益的積極性。
三、懲罰性賠償制度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的現狀
(一)欺詐的認定存在爭議。首先是適用要件標準不統一。當前,絕大多數涉及消費者權益保護的案件爭議焦點都在“欺詐”的認定上,司法實踐中,欺詐的認定標準存在差異,同案不同判現象屢有發生,不法經營者需要承擔的責任也不相同,不利于凸顯司法公正。對于懲罰性賠償制度來說,用什么標準來認定“欺詐”是非常重要的,《侵害消費者權益行為處罰辦法》對市場交易中常見的欺詐行為做了列舉性規定。但是列舉的范圍有局限性,隨著社會化進程的發展,商品和服務的品類增加,信息量增多,現有的立法并不能囊括所有可能發生的欺詐類型,實踐中出現《處罰辦法》中未列舉的情形時,只能依靠法官的個人經驗做出裁判,就會導致裁判結果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由于沒有統一的認定標準,司法實務中對于經營者的行為是否構成欺詐存在著不同的處理。
(二)“消費者”身份未厘清。《消法》明確指出了“消費者”的消費行為必須是“生活消費”,但是對于單位是否屬于消費者主體范圍等問題并未做出明確答復。理論界對此存在較為明顯的分歧和爭議,部分學者認為單位雖然有生活需求,但是實施者均為自然人,遭受侵害導致的損失自然應該由自然人向經營者索賠,因此單位不屬于消費者主體范圍;也有學者認為,從商品以及經營的相關知識層面來看,單位相較于經營者同樣處于弱勢,且單位的消費者身份并沒有被法律明確否認,通常單位消費金額較大,不法侵害損失自然也大,因此單位應該屬于消費者主體范圍。總的來說,單位是否屬于消費者范圍,理論界和實務界有著不同觀點,單位的身份沒有準確的定位,對司法實務也有很大的影響,這個問題就需要法律來厘清。
(三)適用懲罰性賠償的行為類型有限。單純將欺詐和惡意致害指定為適用懲罰性賠償制度的行為模式是不合適的。僅僅規定“欺詐”和“惡意傷害”兩種類型,這使得現有規定過于單調,難以規制抱著僥幸心理的經營者不法行為,不能有效地懲處惡意經營者。在合同領域,除了欺詐以外,還有許多惡意行為。如果僅規制欺詐行為而忽略其他惡意行為,就無法更廣泛地應用該制度,這與立法目的背道而馳。應擴大適用范圍,增加其他惡意行為的適用,以更好地打擊惡意經營者,更加全面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因此,在適用客體范圍上,《消法》需要做出更詳細的規定。
四、懲罰性賠償制度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的完善建議
(一)規范消費欺詐的認定要件。首先要統一適用要件標準。《消法》是對處于弱勢地位的消費者提供的保護,若以民事欺詐的適用要件認定消費欺詐,不免會削弱消費者的被保護地位。因此,消費欺詐與民事欺詐僅僅使用同一個詞語,但是其內在并不相同,也不應混為一談以同樣的標準來認定。在當前的市場環境下,應逐步放寬對經營者欺詐的認定要求,即僅限于經營者主觀狀態和欺詐行為兩個方面,對消費者的主觀狀態不予考慮。建議對消費欺詐的認定應以經營者的主觀和客觀行為作為認定標準,對消費者的主觀狀態在所不問,可以有效保護消費者權益,同時也不會對市場活力產生較大影響,更貼合市場規制的要求。
(二)區別對待單位的“消費者”身份。單位作為消費者維權較員工個人維權難度和成本都降低,因為員工個人維權承擔的舉證責任重,既要證明經營者的主觀故意,還需要證明自己與單位的關系,給消費者維權制造障礙。因此,賦予單位消費者身份有助于保護弱勢消費者,符合《消法》的立法宗旨。單位直接作為權利主體提起訴訟和要求賠償,也有助于節省司法資源。筆者認為,在明確列舉和解釋相關概念的前提下,我國《消法》應對單位消費進行兩種情況的處理:一是單位購買福利產品滿足員工需求時,應作為自然人消費原則納入《消法》的調整范圍;第二,當單位購買產品是為了滿足其擴大再生產的需要時,它將不再受《消法》的調整。
(三)梳理適用懲罰性賠償的違法行為。現行《消法》對于懲罰性賠償,主張只有經營者滿足特定條件,且存在欺詐行為和惡意侵害行為時,消費者才能向經營者主張懲罰性賠償。懲罰性賠償制度的適用范圍的不足在現行市場經濟中無法有效保障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實踐中,脅迫交易、強迫交易等不法交易屢有發生,其產生的后果甚至要重于欺詐行為和惡意侵害行為,《消法》懲罰性賠償制度應進一步完善適用范圍,對于在實際經營活動中存在的除欺詐行為和惡意侵害行為以外的其他惡意行為應根據危害性適時納入懲罰性賠償范圍以內。如果在懲罰性賠償制度中包括違反合同和侵權方面的有害行為,則對消費者的保護將更加全面和具體,懲罰性賠償制度可以適用于社會實踐中嚴重侵害消費者的違法行為,最大限度地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參考文獻:
[1]夏瑩秋. 論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的懲罰性賠償制度[D].遼寧大學,2021.
[1]米卡熱木·努爾麥買提.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完善研究[J].法制與經濟,2020(06):53-55.
[1]陳思思.淺議懲罰性賠償制度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的發展與完善[J].法制博覽,2018(21):158-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