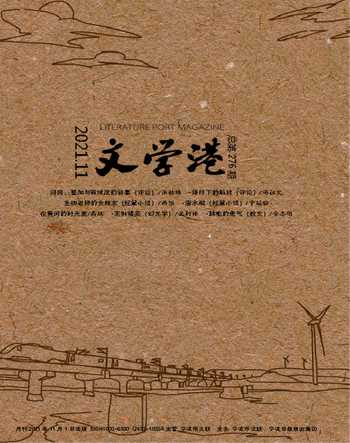蘇戲墨探案之雜藝記
蔣話
0
子不語(yǔ)怪力亂神。
然而,這個(gè)世界上,真的存在怪力亂神的奇異事件嗎?
還是,人心才是最難以捉摸的罪魁禍?zhǔn)祝?/p>
我叫蘇戲墨,而立之年的我,尚未婚配,在京城經(jīng)營(yíng)一家名叫“戲墨軒”的藥房。除了出診瞧病,到齋冷山莊找賦閑在家的好友左飲寒下棋外,還喜歡搜集各地的奇聞異事,將它們一一記錄下來,探尋合情合理的謎底。
朋友們知道我這個(gè)嗜好,總是會(huì)把道聽途說的故事轉(zhuǎn)述于我,這其中不乏華麗、吸引人的謎面,例如遼東軍營(yíng)夜半怪吼事件(所謂的神怪吼叫,其實(shí)是軍營(yíng)里一個(gè)胖子半夜打呼嚕)、徐州書僮魑魅附身異聞(書僮偷懶不想去私塾陪讀,假裝被魑魅附身)、西川奇人水面疾走消失疑云(水下有建橋時(shí)殘留的七八個(gè)木樁子,走出幾步后木樁子沒了,奇人掉水里淹死了,如此“消失”)等等,大多被證實(shí)是故弄玄虛。
事無怪力亂神,只因斷章取義。這是我一直信奉的。
正心正道,則浮言消散,詭異事件自然不攻自破。
1
“真是一場(chǎng)好雨,難得落個(gè)清凈。”秋公澤推開戲墨軒的紗窗,說道。
雨滴打在窗外的芭蕉上噗噗作響,時(shí)而急促,時(shí)而平緩,像節(jié)奏多變的鼓聲。
“聽說了嗎,歸德那邊鬧了旱災(zāi),許多人失了土地做了流民,怕是你又不得清閑了。”我替秋公澤斟酒,琥珀色的美酒落到杯中。
“是啊,流民沖了當(dāng)?shù)貛讉€(gè)縣衙才作罷,傳言衙門里出了內(nèi)鬼接應(yīng),上峰已派我去調(diào)辦,不用說,又是一趟吃力不討好的苦差。”秋公澤望著桌案上的白玉杯,癡癡道,眼中滿是落寞之情。
秋公澤是我同鄉(xiāng)發(fā)小,年少時(shí)我們便常來常往。二十歲我倆一起進(jìn)京,他第一次就武舉中第,飛魚服加身,而我卻連著幾次落榜。后來他又祖墳冒青煙,被牟斌指揮使看中,連連升遷,不到三十歲已做了錦衣衛(wèi)的百戶,一套秋家鐵拳打得密不透風(fēng),在京城年輕輩里拳術(shù)除了左飲寒外,怕是無人出其左右。
今天的秋公澤頭戴網(wǎng)巾,身著一襲醬色罩甲,腳上踏雙深色粗皮履,便裝出門的他,一到我藥店里二話沒說,就開始喝悶酒。
“歸德那水可不好蹚,那邊的幾個(gè)縣頭都是李閣老舉薦的。”我說。
“問題就出在這里,這事要是辦砸了,閣老和指揮使那邊都不好交代。”秋公澤一臉為難。
“這其中的斡旋,就看你把握了,辦好了我又能喝你的升遷酒。”我說。
“饒了我吧,但求無過即可。建德那邊倒是發(fā)了水患,要是建德的水能自引向歸德,兩難自解。”秋公澤舉杯一飲而盡,飽滿的臉頰已有些泛紅。
“你可真會(huì)做春秋大夢(mèng)。”我笑著說。
秋公澤卻一臉嚴(yán)肅,他將飲盡見底的杯子伸出窗外,說道:“都說萬物有靈,倘若我一伸手,雨露有所感,會(huì)自己拐彎朝杯中有序滴落,該有多妙。”
“哪天你遇上這樣的事情,煩請(qǐng)第一個(gè)告訴我。”我佯裝正經(jīng),“我的異聞錄已經(jīng)吃灰很久了。”
“雨滴的神跡我尚未遇上。”秋公澤說,“可是飛刀自行繞道拐彎的事,卻被我撞上了,且令我頭疼不已。”
“飛刀拐彎?”我一下來了精神,“攤開說說?”
秋公澤拾起桌上一根筷子,在酒杯邊沿敲擊了幾下,忽然將筷子輕輕拋了出去。筷子很快應(yīng)聲落地,滾出不遠(yuǎn)后停下。
“你看,好比這根筷子,我朝前投擲,在沒有人力、外物的干擾下,落地前它就不可能向后飛去,更不可能像長(zhǎng)了眼睛似的,自己瞄準(zhǔn),猛然就偏左偏右拐彎,你說對(duì)吧?”秋公澤說。
“那是當(dāng)然的。”我招呼伙計(jì)換雙新筷子,遞到秋公澤手上,“又不是說書、話本里的傳說,飛出去的筷子也好,刀子也好,怎么可能自己偏轉(zhuǎn)。”
“武功再高也不能夠?”秋公澤確認(rèn)道。
“當(dāng)然,你是武官,該比我更明白吧。”我說。
“可是有人做到了。”秋公澤說,“倒是個(gè)戲子,雜戲的戲子。”(注1:雜戲即現(xiàn)在的雜技表演。)
“你說的是唐元周吧?”我有些失望地說,“他的妖刀把戲倒是好看,但都是一些障眼法,不是真能耐。”唐元周的雜藝最近在京城聲名鵲起,一票難求,很多官員慕名而去。
“就是這唐元周。”秋公澤正色道,“這可不是障眼法,我懷疑他真會(huì)什么妖法,讓飛刀也有了靈性。”
“這你就是癡人說夢(mèng)了。”我說,從長(zhǎng)袖中摸出《戲墨軒筆記》,翻弄著,“我這本子里奇異的事情記的可多了,沒一件能和鬼神搭上關(guān)系。”
“你出京辦藥材走了一個(gè)多月,你是不知道,刑部大牢里這一個(gè)月來可是熱鬧了,月初最多時(shí)抓進(jìn)去百來號(hào)人。”秋公澤說,“大理寺這邊快忙瘋了,就差點(diǎn)借用咱錦衣衛(wèi)的詔獄了。”
“什么案子這么厲害,繞過應(yīng)天府直接通刑部了?”我吃了一驚,也不免心生好奇。
“上月,翰林院侍讀方琦瑜大人在爐斧閣看唐元周雜藝時(shí)被殺了,因?yàn)橐粫r(shí)找不到兇手,就把幾乎所有在場(chǎng)的人逮進(jìn)去了。”秋公澤說,“當(dāng)然,后來經(jīng)過詢問、探查,也陸續(xù)放了一些洗脫嫌疑的人,可是我那未來的老丈人,因?yàn)闆]法子證明自己清白,到現(xiàn)在還在牢里待著呢,吃了快一個(gè)月的牢飯,要是再抓不住真兇,后半輩子終死牢獄也不是不可能。”
“那個(gè)喜歡著書,專寫殺手、刺客的蔣員外?你不是最厭惡他么,他不同意你和她女兒的婚事,進(jìn)去了沒什么不好啊。”我打趣道。
“我倒是沒意見,可人蔣小姐不樂意,讓我疏通打點(diǎn),不快點(diǎn)放老爺子出來,我和她的事就算完了。”秋公澤苦惱地說。
原來,真正讓他煩惱的不是去歸德的公事。我暗暗忖道。
“我沒弄明白。”我數(shù)著酒杯上面的蓮花紋路,“一個(gè)翰林院侍讀而已,又不是多大的官,刑部這次怎么會(huì)這么大張旗鼓?”
“那是劉公公的親戚,五年前從大同調(diào)過來,原本打算歷練幾年就入閣的。”秋公澤將我的杯子搶下,“你就幫我上點(diǎn)心吧。”
“那就難怪了……”我點(diǎn)點(diǎn)頭,劉公公現(xiàn)今如日中天,圣上不怎么管事,自然由著他胡來。
“所以這事我也沒法疏通,只能去明察暗訪,真相一旦浮出水面,我那未來泰山岳丈不也能少受幾天罪么。可是我查了那么多天,都沒有太多頭緒。”秋公澤不懷好意地笑了,目光落在我身上。
“所以……你就想到我了。”我被他瞧得起了雞皮疙瘩,伸手將他臉頰掰向一邊。
他將我的手輕輕打落,說道:“蘇兄,我知道,你會(huì)幫我的。”
“你猜錯(cuò)了,我辦藥材忙乎了這么久,正想好好休息下。”我伸懶腰起身端起酒壺,轉(zhuǎn)過頭對(duì)秋公澤說,“況且,我這些年來總是被你嘲諷光棍一人,是時(shí)候讓你也嘗嘗這滋味了。”我哈哈一笑,就要往里屋走。
秋公澤倒也沒有攔我,整理下網(wǎng)巾,緩緩起身道:“其實(shí)我這半個(gè)多月來,并不是全然沒有收獲,只是我也好,大理寺、刑部的同僚也好,都不相信世界上會(huì)有這么邪門的事情。”
“邪門事情?”我停下腳步。
“長(zhǎng)了眼睛,自己會(huì)拐彎的事物,是確切存在的。”秋公澤幽幽地說,“絕不是障眼法。”
秋公澤的話語(yǔ)戛然而止。他喝下最后一口酒起身,不咸不淡道,“不過,反正你想休息一下,那就算了,當(dāng)我沒說吧。”說完,他徐步走出了戲墨軒,頭也不回。
想吊我胃口?我才不會(huì)輕易上當(dāng)。
我輕撫著《戲墨軒筆記》,傾斜酒壺,從壺嘴吞了口酒。
2
爐斧閣位于京城東邊的明時(shí)坊,距離崇文門不遠(yuǎn)。我和秋公澤閑暇時(shí)喜歡到爐斧閣看雜戲,談不上多癡迷,純屬消遣。有時(shí)候,我也會(huì)與好友左飲寒來光顧,那家伙竟對(duì)雜藝如癡如醉,在坐席間陶醉歡呼不說,還幾次要上臺(tái)和雜藝者攀談,讓我很沒有面子。
我和秋公澤到崇文門附近的時(shí)候,雨已經(jīng)停了,天色朦朦朧朧的,像籠了一層紗,看不到太陽(yáng),路上只有稀稀拉拉幾個(gè)行人。
上月初二,翰林院侍讀方琦瑜方大人正是來爐斧閣看雜藝出的事。那天爐斧閣既有京城雜藝?yán)吓瓢嘧印昂弦话唷钡匿撍鞅硌荩钟袕慕隙鴣韰⒓友惭莸膶O家兄弟的火棍雙絕,當(dāng)然,也少不了今年風(fēng)頭正勁的唐元周。
妖刀是唐元周的成名雜戲,我和秋公澤在爐斧閣看他表演過幾次。兩把飛刀離手后,本該直線飛行卻分別朝左、右劃出弧線,像自己會(huì)瞄準(zhǔn)似地?fù)糁兄本€距離外的標(biāo)靶。
聽秋公澤說,微服出行的方琦瑜逝于爐斧閣內(nèi)的看官坐席,那個(gè)時(shí)候,戲臺(tái)上表演的正是唐元周。起先,左右隨從以為方琦瑜僅僅是睡去,雜藝表演精彩不斷,其間眾人紛紛吶喊鼓掌,他沒半點(diǎn)反應(yīng),身子還漸漸從椅子上滑落,摔到地上,隨從這才意識(shí)到大事不好。致命的,是方琦瑜脖頸后那根毒針,只有半截拇指長(zhǎng)短,而那時(shí),方琦瑜的身子還有些暖意,顯然死亡不久。
“尸身送回宮里驗(yàn)的尸,宮中的仵作說,那是種毒性很強(qiáng)的苗毒,毒液接觸皮膚人即陷入昏迷,如果救治不及時(shí),一盞茶工夫就會(huì)一命嗚呼,死得悄無聲息。”秋公澤嘖嘖稱奇。
就在這時(shí),馬車也停了下來。秋公澤撩開車簾往車外望了一眼,說了聲“到了”便領(lǐng)我一同下車,他轉(zhuǎn)身給車夫一些銅板,讓車夫在街旁候著。
“莫非是葫蔓陀毒?去年我給沐家瞧病時(shí)見識(shí)過,據(jù)說在云南也不常見,大多是土司祭祀時(shí)用到的。”我回憶道,手執(zhí)筆桿,邊走邊將有關(guān)線索記到《戲墨軒筆記》上。
“這一年來這種毒由行腳商人帶入,京城已經(jīng)發(fā)生好幾起中毒事件了。行腳商人流動(dòng)大,大理寺連同錦衣衛(wèi)查了將近一月,也沒查出方琦瑜毒物的具體來源。”秋公澤嘆道。
“也就是說,在看雜戲期間,有人將毒針刺入了方大人頸后?”我說。
“仵作說,方琦瑜確切中毒時(shí)間,也就在隨從發(fā)現(xiàn)他死亡前一盞茶工夫里。”
“你知道的,看雜藝時(shí),看官們免不了在席間起身走動(dòng),從方琦瑜身后經(jīng)過,悄悄將毒針刺入不是難事。左右隨從的注意力又被戲臺(tái)上的表演吸引,沒留意到身后經(jīng)過的人,也屬正常。”秋公澤說,“況且,從方琦瑜進(jìn)入爐斧閣開始,門外就有東廠的廠衛(wèi)守著,不允許人再進(jìn)出,所以下毒的人,一定在爐斧閣里。”
“所以,在不能確定兇手是誰的情況下,干脆把所有人抓起來審問?”我咬著筆桿搖搖頭,“真是胡鬧。”
“可除此之外,也沒好辦法了。”秋公澤無奈地說。
“有一事我不解。”我忽然想到,“方琦瑜大人是雜藝票友?經(jīng)常來爐斧閣看表演么?”
“那倒不是。這唐元周是方大人的老部下,過去一起鎮(zhèn)守大同戰(zhàn)過瓦剌,方大人能來爐斧閣捧場(chǎng),很大程度上是看在他面子上,據(jù)說是他出面邀請(qǐng)才答應(yīng)下來的。”
“還有這層關(guān)系。這事因唐元周而起,他肯定是第一嫌疑人了。”我說。
“恰恰相反。”秋公澤說,“唐元周很快無罪釋放了。””
“啊?”我不解道。
“方琦瑜出事時(shí),唐元周都在臺(tái)上表演,怎么下手?等于說全場(chǎng)人都是唐元周無罪的證人。”秋公澤用手背拍另一只手的掌心。
“就不可能雇兇殺人?不一定得自己下手。”我想到另一種可能性。
“不可能。雇兇的風(fēng)險(xiǎn)是很大的,殺手無義,嘴不嚴(yán),很容易就把雇主供出來了,更何況還是殺頭的案子。”秋公澤說,“況且我們查了抓的那些人的底細(xì),大多是周邊的良民,并沒有可疑人物混入。”
“即是說,事先只有唐元周知道方大人那日會(huì)來看雜戲?”我摸摸下巴,事情似乎變得有點(diǎn)意思了。
“頂多還有幾個(gè)爐斧閣管事的知道。”秋公澤說,“那天方琦瑜和兩名隨從進(jìn)入爐斧閣后,有東廠廠衛(wèi)守在閣門外,看官們才意識(shí)到有大人物在場(chǎng),當(dāng)然具體是誰他們心里也沒譜。”
“奇怪了,既是唐元周邀請(qǐng),又是在唐元周表演時(shí)遇害,這也太巧了點(diǎn),還附贈(zèng)了不在場(chǎng)證明。”我頭也不抬,將疑問記入筆記。
“你終于注意到了。”秋公澤像找到了知音,“不單單如此,我和刑部的同僚還發(fā)現(xiàn),唐元周一年半前被言官?gòu)椲蕾H為庶人,也是替方琦瑜背的鍋,要不是有幾手雜藝絕活,在京城無親無故的唐元周連養(yǎng)活自己都成問題。”
“這樣一來,唐元周的殺人動(dòng)機(jī)也足夠了。”我說。
“可是不頂用。”秋公澤說,“事實(shí)就是,他在戲臺(tái)上,沒有下手的時(shí)機(jī)。除非……”
“那根毒針也像他耍的妖刀那樣,射向看官席后陡然偏轉(zhuǎn),繞后刺入方琦瑜脖頸。”我補(bǔ)充道。
我倆一同沉默,很快我搖了搖頭,說道:“不可能,我怎么也說出和你一樣的瘋話。”
“或許說明,你認(rèn)為的瘋話,其實(shí)并非誑言。”秋公澤堅(jiān)持道。我連連搖頭,避免再次被他蠱惑,快步向前走去。
起風(fēng)了,吹散了天空的濃云,心里的疑云卻越積越多。熹微的陽(yáng)光灑在我的臉上,卻像冷光般,使得雙頰冰涼。
“你說方、唐他倆鎮(zhèn)守過大同?看不出來,這方大人竟是個(gè)儒將?”我放慢腳步,問秋公澤。
“我朝文官領(lǐng)兵是常事,況且這不有劉公公保么?聽說這家伙見了瓦剌軍隊(duì)每次都是聞風(fēng)而逃,在大同有個(gè)‘露背將軍的綽號(hào)。”秋公澤壓低了聲音,“我在宮里見過他幾回,是個(gè)黑胖子,一雙招子平日里閃閃發(fā)光,看上去是個(gè)狠角色,卻不想這么慫。”
“這也能給提拔上來?完全沒有軍功,怕是劉公公也不好辦吧。”我驚道。
“抓不到瓦剌兵,這老小子拿當(dāng)?shù)責(zé)o辜百姓開刀,殺了當(dāng)瓦剌人報(bào)上去。”秋公澤眉頭緊蹙,“前幾年吳縣有個(gè)財(cái)主也遭了殃,吳家小姐聽說還被姓方的糟蹋了身子。”說到這里,秋公澤面露憤慨,也顧不上輕聲細(xì)語(yǔ),大大咧咧說了出來。我連忙讓他收聲,畢竟?fàn)t斧閣已近在眼前,閣門前守著兩個(gè)官差模樣的人,像是順天府派來的。
爐斧閣起著歇山式的青瓦頂,大門朝南,總共兩層,弘治年間二樓遭了火災(zāi)后就被閣主桑青封了,只保留一樓繼續(xù)供雜藝表演。這桑青早年靠雜藝班子起家,也當(dāng)過班主,爐斧閣聲名鵲起后便做起了場(chǎng)子生意,入駐此閣表演的班子都要給他場(chǎng)銀,并且茶水費(fèi)分成,油水不少。
如今,桑青正站在閣門前,一襲青衫的他佝僂著背,國(guó)字臉上滿是皺紋,半年前我還見過他,那時(shí)候的他滿面紅光,氣度不凡,看來這一個(gè)月,他的確是心力交瘁。
“秋大人來了?老朽已恭候多時(shí)。”桑青向著秋公澤作揖道,他的聲音干澀,嗓子含了沙一般。
“今天我告了假,并非公務(wù)出行,只是帶一位探案專家來此地查看,也好早日找出真兇,還你爐斧閣一個(gè)清白。”秋公澤拍拍我肩膀說道,“當(dāng)然,到時(shí)候如果還是毫無進(jìn)展,你拿他是問就行。”
這天譴的秋公澤,又把我往火坑里推。
“不敢不敢……”桑青望著我說:“還未請(qǐng)教這位大人高姓大名。”
我連忙抱拳道:“在下蘇戲墨,一介布衣。”
“哦……”雖然肯定沒有聽說過我,桑青還是抱拳道了聲久仰久仰。
“幸會(huì),幸會(huì)。”我回禮道。
“得了,趕緊吧。”秋公澤打斷例行公事般的客套,向守在閣門口的捕快們亮了腰牌。我們?nèi)隧樌M(jìn)入了爐斧閣。
爐斧閣內(nèi)廳堂寬闊,設(shè)著紫檀桌、雕花靠背椅,能供百余人同時(shí)欣賞雜戲。廳堂正北方設(shè)著戲臺(tái),雜藝者便在臺(tái)上表演。戲臺(tái)后方掛著藏青色的帷布,一直延伸到戲臺(tái)兩側(cè)底部過道。表演之時(shí),窗簾緊閉,廳堂正中上方的三盞九華燈燃起,照亮戲臺(tái),帷布、兩側(cè)過道、看官席則相對(duì)陰暗,看官們觀看雜藝表演時(shí),不會(huì)輕易被端茶送水的跑堂小哥打擾分心。與戲曲表演時(shí)后方用作上妝室不同,雜藝表演時(shí)帷布后并無他人,多是用來放置表演用具器械的儲(chǔ)物室,供雜戲藝人在臺(tái)上更換道具;還未表演時(shí),雜戲藝人也有專門的等待席,在廳堂的最后排,吃著茶水點(diǎn)心。
“唉,自從出了那檔子事,爐斧閣有一個(gè)多月沒開演了。”桑青望著空蕩蕩的廳堂,細(xì)長(zhǎng)的雙眼中充盈著淚水。
“桑老爺子算出獄早的,爐斧閣的掌柜、伙夫、跑堂十幾號(hào)人還沒洗脫罪名,仍在刑部大獄里關(guān)著呢。”秋公澤說,“案子一日不破,這買賣怕是一日不能恢復(fù)了。”
“此事還請(qǐng)?zhí)K爺多費(fèi)心,老朽在此謝過了。”桑青朝我拱手便拜,我趕忙將他扶起。
唉,這攤渾水,看來是蹚定了。
“桑閣主,你便將這事發(fā)前后的經(jīng)歷,詳細(xì)說與我聽,我結(jié)合你說的記錄一些東西。”我執(zhí)筆翻開筆記,說道,“但是我不敢打包票,只能盡力了。”
3
聽爐斧閣主桑青說,那天爐斧閣座無虛席,方琦瑜大人帶著兩個(gè)親信坐在離戲臺(tái)三排遠(yuǎn)的地方。
第一個(gè)上臺(tái)的是合一班的鋼索雜藝,三個(gè)力士大漢在一根細(xì)如蠶絲的鋼索上演練醉拳,竟像是踏在平地上一樣。爾后,孫家兄弟的火棍在兩人手中耍得虎虎生風(fēng),像兩條火龍?jiān)谘g扭動(dòng)著身子,迅猛穿梭。身邊那扎著墜馬髻的女侍從,在羅裙上倒上燈油,于火光中穿行避讓,幾次眼看著就要與火龍相觸,身上卻沒起半點(diǎn)火星子,看得人既揪心又贊嘆。
方琦瑜大人的老部下唐元周在開場(chǎng)不到半個(gè)時(shí)辰后與女侍從一同上場(chǎng)。這人年逾三十,身材頎長(zhǎng),留著一把好胡子,平時(shí)不茍言笑,話也不多。那女侍從正值妙齡,身穿一身鮮綠色對(duì)襟衫,已是這一年里唐元周換過的第四個(gè)侍從助演。
作為近年來雜藝界新星,唐元周先展示的是一身軟功。女侍從從帷布后搬上一只兩尺見方的鐵匣子,再綁住唐元周雙臂,唐元周竟將七尺身軀硬生生折疊縮入其中,引得臺(tái)下驚呼連連。
或許為了緩和眾人吃驚的氣氛,唐元周在表演第二個(gè)雜藝時(shí)讓女侍從從帷布后搬出一把黃花梨圓靠背椅,女侍從蹲下藏匿在椅后,椅背寬厚、椅腿粗大,正好將她蹲下的身體隱去。唐元周在椅子上坐下,換了個(gè)人似地翹起蘭花指作扭捏害羞狀,像極了一個(gè)思君的少婦。他一開口說話,原本的低沉男聲忽然變?yōu)闇赝竦呐暋?/p>
原來,那女聲發(fā)自椅后的女侍從,唐元周則在肢體、口型上配合,一個(gè)粗獷的大男人翹蘭花指發(fā)出女人的撒嬌聲,叫人啼笑皆非。
“我這死鬼丈夫唐元周,三天兩頭不著家,卻是在外面養(yǎng)了一窩小房,騙光了銀兩……”
不久,女侍從越說越快,話語(yǔ)越發(fā)刻薄。唐元周趕緊用雙手將嘴唇緊緊捏住,饒是如此,女侍從的抱怨聲仍如連珠炮似地發(fā)出,喋喋不休,唐元周無法忍受,右拳一捶黃花椅椅背“抗議”,女聲才恢復(fù)如初。如此反復(fù)三四遍,女侍從總是先冷靜后爆發(fā)埋怨,當(dāng)然,每遍說的段子都各不相同,總之,都是些故意讓唐元周出丑,逗樂觀眾的戲碼。(注2:即雙簧表演,雙簧定名于清末,類似表演在明朝時(shí)便有出現(xiàn)。)
后來就是眾所周知的了,閣內(nèi)的氣氛經(jīng)唐元周演繹達(dá)到高潮時(shí),隨從卻發(fā)現(xiàn)方琦瑜遇害了,雜藝表演就此終止。
“怎么,那天唐元周并沒有表演妖刀絕技?”我停下筆,詫異地問道,上當(dāng)般望向秋公澤。
“那是他的看家本領(lǐng),平素都是在軟功前表演的。”秋公澤也是耍賴到底,面不改色,意味深長(zhǎng)道,“那天卻偏偏沒有上演,不是有陰謀是什么?”
“秋大人,事情存在變化,臨時(shí)變換表演,一年里總有那么幾次。”桑青解釋道,“二位不會(huì)是在懷疑阿唐吧?唉,那妖刀伎倆只是障眼法罷了,不是什么真功夫。阿唐在戲臺(tái)周圍放置了磁石,再加上些表演成分,觀眾便誤以為飛刀真的會(huì)轉(zhuǎn)彎,這些話,我也早和秋大人、刑部的諸位大人說過了。”
我闔上筆記,瞪了一眼秋公澤:“在戲墨軒惺惺作態(tài),將我騙來,你也是煞費(fèi)苦心。”
“我是不甘心。”秋公澤嘆道,“手法、動(dòng)機(jī)、淵源,這一案完全像是唐元周一手打造的,可是他偏偏又第一個(gè)排除嫌疑,蘇兄,換成你,你能就此作罷?”
“我可沒有一位老丈人關(guān)在牢里。”我說。
“老丈人?”桑青疑惑道。
“兩碼事,兩碼事。”秋公澤連忙說。
“那我可就走了,反正這事于我也無關(guān)緊要。”我笑著說。
秋公澤連忙將我拉到一旁,輕聲道:“蘇兄要是幫我擺平了這事,我和蔣小姐的姻緣里,你永遠(yuǎn)是高過一頭的恩人。”
“你看,實(shí)在點(diǎn)多好。”我笑著說。
“蘇兄已經(jīng)找到問題所在了?”看到我露出笑容,秋公澤興奮道。
“或許有些眉目了。”我說,在秋公澤恭敬的攙扶下回到桑青身旁。
“桑閣主,唐元周以妖刀絕技享譽(yù)京城,況且有貴客方琦瑜大人在場(chǎng),卻反而沒有表演最拿手絕技,我想,這就是解決問題的關(guān)鍵。”
“我不懂蘇爺?shù)囊馑肌鄙G嗾f。
“我們不妨來假設(shè)一下,僅僅是假設(shè)。”我說,“唐元周因?yàn)榱T官事件,對(duì)方琦瑜懷恨在心,他邀請(qǐng)方琦瑜來爐斧閣看戲,實(shí)際上是伺機(jī)圖其性命。為了讓自己置身其外,洗清嫌疑,他苦心設(shè)計(jì),使得方琦瑜殞命之時(shí),自己正在戲臺(tái)上,便有了強(qiáng)有力的脫罪證明。因此,那一日他絕對(duì)不可在臺(tái)上表演妖刀絕技,不然的話,既然飛刀能射出拐彎,毒針何嘗不可?這樣一來,官差便會(huì)認(rèn)為,即使在戲臺(tái)上,他也有辦法用毒針拐彎的戲法,刺殺方琦瑜。”
“蘇爺是說,阿唐將飛刀的伎倆用在了導(dǎo)致方大人死亡的毒針上?”桑青說。
“不錯(cuò)。只需現(xiàn)場(chǎng)搜查一下,我想一定能發(fā)現(xiàn)某些機(jī)關(guān)。”我轉(zhuǎn)身對(duì)秋公澤道,“令毒針拐彎的奧秘,或許就隱藏在那些機(jī)關(guān)里。”
桑青搖搖頭:“既然這樣,那就請(qǐng)便吧。”
秋公澤也是面露難色,舔了舔干裂的嘴唇,說道:“蘇兄,實(shí)際上……”
“案發(fā)后,東廠、順天府的人很快包圍了爐斧閣,在不放任何人出去的情況下,仔仔細(xì)細(xì)地對(duì)現(xiàn)場(chǎng)進(jìn)行查勘,連半塊磁石都沒發(fā)現(xiàn),更不要說什么機(jī)關(guān)了。”秋公澤說,“除非證明,唐元周確實(shí)有會(huì)令毒針拐彎的妖術(shù),要不然,這案子破不了。”
“這……”我說,“確定沒有任何機(jī)關(guān)之類的物件?”
“千真萬確!”秋公澤說。
我目視著筆記上記下的那些支離破碎的線索,陷入沉思。仿佛憑空出現(xiàn)了一堵墻,阻隔了我的前進(jìn)。
線索明明在那一剎那連接上了,然而很快又像空中樓閣般,瞬間倒塌。
“唉,你和我一樣,也是走到了這個(gè)死胡同。”秋公澤緩緩垂下頭,“這案子,看來懸了。”
“不,事情還沒有完。”我用袖子擦去額頭汗珠。現(xiàn)在,我需要做的,是將線索整合,盡可能詳細(xì)地記入《戲墨軒筆記》中。
“給我些時(shí)間,我得回戲墨軒整理筆記。”我說,“然后,我要帶去見一個(gè)人,他一定有辦法。”
“誰?”
“齋冷山莊莊主,左飲寒。”
“那個(gè)料事如神的左莊主?”秋公澤眸子一亮,“這么忙的大人物,他會(huì)出手相助嗎?”
“只能試試了。”我說,“不過,我聽說最近他和夫人方白雪鬧了別扭,搬去了東廂房一個(gè)人住,咱們可要小心應(yīng)付!”
4
左飲寒確實(shí)很忙。
從我和秋公澤進(jìn)門開始,他就忙著和自己下棋,臉上掛著孩子般滿足的笑容。他將筆記擱在雙腿上,不時(shí)翻開看上幾頁(yè),好似漫不經(jīng)心。
因?yàn)橹浪罱那榍芳眩乙膊桓叶嗾f什么,靜靜地坐著看他下棋。
梳著束發(fā),面容白凈的左飲寒只比我小一歲,他像平素那樣身著一件白色斜襟大袖衫,邊緣鑲著深紫色的錦緞,看上去十分儒雅,任誰都不會(huì)猜出他已是年輕一輩里最強(qiáng)的劍客之一。
“左兄,你這樣一心二用,能看進(jìn)去么?”我終于忍不住問道。自己辛辛苦苦寫的東西,被他這樣對(duì)待,是有些不樂意的。
此時(shí),我們正在齋冷山莊東廂院的首閣,莊主左飲寒臥房里。羅漢床擺在東南方,屋子正中放置桌案一副。我和秋公澤已在桌案前坐著喝了半個(gè)時(shí)辰的茶,秋公澤不好開口,只好我來唱黑臉了。
“自然是看不進(jìn)的。”左飲寒微笑道,“只是蘇兄的字,這些日子卻是有長(zhǎng)進(jìn)的。”
“那是一定的,我這半年來也在精心研習(xí)書法,我就發(fā)現(xiàn),這米芾的字啊……”我大談書法,秋公澤重重咳嗽一聲,我才如夢(mèng)方醒,說道,“那個(gè)……關(guān)于我筆記里記載的唐元周的妖刀,你有什么看法?”
“唐元周……”左飲寒沒有看我,用修長(zhǎng)的雙指夾起一粒黑子,思忖過后落在棋盤上,說道,“啊,唐元周啊,他那雜藝可是有趣得很,咱們多久沒一起去看他表演了?”
“大概有三四個(gè)月了吧。”我說,“你每次去都激動(dòng)異常,還要上臺(tái)和藝人攀談比試,我哪還敢和你一起去?”
“哦,原來是這樣。”左飲寒輕撫掌中的黑子,“要是我答應(yīng)你,改了這毛病,你可愿意與我同去?”
“自然是愿意的。”我說。
“既然這樣,咱們就動(dòng)身吧。”左飲寒粲然一笑,從羅漢床上起身,捋了捋長(zhǎng)袖說道。
“啊?”我沒料到左飲寒這么說,呆立在一旁。
“可是左莊主,爐斧閣現(xiàn)今已被查,暫時(shí)是看不到雜藝的。”秋公澤說,“我們正是為了這件事,來煩請(qǐng)你幫忙。”
“唐元周如今在哪?”左飲寒問道。
“從刑部放回去之后,就在家里候著。”秋公澤說,“我也派了人暗中看著呢,他要是逃跑,就證明和這案子脫不了干系,不過他似乎沒有出走的跡象。”
“那正好,請(qǐng)秋大人先行一步,帶人將唐元周與女侍從請(qǐng)到爐斧閣。雜藝的道具該是還在爐斧閣帷布后存著吧?”左飲寒撫掌笑道,“咱們也享受一次包場(chǎng)看戲,感受下排場(chǎng)。”
“左莊主……這不好吧,還是先把妖刀的事解決了。”秋公澤為難道。
“請(qǐng)我相助,卻不施予恩澤,怕不合禮數(shù)吧?”左飲寒眉目微蹙。
“可這調(diào)用犯案現(xiàn)場(chǎng),被上司知道了,怕是要受責(zé)罰的。”秋公澤說。
“秋大人果然是明理慎行之人。”左飲寒說道,一松手,我的筆記已掉落在地,他好似全無察覺,開始專心于棋局之上。
“都什么時(shí)候了,你還顧這些死板規(guī)矩。”我連忙上前拾起筆記,撣去封面灰塵,對(duì)秋公澤說道。
“錦衣衛(wèi)律例重于泰山,我怎么可以違反。”秋公澤十分為難。
“你真正的泰山岳父還關(guān)在牢里。”我提醒。
“要破案子,由當(dāng)事人親自還原那日表演,左莊主所言極是!”秋公澤立刻轉(zhuǎn)了話風(fēng),朝著左飲寒作揖道,“在下先行,稍后請(qǐng)左莊主移步爐斧閣。”
左飲寒笑笑,他放下棋子,望著秋公澤快步離開后,朝廂房門外叫了聲:“武泰,拿我名帖來,備馬車。”
門外應(yīng)了一聲,沒過多久,一個(gè)生著豹眼紅發(fā)、極具異域相貌的青年進(jìn)屋,恭敬地遞上一張方形名帖:
齋冷山莊莊主。
致仕都察院右都御史。
左飲寒。
“走,看戲去。”左飲寒搓搓手,興奮說道。
爐斧閣里的三盞九華燈此時(shí)已被點(diǎn)燃,左飲寒帶著我在廳堂中兜兜轉(zhuǎn)轉(zhuǎn),挑了個(gè)距離戲臺(tái)不遠(yuǎn),視角最佳的位置坐下。桑青站在桌旁,陪在我倆身邊。
才剛坐穩(wěn),左飲寒便笑嘻嘻地從懷中摸出袋口燒酒、兩只小杯,隨后,又將沿路買的紙包醬牛肉與花生攤開放在桌面上。
“來,蘇兄,咱們先干一杯,再看上它一場(chǎng)大戲。”左飲寒替杯子斟上酒,也不等我舉杯,先喝了一口,“這包場(chǎng),還是暢快的。”
“你就別蒙我了,你不是單單來看表演的吧。”我啜了口酒說。
左飲寒沒有反駁,將花生米拋起,穩(wěn)穩(wěn)落入口中。
“總是對(duì)什么事都不上心的樣子,其實(shí),我的筆記你留心看了吧?自己和自己下棋能費(fèi)多大勁,肯定是在思索唐元周妖刀的秘密。”我說,“而要破解這個(gè)秘密,最好的方法,就是看他親自演一次。”
“知我者蘇兄也。”左飲寒笑道,舉杯與我相碰。
我的心這才安定下來。
這時(shí)的我,完全沒有想到,接下來要發(fā)生的事將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飲酒不到一炷香時(shí)間,秋公澤帶著唐元周和他的女侍從走入爐斧閣的廳堂,他們身后,還尾隨兩個(gè)飛魚服的錦衣衛(wèi)。
“左莊主,唐元周帶到。”秋公澤也在我們身旁就坐,可惜杯子只有兩個(gè),他只能分些花生、牛肉。
那唐元周穿著粗布麻衣,絡(luò)腮胡較之前更加茂密,看上去有些憔悴。他身后的女侍從挽著一個(gè)桃心結(jié),身著碧綠色的無領(lǐng)對(duì)襟上衣,粉撲撲的臉蛋甚是可愛。
“草民唐元周,見過各位大人。不知諸位大人有何吩咐。”唐元周拱手作揖,眼神不安地在眾人身上跳動(dòng)。
“唐兄不必拘謹(jǐn)。我和諸位大人是你雜藝戲法的擁躉,不巧的是上月初二那場(chǎng)我們幾個(gè)公務(wù)在身,錯(cuò)過了。”左飲寒沒有起身,微笑道,“也是托秋大人的福,今日恰好湊到一起,勞煩唐兄一展才華,讓我等過個(gè)眼癮。”
“這恐怕不妥吧……”唐元周說,“爐斧閣如今出了事,我怎么好私自獻(xiàn)丑,各位還是等到風(fēng)波過去,重新開業(yè)再來吧。”
“我們既然已經(jīng)坐在這里,官府、桑閣主那邊自然是打過招呼了。”左飲寒說,“唐兄但演無妨。”
“可是……有些雜藝需要提前布置,我也沒準(zhǔn)備啊……”唐元周無奈道。他身邊的女侍從一直沒有說話,只是低著頭。
這倒是實(shí)話,比如他的拿手絕技妖刀,需要在開場(chǎng)前布置下磁石,不然障眼法無法施展。
“上月初二時(shí),我聽說你表演了兩項(xiàng)雜藝,那兩項(xiàng)似乎不需提前布置吧?鐵匣子和椅子,都在帷布后放著呢。”左飲寒抓了把花生米,每吃一粒花生米,便喝上一口酒,“總之,今天不看到你的雜藝,我是不會(huì)走的。”
“阿唐,你就聽諸位大人的吧,別再推脫了。”桑青接過話茬。
“那……好吧。”唐元周用余光瞟了眼身旁的錦衣衛(wèi),說道,“我和蕓兒需要去儲(chǔ)物室準(zhǔn)備一下,請(qǐng)稍等。”
“請(qǐng)便。”左飲寒說。唐元周嘆了口氣,帶著女侍從蕓兒徑直走入戲臺(tái)帷布后,兩個(gè)錦衣衛(wèi)一路尾隨,守在戲臺(tái)旁的兩條過道上。
“喂,你弄錯(cuò)了,初二那天可沒表演妖刀啊。”唐元周剛走,我連忙對(duì)左飲寒說道,“他不演你怎么破解妖刀把戲?”
“蘇兄,我從沒說過要來破解什么妖刀詭計(jì)。”左飲寒鎮(zhèn)定自若道。
“可你剛才不是說……”我磕磕巴巴道,“說什么知我者你也?”
左飲寒努努嘴,邪邪一笑:“蘇兄,你也知道我,最近和白雪姑奶奶鬧了別扭,就不允許我看個(gè)雜藝開開心?”
這……我無言以對(duì),雙肩一聳,面無表情。
“怎么了現(xiàn)在?”秋公澤看出端倪,用手肘捅了我一下,問道。
我哪里知道怎么回事,支支吾吾說不出話來。
“看雜藝吧,難得包場(chǎng)!”我仰頭喝了滿滿一杯酒。
5
身邊的左飲寒的確沉浸在欣賞雜藝的氛圍中,從唐元周和蕓兒出場(chǎng)開始,他便歡呼雀躍,哪里還有一點(diǎn)莊主的樣子。
當(dāng)唐元周用軟功將身子折疊放入鐵匣子里時(shí),左飲寒的雙眼瞪得簡(jiǎn)直像核桃一般,連連驚呼不可思議,弄得我和秋公澤都有些尷尬。
總算捱過了軟功表演,侍從蕓兒從帷布后拖出那把黃花梨圓背大椅,唐元周坐在椅子上,蕓兒則躬身蹲在椅后,蕓兒出聲,唐元周對(duì)口型表演,再次將一個(gè)扭捏的小媳婦形象表現(xiàn)得惟妙惟肖。當(dāng)然,女聲再次喧賓奪主,對(duì)唐元周大吐苦水,即使唐元周捂住嘴口,蕓兒的埋怨聲仍在不斷涌出。
這時(shí)的左飲寒,忽然停下了已拍得緋紅的雙手。
左飲寒收起笑容,搖了搖頭面露不悅:“女人家家的,對(duì)當(dāng)家的怎么能這么多微詞。”
“哈哈,莫不是讓你想起了方白雪姑娘。”我抓住機(jī)會(huì),趁機(jī)報(bào)仇道,“誰不知道你在言語(yǔ)上從沒贏過她。”
左飲寒輕哼了一聲,不理睬我,接著看戲。
戲臺(tái)上女侍從的聲音仍在喋喋不休抱怨,左飲寒皺緊眉頭,騰地站起來,氣沖沖朝前走去。
“不至于吧,這都是演出來的!”我見情況不妙,連忙橫身阻擋,左飲寒輕易甩開我雙臂,快步向前,幾步便踏上了戲臺(tái)。
這家伙,想干什么?我一時(shí)摸不著頭腦。
唐元周也是一臉疑惑,見左飲寒走近,不知何意,翹起的蘭花指還停留在半空。只見左飲寒二話沒說,左拳忽然發(fā)難,向著唐元周前胸攻去。
唐元周也是武官出身,反應(yīng)奇快,變指為掌,雙掌交叉胸前防御。不料左飲寒左拳乃是虛晃,右拳隨后而至,擊在唐元周腹部。
我和秋公澤都是大驚失色。戲臺(tái)兩側(cè)的錦衣衛(wèi)也是長(zhǎng)刀出鞘,警覺地看著左飲寒。
“大人,這是做什么?!”唐元周被打落在地,因?yàn)槌酝矗~間滿是汗水,一手護(hù)住受傷的腹部。蕓兒這時(shí)也從椅子后出來,望著受傷的唐元周,一臉驚恐,上去替他輕揉。
左飲寒這時(shí)卻仿佛清醒,他轉(zhuǎn)身走下戲臺(tái),回到呆若木雞的我與秋公澤身邊。
“唐兄,請(qǐng)繼續(xù)。”左飲寒說,就像是什么都沒有發(fā)生過。
我不禁懷疑自己的雙眼:剛才是出現(xiàn)了幻覺嗎?還好身邊張大嘴的秋公澤提醒了我,一切都是真的。
“這位大人,哪里招待不周啊?”桑青也慌了神。
“你……欺人太甚了。”唐元周掃視周遭,像是尋求我們聲援,“各位大人評(píng)評(píng)理,有這么欺負(fù)人的?”奈何我們還處于懵圈狀態(tài),沒人幫他說一句話。
“我還是想把剛才的雜藝看完。”左飲寒開口道,“等到看完了,我保證,讓你打上一百拳也絕不還手。”
“我這個(gè)樣子,還怎么演?”唐元周捂著腹部,喘著大氣道。
“你傷的是腹部,又不是嗓子,為何不能演?”左飲寒將酒杯置于掌心,聞了聞酒香道,“除非,這里面有什么玄機(jī)不成?”
唐元周擦去側(cè)額沁出的汗水,定了定神說道,“蕓兒,去椅子后面,咱們演完這出。”蕓兒紅著眼,搖了搖搖頭,唐元周雙目一瞪,厲聲道:“我說繼續(xù)!”蕓兒只得再次回到椅子后方。
唐元周閉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氣,然后張開,重新作出少婦模樣,口型已出,但是椅背后的女侍從聲音卻像卡殼的烏龜,久久未出現(xiàn)。
“倒是出聲啊!”唐元周臉漲得通紅,用力捶了捶椅背,女侍從這才磕磕巴巴,斷斷續(xù)續(xù)地發(fā)聲,臺(tái)詞顯得極為生疏,好幾次與唐元周口型不能相配。最重要的是,這次的女聲聽起來清脆上揚(yáng),與之前表演時(shí)溫婉的女聲相差天壤。
“奇了,這聲音不對(duì)啊!”我輕撫耳垂,歪了歪頭。
左飲寒狡黠一笑:“的確和之前的不同,因?yàn)樘圃埽褪欠界な录膬词帧!?/p>
“啊?”桑青、秋公澤和我一同驚嘆道。
我如墜五里霧中:“你這結(jié)論下得未免太快,猝不及防!況且方琦瑜出事的時(shí)候,唐元周演的正是現(xiàn)在這出雜藝,你也看到了,他和女侍從一直就在戲臺(tái)上,他沒有作案的時(shí)間。”
“在戲臺(tái)上,難道就沒法子分身去臺(tái)下刺殺方琦瑜了么。”左飲寒顯得風(fēng)輕云淡。
“好了。”我下結(jié)論道,“我越聽越糊涂了。”
“唐兄是個(gè)聰明人,一個(gè)妖刀詭計(jì),就將大家徹底鎖死在推理的誤區(qū)。”左飲寒望了眼戲臺(tái)上神情凝重的唐元周,修長(zhǎng)的手指像撫琴似地,在桌面輕輕敲擊,“盯著妖刀不放,就會(huì)忽視很多重要的信息。比如,你們以為,剛才的那出雜藝是唐元周和女侍從兩個(gè)人,一人發(fā)聲,另一人對(duì)口型合作而成,事實(shí)上,在上月初二的戲臺(tái)上、在方琦瑜中毒針時(shí),戲臺(tái)上只有唐元周一人。你們以為的女聲,也是他自己發(fā)出的。”
“這怎么可能?男人模仿女聲說話,的確有人能做到以假亂真。”我反駁道,“可是,你剛才也看到了,即使唐元周捏住、捂上嘴巴,女聲還在繼續(xù)。就證明,那些女聲并不是他發(fā)出的。”
“蘇兄,你有沒有聽說過腹語(yǔ)?”左飲寒托著下巴,瞧著我緩緩說道。
“腹語(yǔ)……”我瞇起眼睛回憶,在前朝的某本紀(jì)實(shí)錄里翻到過,“似乎是一種利用腹部發(fā)聲的方法。”
“并不全對(duì)。腹語(yǔ)不是腹部發(fā)聲,卻需要將氣息先進(jìn)入腹腔內(nèi),再由腹腔肌肉調(diào)和,氣息最終向上沖擊嗓子,形成發(fā)音。腹語(yǔ)最大的妙處,就是不張嘴,照樣能說話。”左飲寒說,“而我們這位唐兄,就是一位腹語(yǔ)高手。上月初二表演時(shí),他先是與女侍從一同上臺(tái)表演軟功,造成一種兩個(gè)人同在戲臺(tái)上的錯(cuò)覺,之后所有的女聲,卻是他利用腹語(yǔ)的獨(dú)角戲。表面上女侍從躲入椅后,實(shí)際上她是趁機(jī)鉆入帷布后。”
“女侍從進(jìn)入帷布后,換上準(zhǔn)備好的長(zhǎng)袍,裹住發(fā)髻,偷偷潛入戲臺(tái)最旁側(cè)陰暗過道。看戲時(shí)窗簾緊閉,看官席光線昏暗,加上套著套頭長(zhǎng)袍,自然沒人認(rèn)出她就是剛才臺(tái)上的女侍從。女侍從混入看官席,從方琦瑜身后經(jīng)過時(shí),將毒針刺入了方琦瑜的脖頸后。”左飲寒道。
“然后,再神不知鬼不覺原路返回,當(dāng)什么都沒發(fā)生過。”我喃喃道,視線與戲臺(tái)上的女侍從相觸,她逃避似地偏轉(zhuǎn)頭去。
“蘇兄,大致就像你說的這樣。”左飲寒說,“整個(gè)行兇過程,其實(shí)和妖刀毫無聯(lián)系。”
“所以,剛才你出拳是有意打傷唐元周腹部肌肉。”我如夢(mèng)初醒,“這樣一來,他便無法順利發(fā)出先前的女聲,這才露出馬腳。”
“我一直在找尋上臺(tái)的時(shí)機(jī)。”左飲寒笑著點(diǎn)點(diǎn)頭,“也是挺不容易的。”
“我說嘛,你跟變了個(gè)人似的。”我松了口氣。
“這次的事件,兇手幾乎完成了完美犯罪,沒有留下任何指向性的證據(jù)給我們。”左飲寒說,“于是乎我只能劍走偏鋒,令他露出馬腳。”
“這馬腳露得精彩!”最興奮的還是我身邊的秋公澤,我都不能確定他是否聽懂,然而我話音剛落,他已右手一揮,登上戲臺(tái)的兩位錦衣衛(wèi)心領(lǐng)神會(huì)抽出繡春刀,架在唐元周與蕓兒脖子上。
“勞煩你再跟我們走一趟吧。”秋公澤瞪著唐元周說道。
蕓兒似已放棄抵抗,反而有種解脫般的灑脫,她望向唐元周,目光中似有淚光閃動(dòng)。
“不,各位大人,這事與蕓兒無關(guān)。”唐元周擋在女侍從蕓兒身前,“蕓兒只是按照我說的做,她并不知道針上有劇毒,一切的一切,都只是我與方琦瑜那賊人的私人恩怨。”
“你只是因?yàn)樗麃G了官,他卻因?yàn)槟銌柿嗣!鼻锕珴烧溃澳氵@手段也太黑了點(diǎn)。”
“方琦瑜這賊人,濫殺無辜,欺瞞圣上,雖萬死不足惜。”唐元周罵道,“只是,連累了我的蕓兒,我……”
蕓兒眼中噙滿淚水,上去捂住唐元周的嘴,凄然笑道:“唐爺,事到如今,你又何必替我脫罪。”
“蕓兒,你……”唐元周嘴角沁出血漬,此時(shí)也是老淚縱橫。
“各位大人,五年前,大同的吳縣,方琦瑜那個(gè)賊人謊報(bào)軍功,屠殺了我的家人,玷污了我姐姐的身子。當(dāng)時(shí),我還小,裝死躺在父親的尸體旁,唐爺來檢查,不忍戳穿,這才躲過一劫。我這輩子,早已沒了他念,只想快些長(zhǎng)大,替家人報(bào)仇。三個(gè)月前,我只身進(jìn)京,卻是孤援無助。”蕓兒眼波溫柔,望著唐元周,“天幸再次遇見了唐爺,大仇才得報(bào)。”
“蕓兒,別說了……”唐元周無力地蹲下,整張臉埋入長(zhǎng)滿老繭的手掌里。
“殺意在我,也是我親自動(dòng)手,唐爺只是替我出了些主意罷了。”蕓兒挺直身子,一字一句道,“還請(qǐng)各位大人明察。”
“不不,她是胡謅的,各位大人萬萬不可相信!”唐元周疾呼道。
“怎么辦?”秋公澤一臉愁容,問我道,“到底聽哪邊的?”
我能有什么辦法,只得側(cè)過臉向左飲寒求助。
“啊呀,男女之間這種事情,我也是最頭疼了。”左飲寒苦笑道,按了按額角。
尾聲
五日后。
齋冷山莊東廂房槐樹下。
“蘇兄,又是將軍。”左飲寒在石桌上落下棋子,將我的紅帥徹底將死。
“來來,再殺一局。”我笑著說,重新擺正棋子。
一連輸了五把,今天的我卻沒有泄氣。
“看來今天你心情不錯(cuò)。”左飲寒說。
“有時(shí)候,我是真的佩服你。”我說,“隨便翻翻我的筆記,就能看穿唐元周腹語(yǔ)的把戲。”
“我唯一能確定的是,妖刀絕不存在于世上,排除這點(diǎn)后,再看問題便清晰了許多。不過,說實(shí)在的,我也只是瞎猜罷了,沒有足夠證據(jù),碰上了便是運(yùn)氣。”左飲寒跳馬,笑道:“沒碰上,卻也只當(dāng)去看了場(chǎng)雜藝。”
“不管怎么說,我和秋公澤都得謝謝你。”我挑挑眉毛,“這個(gè)月中爐斧閣新開張,我們定了最好的位置,邀請(qǐng)你一同去,這次,你就是躥上臺(tái),我們也跟著一起!”
“那我就恭敬不如從命了?”左飲寒說。我倆同時(shí)放聲大笑起來。
“對(duì)了,這次的方琦瑜命案,后來三法司怎么判的。”左飲寒目光不離棋桌,忽然問道。
“蕓兒主謀,并且也是行兇人,判了斬立決。”我說,“唐元周雖無殺人,卻知情不報(bào),還參與了策劃,加上劉公公在皇上那邊吹風(fēng),現(xiàn)在已在發(fā)配桂林的路上了。”
“蕓兒的身份被證實(shí)了?”左飲寒問道。
“吳縣被毀,吳縣的人也早已散落在各地,況且那時(shí)蕓兒才十歲上下,身份已然成謎。”我說,“但是,這可是生死攸關(guān)的大事,一個(gè)妙齡大姑娘怎么也不可能說謊求死來保全唐元周吧?”
左飲寒抿起嘴,沉默了半晌。在吃了我一個(gè)車、兩個(gè)炮后,他突然開口道:“蘇兄,這案子恐怕審錯(cuò)了。”
“不會(huì)吧,這可是刑部、大理寺、督察院三司會(huì)審吶。”我說。
“你想想。”左飲寒終于停止下棋,對(duì)我說道,“唐元周是一年半前被貶的官,為生計(jì)糊口,他開始表演雜藝。妖刀也好,軟功也好,卻缺少了一樣同樣精彩的絕技。”
“你說的是……腹語(yǔ)?!”我吸了口涼氣,說道。的確,腹語(yǔ)這種極需天賦的技藝,用來戲臺(tái)表演再合適不過,為什么他從未表演過呢?
一念至此,我“啊”地叫出聲來。
“唐元周想要?dú)⒑Ψ界ぃ缇筒皇且怀幌α耍踔梁芸赡埽谒麆倓傋呱想s藝道路時(shí),便已經(jīng)定下了。”我打了個(gè)寒顫,“所以他絕對(duì)不能在公開場(chǎng)合使用腹語(yǔ),要不然,他上月初二的詭計(jì)便無法實(shí)行。”
“而蕓兒卻說,自己是事發(fā)前三個(gè)月進(jìn)京遇到唐元周,然后策劃的謀殺。”左飲寒說,“她在說謊,在替唐元周頂下罪責(zé),真正起殺意的人,就是唐元周!”
“這……我立刻去找秋公澤!”我站起身來,連忙說道。
“恐怕,來不及了。”左飲寒說,“三法司定下的斬立決,是無法更改的。”
一股絕望之意由心底而生。我雙腿一軟,結(jié)結(jié)實(shí)實(shí)地坐在了石椅上。
這個(gè)唐元周,竟讓人心甘情愿為他而死,究竟是多可怕的人啊……
“這背后,一定有更深的陰謀。”左飲寒起身仰著頭,碧空如洗,一輪金烏斜掛于南山之巔。
“著了唐元周的道,害無辜的人喪命,你倒是悠閑,還有心情下棋!”我說。這才發(fā)現(xiàn)原本要落的棋子,已被我緊緊攥在手心,變得溫?zé)幔踔劣辛俗茻岬腻e(cuò)覺,像是受傷的手握著一枚茱辣。
左飲寒望著天空出了會(huì)兒神,然后微笑著說道:“蘇兄,我們一定會(huì)再次與唐元周會(huì)面的,說不定,蕓兒也會(huì)一同出現(xiàn),我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