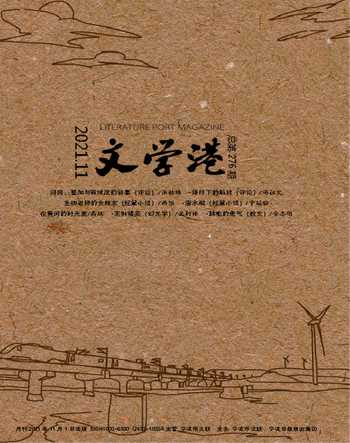來日何曾長(外一題)
陳怡伶
打掃書房時,金色帶碎芒的宣紙從書架滑落,回憶夾帶著微塵撲面而來,有濕熱的東西止不住滑落,爬滿臉龐。
彼時夏天,我不斷寫字,發給秦生點評。他硬撐著回復:“自如一點,下筆別太用力。”等到他說還可以時,視頻里的秦生已形銷骨立,全然不復叱咤商場的風采。來年一月,信息突然發不出去了,我腦子里轟地一下,想起他說的,“如果覺得自己快不行時,會把你拉黑”,我渾身發顫,眼淚止也止不住。說好的去看他還沒成行,人已經不在。為什么要說以后,為什么要等,有些見面,就是永別。
我們總說來日方長,仿佛說了這句話就跟下過見面的定金一樣篤定,我們總說空了就聚,來得及。事實上,生命是一條單行道,你無法預知將來,更無法給重逢下單。
秦生希望我向他許一個諾言,卻從不說要我許什么內容的諾言。他總定時送來一瓶瓶的藥,我看著被外文包裹的罐罐,莫名煩躁,難道叫我承諾吃下這些不見得治好病的烏漆麻黑,怎么想的?他給一瓶我就扔一瓶,包括那些漂洋過海而來的營養品。如此氣盛如此茂盛,年輕驕縱得不知所謂。
春天最后一朵薔薇落在帽檐時,我恍然意識到秦生已經失聯了整整八個月。那個空氣里散發著焦躁的十七點,我突然接到了電話,時間戛然而止。許多年后,每到春末夏初,下雨的傍晚,我腦海里總跳出來這個畫面,反反復復:小賣部門口,帽檐上滿是雨水,我一遍又一遍擦手機上的淚,一遍又一遍語無倫次地說:“我來看你,沒事的,我們來看你好不好……”
秦生去后,我并沒有大哭,只是看到那些瓶罐,看到那些疊得齊齊的大字,腹部就會劇烈抽搐。
也許凡人皆如此,我們總習慣忽視擁有的東西,然后把喜歡的東西寄存到以后,總有一天。以后我要去買那條玲瓏的裙,以后要去那座雍容的城,總有一天要去見那個海邊的人。而事實往往是,年復一年,等到兩鬢添白,變故突來,我們也沒能穿上那條第一眼相中的裙子,去到心目中的城市,和那個他/她圍爐言歡。我們總是錯過,習慣錯過,并一再暗示自己,來日方長,歲月且長著呢。
記得有一次,秦生站在鏡子前看我試耳環,說如果你的毛病治好了,你會做什么?我不假思索:“當然是大吃一頓了,把全世界所有能吃不能吃的吃一遍。”我笑得肆意明媚,窗外的花兒都忍不住為我曳動。秦生的菱形袖扣在日光照耀下泛著暗啞的光澤,剪裁合體的西裝將他精壯的身軀襯得意氣風發。而我仍舊孔雀般驕矜,三色堇滾金邊裙擺順著高腳椅垂散到地毯,并不憚以最調皮的一面呈現在他面前。現在回想起那個場景,覺得世事多諷,明明體弱多病的是我,明明生龍活虎的是他,也明明,沒有那么多如果。
后來我再也不提以后,不想說明年要干嘛、五年后會如何;面試官問我的人生打算是什么,五年內有無工作計劃,我一個字也不想說。腦子里跳出秦生問我的話:等你身體好了,要答應我一個承諾。一個承諾。秦生,睿智如你,到生命最后一刻,有沒有后悔過,有些話,要早說,有些事,不能拖呵。面試官點評我缺乏遠見,我心里平靜如水。來日若朝露,且莫談高遠。我輾轉多個城市,去看更多自己。我在典雅的禮堂領著大家走步,戴著白手套撫觸最精細的瓷杯;我給英國人翻譯黿頭渚的前世今生,捧著實驗數據穿梭在各大廠房;也戴著眼鏡教過愛翻墻的大孩子,也做過最隨心所欲的撰稿人。我想吃就吃點,重了許多斤,想買就盡力去買,把自己打扮成舒服的模樣;我還告訴學生,不要等待,有喜歡的愛好就堅持,有心儀的女孩就用心追,有舍不得用的寶貝一定現在就用,甚至一簇原野上的花,一汪遠山里的水,如果真的喜歡,就馬上去看。一定不要等到不確定的以后,某一天。因為只要活著,就是最特別的一天,就是最值得的一日。
書桌上溫柔地鋪滿陽光,幾枝蠟梅從白瓶里探出,錯落柔曼。多年后的冬日正午,手腕纖細的人在金底碎花的宣紙上寫字。最后一捺收筆時,我恍然明白了秦生沒來得及讓我許下的諾言。他是要我,“好好的,健健康康。”
我會的,秦生。我扶著書桌,沒有淚,而腹部,開始痙攣。
至親至近至味
四月里回老家,經過長長的瀆邊公路,兩旁花樹盛開,濕地公園上鷂子高飛。那些迎面而來令人心中暢樂的,除了穿過碎金般日光迎風飛舞的柳條,橫塘河邊一千八百多歲的巍巍銀杏,紅了櫻桃綠了芭蕉的蔣捷執教過的書院,還有最難忘的人生至味,鹵味。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船是橋頭過,水從門前來”的家鄉迎來了改革開放的春風,市場經濟如雨后春筍般生根發芽,除了落實分田到戶的激勵政策,鄉政府大力鼓勵個體經營。天時地利俱備,素有巧手娘子之稱的母親開始下海開鹵店。每天凌晨,母親就起身在灶頭忙碌;天蒙蒙亮,母親就把沉重的菜麻袋綁在腳踏車后座運往橋頭(鎮中心的俗稱)。到了買賣人集合的長春橋下,嗓音清脆的母親就推著熱氣騰騰的玻璃櫥車兜售鹵菜。初冬的寒風里,母親的湖藍格子兩用衫鼓鼓地飏起,圍巾上方露出一小片通紅的面頰,像逆風而行的女戰士。當時的鄉親們注重果腹,對于兩位數一斤的新食物并不特別感興趣。而母親堅持用最新鮮的牛腱子肉和不斷改良的烹飪手法來提升食材的鮮美,并不介意一時失利。直到有一天,母親帶回來一小塊牛肉。昏黃的灶臺前,這塊拳頭大小的醬肉散發著誘人的赭色光澤,一口下去,我忍不住低呼:“好香啊!”它的噴香鮮嫩讓我遲遲不舍得咬下第二口,以至于長大后在別處吃牛肉時,無論多么好吃,總覺得少了點什么,腦子里總想起三十多年前暖暖偎在灶頭前享用的那一小塊美味。
母親邁出了成功的第一步。開業第七天,一百多斤鹵味售罄。半年后,老街長春橋下多了一家群英鹵菜店,店里只放得下一爿櫥窗一個灶臺,外加一張家里帶過來的原色方桌兩張凳。那一年,是1987年。
三年級時我們舉家遷到了鎮上,放學后我第一件事是做作業,第二就是幫著母親拆豬骨頭。店里的豬頭肉是母親起早去攤位上整爿整爿買回來的。洗凈、剁開、腌制是第一道工序;然后烹至半熟并褪毛,重新加料燒煮;時辰一到,立刻出鍋剔骨。這樣鹵煮出來的豬頭肉肉質細嫩,肥而不膩,特別適合當下酒菜,隨你白切或者蘸著醬醋蔥等調制的佐料吃,一口咬下去,肉仿佛化了,那叫一個香。作為剝皮剔骨的犒賞,除了小人書,每次的豬骨頭都歸本姑娘所食,我邊呼呼地吹著熱氣邊津津有味地啃大骨頭邊肉,渾身毛細孔都充溢著饜足。
考究新鮮的菜肴,整潔衛生的環境,使得回頭客劇增。母親有感于大家信賴,除了價格公道,還常多送雞爪鴨翅,一傳十十傳百,小店生意蒸蒸日上,漸成鹵菜招牌。慢慢地,一些嬸娘也跟隨母親步伐踏上了個體經營之路,有抱負的年輕男人則開始走南闖北尋求發展。隨著做樁機生意的創業者功成名就,小鎮第一批老板開始崛起。而父親也終憑勇氣和膽識,工程遍布大江南北,做得風生水起。在我們搬進鎮上首期商品房后,母親成了拎著小包的陳太,梧桐樹旁那棟美麗的大房子,承載了我兒時最甜蜜的回憶。周末午后,鳥雀聲聲,風拂過頭頂,木槿花瓣飄墜如雪,日光從蓊郁的枝葉縫隙漏下來,劃出輕煙斜線,落在鋪滿花瓣的通往電影院的林陰道上,留下各種形狀的斑紋。我歌聲婉轉如乳燕鶯啼,一手挽著溫婉美麗的母親,一手拉著意氣風發的父親,溜冰鞋在斜斜的拱橋上彈起歡快的音符。那一年,是1992年。
俗話說,花無百日紅。就在我徜徉于每天一本連環畫時,老天爺扔了個晴天霹靂。1993年末,父親的生意陡然失利,在他從武漢回來前,從沒想過一無所有四個字會出現在我的人生字典里,更沒想過尚未滿月的弟弟要跟著我們顛沛流離居無定所。母親仍舊平靜自持,推著嬰兒車在菜場門口賣冰棍的她,瘦削如風中紙片。我打定主意多分擔一點,哪怕幫著洗幾件衣服炒一個青菜。十四歲那年初秋,我和弟弟吃到了家道中落以來的第一罐八寶粥,我給弟弟舀第一勺,弟弟一邊給我吹手指一邊眼睛亮亮地說,姐先吃,姐吃力。我抱住穿著“撿落舊”衣服的小弟,笑了。
1996年夏,在鄉政府的扶持和親人的幫助下,母親在小街岔路口又租賃了個30多平米的門面。餐館靠窗一面開滿迎風搖曳的綠蘿,桌上鋪了米色格子餐布,上擺紫色的木槿花束。有母親的手藝,有清雅的布置,生意很快又火了起來。秋日午后,微風徐徐,街坊四鄰就湊在小店吃茶,些許花生、一盤棋,天南地北,自舒心。當時的正菜也是豐盛,除了牛羊雞鴨等招牌鹵菜,還經營各式炒菜、面食、點心,也有客人指定菜肴由母親烹制,說自家做不出此等美味。每逢年節時,櫥窗口挨挨擠擠掄著手臂搶菜的鄉親們,店內頭碰頭大快朵頤的老主顧們,成了鎮上一道獨特的風景。
漫長的奮斗生涯中,母親從不喊累,她用言行給我們上了人生第一課,堅韌。此后的許多年,當苦難如黃沙迎面劈來時,一想到母親用孱弱的左手扶著右手,舉起沉重的鐵鍋炒菜的樣子,想到母親早三點起身晚十點打烊不管多難都義無反顧的模樣,我都會咬緊牙關爬起來,不為別的,只因為我是母親的女兒。母親永不氣餒的拼搏勁也感染了身邊人,大起大落后的父親最終以勇氣和毅力力挽狂瀾,迎來勝利的曙光;他和母親夫妻同心,將小店打造成了遠近聞名的特色飯店,也讓我和小弟明白,人生在世,堅守本心勇擔責任,有所為有所不為最是要緊。五年級暑期,父親送了我一本字帖,扉頁上書六個字——有志者,事竟成。盡管我始終沒有寫出鋒如蘭竹的瘦金體,但每當執筆,腦子里總會浮現父親手把手教我練字的畫面。歲月是匆匆行進的列車,要么成為流逝的風景,要么去做看風景的人,而我們,終將一步步向前。
待得邁進大學門檻,家中已是云開月明。熟食店、飯館,都經營得有聲有色。在母親影響下,鎮上飲食店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從十余年前的三家小店,到現在的上百家飯館,越來越多的鄉親加入餐飲行業。古鎮人的厚道是千年傳承下來的品質,是骨子里透出來的由己及人,門挨門開店的從不傷和氣,誠信經營、貨真價實始終是周鐵人的經商之道。
2003年,鎮上菜場重整改造,煥然一新。門楣上LED顯示屏滾動播放最新的招聘信息及時令菜品,菜場內布置溫馨,地面光潔,點綴四周白墻的是古鎮名家字畫。往里走是左右兩排果蔬攤,南面是排列整齊的兩大爿熟食店。為了保證公信力,市場管理處采取抽簽制分配店面,那一年,我家抽到了倒數第二,但這并不影響客人們的熱情,相反有種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感覺。有滬上朋友早兩個月預定菜肴,只為了大年夜吃到一口陳氏醬牛肉。寒假回來,我常往返店面和飯館幫忙,中午得空就牽著弟弟在菜場找漂亮春聯。逛了一圈回去時,四只手里春聯不見得有,但鐵定不落空,甜甜的草莓、可口的甘蔗還有噴香的烤紅薯,都是自產自銷的阿姆們送的。應著水土肥沃,瀆上建了很多生態大棚,這些蔬果是新鮮采摘下來的呢。
2004年,我們搬進了解放路上的新小區。提著喜秤進門時,母親兩鬢的微白在薄霧籠罩下泛著溫柔的光澤,我突然想起她早些年常說的那句話:“瓦片也有翻身日。”我把一束木槿插進家中白瓷瓶里,紫色的薄如蟬翼的花瓣歪著腦袋看著我,朝我微笑,此刻,我的母親,不也正像是打贏翻身仗的披了晨輝薄紗的木槿么。
艱難是幸福的底色,歷史是發展的車輪。因為有了千百個如母親般吃苦耐勞誠實守信的人兒,依山傍水的家鄉周鐵,正在新時代號召下煥發出別樣風采。應有盡有的大夢想城商業區近在咫尺,巍峨壯觀的岳飛文化園二期即將竣工,宜馬快速通道即將完工……假日回去,玩得不亦樂乎的小胖墩從噴泉過道里奔來:“媽媽,大拈花灣什么時候開啊?”
“快咧,到辰光帶上你小伙伴一起去白相好伐?”
“那我要在里面開一個店,專門賣吃的。”兒子腳步朝我,頭卻向著屺亭(家鄉鄰鎮)人新開的黃牛肉鋪子,我不禁莞爾。工作在外十余年,我早已從鄉音不改慢慢隱退到將普通話作為交流的基本語言,但一看到菜場里翠綠深紅的各色菜肴蔬果,看到浸潤著家鄉風味的鹵菜熟食,就會停住腳步,用內行的眼光打量一下。而這些,又似家規傳承般影響到了孩子。
我在竺西文化廣場上慢慢徘徊,花木蔚然中掩映其間的是一塊塊從兩千七百年歷史長河里脫穎而出的鐫刻了文才武將的石碑。漫長的時間壓縮在一起,將洋洋灑灑說不完道不盡的歷史故事濃縮在方寸間。質潔而亮,光耀千古。我想,我們對家鄉的感情,可以具體到半面墻垣,一種記憶中的味道。同時也可以衍生為一縷生生不息的煙火氣,一座錫宜一體化發展的“橋頭堡”。今天的家鄉周鐵毋庸置疑已經拉開了存故鼎新的序幕,各行各業會以交融發展的更多模式運營推進。但無論走多遠,那些伴隨著酸甜苦辣和溫情洋溢的奮斗的日子,那些有著家鄉人情味和純樸美食的味道,都如云如水,水流云在,是我們奔向共同富裕的原動力,也是家鄉成為湖韻特色小鎮的向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