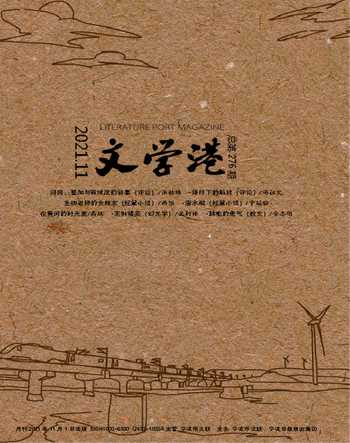水潤(rùn)江南映鄉(xiāng)戀
趙暢
每每想到江南,我總會(huì)想到古人吟詠江南的詩(shī)句,并信手拈來(lái):“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lái)江水綠如藍(lán)。”“一葉舟輕,雙槳鴻驚。水天清、影湛波平。”“猶有桃花流水上,無(wú)辭竹葉醉尊前。”“澄明遠(yuǎn)水生光,重疊暮山聳翠。”……是啊,詩(shī)人們的詩(shī)句,每一首甚至每一句似乎都與江南的水有關(guān)。為此,我常常自問(wèn):江南莫不是水做的?
江南當(dāng)然是水做的,水做的江南總是舞動(dòng)輕盈的水袖,把萬(wàn)千柔情蜜意織進(jìn)綿密的流水,于是,江南也就出落得格外楚楚動(dòng)人、亭亭玉立了。作為江南中人,我自然發(fā)現(xiàn)并見(jiàn)證了這一不爭(zhēng)的事實(shí):正是江南的水滋養(yǎng)了故鄉(xiāng)的土地,滋養(yǎng)了故鄉(xiāng)的人,也滋養(yǎng)了故鄉(xiāng)的事——從古至今,從未歇息。
“舜井”的念想
江南多雨,風(fēng)輕雨斜、云蒸霧罩,千絲萬(wàn)縷、交織纏繞。雨水順著溝溝壑壑的山澗流淌,沿著長(zhǎng)滿青苔的屋檐滴下,流淌過(guò)千百年的時(shí)光,滴穿了千百年的思念,訴說(shuō)著千百年的滄桑。大地上的每一口井,就恍如時(shí)光的眼睛、思念的鏡子、滄桑的倒影,總是有打不完、撈不盡的感人故事。
不知有多少次從“舜井”邊走過(guò),每一次,我都會(huì)不由自主地放慢腳步。不為別的,只因?yàn)檫@口井與舜帝有關(guān)。
“舜井”,位于紹興市上虞城區(qū)一座曰“龍山”的山麓。這里是一片青翠的叢林,沿著石階而下,便可一睹“舜井”的芳容了。“舜井”的記載,最早見(jiàn)于酈道元的《水經(jīng)注》,而《水經(jīng)注》引《晉太康三年地紀(jì)》云:“舜避丹朱于此,故以名縣。百官?gòu)闹士h北有百官橋。”又云:“舜與諸侯會(huì)事訖,因相虞(“虞”通“娛”)樂(lè),故曰上虞。”另《史記·五帝本紀(jì)》引《會(huì)稽舊記》云:“舜上虞人。去上虞三十里有姚丘,即舜所生也。”姚丘就是現(xiàn)在上虞的上浦虹養(yǎng)村。
除了典籍的記載,百官、舜江、“舜井”等等,如此眾多的地名和古跡,終讓上虞人自豪地相信,舜帝不是遠(yuǎn)古的傳說(shuō),而是真真切切的鄉(xiāng)鄰。“舜井”,原本坐落在城區(qū)一個(gè)糧管所的老房子里,后來(lái)因城市拆遷,為保留這一古跡,人們依循泉脈而將其移建在了位于上虞賓館的龍山山麓。時(shí)至今日,這口“舜井”是否為舜親自開(kāi)鑿,似乎難有定論。就如我去山東濟(jì)南獲頒“第六屆冰心散文獎(jiǎng)”,下榻歷下區(qū),聽(tīng)說(shuō)那里也是舜的出生地,同樣有舜井等古跡一樣,在我看來(lái),不論是或不是,其實(sh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口井以“舜”命名,當(dāng)是后來(lái)的上虞人出乎一種長(zhǎng)久的紀(jì)念而為之。
想起當(dāng)年“舜避丹朱于此”之時(shí),便教民馴服野獸,到漁捕湖(今上虞境內(nèi)、緊挨春暉中學(xué)的白馬湖)捕魚(yú)傳藝,推廣種櫟養(yǎng)蠶的經(jīng)驗(yàn),授民制陶術(shù)而使上虞成為中國(guó)陶器最早的發(fā)源地。更兼“舜為人子,克諧以孝,故其俗至今蒸蒸是效;舜為人臣,克盡其道,故其俗至今孳孳是蹈;舜為人兄,怨怒不藏,故其俗愛(ài)而能容;舜為人君,以天下禪,故其俗至今廉而能遜。”因之,《史記》贊曰:“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面對(duì)這樣一位人們心目中的“仁君”“圣君”,后人怎能不深情緬懷?其功其德,不就如這“舜井”之水,恩澤浩蕩、澤被后世的嗎?“舜井”之名,這實(shí)在是百姓對(duì)舜帝的最佳口碑和出乎內(nèi)心的頒獎(jiǎng)辭,它比碑銘上鐫刻的忠孝節(jié)烈更有價(jià)值,比殿宇里涵納的社稷理想更有意義。
也許,在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不斷發(fā)展的今天,人們生活水準(zhǔn)越來(lái)越“小資”,水井的概念早已在大家的記憶中逐漸模糊被淡忘了。然而,這口“舜井”卻依然一直陪伴著人們。就這樣,年復(fù)一年,它與我們一起領(lǐng)受“寄蜉蝣于天地,渺滄海之一粟”的況味。
如同其他的老井一樣,畢竟過(guò)了綿綿光陰、漫漫長(zhǎng)年,那斑駁的井欄,那綿厚的苔蘚,以及汩汩長(zhǎng)流的清冽,分明昭示著“舜井”就是一位時(shí)空老人、一件活著的文物。“舜井”很象形地讓人們的家園圍坐在它的膝下,讓它端坐在一個(gè)城市的一隅,讓城里的一切活物,悠揚(yáng)舒暢地滋生歲月的經(jīng)緯,漸次地編織進(jìn)生命的脈絡(luò),滋潤(rùn)綿延不絕的歌喉和聲聲不絕的祈禱。
這口疊印歲月的蒼茫和醇厚的“舜井”,也有人譽(yù)之為“神井”。原來(lái),旱時(shí),它絕不干涸;澇時(shí),它也絕不溢出。數(shù)九天東西吊里不凍,三伏日放東西不爛。“不思波濤涌似山,胸中浩蕩渺無(wú)邊。收來(lái)萬(wàn)壑清泉水,滋養(yǎng)蒼生代代甜。”清人李碧清的詠古井詩(shī),只是道出了一般水井的特點(diǎn),似乎遠(yuǎn)未能道出“舜井”之神韻所在。是啊,“舜井”的神髓,源于龍山。背靠龍山,故其吞吐自如;因襲舜恩,故其福瑞廣隆。于是想及,凡是來(lái)到“舜井”汲水的人,絕不僅僅是為了打一桶井水。是啊,站在“舜井”邊,情不自禁地彎下腰,輕輕地垂下小木桶,猶如伸向悠悠歲月深處,伸向遙遙歷史深處;恍如從舜帝手里捧過(guò)一掬神水,接過(guò)一柄掘井神具。從“舜井”里汲水,又像探索人生點(diǎn)點(diǎn)滴滴的秘密,一點(diǎn)點(diǎn)打撈出來(lái),沿著胃腸的腔隙澆鑄,生命的精奧便不假思索地從歲月的深處抖露出來(lái)。此時(shí)此刻,水成了對(duì)人心靈的獻(xiàn)詞,與歲月長(zhǎng)河中讀懂它的人傾訴心語(yǔ)。這般滄桑迭代的氛圍,能不讓人產(chǎn)生一種崇敬之意、憑吊之心?
“舜井”,或許不是最早的水井,且少有精致的構(gòu)造和設(shè)施。先秦的《擊壤歌》里有“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的句子,這是水井出現(xiàn)于中原之地的最早記載,而上虞毗鄰的余姚河姆渡文化遺址中的水井遺址,則更讓水井的歷史提前到了5700多年前。但在我看來(lái),沒(méi)有哪一口井能像“舜井”這般執(zhí)著,至今依然鮮活流淌,如一盈大地的乳房、一脈生命的乳汁。是的,“舜井”在那里默默地迎候著每一個(gè)前來(lái)汲水的人。它是一位慈祥的長(zhǎng)者、一位德高望重的祖先,它更是一個(gè)城里的鄰居、一個(gè)家庭的成員。斗轉(zhuǎn)星移、歲月更迭,不論發(fā)生什么事情,“舜井”都不會(huì)消失在我們的視野,更不會(huì)消失在我們的生活中,因?yàn)椤八淳薄罢{(diào)和過(guò)青瓷的泥土,澆灌過(guò)華滋的草木,浸染過(guò)錦繡山川”,它依然活著。著名電視人劉郎說(shuō)得好:“這‘舜井’的水里,有著在殿堂里看不到的平凡之意、平民之情和平易之心。碑文可以剝落,彩繪可以凋零,然而,這股從未枯竭的井水,四季琤琮,卻會(huì)一直流淌下去……”
我總以為,一個(gè)城市是很需要一些原始狀態(tài)的晶瑩露珠般的本然情趣,成為現(xiàn)代快速生活情緒上一種很恰當(dāng)?shù)难a(bǔ)償,“舜井”即是。“舜井”之地,委實(shí)疏曠、清幽。平日里,若沒(méi)有風(fēng)聲雨聲?shū)B(niǎo)叫聲,這里便是一處?kù)o謐又安詳之地。有一次,我去“舜井”汲水。剛要離開(kāi),突然,一只不知名的飛鳥(niǎo)竟棲落在了井欄上,并不時(shí)發(fā)出悅耳的鳴叫。或許,它就是承載著舜帝夢(mèng)想的神鳥(niǎo),或許它要告訴我們:每個(gè)人都該有一口真實(shí)的水井。從自己生命山麓挖掘儲(chǔ)藏著的與生俱來(lái)的清澈的水,不用木桶提取——它像虞舜大地深處的水,直接滋養(yǎng)我們的身體,也滋養(yǎng)我們的靈魂。
“覆卮”讀“石河”
我喜歡江南的雨,是因?yàn)樗虧?rùn)萬(wàn)物,點(diǎn)點(diǎn)滴滴,沒(méi)完沒(méi)了,就像少女的情。是的,江南的雨水一旦跌落在江南的大地上,不管是在平地還是在高山,它總是留戀最初收納它的山川大地,甚至久久不愿離去,并牢牢扎根在那里又盡情彰顯其流芳千年的魅力,就如地處浙江省上虞、嵊州、余姚三市交界地帶上虞境內(nèi)的覆卮山。
覆卮山,主峰海拔高度達(dá)861.3米,為上虞區(qū)內(nèi)的最高峰。相傳南朝大詩(shī)人謝靈運(yùn)回鄉(xiāng)后,隱居在附近的姜山下,每每晨起開(kāi)門(mén)即見(jiàn)此山。心儀已久之后有一天,他攀游至山頂,“飲酒賦詩(shī)畢,覆卮(酒杯)于其上,山因而得名”(舊《上虞縣志》)。南宋王十朋有詩(shī)云:“四海澄清氣朗時(shí),青云頂上采靈芝。登高須記山高處,醉得崖頂覆一卮。”如此一說(shuō),這覆卮山終因大詩(shī)人謝靈運(yùn)的曾經(jīng)光臨而愈發(fā)顯得神奇。
然而,神奇非止于此,覆卮山給人們留下另一道神奇之光的,則是12條巨石陣匯成的石冰川群,呈扇形從山頂一直奔瀉到山麓。遠(yuǎn)遠(yuǎn)望去,恍若群龍起舞。其中,最大的一條石冰川長(zhǎng)近1000米,最寬處約50米。前些年,我國(guó)冰川研究專(zhuān)家韓同林,深入覆卮山考察,發(fā)現(xiàn)了大量U形谷、冰斗、冰川漂礫、冰磧礫石和冰蝕洼地等冰川形態(tài),并結(jié)合分布在當(dāng)?shù)氐谋姸嘈稳缡拥谋屎蟠_認(rèn),上虞覆卮山“石河”地貌,系第四紀(jì)冰川時(shí)期由冰川侵蝕和堆積作用形成的古冰川遺跡,距今約200萬(wàn)至300萬(wàn)年。
懂得一點(diǎn)氣候?qū)W知識(shí)的人都知道,地球自誕生后,氣候也一直在變遷中。在震旦紀(jì)以前,亦即大約在六億年以前,我們并不清楚地球上的氣候。從六億年前古生代震旦紀(jì)起一直到一萬(wàn)年前新生代的第四紀(jì)止,地球上的氣候共經(jīng)歷了三次大冰川氣候,其中第三次是新生代第四紀(jì)冰川期。在第四紀(jì)大冰川期氣候中,目前我們已經(jīng)確知其間氣候仍是寒冷與溫暖交替出現(xiàn)。第四紀(jì)冰川,是地球史上最近一次大冰川期。冰川的發(fā)生是極地或高山地區(qū)沿地面運(yùn)動(dòng)的巨大冰體。由降落在雪線以上的大量積雪,在重力和巨大壓力下形成,冰川從源頭處得到大量的冰補(bǔ)給,而這些冰融化得很慢,冰川本身就發(fā)育得又寬又深,往下流到高溫處,冰補(bǔ)給少了,冰川也愈來(lái)愈小,直到冰的融化量和上游的補(bǔ)給量互相抵消。
生物進(jìn)化論同時(shí)告訴我們,經(jīng)過(guò)了幾個(gè)冰川世紀(jì),地球上生物微生物的發(fā)展都日趨成熟。到第四紀(jì),地球上主要的地勢(shì)地貌都顯現(xiàn)出來(lái),生物活動(dòng)更加頻繁。這個(gè)時(shí)期,也正是人類(lèi)出現(xiàn)、文明形成的關(guān)鍵時(shí)期。由于冰期使得歐洲、亞洲大部分地區(qū)處于嚴(yán)寒,而熱帶地區(qū)又比現(xiàn)在干旱,森林大面積退化為草原, 這就使得人類(lèi)的祖先——樹(shù)棲的猿類(lèi),不得不下地生活,從而邁出了從猿到人的關(guān)鍵一步——直立行走。一旦知曉第四紀(jì)冰川與文明之間這般密切的關(guān)聯(lián),我們自然對(duì)第四紀(jì)冰川投以敬畏的目光,而對(duì)覆卮山則油然而生朝圣之心。
覆卮山冰川遺跡的發(fā)現(xiàn),或許是偶然中的必然。這種偶然到必然的跨越,我們不應(yīng)該忘記一位叫杜又常的地理愛(ài)好者。自他發(fā)現(xiàn)這“石河”并奔走呼吁到最終被證實(shí),這“猜想”橫亙?cè)谒男拈g已經(jīng)有29年。29年,他在尋找答案的過(guò)程中,有過(guò)挫折、有過(guò)懷疑,而當(dāng)一萬(wàn)多個(gè)日日夜夜的疑惑一朝得解,他竟如孩子般地笑了。
揭開(kāi)神秘的面紗,覆卮山“石河”便迎來(lái)了絡(luò)繹不絕的訪客,而我自是其中的一位。仲秋的一天,我驅(qū)車(chē)來(lái)到位于覆卮山山麓的東澄村,但見(jiàn)石墻黛瓦,古樟參天,尤是那條條鵝卵石鋪就的小石徑,一下就把我的情思帶到了“石河”。“喏,‘石河’就在上面!”一村民用手向不遠(yuǎn)處一指,便讓我一眼看到了“石河”。大自然的偉力何等壯觀!其以大山為紙,以冰川為筆,終讓這條條“石河”成了地球上永恒不變的畫(huà)圖,破解地球氣候變化的初始密碼。
不知何故,凡有“石河”處,多為荒蕪之地,恍如盤(pán)古剛完成開(kāi)天辟地。尋思著,尋思著,突然醒悟過(guò)來(lái)——我覺(jué)得山的其他地方的確應(yīng)該是蔥蘢蓊郁,而唯獨(dú)這一帶應(yīng)該是裸露的、骨感的、剛健的,因?yàn)橹挥羞@樣,它才讓人放心——撐起我們頭頂上這片藍(lán)天的覆卮山,難道不應(yīng)該是一身雄風(fēng)、力挺萬(wàn)鈞的樣子嗎?否則,讓青青翠翠之地來(lái)承載這曾經(jīng)的歷史變遷,是不是太秀氣、太柔弱了呢?是的,我自以為這“石河”是突出大地肌膚的骨頭,其像一道道漫長(zhǎng)的脊梁,它是物質(zhì)的,同時(shí)也是精神的,它足以讓人產(chǎn)生深刻的崇拜感。北朝人說(shuō)過(guò):“縑竹易銷(xiāo),金石難滅,托以高山,永留不絕。”人生短暫,自使人更加倚重巨大之物。而當(dāng)“石河”突兀在面前時(shí),我怎能不將自己之所見(jiàn)所想寄寓于“石河”呢?“石河”風(fēng)骨堅(jiān)硬,當(dāng)擔(dān)得起崇高的分量。
喘息于覆卮山的威儀之下,潛行于這片古老的土地和神奇的曠野,我剎地覺(jué)得,人類(lèi)只有置身于這樣的空曠山野,完全成為自然的陪襯、自然的點(diǎn)綴時(shí),才能真正感受到自然的恢宏、時(shí)光的深邃以及個(gè)體生命的渺小和短暫。此時(shí)此刻,我欣然吟出一位詩(shī)人的詩(shī)句:“山上也有河么,從遠(yuǎn)古的荒涼里奔騰而來(lái),被冰川召集在這里,凍結(jié)成歲月的圖騰。河化為石,三百萬(wàn)年夠否,第四紀(jì)冰川撤退進(jìn)課本,作業(yè)卻布置在了覆卮山的山溝。”是啊,“石河”守著一個(gè)數(shù)百萬(wàn)年不變的承諾,等待著每一個(gè)游人與之作親密的互動(dòng)。繞開(kāi)平日多為游人行走的山徑,我徑自攀“石河”而上。走近“石河”,發(fā)覺(jué)“石河”之石為火山巖質(zhì),灰黑色,粗糙如樹(shù)皮。這似屋、如床、像桌的石頭,層層疊疊,默然無(wú)語(yǔ)。當(dāng)?shù)氐拇迕瘢唬骸笆勁铩!泵鎸?duì)這片“石河”,無(wú)異于展讀一部再現(xiàn)我們這個(gè)地球波驚浪詭的史詩(shī),叩問(wèn)300萬(wàn)年前奇特、神秘的歲月。它使人記住了英國(guó)詩(shī)人布萊克的名詩(shī):“一顆沙里看出一個(gè)世界,一朵野花里現(xiàn)出一個(gè)天堂。把無(wú)限放在你手掌上,永恒在一剎那里收藏。”撫摸這些石頭,當(dāng)你讓心和它貼近、相擁時(shí),你才覺(jué)得仿佛沉在遠(yuǎn)古的聲音又活了起來(lái),才覺(jué)得這里曾經(jīng)有多少驚天動(dòng)地、驚心動(dòng)魄的場(chǎng)面。這里的每一塊石頭,都凝結(jié)著山崩的黃昏和地裂的月華。
是啊,我想象,第四紀(jì)冰川在覆卮山的分娩是漫長(zhǎng)的,但量變必有質(zhì)變的那一天。我相信,在生就質(zhì)變的那些時(shí)日里,那一浪浪的石頭牙齒,銳利地撕咬著厚厚的冰川;冰面上明亮亮地浮著一層熱氣,經(jīng)了陽(yáng)光的筆墨,像一朵朵紫煙,裊裊然在那里開(kāi)合聚散……那碎裂的冰川,或巨碩,或玲瓏,你擠我,我推你,你包我,我裹你,滿坡碰撞著,交疊著,響亮著,順勢(shì)滾滾而下。如果能用電影膠片表現(xiàn),在快鏡頭里,那狀態(tài)那聲音,定如千百萬(wàn)鐵騎從遠(yuǎn)處奔馳出來(lái),怒吼長(zhǎng)嘯,風(fēng)卷殘?jiān)疲案昂罄^,排山倒海。那種義無(wú)反顧前行的身軀和回聲悲愴的壯美,氣吞山河。呱呱墜地的冰川“嬰兒”,一旦化為“石河”,從此便成了一個(gè)個(gè)久臥不起的“睡美人”。
仲秋時(shí)節(jié),雖不能說(shuō)氣候酷熱,但覆卮山海拔高,在太陽(yáng)的直射下,你便有了初夏之際的那種熱辣。于是,我趕緊找巨石遮陽(yáng)。剛剛坐下,便有絲絲涼風(fēng)從近旁竹林里吹來(lái),好不爽利。而隨著心閑神寧,靜靜諦聽(tīng),除了有啁啾的鳥(niǎo)聲,忽覺(jué)得“石河”間似有斷斷續(xù)續(xù)、低回反復(fù)的泉水聲,恍若臨風(fēng)撫琴,恰似珠落玉盤(pán)。我千尋萬(wàn)覓,終不得見(jiàn),猜想怕是很深很深的了。于是想及,這里該是地下泉豐沛之地。可不是?否則,當(dāng)?shù)卮迕窈我苑Q(chēng)之為“石硠棚”呢?“硠”者,水石撞擊之聲也。難怪從山麓往上走,羊腸小道旁淌水,山腰人家挖塘汲水,山頂巨石下滲水。這水對(duì)于覆卮村民是何等的珍貴!莫非這是第四紀(jì)冰川化冰為水一直流淌至今?抑或當(dāng)年大詩(shī)人上山“覆卮”令酒成水,惠澤如今?我們距離謝靈運(yùn)的年代實(shí)在是太遙遠(yuǎn)了,但覆卮山猶在,我雖無(wú)緣與謝靈運(yùn)一起上覆卮山品酒“覆卮”,但我以為在“石河”旁過(guò)夜也該是別有一番詩(shī)情畫(huà)意的。古人說(shuō)過(guò):“山堂夜坐,汲泉煮茗。至水火相戰(zhàn),如聽(tīng)松濤清芬滿懷,云光瀲艷,此時(shí)幽氣,故難以俗人言矣。”坐在“石河”邊,若能直接從“石河”下取水煮茗而品,這景致還能不羨煞當(dāng)年的謝靈運(yùn)?
我終以為,覆卮村民是有福的,上蒼賜給他們?nèi)缢箤毜?我更以為,覆卮先民是勤勞而智慧的。不是嗎?站在“石河”邊,但見(jiàn)曲曲折折、層次井然的田埂起伏于山坡之上。這一片片沿山而成的梯田,既是先民們憑一身硬朗、掄起鐵鋤打造的生存資本,也是先民們留給后代的希望所在。這資本,這希望,這1500畝左右的梯田,自巧借了石硠棚水的灌溉。因?yàn)槭勁锼@里大旱天不斷流,莊稼年年旱澇保收。張?jiān)健敦瓷讲萆嵋罢Z(yǔ)》曰:“覆卮山前溪水綠,覆卮山后雨滿谷。溪南溪北數(shù)椽屋,屋里有書(shū)書(shū)可讀。老翁鋤地種菜菔,老嫗攜筐采野菊。小兒開(kāi)門(mén)放雞畜,大兒刈草飼黃犢。春來(lái)桑上催布谷,秋后縣中輸歲粟。百年歡騰親骨肉,一生不知榮與辱。早起夜眠貧亦足。”這山美水美人更美里,不也暗合了人與自然和諧的真諦嗎?
暮色始降,金色的花粉轉(zhuǎn)瞬變成了紫色的煙霧。山脈與“石河”被這凝重又渾厚的色彩削減成一個(gè)美麗而悲愴的剪影。這是一種內(nèi)斂又博大的力量,它讓人窒息與收縮,讓人不由自主地想到了瞬間與永恒,歷史與現(xiàn)實(shí)。是的,于我則似乎站在了一種近乎歷史的洪荒的情緒里。再次與“石河”對(duì)視,再次側(cè)耳諦聽(tīng)潺潺不絕的泉水聲,終勾起了我無(wú)限念想,令我超越時(shí)空,想到了而今的冰川。如果說(shuō),第四紀(jì)中的間冰期,氣候轉(zhuǎn)暖,冰川融化,給人類(lèi)帶來(lái)福音的話,那么,而今的冰川早已成為地球生態(tài)環(huán)境的重要鏈條,是滋養(yǎng)我們生命的生態(tài)環(huán)境。每一座冰川都與人類(lèi)生活密切相關(guān)。冰川的每一點(diǎn)變化,都是人類(lèi)生態(tài)環(huán)境的晴雨表。冰川悄然融化,那水滴該是冰川流下的“眼淚”。幽靜的夢(mèng)被人們驚擾,和諧的家園被人們破壞,它們傷感莫名,唯有默默落淚。是的,有環(huán)境科學(xué)家指出,隨著氣候變暖,冰川將消融并導(dǎo)致海平面升高,地球上的很多城市會(huì)因此永遠(yuǎn)消失;極端天氣災(zāi)害也將頻頻發(fā)生,會(huì)導(dǎo)致糧食短缺、疾病肆虐,人類(lèi)生存面臨威脅。這絕非危言聳聽(tīng)。英國(guó)歷史學(xué)家湯因比在《人類(lèi)與大地母親》中說(shuō):“人類(lèi)將會(huì)殺害大地母親,抑或使她得到拯救?如果濫用日益增長(zhǎng)的技術(shù)力量,人類(lèi)將置大地母親于死地;如果克服了那導(dǎo)致自我毀滅的放肆的貪欲,人類(lèi)則能夠使她重返青春,而人類(lèi)的貪欲正在使偉大母親的生命之果——包括人類(lèi)在內(nèi)的一切生命付出代價(jià)。”制止冰川“流淚”,主動(dòng)權(quán)自在人類(lèi),要求人類(lèi)敬畏自然、慎思慎行。
走進(jìn)覆卮山,第四紀(jì)冰川已經(jīng)逝去,唯有“石河”還記憶著滄海桑田的變遷,讓人們可由此潛入結(jié)著霜華的夢(mèng)境。在它的孤寂里,更是傳遞著構(gòu)架和諧家園的訊息,并且,還能在驚鴻一瞥中,驚艷它那傲視萬(wàn)年的身姿。須知,要確切還原這第四紀(jì)冰川在覆卮山運(yùn)動(dòng)的所有細(xì)節(jié),怕是很難的了,可這條條“石河”引起的好奇和追問(wèn)、懷想和啟迪,遠(yuǎn)比那個(gè)充滿神奇和幻想的時(shí)代更具有吸引力。
“春暉”圖書(shū)館
享譽(yù)“北南開(kāi),南春暉”的上虞春暉中學(xué),就在白馬湖邊。白馬湖,雖小卻夠美夠精致。這個(gè)江南名湖究竟有多美多精致呢?當(dāng)年,朱自清在《春暉的一月》中是這樣描寫(xiě)的:“山的容光被云霧遮了一半,仿佛淡妝的姑娘。但三面映照起來(lái),也就青得可以了,映在湖里,白馬湖里,接著水光,卻另有一番妙景。我右手是個(gè)小湖,左手是個(gè)大湖。湖有這么大,使我自己覺(jué)得小了。湖在山的趾邊,山在湖的唇邊;他倆這樣親密,湖將山全吞下去了。吞的是青的,吐的是綠的,那軟軟的綠呀,綠的是一片,綠的卻不安于一片;它無(wú)端的皺起來(lái)了。如絮的微痕,界出無(wú)數(shù)片的綠:閃閃閃閃的,像好看的眼睛……真覺(jué)物我雙忘了。”
我曾風(fēng)塵仆仆赴上虞白馬湖畔參觀,除了觀風(fēng)覽景,更是想去看看春暉中學(xué)的圖書(shū)館。這并非因?yàn)閳D書(shū)館是整座春暉園的有機(jī)組成部分,它的建筑同時(shí)與仰山樓、曲院、西雨樓、山邊一樓等一起帶著濃重的歐式風(fēng)格,約屬“五四”以后西風(fēng)東漸的時(shí)代風(fēng)尚和江南地域文化品性有機(jī)融匯的典型體現(xiàn),而是由于它是春暉中學(xué)的“心臟”。
是啊,一流的建筑形態(tài)須有資金的保障,能邀請(qǐng)到一流的規(guī)劃師、建筑師就可以了,然而,對(duì)于一座泊于白馬湖畔的鄉(xiāng)野中學(xué)來(lái)說(shuō),它的脈動(dòng),既靠師生與之互動(dòng),也依恃于圖書(shū)館的帶動(dòng)。畢竟,圖書(shū)館藏什么書(shū),給師生的導(dǎo)引、給學(xué)校的助推,是無(wú)可替代的。
曾記否,二十世紀(jì)二十年代初,正是新舊文化交替、沖突,各種學(xué)說(shuō)、流派紛呈時(shí)期,一大批志趣相近追求新文化和理想教育的名家大師,在著名教育家經(jīng)亨頤的振臂一呼里,先后聚集到了白馬湖畔,其中有夏丏尊、朱自清、豐子愷、朱光潛、匡互生、楊賢江、劉薰宇、張孟聞、王任叔(巴人)、范壽康、吳夢(mèng)非、何香凝、柳亞子、葉圣陶、俞平伯、陳望道、黃炎培、張大千、黃賓虹、張聞天、胡愈之、劉大白、吳覺(jué)農(nóng)、蔣夢(mèng)麟、于右任、吳稚暉、陳鶴琴等。
如果說(shuō),當(dāng)年春暉中學(xué)的教育深深刻上了“深受新文化運(yùn)動(dòng)的影響”“是新教育的實(shí)驗(yàn)地”“實(shí)現(xiàn)了文學(xué)與教育的精神一致”“教育與救國(guó)相結(jié)合”等時(shí)代印痕,那么,這些似乎能從白馬湖圖書(shū)館里找到答案。不是嗎?因?yàn)榘遵R湖圖書(shū)館,“與時(shí)俱進(jìn)”的校訓(xùn)終究成為一種教育思想、教育革新而在這里繁衍,并成為一闋令人怦然心動(dòng)的佳詞而在這里長(zhǎng)傳,成為一抹穿越百年時(shí)空的清晰記憶而在這里復(fù)活。
暫且不說(shuō)“男女同校同學(xué)”先河的開(kāi)掘,《新青年》《向?qū)А贰墩Z(yǔ)絲》等進(jìn)步刊物被無(wú)所顧忌地選為課本,就讓人想及白馬湖圖書(shū)館當(dāng)年的教育擔(dān)當(dāng)。翻閱1923年11月1日第十八期《春暉》半月刊,讀到夏丏尊《叫學(xué)生在課外讀些什么書(shū)》一文,其中講到“我們要叫學(xué)生讀的書(shū),當(dāng)然是指知識(shí)上修養(yǎng)上必讀的書(shū),至于愛(ài)讀書(shū),不容說(shuō)要讓學(xué)生將來(lái)自定的了。那么,現(xiàn)在中等學(xué)校的學(xué)生,什么書(shū)是必讀的呢?我們以為我們學(xué)生所讀的書(shū),應(yīng)照下面所列的兩個(gè)條件決定:(1)做普通中國(guó)人所不可不讀的書(shū);(2)做現(xiàn)代世界的人所不可不讀的書(shū)。”為此,他暫定叫學(xué)生閱讀的書(shū)目有近百種,其中有《論語(yǔ)》《孟子》《老子》《莊子》《墨子》《呂氏春秋》《史記》《文心雕龍》《唐詩(shī)》(選)《宋詞》(選)《新舊約》《希臘神話》《佛教大綱》《天演論》《共產(chǎn)黨宣言》《一元哲學(xué)》《科學(xué)大綱》《中國(guó)哲學(xué)史大綱》《易卜生集》《隔膜》《吶喊》《魯賓遜漂流記》《威尼斯商人》《天方夜談》,等等。夏丏尊同時(shí)強(qiáng)調(diào)指出,“課外讀書(shū),是中等教育上重要問(wèn)題,近來(lái)學(xué)生能力的薄弱,或許是課外沒(méi)有讀書(shū)的緣故”,由此足見(jiàn)白馬湖圖書(shū)館對(duì)于學(xué)生開(kāi)拓視野,增添識(shí)見(jiàn),提升學(xué)習(xí)能力的作用了。
學(xué)生離不開(kāi)課外閱讀,教師又何以不需要通過(guò)“常汲水”、蓄滿“一桶水”而確保給學(xué)生“一杯水”呢?比如朱自清,在春暉中學(xué)這段“難得的愜意時(shí)光”里,除了認(rèn)真教書(shū)外,還勤于寫(xiě)作。而今想來(lái),他能教出一堂堂令學(xué)生叫好的國(guó)文課,寫(xiě)出一篇篇經(jīng)典傳世之作,沒(méi)有充足的底氣,行嗎?充足的底氣,從哪里來(lái)?讀書(shū),該是第一要著。要知道,朱自清是當(dāng)年白馬湖圖書(shū)館的常客,從當(dāng)年《春暉》半月刊上“白馬湖讀書(shū)錄”和“課余”兩個(gè)專(zhuān)欄來(lái)看,他除經(jīng)常閱讀《東方雜志》《太平洋》《語(yǔ)絲》等雜志外,主要閱讀的有清代周濟(jì)的《介存齋論詞雜著》、沙剎的詩(shī)文集《水上》、英國(guó)馬文的《歐洲哲學(xué)史》、普福的《美之心理學(xué)》等名著。1924年暑假,朱自清蟄居白馬湖消暑。他的手記見(jiàn)證了當(dāng)時(shí)的勤學(xué)苦讀:“7月29日,讀《學(xué)者氣質(zhì)》,頗似讀偵探小說(shuō)。偵探小說(shuō)益處;文學(xué)史方法——待錄。30日,要看《精神分析與文藝》。張東蓀有《科學(xué)與哲學(xué)》之著。擬買(mǎi)《文藝復(fù)興史》。哲學(xué)、國(guó)語(yǔ)、古文、文學(xué)四書(shū);概論免。31日,讀《毋違夫子》八股,覺(jué)得有新趣……”短短3天時(shí)間,他竟讀了這么多的書(shū),且涉及哲學(xué)、文學(xué)、藝術(shù)、心理學(xué)等眾多領(lǐng)域,這需要多大的定力啊!
每當(dāng)誦讀朱自清的一篇篇散文,都會(huì)想到白馬湖圖書(shū)館,總以為那篇篇散文是由白馬湖圖書(shū)館鋪就的知識(shí)臺(tái)階、思想臺(tái)階、情感臺(tái)階,或者說(shuō)是白馬湖圖書(shū)館的無(wú)形延伸和升華。是啊,朱自清的散文是深沉夜里的月華,是一種像水一樣寧?kù)o,在大地上無(wú)形而極具張力的流淌,看起來(lái)它那么散漫隨意,卻一直通向人最本原的深處——心靈或者靈魂。是不是可以這樣說(shuō)呢?朱自清的散文能臻此境界,只是因?yàn)樗艿搅税遵R湖圖書(shū)館的浸淫與滋養(yǎng)。
著名作家肖復(fù)興在參觀春暉中學(xué)后寫(xiě)就的《白馬湖之春》一文中說(shuō):“在世風(fēng)跌落、萬(wàn)象幻滅之際,世外桃源只不過(guò)是心里潛在理想的一種轉(zhuǎn)換,散發(fā)弄扁舟,從來(lái)都是猛志固常在的另一種形象。上一代文人的清高與清純,首先表現(xiàn)在對(duì)理想實(shí)實(shí)在在的實(shí)踐上,而不是在身陷軟椅里故作的姿態(tài)或高頭講章的言辭之中。”可不是?在談?wù)摪遵R湖和春暉中學(xué)的時(shí)候,現(xiàn)在的人們都愿意談?wù)撍麄兊奈幕删汀R劳邪遵R湖圖書(shū)館,夏丏尊坐于“平屋”,在一燈如豆的洋燈下艱苦工作,翻譯了亞米契斯的《愛(ài)的教育》;朱光潛則寫(xiě)就了他的美學(xué)處女作《無(wú)言之美》;豐子愷創(chuàng)作并首次發(fā)表漫畫(huà)《人散后,一鉤新月天如水》。如果說(shuō),相較文化成就,上一代文人在歷史轉(zhuǎn)折的時(shí)候走向鄉(xiāng)間的民粹主義和平民精神,是讓現(xiàn)在的人更加嘆為觀止的話,那么,軍功章里當(dāng)有白馬湖圖書(shū)館的一半。為何?因?yàn)槔硐氲母⒌滦缘母瑫r(shí)需要扎在肥沃的知識(shí)泥土里。
我篤信,這座高不過(guò)二樓、建筑面積也不過(guò)三、四百平米的白馬湖圖書(shū)館,雖并不起眼,但在八十多年前的春日和星夜、秋天和冬天,它一定像一位無(wú)私的慈母,展胸容納過(guò)滿懷宏愿的莘莘學(xué)子,滋育過(guò)在春暉講臺(tái)上傳道解惑縱橫捭闔的學(xué)者名流。誠(chéng)如一位作家所感慨的那樣:“春暉中學(xué)能從一株鵝黃的文化春筍最終崴蕤成一片蒼翠的文化竹林,在二十世紀(jì)的中國(guó)文化沃野中風(fēng)姿綽約,白馬湖圖書(shū)館的施肥和耕耘,當(dāng)不言而喻。一座聳立于鄉(xiāng)野里的中學(xué)的圖書(shū)館,能聆聽(tīng)過(guò)如此多的文化星辰敲擊它的足音,能注視過(guò)如此多學(xué)者名流出入它的身影,能灌濯過(guò)如此多學(xué)子終成名士翹楚,這在中國(guó)怕是無(wú)出其右的。”
想起10年前我去杭州拜訪魯迅?jìng)魅恕⒋簳煹膶W(xué)子黃源,說(shuō)到當(dāng)年春暉中學(xué)求學(xué)的情景,老人最難忘的除了學(xué)校自由民主的氛圍,竟是圖書(shū)館。他告訴我,課余自己跑得最勤的地方就是圖書(shū)館,花時(shí)間最多的便是讀書(shū)。我知道,在黃源心中,白馬湖圖書(shū)館里有著他晶瑩至愛(ài)、欲罷還休的忍耐,有靈魂震顫的激奮。“結(jié)嘆隨過(guò)隙,懷舊益沾襟。”對(duì)于黃源,白馬湖圖書(shū)館自有其刻骨銘心的片段。否則,當(dāng)我將新近出版的《永遠(yuǎn)的白馬湖》一書(shū)請(qǐng)其題詞時(shí),他何以只題寫(xiě)“白馬湖的學(xué)生——黃源”這出乎我意料卻又合乎情理的簽名呢?我總以為,白馬湖圖書(shū)館是屬于那個(gè)年代的,里面的每一個(gè)書(shū)架、每一本書(shū)都在訴說(shuō)一所老校、一所名校的夢(mèng)境;白馬湖圖書(shū)館更是今人的,每一個(gè)座位都在接續(xù)亙久長(zhǎng)存的讀書(shū)溫情,每一朵知識(shí)之花、思想之花、感情之花都在點(diǎn)燃當(dāng)今學(xué)生心中的彩燈。“春風(fēng)夏雨,暉光日新”,江澤民同志給春暉中學(xué)的題詞,其實(shí)不也給白馬湖圖書(shū)館作了最生動(dòng)的詮釋嗎?
阿根廷國(guó)立圖書(shū)館館長(zhǎng)博爾赫斯曾自問(wèn):“什么是天堂?”自答:“天堂是一座圖書(shū)館。”這位浸泡在滿是灰塵的圖書(shū)館里破萬(wàn)卷書(shū)、下筆有神的學(xué)者,曾不止一次說(shuō),“我是一個(gè)作家,但更是一個(gè)好讀者。”直至他近乎完全失明,又不無(wú)苦澀地寫(xiě)了一首詩(shī)向上帝致敬:“他以如此妙的諷刺/同時(shí)又給了我書(shū)籍和失明。”圖書(shū)館的誘惑,自是深湛的。一位居于白馬湖畔的老者曾告訴我,當(dāng)年之所以選擇住在歷史悠久的春暉中學(xué)旁邊,除了享受草木的繁幽深秀,更多的還是為了獲得一份心理上的文化撫慰。那泓溫煦芳洌的書(shū)香流脈,那種昔日重來(lái)的錯(cuò)覺(jué)美,那種流淌著的青春氣息,那份清澈如山泉溪流般沒(méi)有世俗“污染”的特有氛圍,讓人更加淡定平和。與其說(shuō),這位老者是在向儒雅的文化氛圍致敬,不如說(shuō),他是在向白馬湖圖書(shū)館敬禮。
正要離開(kāi)春暉中學(xué),忽然刮起了不小的風(fēng)并下起了蒙蒙細(xì)雨。回望時(shí),那八角屋頂、西式長(zhǎng)窗、黛瓦粉墻的白馬湖圖書(shū)館恍若一位玉樹(shù)臨風(fēng)的君子,而那由葉圣陶題寫(xiě)的館名此時(shí)顯得格外耀眼,在雨簾中一閃一閃,恰似顧盼的雙眸,又好似熱烈的心跳。哦,這就是人們心靈圣地的圖書(shū)館,一座百年甚至千年不衰的“未來(lái)的歷史建筑”。
走出校門(mén),來(lái)到白馬湖畔,隱約間我似乎依然能夠聽(tīng)聞瑯瑯書(shū)聲。這書(shū)聲自是從教室中傳來(lái)的,但又何嘗不是從那座世人心儀的白馬湖圖書(shū)館里傳出來(lái)的?它似乎要告訴我們這樣一個(gè)道理:讀書(shū)是一個(gè)民族靈魂的核心,是一個(gè)民族精神的支撐,是一個(gè)民族文化的本質(zhì),是一個(gè)民族精神的最強(qiáng)大、持久、熱情、富有創(chuàng)造性的力量。難怪有人說(shuō),要?dú)缫粋€(gè)國(guó)家,沒(méi)有比毀滅它的圖書(shū)館更直接更有效的了。想一想吧,如果一個(gè)民族失掉了圖書(shū)館,丟掉了書(shū),那么,“我們的心靈中就會(huì)沒(méi)有了詩(shī)意,我們的記憶中就會(huì)沒(méi)有了歷史,我們的思考中就會(huì)沒(méi)有了智慧和哲理,民族的文化歷史從此將被割斷,民族的心靈也會(huì)日趨淺薄,會(huì)泯滅了我們的文化感受性、道德同情心和人類(lèi)終極精神價(jià)值的追求……”是的,守望讀書(shū)精神和文化精神,使我們庸常的生活有一種價(jià)值,使我們沉湎在物質(zhì)與欲望中的人生和精神有了一種尊嚴(yán)。這不也是八十多年前的白馬湖圖書(shū)館給予我們的答案么?
江南的水古老了五千年的神秘日子,五千年的神秘日子也織就了多情的江南。我在如夢(mèng)如幻的江南水鄉(xiāng)里陶醉,我在“小橋流水人家”的鄉(xiāng)戀里流連。在水性柔情的江南,我愿意成為泛舟江渚的漁人、早起涉水的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