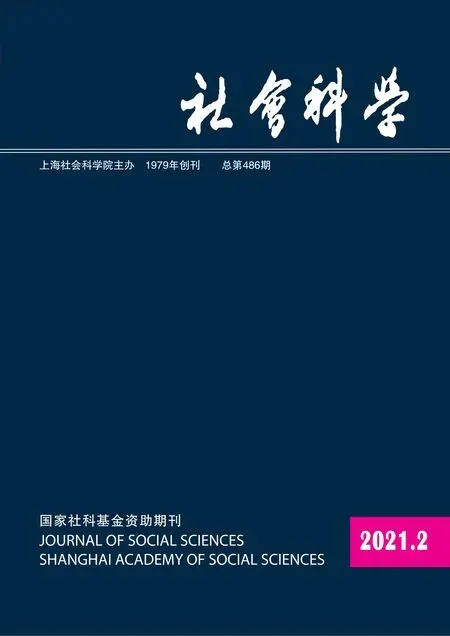“人類命運共同體”國際傳播的“共通的意義空間”研究*
金天棟 任 曉
*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外交思想研究”(項目編號:18ZDA007)的階段性成果。
“人類命運共同體”自提出以來,中國官方與學界分別在實踐和學理層面取得豐碩的成果。其中,以區域主義為起點、多邊主義為目標和歸宿的“一帶一路”倡議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打下了現實基礎。據中國官方公布,截至2020年5月,中國已與138個國家簽署了“一帶一路”合作文件,共同展開了2000多個合作項目(1)王毅:《中國與各國攜手推進“一帶一路”的信心不減,決心未變》,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lh/2020-05/24/c_1210631791.htm,2020-05-24。。學界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研究也極為重視。通過對中國知網(CNKI)相關論文的分析,截至2020年,國內有關“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研究成果多達600余篇(2)錢文靜、張有奎:《人類命運共同體研究的可視化知識圖譜分析》,《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7期;秦龍、劉倍功:《“人類命運共同體”研究的現狀、熱點與演化路徑——基于CiteSpace可視化工具知識圖譜分析的研究視角》,《河南社會科學》2020年第4期。。但數據顯示,相關研究雖然涉及的領域較多元化,可內容上有著較明顯的單一學科導向,主要集中于馬克思主義理論領域。
如此一來,涉及面雖廣,但其它學科的參與度稍顯不足,并間接導致研究的疊合性較強。并且,部分成果由于學科的研究對象、邊界及研究環境的限制,以致特殊性較明顯、主觀性較強,有著一定的局限。但是,“人類命運共同體”不該是某個學科的研究專項,其內涵之深邃、目標之遠大,也絕非單一學科所提供的智識就能學理化的。況且,即便部分學科會有特殊性,但“人類命運共同體”從話語角度而言,它應該成為一個普世的“全球話語”,而非僅僅強調殊相的“中國話語”。這就更要求相關研究應從“世界學問”出發,傳播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而不能只作為一門“中國學問”,講述自己的獨特(3)國內外學界對于“世界主義”與“全球主義”有著定義上的差異,既有將兩者等同的觀點,也有認為兩者是不同概念的觀點。本文不對此展開探究,并將兩者視為同一概念。。
所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提出,其目標遠非超越西方價值那么單一,價值也絕非強調自身的特殊性那么簡單。從中國官方表述來看,作為全球治理“中國方案”的“人類命運共同體”(4)黨的重要會議,如十九大報告與十九屆四中全會,都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與“全球治理”聯系在一起。參見《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全文公布》,http://www.chinanews.com/gn/2019/11-05/8999232.shtml,2019-11-05;《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http://cpc.people.com.cn/n1/2017/1028/c64094-29613660.html,2017-10-28。,其意不在于指涉“中國想要什么樣的國際社會”(5)阮宗澤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中國的“世界夢”,旨在回答“中國到底想要一個什么樣的世界”。但本文認為,從傳播學的信息共享和“共通的意義空間”來分析,如此大氣磅礴的表述會不利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國際傳播。參見阮宗澤《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的“世界夢”》,《國際問題研究》2016年第1期。,而在于“中國能夠為國際社會提供哪些發展設想”。它不僅是中國應對西方國家的“污名化”而生成的話語防御機制,更是中國察覺到國際社會基礎變化而產生的具有前瞻性的現實認知。它是和平發展、自由多元、良法善治、公平正義、相互依存、合作共贏等人類共同價值的集合體,是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則構建國際社會“和合共生”的方案構想,是中國能夠給世界提供建設性思想資源的原創性新世界主義(6)任曉:《論中國的世界主義——對外關系思想和制度研究之二》,《世界經濟與政治》2014年第8期;蔡拓:《世界主義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比較分析》,《國際政治研究》2018年第6期。,是以新型國際關系、國際法治對沖“修昔底德陷阱”的國家間新互動模式。這些內容早已超出單一學科的范疇。
因而,作為集中國數千年文化之思想、西方文明之精華、國際社會現實之需求為一體的“人類命運共同體”話語,理應成為中國與世界交往互通的社會信息。并且,為了讓“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個互動符號發揮效力,應該構建一個彼此都能產生共同理解的“共通的意義空間”(7)“共通的意義空間”是傳播成立的重要前提之一。它是指傳受雙方對符號意義擁有共通的理解。廣義上的意義空間還包括人們大體一致或接近的生活經驗和文化背景。參見郭慶光《傳播學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0-11頁。,以便減少其面臨的傳播障礙與隔閡,使之更好地在國際社會傳播,讓受眾更廣、更多元化。但從既有文獻來看,該方面的學理探討仍有待加強。那么,如何通過話語的調整去實現該目標?
本文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研究需要在學理層面進一步重視本土知識的主體性與連貫性,但同時需要注意可行性與兼容性的問題,并從傳播的原點即概念本身展開省思,加強中西方話語共通性的研究。對此,本文首先梳理了既有成果的研究路徑,指出其不足之處與國際傳播的關聯。其次,通過進一步細化國內外既有文獻的觀點,指出“人類命運共同體”國際傳播的困境與潛在風險。最后,厘清國際(政治)傳播概念,以構建“共通的意義空間”作為破題之解。
一、文獻回顧與評析
本文根據國內學界的主要觀點,從“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研究進路,將它們分為現實主義/實用主義研究、話語詮釋/價值研究和哲學/規范研究。
第一,以現實主義/實用主義為研究進路的著述,一般散見于中國對外戰略的研究中,其敘述結構通常為“現實主義/實用主義+政策釋義”,并聯系“中國崛起”、國際秩序“失序”等國內外前沿話題,對“中國威脅”論、全球治理危機等西方關注的重點予以回應。其中,部分研究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為實現“中國崛起”而服務的,旨在塑造新的區域合作機制,將中國周邊視為崛起的戰略依托帶(8)張蘊嶺:《中國的周邊區域觀回歸與新秩序構建》,《世界經濟與政治》2015年第1期;阮宗澤:《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助力中國戰略機遇期》,《國際問題研究》2018年第1期;凌勝利:《構建周邊安全共同體:挑戰與對策》,《國際問題研究》2017年第5期;盧光盛、別夢婕:《新型周邊關系構建:內涵、理論與路徑》,《國際觀察》2019年第6期。。它既是中國周邊戰略的理念支柱和政策表達,也是對彼時美國“重返亞太”的政治話語回應。另有觀點則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與中國的對外戰略是互構共生的(9)李向陽:《“一帶一路”:區域主義還是多邊主義?》,《世界經濟與政治》2018年第3期;劉建飛:《新時代中國外交戰略基本框架論析》,《世界經濟與政治》2018年第2期;趙可金、翟大宇:《互聯互通與外交關系——一項基于生態制度理論的中國外交研究》,《世界經濟與政治》2018年第9期。,即將中國的發展與世界的發展相捆綁,實現中國與世界的共贏,其實踐基礎是“一帶一路”倡議。
第二,有關“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話語詮釋/價值研究分散于不同學科領域。第一類是用中國傳統文化的相關概念詮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內涵,例如,將“天下”“義利”“和”等概念嫁接其中;第二類是意識形態化“人類命運共同體”,強調意識形態建設、提高國內媒體話語表達的質量、優化敘事策略等(10)劉桂榮:《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理論創新與話語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2017年第5期;周翔:《“命運共同體”的話語體系建構——概念再造、語境重置與方式轉換》,《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8年第4期;劉昌明、楊慧:《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從外交話語到外交話語權》,《理論學刊》2019年第4期。;第三類是闡發與解讀習近平總書記的“人類命運共同體”論述,旨在表明中國外交的價值原則(11)胡鞍鋼:《習近平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與中國方案》,《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5期;王海東、張小勁:《新時代中國國際戰略:以“命運共同體”論述為重點的解讀》,《國際論壇》2019年第6期;岳圣淞:《話語、理念與制度創新:“人類命運共同體”視角下的全球治理》,《戰略決策研究》2020年第1期;熊杰、石云霞:《論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思想來源、發展邏輯和理論貢獻》,《國際觀察》2019年第2期;王寅:《人類命運共同體:內涵與構建原則》,《國際問題研究》2017年第5期;阮宗澤:《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的“世界夢”》,《國際問題研究》2016年第1期;吳志成:《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論析》,《世界經濟與政治》2018年第3期。。
第三,以哲學思辨的方式,從規范研究維度深度剖析“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內在原理(12)劉同舫:《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對歷史唯物主義的原創性貢獻》,《中國社會科學》2018年第7期;張輝:《人類命運共同體:國際法社會基礎理論的當代發展》,《中國社會科學》2018年第5期;張曙光:《“類哲學”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5年第1期;金應忠:《從“和文化”到新型國際關系理念——兼論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社會科學》2015年第11期;金應忠:《試論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兼論國際社會共生性》,《國際觀察》2014年第1期;羅云、金天棟、戴軼:《國際話語視角中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和”文化內涵解讀》,《廣東社會科學》2020年第2期;邱耕田:《“命運共同體”:一種新的國際觀》,《學習時報》2015年6月8日;陳沫、劉鴻鶴:《從古代家國天下觀到新時期世界新秩序——兼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8年第5期;賀來:《馬克思哲學的“類”概念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哲學研究》2016年第8期。。該部分的研究主要傳遞一種觀照社會關系、國際關系的新路徑,并對二者內部行動者之間的互動與相處模式作出新展望。因此,相關研究從人類交往的沿革、人與社會資源、國家之間的共生關系出發,以抽象和哲學化的方式,著重表達“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的一種秩序觀,并立足人類社會,在本體論上把個體調整為“類”本位,吸收與發展歷史唯物主義,強調事物的共通性與共生性,希冀在國際社會的差異性與依存性、個體利益與公共利益之間尋求新的銜接與融合之道,將人類社會推向更美好的世界圖景。
上述成果不乏真知灼見,但仍存有三點不足:其一,詮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論深度與主體性稍顯不足,或是移用中國傳統文化的相關概念,或是逡巡于主流國際關系理論;其二,對“人類命運共同體”話語的描述性研究、評價性研究較多,而學理性、解釋性研究稍顯不足,以致于該話語在概念界定上仍顯模糊;其三,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缺乏案例分析,未能充分地將其上升到社會科學的實證研究層面。
這些不足也延伸到“人類命運共同體”話語的國際傳播。傳播學領域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研究成果大多沿用上述幾條進路的觀點或與之相關,且側重于傳播情況、傳播策略的分析(13)袁靖華:《中國的“新世界主義”:“人類命運共同體”議題的國際傳播》,《浙江社會科學》2017年第5期;廖衛民:《新世界主義與對外傳播戰略——基于“傳播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穹頂模型的理論思考》,《浙江社會科學》2017年第5期;陳鑫:《“人類命運共同體”國際傳播的困境與出路》,《寧夏社會科學》2018年第5期;陳華明、李暢:《展示政治視域下“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對外傳播研究》,《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6期;李青青《“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戰略傳播》,《區域與全球發展》2019年第4期;梅朝陽、孫元濤:《中國話語“人類命運共同體”國際傳播的媒介生態思考》,《浙江社會科學》2020年第9期。,對傳播的認同問題則不夠重視(14)李雪婷:《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海外傳播與認同的研究現狀及展望》,《對外傳播》2020年第10期。。但溯源“人類命運共同體”國際傳播的困境,可以說其癥結不在傳播策略、傳播媒介、傳播平臺、議程設置或傳播基礎結構等方面,而在于國際認同度(15)朱玲玲、蔣正翔:《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論闡釋與國際傳播》,《黨政研究》2019年第1期。。固然,給相關方面進行針對性的建言獻策是重要的。但考慮到“人類命運共同體”即是話語/概念本身,所以從知識論上講,任何話語/概念包括“人類命運共同體”在內,都是“我”對事物的認知,其“客觀實在”是通過話語(知識)來建構的。它雖是蘊涵“我”之價值偏好的容器,是傳播與灌輸觀念的社會化機制,但同時也源自現實、指涉現實,是有所指的觀念和經驗所建構的實在對象。因此,盡管傳播策略的研究與思索是必要的,但在“人類命運共同體”被“他者”情感認同和行為認同之前,須先達到認知認同。只有“他者”認為話語是符合現實及自身所需時,才可能認可與接受。這就要求相關研究必須回到原點、回到基礎工作,即回歸學理維度的知識構建,對其進行概念界定與實證分析。
這里也需要提及“政策話語”與“學術話語”的差異。前者是為了政策宣言,對信息傳遞的方式與過程會關注多些。在涉外時,它就成為國際政治傳播的符號。“學術話語”就是概念,是對事物規律的高度概論與抽象化。它在具有現實意義的同時,還必須具備學理意義,以顯得更有說服力與解釋力。目前,“人類命運共同體”更側重于作為“政策話語”,缺乏作為“學術話語”的自覺。所以不難發現,它出現與傳播的場域多為國際會議和新聞媒體,而國外學界對其論述有限。該現象很大程度上是受“共通的意義空間”缺位的影響,致使傳播障礙與傳播隔閡較大,進而造成“人類命運共同體”在國外學術界的界定與認知中并未產生應有效應。
二、“人類命運共同體”國際傳播面臨的難題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國際傳播,廣義上是指大眾傳播,狹義上則是指國際政治傳播,即國家(包括非國家行為體)之間具有政治傾向與意識形態色彩的跨文化信息傳遞或信息系統運行。羅伯特·福特納(Robert S.Fortner)認為,“政治本質”是國際傳播的主要特點,“從某種意義上說,所有的國際傳播都具有政治性,都帶有政治色彩,政治因素是其本質固有的,區別只在于,有的是公開的政治傳播,有的是隱含的政治傳播”(16)[美] 羅伯特·福特納:《國際傳播“地球都市”的歷史、沖突與控制》,劉利群譯,華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8-9頁。。
傳播既是行為,也是過程。與任何傳播一樣,國際傳播過程也必然會出現障礙。在話語傳播過程中,受眾會對信息進行自我甄辨。這是一個與受眾已內化的認知交互作用的過程。受眾作為理性人,自然會作出思考、反思與選擇。所以,話語的傳播與接收包含著從“信源到信宿的一系列環節和因素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響關系”(17)郭慶光:《傳播學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1頁。。該過程會因受眾的價值、本能、情感利益影響而可能出現“認知論障礙”(Epistemological Obstacles)(18)Gaston Bachelard, The Formation of the Scientific Mind: A Contribution to a Psychoanalysis of Objective Knowledge, Manchester: Clinamen Press Ltd., 2002, pp.1-8.,其實質就是受眾因文化與慣習而產生的認知慣性可能會抵觸新信息。傳播學通過“群體規范”對此問題已有深入研究,本文不再贅述。
另外,國際傳播必須考慮到國際政治中的國家利益問題。無論是社會傳播的何種類型(19)社會傳播有五種基本類型,即人內傳播、人際傳播、群體傳播、組織傳播和大眾傳播。參見郭慶光《傳播學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頁。,作為單元與次體系層次的概念,一旦進入體系層次,其主體、受眾、性質、方式都會發生變化(20)陳岳、雷伯勇:《國際傳播在國際政治中的作用》,《國際新聞界》1997年第4期。。國際政治傳播的主要行為體是主權國家(但不排除非國家行為體),受眾也是主權國家及其公民,性質為政治屬性與意識形態屬性,方式為國際宣傳與公共外交。例如,在根本上,國際傳播會從國家(政府)對“他者”(國家)民眾的政治傳播上升為國家對國家的政治宣傳。部分信息對于“他者”來說,可能會威脅到政權正當性、合法性的知識基礎,進而衍生為國家間圍繞權力與利益的博弈。故而,此類話語的國際傳播一般會受阻或無效化。
大體厘清國際政治傳播的內涵之后,再來觀察政治宣傳和媒體宣傳以外的國際社會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認知,可以發現,后者的傳播存在一種潛在風險,即可能使中國滑向意識形態對抗與大國戰略對抗。
(一)意識形態溝壑
“人類命運共同體”話語在國外學界的影響力稍顯微弱。這不僅有國外學者意識形態偏見的原因,同樣也是國內“人類命運共同體”研究存在一定的偏差所致。例如,冗雜的價值研究不一而足,研究與成果的疊合度過高,新知識有限。
第一,“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研究偏多,缺乏實證分析。國內有關“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研究基本停留在價值規范層面,多數從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傳統文化進行內涵解讀與價值詮釋(21)參見李愛敏《“人類命運共同體”:理論本質、基本內涵與中國特色》,《中共福建省委黨校學報》2016年第2期;徐艷玲、李聰《“人類命運共同體”價值意蘊的三重維度》,《科學社會主義》2016年第3期;邵發軍《習近平“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及其當代價值研究》,《社會主義研究》2017年第4期。。內容通常是對中國官方言論做文本分析,抑或是移用傳統文化的概念。但后者未能充分地將兩者之間的邏輯關系論證清晰,也缺乏案例分析與經驗確證。所以,有國外學者指出,這只是一種“話語表達”和“道德敘事”(22)William A.Callahan, “China 2035: From the China Dream to the World Dream”, Global Affairs, Vol.2, No.3, 2016, pp.247-258; Jacob Mardell, “The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in Xi Jinping’s New Era”, The Diplomat, October 25, 2017, https://thediplomat.com/2017/10/the-community-of-common-destiny-in-xi-jinpings-new-era.,并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僅提出了“空洞原則”而已,其意義并不明確,如何將原則付諸于實踐也有待回答,比如,怎樣為不同的伙伴國家、領域制定合適的計劃(23)Denghua Zhang,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in China’s Diplomacy: Meaning, Motives and Implications”, Asia & the Pacific Policy Studies, Vol.5, No.2, 2018, p.198.。顯然,僅憑價值研究不足以回答國外學者的質疑。繼而,“人類命運共同體”應該作為“學術話語”予以應對,在概念的科學化、操作化上,使之具有更深厚的學術生命力,提高中國的國際話語權。畢竟,西方理念與理論并非僅是作為價值傳播或依靠武力征服而為“他者”所接受的,同樣,唐宋明時代的中國為周邊政治共同體所學習與研究,也不單純是因為儒家文化本身,產生這些現象的根本原因在于物質性的成功使得文化吸引力、制度吸引力增強。后面二者是話語價值的來源與載體。如此,讓“他者”在制度規束下形成一套穩定的行動模式,使價值內化于自身。哪怕是本土文化受到沖擊,也不能完全阻擋政治共同體對物質利益的追求。因此,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在價值規范上,而是要通過經驗分析與實證研究,提高其學理化程度,不僅讓它作為價值進行推廣和傳播,更要作為人文社科領域的“世界知識”進行推廣和傳播。
第二,對“人類命運共同體”話語詮釋的意識形態色彩過重。意識形態屬于價值范疇(24)[美] 戴維·伊斯頓:《政治生活的系統分析》,王浦劬等譯,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77頁。。戴維·伊斯頓(David Easton)把價值分為運作價值(Operating Value)和意識形態。前者是實踐傾向的,后者是理想向度的。在運作價值上,“人類命運共同體”通過闡明平等相待、相互協商、相互理解的伙伴關系,公平正義、共商共建的安全架構,開放、創新、包容、普惠的發展,尊重差異、加強文明交流,構建綠色環保的生態體系等內容,向國際社會予以釋疑。在國家間互動規范上,也以“親、誠、惠、容”和“共商、共建、共享”來展現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溫和與防御性態度。可以說,“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上述運作價值是得到國際社會的極大認可的,只是在學理層面上受到的意識形態詰難較多。國外學者會強調中國對歷史敘事的工具性利用,認為中國試圖挑戰自由民主,以“共同價值”對抗“西方價值”來傳播自身的政治價值(25)Michael J.Mazarr, Timothy R.Heath and Astrid Stuth Cevallos, China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2423.html.,為國際秩序的“中國化”(Sinified)進行辯護(26)Jian Zhang, “China’s New Foreign Policy under Xi Jinping: Towards ‘Peaceful Rise 2.0’”, Global Change, Peace & Security, Vol.27, No.1, 2015, pp.5-19; Stephen N.Smith,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China’s ‘New Assertiveness’ and the Changing Asian Ord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73, No.3, 2018, pp.449-463.另外,大部分相關研究都是從維護自由國際秩序與探討其走向,論及中國對自由國際秩序的影響,且這些研究表達的意向是與“中國中心主義”相似的,參見John G.Ikenberry, “The End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4, No.1, 2018, pp.7-23; Denghua Zhang,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in China’s Diplomacy: Meaning, Motives and Implications”, Asia & the Pacific Policy Studies, Vol.5, No.2, 2018, p.198; John G.Ikenberry, “The Next Liberal Order: The Age of Contagion Demands More Internationalism, Not Less”, Foreign Affairs, Vol.99, No.4, 2020, pp.133-142。。對此情況,國內研究雖認清“西方國家在意識形態上的偏見、話語霸權以及國內媒體話語表達與敘事策略不妥”,但提倡加強“中國意識形態”研究就稍顯激進(27)周翔:《“命運共同體”的話語體系建構——概念再造、語境重置與方式轉換》,《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8年第7期;周銀珍:《國際情懷與擔當:“人類命運共同體”建構中國國際話語權》,《寧夏社會科學》2018年第1期;張志丹:《人類命運共同體視閾中的中國意識形態國際話語權》,《河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2期。。如此循環往復,恐怕中美會陷入意識形態對抗。當前,美國正在搭建“意識形態陷阱”。通過意識形態施壓、攻擊中國,試圖逼迫后者陷入戰略焦慮,出現戰略失誤、跳入陷阱。同時,美國也正在組織“反華價值同盟”,以重塑“我們感”(We Feeling)來提醒其它國家“我們是誰”(Who We Are),其目的是在政治身份上將中國擠出“同一個世界”。如果加強“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意識形態構建,那么中國就是順著美國的戰略意圖加劇意識形態矛盾。而且,中國外交的特色之一就是弱化意識形態,作為中國的外交話語、“政策話語”,“人類命運共同體”在性質上也理應是弱意識形態的。但需要指出,價值與意識形態研究是必要的,只是同類的疊合成果較多,對于提高和增進“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話語效力和國際傳播意義有限。
(二)戰略競爭壁壘
國家的戰略行為不可避免地受到認知與文化因素的影響,其會反映在戰略思維上。中國由于受西方國際關系理論與西方主導的國際互動規范的影響,在戰略思維上與西方國家有些許趨同。現實主義范式作為西方國家長盛不衰的政治文化與國際關系理論,它是國外學界借以分析“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本路徑,并且研究成果基本取得共識,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對外戰略更為進取的話語表達(28)參見Micheal R.Auslin, The End of the Asian Century: War, Stagnation and the Risks to the World’s Most Dynamic Region,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9, 200; Denghua Zhang,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in China’s Diplomacy: Meaning, Motives and Implications”, Asia & the Pacific Policy Studies, Vol.5, No.2, 2018; Jian Zhang, “China’s New Foreign Policy under Xi Jinping: Towards ‘Peaceful Rise 2.0’”, Global Change, Peace & Security, Vol.27, No.1, 2015; Stephen N.Smith,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China’s ‘New Assertiveness’ and the Changing Asian Ord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73, No.3, 2018。,中國意圖在全球政治領域重塑國際秩序,使之獲得與其實力相匹配的權力地位(29)Ali Wyne, “Book Review Elizabeth Economy’s the Third Revolution”, The RAND Blog, https://www.rand.org/ blog/2018/06/book-review-elizabeth-economys-the-third-revolution.html; Melanie Hart and Blaine Johnson, “Mapping China’s Global Governance Ambitions”, Foreign Policy and Security Cap, 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rg/issues/security/reports/2019/02/28/466768/mapping-chinas-globalgovernance-ambitions.。
顯然,這是持工具理性對“人類命運共同體”進行的審視,以“中國威脅”“中國野心”“修正主義者”等話語對中國進行“污名化”。但國內一些學者同樣也是持工具理性,似乎對現實主義形成了路徑依賴(30)參見阮宗澤《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助力中國戰略機遇期》,《國際問題研究》2018年第1期;凌勝利《構建周邊安全共同體:挑戰與對策》,《國際問題研究》2017年第5期;張蘊嶺《中國的周邊區域觀回歸與新秩序構建》,《世界經濟與政治》2015年第1期。。雖然此類研究言之有物,極具戰略遠見,可“人類命運共同體”不該是某一種理論范式就能夠全面觀照的,否則無法解釋它的深厚意蘊,更別說中國傳統文化、馬克思主義還占據著其內涵的大部分。如果雙方皆以現實主義視角看待“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下的中國對外戰略,那么該話語存在與否對戰略博弈并無影響。如此,也就顯得中西方不同文化所塑造的思維差異被同一了。以中美為例,中國人更擅長辯證思維、關系思維,美國人更擅長邏輯思維、類屬思維(31)潘忠岐:《中國人與美國人思維方式的差異及其對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寓意》,《當代亞太》2017年第4期。。但在中美都依賴現實主義路徑的情況下,戰略思維差異就縮小了。看似便于理解與預測對方的行動,實際上雙方將認知對方的進路不斷地狹隘化。
何況中國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要目的不在于解構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并與之進行對抗。與這種“進攻性”的解讀相反,“人類命運共同體”所蘊涵的中式戰略思維決定它應該是“防御性”的、“內斂”的。它是為了回避與美國的對抗,將注意力擴散至國際社會,而不是限制在中美關系上。所以,國內學者也應該有限地跨出思維定勢,創新國際關系理論,從理論與實踐中,同步發展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三、“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國際傳播如何破解難題
(一)反思國際傳播
從“人類命運共同體”當下國際傳播的境況來看,它作為“學術話語”的效果未達到預期,原因有三點:
第一,國際傳播中意識形態色彩較重,有些過于突出自身的文化自覺。盡管意識形態不可避免,獨特文化也是構建話語的基礎,而且西方同樣會進行意識形態的國際傳播。但如果中國也采取該路徑,與西方進行意識形態的國際傳播攻堅戰,那么恰恰為西方提供了塑造聯盟型“共同體”所必需的凝聚力。
第二,傳播主體混淆了“政策話語”與“學術話語”兩種不同的話語類型。“政策話語”不同于“學術話語”。后者的說服力是通過對假定與假設的實證檢驗與邏輯演繹,得出一般性規律,有著學理的支撐,使得信源的可信度相對于純粹的“政策話語”要更高。這是影響傳播效果的前提條件。如果缺乏學理支撐,那么受眾根據先在的知識,在對信息的真偽與價值作出判斷時,理論面前的“政策話語”就可能被誤解或顯得說服力不足。因此,西方事實上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認知也只是停留在政策宣言層面。對“他者”而言,“人類命運共同體”話語是否存在不影響其體認中國的戰略行為。該現象的部分原因正是話語的學理薄弱。
第三,未區分“國內話語”和“國際話語”。對內傳播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以特殊語境和社會結構為基礎的。在對應的政治環境與社會關系中,其意義解讀與越過國界、跨文化的“國際話語”理應有所差異。然而,“人類命運共同體”在國際傳播中運用的是與國內話語相同的話語體系。這樣,雖然體現了“人類命運共同體”話語的主體自覺,但不一定有利于面向“他者”的國際傳播。
那么,“人類命運共同體”該如何進行國際傳播才能更有效?其一,加強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學術話語”建設,使之言之有據、言之有物、言之有理;其二,在單元層次的基礎之上,從體系層次對“人類命運共同體”進行話語建設和傳播;其三,強調文化的共通性,降低意識形態色彩。
尤其是第三點,國際傳播是有關信息共享的國際行為體之間的互動。信息符號化后,進行傳播是會被“他者”詮釋與再理解的,之后可能通過“他者”再符號化予以反饋。例如,中國對“中國威脅論”與“修昔底德陷阱”的反饋符號就是“人類命運共同體”與“新型大國關系”。若要減少“人類命運共同體”國際傳播的阻力,那么就需要塑造“共通的意義空間”,必須讓它在國際社會有一定基礎的共同理解。所以,如何構建“共通的意義空間”將是“人類命運共同體”國際傳播過程中需要注意的重點。
國際傳播主要指涉國際政治傳播,因為體系層次中能夠發揮較大影響力的通常是國家行為體,而國家間關系的主導領域為政治關系,所以,從國際政治傳播來分析“共通的意義空間”是合理的。根據其概念內涵,國際政治目標與意識形態分別為中介變量與干預變量(見圖1)。又由于在國際政治中,國家行為體逐利是不言自明的假定,所以在不考慮具體目標的情況下,可將其視為恒量,進而從信息(話語)到傳播效果之間的影響因素就鎖定為意識形態(包括文化差異在內)。

圖1 國際政治傳播效果公式
因此,鑒于“人類命運共同體”強意識形態的解讀可能會帶來潛在風險,該話語最好通過弱意識形態來詮釋,以側重“共同價值”而非“價值排序”的方式,擴大中西方之間“共通的意義空間”。它的具體路徑為挖掘中西方之間文化、理念等方面的共性,并運用“學術話語”進行信息傳遞,同時也要注重實證研究。
(二)尋找“共通的意義空間”
那么,如何構筑中國對外傳播“共通的意義空間”?從探尋話語的共通點出發,本文初步提出以下幾條進路。
共通點一:中西方都有構建共同體的價值追求。其一,中西方都表達出對理想社會的向往。共同體思想在西方源起于古希臘,其理念最早可見諸于柏拉圖與蘇格拉底的對話,但系統性的提出者是亞里士多德,意在追求“至善”的幸福高尚生活。在中國,共同體思想最早出現在《詩經》中,如《魏風》中的《碩鼠》,先秦諸子百家也對其多有論述,體現了中華民族先賢對“樂土”的追求,只是所用表述為“大同”。其二,中西方對施政者的價值要求相同。古希臘城邦共同體是一種探索正義的社會治理設想,關注精神層面的“善”,重視法治作為維持社會秩序的基礎。“大同”理念則體現在儒家的“仁政”與宗法制度上,強調“禮治”與“儒法互用”,以確保“權位分配”的合理,鞏固官僚的權力基礎并穩定社會(32)本文的“權位分配”是指權力與社會地位或職業的關聯匹配。古代中國社會結構穩定與“權位分配”的合理性密不可分。參見瞿同祖《中國階級結構及其意識形態》,載[美] 費正清編《中國的思想與制度》,郭曉兵等譯,世界知識出版社2019年版,第250-268頁;相關討論也可參見Kingsley Davis, Human Society, New York: Macmillan Co., 1949, p.95。。然而,社會基礎變化與理念滯后所產生的矛盾使中西方各自面臨共同體困境,并引出“后現代”思考。
舊的共同體模式與現實之間的張力自然要求創新共同體理論。如果說西方的共同體困境只在于價值理性被“物化”,那么中國所面對的問題是連能夠“物化”的價值理性都缺乏(33)因而,西方需要整合多元價值,而中國需要生產核心價值以應對價值虛無的困境。。歸根結底,中西方面臨的共同體困境是相同的,即人類如何在社會基礎變化的情況下更好地發展。對此,中國提出的解決辦法是“人類命運共同體”。它以“實現共同利益,追求至善”為基礎理念向上糅合,從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價值共同體三個維度,以“滿足生活”“使人們生活得更美好”為導向(34)[古希臘] 亞里士多德:《政治學》,高書文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2-7頁。,創新共同體理論,指引人類發展。因此,“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以共同體理論為基底、以追求共同利益為核心假定、以共同體能夠實現共同利益為主要假說,與安全共同體、國際共同體等概念相通。
共通點二:人類活動若無協作,社會難以存在(35)[法] 埃米爾·涂爾干:《社會分工論》,渠敬東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年版,第235頁。。該命題及其客觀實踐必然使“和”文化與西方國際合作理論有理念相似之處。其一,目標一致。社會學與生物學都已論證“共在”“共生”的重要性,所以“和合共生”與西方國際合作理論都指向以協作實現共同利益、緩解沖突。其二,相似的假定。“和”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本體論,它不是簡單指稱“和平”“和諧”,而應該理解成以“中”為基礎的理性原則,西方國際合作理論同樣以“理性人”“經濟人”為前提假定(36)根據《禮記·中庸》,“中”即理性原則。“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但“和”是關系理論,西方國際合作理論是個體理性。所以,兩者只是相似。。其三,合作方式類似。兩者都重視規則治理,但“人類命運共同體”在強調國際法治的同時,也嘗試規避“價值物化”的陷阱,重視“關系治理”。其四,合作演化。以“和合”為核心理念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內涵——“和實生物”與“和而不同”兩個概念,在“中和”與“和同”螺旋上升結構中交互影響,塑造“重疊共識”進而“生物”,而國際合作理論則用“報償結構”同樣解釋了行動者如何相互調適邁向合作(37)[美] 肯尼思·奧耶:《解釋無政府狀態下的合作:假說與戰略》,載[美] 肯尼思·奧耶主編《無政府狀態下的合作》,田野、辛平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21頁。。盡管當下的國際合作理論似乎陷入了困境。
共通點三:中西方的共同體都是弱利他主義。心理學與生物學已有相當多的研究成果論證了人類只具有弱利他性,強利他是難以實現的理想狀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義利觀”是指國家不應“隨國力增長而無限擴大核心利益”(38)秦亞青:《正確義利觀:新時期中國外交的理念創新和實踐原則》,《求是》2014年第12期。,不是否定利己。它從大國實力與國際責任以及讓國際社會變得更好的價值取向出發,認為“大國有時需要先從道義層面來考慮責任問題,給予發展中國家力所能及的幫助以體現負責任大國應有的風范”(39)王毅:《堅持正確義利觀:積極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深刻領會習近平同志關于外交工作的重要講話精神》,《人民日報》2013年9月10日。。所以,“人類命運共同體”與其它共同體的實體化結構如聯盟、國際組織等一樣,認同個體利益的重要性,并以之為行動底線,而非“義”先于“利”的強利他主義。不同之處在于,“人類命運共同體”追求義利平衡。
共通點四:“人類同命運”、全球化與相互依賴理論都以關系的程度與狀態為變量。傳統共同體因社會分工和工業主義而發展為聯合體,又隨殖民主義和國際分工而擴展為國際共同體。其間,共同體的內涵與空間發生改變,它們的關聯程度與表述也隨之分化。全球化是對進程的描述和解釋,及對行動者相處狀態與趨勢的寬泛概括;有著敏感性與脆弱性特征的相互依賴是國家間關系與全球化的狀態;“人類同命運”則表達了休戚與共的聯結景象,是人類之于國際社會的寄生現象,亦是國家之間的均衡共生。三者都以關系的緊密程度為變量。另外,結構建構主義在討論“無政府結構”變化時也提出了“共同命運”(40)參見[美] 亞歷山大·溫特《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秦亞青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39-342頁。,而且與“人類命運共同體”一樣,認為“共同體”是因第三方而建構的(41)A國與B國同受C國威脅,即便A與B之間不存在直接互動,但情景結構會促使二者產生“群我”認同,所以,這種“共命運”是針對C國而產生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情景結構是根據“全人類”(共同體主體)的第三方來界定的。,只是兩者在建構主體與客體的指向上有所差異,但都需要“‘倡導者’和/或‘認知共同體’(Epistemic Communities)的作用,這些人會率先界定行為體悟知自我的方式”(42)Peter M.Haas, “Introduction: Epistemic Communiti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cy Coordin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6, No.1, 1992, pp.1-35;[美] 亞歷山大·溫特:《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秦亞青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42頁。。
共通點五:“人類命運共同體”、全球化和相互依賴理論在“政治空間”(Political Spaces)(43)“政治空間”可被視為由政治關系與符號關系組成的動態網絡,那些關系直接或間接地受地理環境的影響。簡言之,政治空間就是空間與社會互動的產物。參見Orit Gazit, “A Simmelian Approach to Space in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Theory, Vol.10, No.2, 2018, pp.219-252。上重疊。“現代性”的互動模式構成新的互動網絡與制度化均衡及其控制機制,推動全球化,破壞了舊的政治共同體的內部構型與外部互動模式,宗主型或帝國型等級關系轉向主權平等關系(44)全球化與現代性之間的關系定性有三種:第一,全球化是現代性之結果;第二,全球化是現代性之終結;第三,全球的多元現代性或者全球的同質現代性。觀點各異的核心原因在于學科和分析框架的差異。本文從國際政治學視角出發,采用全球化是現代性之結果的觀點,理由為:第一,現代性具有“當下”的時間意義。當下的全球化是由西方主導的,其規則制定反映的是現代性的思維與行為方式,因而這是西方現代性的全球化。第二,雖然全球化進程先于現代性的出現,但現代性作為全球化的動力,塑造了當下的全球化以及全球秩序。第三,國際政治關注的是沖突與和平的問題,其核心為利益。圍繞利益的競爭與分配,實踐與主流理論充斥著西方的現代性理念。第四,國與國之間構成的系統是強調國際制度與規范作用的國際社會。通過權力推行和話語塑造,西方使它們的國內制度外溢,成為指導和約束國家間互動的國際機制。正如吉登斯所言,現代性制度與全球化制度相對應。第五,由全球化內在張力引起的“碎片”現象雖不可忽視,但只要全球秩序中起決定性作用的主權原則、大國政治原則、均勢原則未變,那么,“后現代”就遠未到來,至少在國際政治領域暫時還不能將全球化視為現代性之終結。第六,無論是多元還是同質,都是西方把持著關于現代性的話語權。即便如英國學派的赫德利·布爾那般,提出要考慮文化的多樣性,吸納異質文化,但其本質仍是以西方為中心。因此,植根于現代性理念,西方會根據現實變化和自身利益需求來重塑全球化。例如,前些年美日歐提倡新的共同市場,便可視為試圖重塑全球化的案例。綜上所述,全球的價值觀念與制度的西方化正是全球化作為現代性后果之表征。,這是國際政治成型的政治與法律基礎。共同體概念也溢出國界,形成聯盟、國際組織等國際共同體(45)聯盟與國際組織的基礎是共同利益與價值規范的認同,它們與共同體的構成要素基本相同,所以是國際共同體的實體化。。全球化深入發展后,國際關系的主體、內容、性質、目標繼續變化,逐步凸顯國際政治經濟與國際機制的重要性,使國際政治轉向世界政治。復合型相互依賴正是該時期的特點。國際共同體也從政治功能向道德功能回流(46)有關國際共同體道德功能和政治功能的論析,參見Barry Buzan and Ana Gonzalez-Pelaez,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fter Iraq”,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81, No.1, 2005, pp.31-52。,如聯合國從安全機構發展為包含經濟、環保等在內的綜合性組織。之后,全球化又引出新的政治空間,即全球政治。“人類同命運”的愿景正是以之(及“全球主義”“全球性”等相關概念)來觀照的。這看似是“國內政治→國際政治→世界政治(全球政治)”的發展脈絡(47)學界對“世界政治/世界主義”與“全球政治/全球主義”兩對概念的認識存在分歧,有的認為不同,有的認為相同。本文采用后者的觀點,只是引文中有將兩者區分的內容。,其實不然。全球主義是“松散靈活的政治路徑,它強調世界的物質性統一(Oneness),并尋求在世界范圍內重組國際關系”,但這“不意味著忽視其它政治空間”,反而強調不同政治空間之間的聯系(48)Or Rosenboim, “State, Power and Global Ord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33, No.2, 2019, pp.13-15.,所以不難理解為何中國官方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表述是國家中心主義的。正因為它是涵蓋國內、國際、世界、全球四種不同政治空間的政治愿景(49)有觀點認為,世界政治與全球政治其實是可等同的,也有觀點認為兩者是有差異的,本文不涉及對它們的概念辨析,兩者可相互替換。但部分引文是將它們區分開的,因此,該部分引文仍按原文進行區分。,故而“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復合型“國際共同體”。
共通點六:“人類同命運”、全球化和相互依賴理論對全球政治有認同感(程度各異)。社會學的全球化理論包含對全球政治的關注。這不僅是因為全球化對于“社會”來說具有時空假定,也是因為全球化問題需要全球意識探究全球制度與機制的可能性。政治哲學對此也有相關思考(50)趙汀陽:《從國家、國際到世界:三種政治的問題變化》,《哲學研究》2009年第1期。。相互依賴狀態是全球治理的成因,其理論是關于世界政治的機制化研究。它決定了國家間的報償結構,是國際合作與制度運行的前提。盡管新自由主義是對現實主義理論的補充,但重視跨國現象無疑提高了“全球性”的地位。“人類命運共同體”自不必說,官方的“全球性”措辭和學理上的“全球主義”內涵都映射出它以“全球政治”為發展目標。“人類同命運”則通過“種”“類”之別揭示人的動態性與后天特征(51)參見高清海《“人”的雙重生命觀:種生命與類生命》,《江海學刊》2001年第1期。,體現了“人類中心”的價值取向及重視國際法治的“全球性”發展。
總之,中西方皆對“國家中心”有改良愿望(52)不同政治、理論和意識形態立場的學者,都因接受全球視角的政治秩序而被稱為全球主義者。他們都認為,全球性是世界政治的一個有意義的條件,并提出調整國際秩序的計劃。參見Or Rosenboim, “State, Power and Global Ord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33, No.2, 2019, pp.1-28。。“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是中國吸收西方知識提出的方案。它雖然超越國家領土疆界,但不以損害國家主權與利益為前提;也非世界主義那般追求政治價值同一,而是以治理功能為導向。盡管“人類命運共同體”在意識形態上有或明或暗的規范立場,但不是“一種連貫的意識形態”(53)“For an Account of How Global Thinking Embraced Neo-Liberal Economic Views”,參見Quinn Slobodian, Globalists: The End of Empire and the Birth of Neoliberali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8。。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引用的“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54)《禮記·中庸》,載《習近平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表60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http://news.cnr.cn/special/hpgc/wz/201406/t20140628_515747057.shtml,2019-05-12。,“人類命運共同體”展現出尊重多元與平等差異的包容思想,是功能性與動態性的全球政治愿景。它與追求同一的自由國際秩序不同,而是主張“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55)《孟子·滕文公上》,載《習大大博鰲講話引經據典:“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http://news.cnr.cn/native/gd/20150328/t20150328_518159151.shtml,2019-05-12。的多元共生。當然,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鑒而豐富,但要以“移情”(Empathy)為“相互理解”的基礎,同時還需“共性”而使“移情”生效。如果任何事都可以用“人類”去賦予意義,那么這些由“人類”充分共享的東西就能使理解成為可能(56)Isaiah Berlin, 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 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London: Pimlico, 2003, p.60.。
上述內容對于中西方都可以視作“共同理解”。由此可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立論基礎與本體論是“人類”。正因如此,無關乎國界、民族、文化等差異,這樣才能發掘人的“類屬性”所共通的理解。當然,共通點肯定不止這些,此處僅為芻議。另外,也需要注意一些看似共通但實際卻在理解上存在相當大差異的概念,如“天下”能否指向“全球”或“世界”。
(三)“天下”為何不利于構建“共通的意義空間”
“天下”通常會包含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話語解讀中。但能否把它運用到國際傳播領域,仍是一個值得商榷的議題。
以“天下觀”“天下主義”“天下性”與“全球觀”“全球主義”“全球性”的比較為例,趙汀陽認為,“天下觀”是以世界為整體政治單位,天下體系是使世界成為政治主體的世界體系。從“天下”去理解世界,就是以世界為分析單位;天下體系則是一個基于存在論理由而與價值觀無關的世界,是以共在存在論為基礎的世界體系,而全球政治是新天下體系整個政治概念的理論基礎(57)需要指出,趙汀陽認為世界政治等于全球政治。參見趙汀陽《天下觀與新天下體系》,《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9年第2期。。“全球觀”不僅描述空間規模,也同樣把世界視為“單一整體”。“全球性”則指涉“全球化的特征;多元性、整體性;特別是具有世界性的包容度、覆蓋面或相關度的特質;(潛在的)全球一體化、行動、影響(特別是在商業和金融領域)”(58)Rens van Munster and Casper Sylvest, “Introduction”, in Rens van Munster and Casper Sylvest, eds., The Politics of Globality since 1945: Assembling the Planet, Abingdon: Routledge, 2016, pp.2-3.。顯然,“天下”與“全球”都有著相似的規范特征,即視地球為“一體”的物質性認知構成人類活動的重要條件(59)Or Rosenboim, “State, Power and Global Ord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33, No.2, 2019, p.13.。但從歷史發生學來看,它們的生成路徑與根本屬性是不同的。而且,歷史現實的“天下”在國內外史學界已形成“共有知識”(60)關于古代中國的天下研究及學術論爭,本文不再贅述,相關研究參見陳尚勝《朝貢制度與東亞地區傳統國際秩序》,《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5年第2期;陳尚勝《試論中國傳統對外關系的基本理念》,《孔子研究》2010年第5期;陳尚勝主編《中國傳統對外關系思想、制度與政策》,山東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陳尚勝《中國傳統對外關系研究》,中華書局2015年版;葛兆光《對“天下”的想象——一個烏托邦想象背后的政治、思想與學術》,http://www.aisixiang.com/data/92884.html;葛漢文《武力與道義:周人謀取天下的大戰略》,《國際政治研究》2019年第4期;陳玉屏《略論中國古代的“天下”、“國家”和“中國觀”》,《民族研究》2005年第1期;何新華《試析古代中國的天下觀》,《東南亞研究》2006年第1期;[日] 渡邊信一郎《中國古代的王權與天下秩序》,徐沖譯,中華書局2008年版;William A.Callahan, “Chinese Vision of World Order: Post-hegemonic or a New Hegemon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10, No.4, 2008, pp.49-61;陳赟《天下觀視野中的民族-國家認同》,《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05年第6期;[日] 安部健夫《中國人の天下觀念》,載安部氏《元代史の研究》,附錄一,東京創文社1972年版,第425-526頁;Benjamin I.Schwartz, “The Chinese Perception of World Order”, in John K.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266-288。,而政治哲學的“天下”其實是接受“元史學”范疇,有“杜撰”之嫌。
在概念的確定性上,中華民族先賢使用的“天下”概念與“國家”概念的內涵是同一的,基本特征是一國邊界(際)之內的事。古代也沒有現代人的“世界觀”。“天下”成為一個普世概念,變得無邊無際,這是現代人的話語體系。把古代話語與現代話語混雜在一起,不僅發生時空錯亂,而且發生內涵混亂。傳統上,先賢是用“天下”來表述“國家”內部,用“四海”來表達“國外”、超越“國界”的各國。荀子曰:“四海之內若一家。”(61)《荀子·儒效》:“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此外,還有“四海為家”“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四海翻騰云水怒”“五洲四海”等話語,都是講述超越“國界”之事。
然而,學者們往往在追求“天下一家”、國際新秩序等各個層面上使用它,卻忽略了一個問題,即歷史敘事與文學敘事中的“天下”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有著強烈的現實主義色彩,而且是基于物質基礎之強大和文化觀念為他者所崇拜,所以與葛蘭西的“霸權”概念相同(62)葛蘭西將霸權看作不僅僅是建立在強力的基礎上,而且也是建立在文化優勢之上的權力體系。參見[美] 佩里·安德森《霸權之后?——當代世界的權力結構》,海裔譯,《文化縱橫》2010年第1期。;后者則是一種道德理想,即無外、無他、普世平等的大同愿望。哪種詮釋更重要,這里不予評判。畢竟就概念本身來說,能夠觀照現實是必要的,但道德追求也應有一席之地。不過,至少就部分史實和中國傳統政治話語而言,“天下”是中華帝國自詡為核心的東亞秩序,而“天下觀”則是“華夷觀”的某種延伸。因此,西方有不少學者認為,“天下”話語有著規范例外論的隱喻,即把中國置于世界之巔(63)Ban Wang, ed., Chinese Visions of World Order, Tianxia, Culture and World Politics, Durham, NC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7; Mingming Wang, “All under Heaven(tianxia)Cosmological Perspectives and Political Ontologies in Pre-modern China”, 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 Vol.2, No.1, 2012, pp.337-383; William A.Callahan, “Chinese Vision of World Order: Post-hegemonic or a New Hegemon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10, No.4, 2008, pp.49-51; Maximilian Mayer, “China’s Historical Statecraft and the Return of Histor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4, No.6, 2018, pp.1217-1230.。顯然,這種認識和解讀已經偏離中國傳統“和”文化的內涵,背離了“人類命運共同體”倡議、不同文明和諧共處和不同文化平等交流合作的初衷。
因此,“天下”僅作為純粹的空間單位、地理概念,體現為一種整體主義方法,這是可以接受的;作為當前人類共處天下、同命運的描述,也是正確的。但如果要將之視為一種秩序觀,那就需要甄別這是歷史現實的“天下”還是理想社會的“天下”,是中國的“天下”還是人類的“天下”。顯然,這在國際社會產生了誤讀。可見,囿于自身認識而忽略或不夠重視“他者”是否接受的單向認知方式,會導致“共通的意義空間”的匱乏。這既難以避免“人類命運共同體”被誤讀,也無助于其國際傳播。
所以,“天下”雖是極具發展潛力的元概念,但既然目前是有爭議性的,那就應該謹慎使用,甚至還要主動地、嚴謹地對其加以論證和釋疑(64)必須聲明,本文只是從國際傳播效果來判斷,“天下”暫時不應置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內涵中,那樣不利于塑造中西方“共通的意義空間”,因為顯然中西方乃至中國學界內部對“天下”的認知也存在較大分歧。但是,本文認為,對“天下”的創新研究是一項極具學術價值的工作。這很可能成為中國提出原創性“新世界主義”的契機,能夠為國際社會提供世界意義的“現代中國思想”。這項研究議程正在進行中,對“天下”本身的內涵也亟待研探。例如,任曉就指出,從“新世界主義”而言,“天下”應進行轉化性創造,并“剔除上下尊卑”的成分。參見任曉《論中國的世界主義——對外關系思想和制度研究之二》,《世界經濟與政治》2014年第8期。。至少從國際傳播而言,概念內涵模糊必然會影響傳播效果。如果不加辨析地引用爭議概念,可能會削弱中國的國際話語權,也不利于中國傳播自身的價值理念。例如,“命運共同體”的一系列子概念——“雙邊命運共同體”“周邊命運共同體”“亞洲命運共同體”“亞太命運共同體”等,就容易使西方聯想到以中國為中心、呈同心圓狀的差序格局。與之類似的格局在歷史中被定義為“天下”,并形成包含“我他”“內外”“華夷”“尊卑”的政治秩序(65)葛兆光:《對“天下”的想象——一個烏托邦想象背后的政治、思想與學術》,http://www.aisixiang.com/data/92884.html。。另外,由于理想“天下”尚未解決誰是制定規則的“大家長”的問題(66)[法] 雷吉斯·德布雷、趙汀陽:《兩面之詞:關于革命問題的通信》,張萬中譯,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所以歷史“天下”的霸權色彩和理想“天下”的不確定性與模糊性使國外學者質疑“命運共同體”是“誰的命運和誰的共同體”(67)Ruben Gonzalez-Vicente, “The Empire Strikes Back? China’s New Racial Sovereignty”, Political Geography, Vol.59, 2017, pp.139-141.。事實上,已有學者提出“天下理想轉向新世界主義”的觀點,以此來更為明確地擺脫“天下”的霸權隱義(68)劉擎:《從天下理想轉向新世界主義》,《探索與爭鳴》2016年第5期。。
如果非得使用“天下”概念,那么如何準確地使用它將是極為關鍵的。否則,西方基于思維慣性和歷史敘事,會懷疑中國提倡“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意圖所指。當然,它作為學術爭鳴是極好的,可作為“政策話語”而言,進行國際傳播還為時尚早。只是目前似已約定俗成,恐難遽改。
四、研究啟示與展望
總體而言,“人類命運共同體”無論是在實踐還是在學術層面都進展頗大,但目前似乎陷入價值研究扎堆的怪圈。因此,為了使其國際傳播更為順暢,被接受度更高,“人類命運共同體”研究應該做到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成為一項開放性研究。如果是閉環式研究,那就是高掛“話語溝壑”“理論主權”,將“他者”排斥在外。如此,與其倡導的包容性是相悖的。而且,封閉狀態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研究,恐怕會出現如自由國際秩序那樣的價值物化問題。這也是與中國的“和”文化相悖的。另外,學科層面亦如此。僅從中國傳統文化或馬克思主義進路進行解讀,其國際受眾面是有限的。“人類命運共同體”與各學科應該是互構關系,而不是單向構建。它不是某個學科或領域的專項研究,而是要聯通各學科的智識,增強知識的有效性與可行性。所以,應該注意中西馬的結合研究(69)國內已有學者注意到這個問題。參見趙可金、馬鈺《全球意識形態大變局中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國際論壇》2020年第2期。,更要注重實證主義以提高其學理性,并使價值導向研究轉變為實踐導向、制度導向研究,以期突破“人類命運共同體”研究的瓶頸。
第二,以“人類”為主體去構建全球性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雖然是“人類中心”,但也包容“國家中心”。如果沖擊或消解“他者”的價值內核,那就會刺激到“我們是誰”的共同體的核心問題。這會給傳播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增加阻力,而且還影響到中國的對外戰略與本土國際關系理論的創新。中國應該持“人類中心”思維,將國際傳播重點置于國際社會,而非與美國進行“話語競爭”“話語對抗”的宣傳戰。但這不代表要向美國示弱,而是要從“人類中心”視角出發,使中國對外傳播的客體多元化。在周邊外交中,發揮更大的靈活性,將對美國際傳播納入對國際社會的傳播中,盡量避免“話語沖突”。
第三,重視“共通的意義空間”的塑造和“守門人”(Gatekeeper)的作用。傳播的具體手段與方式及其各種理論模型的研究,本質上是一個技巧性問題,它講究的是宣傳策略。“人類命運共同體”國際傳播的根本問題在于傳播本身,也在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話語研究。因為在國際(政治)傳播中,話語的中介變量與干預變量是“共通的意義空間”的來源,它們是決定傳播效果的原初因素。只有“共通的意義空間”得以實現,國際傳播才可能有效。不然,哪怕宣傳策略再高明,一旦缺乏共通性,那么“我”與“他”之間的理解將會變得困難。首先在認知維度上就會阻斷,進而也就無法上升到行動層面。因為缺乏“共通的意義空間”的國際傳播不僅是無效的,還可能導致“我”與“他”之間發生價值沖突(70)傳播效果中的“價值形成與維護效果”是涉及價值判斷的。傳播功能是用輿論去引導受眾形成新價值與新規范。它是工具,但不能決定有效性與可信度。作為社會交往互動的實踐方式之一,倘若傳播無法以“共通的意義空間”為前提,那么連“環境認知效果”這關都過不了。所以,“守門人”同樣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國際傳播非常重要。它影響著信息本身的可信度,是一種篩選機制。。所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研究應該跳出思維定勢,與西方文化、思維、理論結合起來進行解讀,使之更易于理解與接受,從而塑造和擴大“共通的意義空間”,促進國際傳播。這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另外,“守門人”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國際傳播也非常重要。它不僅指涉媒體人,同樣也包括國內學者。后者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研究影響著傳播過程的信息篩選機制,更決定著信息的可信度。
第四,要求中國學者在開放視野、中西方對話中探尋答案。在理論構建上,也需要注意中西方理念的取舍與對接、案例選擇的多元性與平等性,從中國與國際社會的聯動視角發展“中國學派”:既要有主體性、原創性,也要有全局性、統合性;既要避免理論溝壑與知識論主權思維,也要在構建“中國學派”的同時,思考如何形成哲學社會科學的“中國方法”。
所謂“中國學派”就是廣義上的“理論”。后者泛指發軔于哲學思辨的“解謎工具”(71)Thomas S.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pp.35-42.。它不單指稱探索因果規律與變化機制的解釋性(科學性)實體理論,同樣也包括構成性(哲學性)理論,即哲學范疇的方法論探索。要建設、發展“中國學派”,理應兩者兼備。換言之,“中國方法”也需要在場。任曉也指出,“‘中國學派’的社會科學應發展出自己的方法路徑和方法自覺”(72)任曉:《走向世界共生》,商務印書館2019年版,第198頁。。例如,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發展雖由現實問題推動,但其實體理論的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作為“方法工具”,皆由哲學社會科學提供(見圖2)。所以,“中國學派”不僅要構建實體理論,更要在本體論、認識論與方法論上創新普世性知識。
在實體理論的構建上,秦亞青通過考察中國國際關系現有理論成果,提出“文化塑造社會科學理論”的命題,認為文化要素構成社會科學理論的內核(73)秦亞青:《文化與國際關系理論創新——基于理性和關系性的比較研究》,《中國社會科學評價》2019年第4期;秦亞青:《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發展與貢獻》,《外交評論》2019年第6期。。然而在涉及“中國方法”時,“中國學派”更多是以本土特色的思維方式,如“辯證法”“關系性”“一物兩體性”“和合主義”等“方法論雛形”,作出籠統且模糊的表述,未能明確一種本土的哲學社會科學方法論(74)本文在此提供一點想法,或能形成對構建“中國方法”的啟示,即有中國特色的“公共性哲學”“類哲學”都在探索“個體與公共”“主體與客體”的關系和相處模式,也都在思考如何將個體與整個人類發展內在統合起來,從而構成“類利益”。以此為方法論,或許能給關系理論與共生理論的規范研究提供新論點。比如,通過“公共性哲學”與“類哲學”分析關系如何互動,互動中又如何構建“公共利益”。參見郭湛等《公共性哲學——人的共同體的發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版;高清海《人的未來與哲學未來——“類哲學”引論》,《學術月刊》1996年第2期。。所以,本文以“理論的文化塑造論”為基礎,進一步提出假設,即構建有地方文化印記的社會科學理論,需要相應的社會科學方法論,而后者由反映該文化印記的哲學社會科學所提供。雖然暫時不能斷言此拙見是“真問題”,但從美國特色哲學——實用主義對構建社會科學范式的意義來看(75)趙鼎新:《從美國實用主義社會科學到中國特色社會科學——哲學和方法論基礎探究》,《社會學研究》2018年第1期。,似有幾分道理。在國際關系理論中,也可以發現實用主義身影。巧合的是在實用主義的“分析折中主義”(76)[美] 魯德拉·希爾、彼得·卡贊斯坦:《超越范式:世界政治研究中的分析折中主義》,秦亞青、季玲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誕生后,國際關系理論似乎踟躕不前,“國際關系學”也越走越窄,變得輕理論而重即時效果,只講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圖2 哲學社會科學與西方國際關系理論
由此可見,哲學范疇的方法論對社會科學的發展影響很大。所以,“中國方法”的再明晰與再考究及其發展,或許能夠成為“中國學派”的理論增長點(77)目前,(新)天下主義似乎是將“中國闡釋學”作為構建理論的工具,但本文不作相關探討。有關“中國詮釋學”的內容,參見湯一介《論創建中國解釋學問題》,《學術界》2001年第4期;張江《“闡”“詮”辨——闡釋的公共性討論之一》,《哲學研究》2017年第12期;干春松《中國闡釋學傳統及轉向》,《中國社會科學評價》2019年第1期;朱孝遠《中國世界史闡釋學的構建:路徑與方法》,《中國社會科學評價》2019年第1期。,即不僅能進一步構建與完善相關實體理論,也能夠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扎實可靠的學理基礎,避免被西方理論所消融。只有如此,方能與西方的本土知識進行平等對話,在思想交流、碰撞、較量中深度發展“中國學派”,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