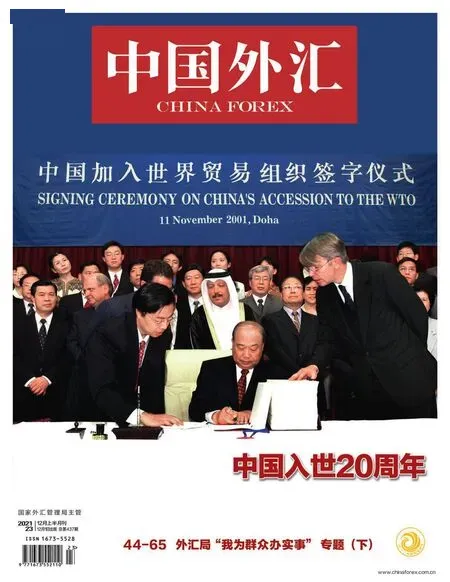雙向投資推動中國融入世界
文/周密 編輯/孫艷芳
世界貿易組織(WTO)不僅是全球最大的多邊貿易平臺,也對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活動有著直接和明顯的影響。跨國公司在WTO所創造的環境中將市場內部化,實現資源更有效的利用,以及生產、服務能力的提升。更為重要的是,WTO所推動的最惠國待遇、國民待遇和透明度等基本原則,為跨國公司以公平的方式進入其他國家的市場創造了條件。我國自入世以來,不斷學習國際規則,全面履行承諾,吸引了全球跨國公司的進入,也為我國企業的全球化提供了充足的信心,以雙向直接投資促進了我國融入世界的進程,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提供了保障。
市場持續擴大開放,吸引外資在華穩定發展
利用外資一直以來都是我國對外經貿工作的重點,并通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設,為外資在華發展提供穩定和成本有吸引力的投資環境。加入WTO之后,我國按承諾多次修訂了與外國投資直接相關的“外資三法”,為外商以合資、合作或獨資在華經營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保障。這些法律的修訂,減少了外資企業需要將生產的產品出口國際市場的約束,增加了企業在用匯方面的渠道。與此同時,按照國際通行規則為保障勞動者利益建立了工會組織,為企業在原材料、燃料等使用上從國際、國內市場自由獲取提供條件。
此后,“外資三法”修訂為《外商投資法》,外商準入負面清單一直在持續改進,中國以立法、執法、司法和行政管理等多渠道優化營商環境的努力也一直沒有停止。其中,對外商投資負面清單的管理模式不僅為當前的外商投資提供了清晰明確的準入條件,而且確定了未來更為開放的投資環境。這些調整和修訂,不僅保障了在華跨國公司可以與本地企業進行更為公平、合理的競爭與合作,也更堅定了企業通過持續投資不斷擴大本地供應鏈網絡的信心。
外資的行動表現在數據上。乍一看,從2001到2020年,按照聯合國貿發會議的《世界投資報告2021》的數據,中國的外資流入量似乎并不大。與2001年的468.8億美元相比,2020年外資流入量不過為1493.4億美元。平穩的直線似乎顯示外資流量的增速不快,年均增速為6.3%。但是,把中國外資流入放到全球來看,就顯得不那么簡單了。在同樣的時期,全球外資流入量年均增速為1.4%,而歐盟、美國、日本這些經濟體的外資流入量分別出現了-5.4%、-0.1%和2.6%的年均變化率。20年來,除2009年(-13.2%)、2012年(-2.3%)和2016年(-1.4%)的外資流入量出現比上年下降外,其余17年我國的外資流入均保持了增長。在全球外資流入量大幅波動而中國表現穩定的情況下,中國外資流入量的全球占比則從2001年的6.1%增加到了2020年的15.0%,全球排名逐漸從第六位上升至第一位。當然,也應該看到,2020年我國的外資流入占比的增加有著較為特殊的背景,疫情下的美、歐、日的外資流入量分別同比下降了40.2%、72.9%和29.5%,這更顯出外國投資者對中國的青睞與信心。
伴隨中國逐步實現從全球產業鏈供應鏈上的一個環節向著全面融入甚至引領全球經濟的轉變,外資在華發展的動力在20年間發生了明顯變化,對市場的把握和響應也顯著提升。入世伊始,在華外資企業大多只將中國作為其生產和制造基地,為其全球化的網絡提供產能。但伴隨互聯網的興起,電子信息產品的生產自新世紀之初逐步成為跨國公司追逐的熱點,中國豐富的人力資源和優惠的政策吸引了外資的進入,韓國三星電子、國際商用機器(IBM)和諾基亞成為當時中國最大的3家出口商;同時,在華跨國公司的出口額也占據了中國出口總額的半壁江山(51%)。伴隨時間的推移,中國的市場更加開放,入世承諾逐一兌現。在WTO多哈回合談判受挫的情況下,中國并未坐等其他國家開放市場,而是在包括汽車制造的一般制造業,以及金融在內的諸多服務業領域主動敞開大門,推出一系列超過入世承諾的開放舉措。外資企業則充分把握發展機遇,在中國市場實現共贏發展,推動中國產業升級和人力資源供給的優化。2020年,服務業的外商直接投資占比達到77.7%,高技術產業投資額同比增長11.4%,高技術服務業同比增長28.5%。而疫情沖擊下的研發與設計服務、科技成果轉化服務、電子商務服務、信息服務的外商投資額分別同比增長了78.8%、52.7%、15.1%和11.6%。盡管東部地區仍是外資的主要投資區域,但在遼寧、湖南、河北等東北和中西部地區也呈現出快速增長。
外部市場吸引力強,中國企業加快投資海外市場
與利用外資相比,我國的對外投資起步要晚得多,這也符合普遍的經濟規律。伴隨一國或地區以人均產出為代表指標的經濟實力的增長,其對外投資的能力和規模也會不斷提升,在努力實現雙向跨國投資平衡的過程中,會出現從凈流入向凈流出的轉變。在入世前的世紀之交,我國提出實施“走出去”戰略,鼓勵企業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通過全球化發展提升自身的國際競爭力。入世之后,我國政府在鼓勵和培育中國的跨國公司方面做了更多努力,主要集中于便利化、引導和規范。通過優化對外投資管理的方式,減少了企業對外投資流程時間和成本上的不確定性;通過發布《對外投資合作國別(地區)指南》、國別產業導向目錄及在企業社會責任、綠色環保等方面的指南,提醒企業在對外投資中應遵守的行為準則;通過完善全球經商參處和境內中介服務機構,提高企業融入東道國當地社會的能力。伴隨“一帶一路”建設的推進,我國企業對外投資在中國與東道國政府的協同下獲得了更快發展,成為推動相關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
與外資流入相比,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在2016年前保持了穩定增長,此后出現下滑。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的《世界投資報告2021》,2001年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為68.9億美元,2016年增加到1961.5億美元,后又逐漸降至2020年的1329.4億美元。與2001年相比,中國企業2020年的對外投資額實現了年均16.9%的增速,比同期的外資流入量快10.6個百分點。
伴隨企業國際化發展進程的推進,對外投資的行業也在發生變化。根據2003年我國第一次發布的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投資行業的前三位分別是制造業(27%)、批發零售業(19%)和商務服務業(14%);而2020年,排名前三位的分別是租賃和商務服務業(25.2%)、制造業(16.8%),以及批發和零售業(15.0%)。金融業和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占比分別為12.8%和6.0%,成為我國企業對外投資新的重要行業領域。

圖1 中國與全球的外資流入規模

圖2 中國與全球的外資流出規模
盡管增速更快,我國企業對外投資額的全球占比卻比較低。2001年的占比僅為1.0%,此后迅速提高,增速遠快于外資流入量占比的增速。2014年成為重要的分界點,當年中國外資流入量的全球占比為9.2%,在2001—2020年中,最后一次高于對外投資額的占比(9.0%);此后的中國對外投資按照全球占比計算,扮演著比外資流入中國更重要的作用。
雙向投資支持了我國跨國公司的發展,使其競爭力不斷增強,營業收入和利潤總額持續增加。中國企業與跨國公司在境內外開展廣泛協同,通過優勢互補與合作,支持了全球經濟的發展。2001年,上榜《財富500》的中國企業只有12家,美國和日本企業則分別達184家和104家。而2021年,中國(含香港)上榜公司數量連續第二年居全球首位,達135家;如果加上中國臺灣,我國共有143家公司上榜。而美國和日本的上榜公司數量,分別減少為122家和53家。截至2020年年末,金融領域的中國國有商業銀行共在美國、日本、英國等51個國家(地區)開設了105家分行、62家附屬機構,員工總數5.2萬人。其中雇用外方員工比例達94.2%。2020年當年,非金融領域的中國境外企業向東道國或地區繳納各種稅金總額為445億美元,年末企業從業員工總數361.3萬人,其中雇用外方員工的比例達60.6%。在疫情給各國經濟帶來嚴重沖擊的情況下,中國企業為東道國創造了大量穩定的就業崗位,成為東道國經濟保持穩定的積極參與方。

圖3 中國雙向投資的全球占比
展望未來,雙向投資將在開放進程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過去20年,我國從加入WTO中獲益,也積極以自身行動維護多邊經貿體系的穩定,為各種規則的發展發出中國聲音,貢獻中國智慧。跨國投資盡管在近年來連續受到經濟危機和疫情沖擊的較大影響,但在未來仍將是各國企業謀求后疫情時代全球經貿新平衡下發展的必然選擇。基于比較優勢的互利合作,仍是各國實現供需對接的可行方式。
各類經濟要素正在加快重新配置,以供應鏈重構為代表的跨國經濟活動正在改變各國間的經濟關系,而各主要經濟體在企業稅方面的共識也在很大程度上重塑著全球的經濟版圖。疫情后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為包括數據在內新的要素流動創造了平臺。作為開放合作的堅定支持者,中國與WTO成員積極推動數字經濟領域國際規則的制定,分享成功經驗,商討合理、有效的支持措施。
跨國投資活動是微觀市場主體行為和宏觀層面國家甚至國家間政策環境交互作用的結果。企業在尋求最大收益的同時也在盡量減少業務發展的風險。經濟活動日益復雜,一些國家對本國企業對外投資和外來投資者的態度也變得更為微妙。對于跨國公司而言,在哪個地方投資,與哪些伙伴開展合作,取決于其公司戰略。微觀的企業行為匯聚起來就構成了全球跨國投資的宏觀圖景。作為全球主要經濟體之一,中國理念與行動在全球治理領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關注,其中不乏以安全為由對投資行動的擔憂。在未來的發展階段,中國經濟的規模和體量將持續增加,高質量的經濟增長也需要建立更為完整、有效和恰當的跨國投資網絡,這需要包括政府、企業和相關機構的更多協同和相互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