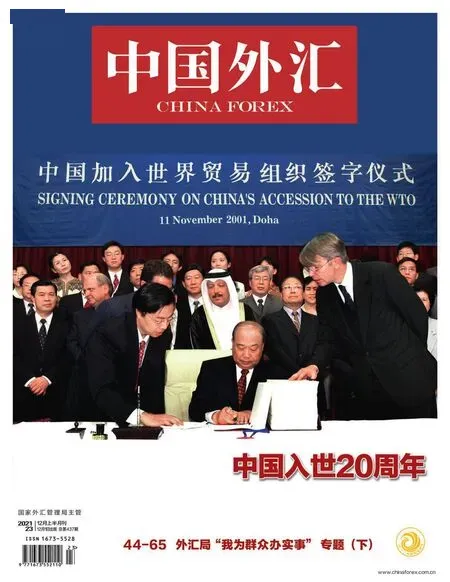從中概股回歸看我國資本市場開放發展30年
文/方云龍 劉佳鑫 編輯/張美思
20世紀90年代初,隨著滬深交易所的相繼建立并運行,我國資本市場建設發展的大幕徐徐拉開。相較于西方國家400余年的資本市場發展史,我國資本市場起步晚,發育尚不成熟。在我國資本市場發展的起步階段,考慮到國內資本市場上市條件的限制和企業自身發展戰略的需求,陸續有一批經營地及利潤來源主要在國內的企業選擇赴海外上市。這些公司被稱作“中概股”企業。近年來,國內資本市場日益成熟,釋放出了持續開放發展的強烈信號;與此同時,中美博弈升級,中美資本市場呈現局部脫鉤的趨勢。在外部推力與內部引力的雙重驅動下,中概股回歸意愿強烈。截至2021年7月30日,共有102家中概股企業退市并完成私有化。中概股從“西游”到“東歸”,既是我國資本市場不斷發展,進入更加開放、成熟階段的有力證明,也是進一步促進我國資本市場改革開放的重要機遇。持續推進我國資本市場規范化、法制化以及國際化建設,強化制度改革和市場監管,不僅是促進資本市場高質量發展的重要途徑,也是應對中美資本市場局部脫鉤挑戰的重要舉措。
中概股的“西游”與“東歸”貫穿了我國資本市場改革開放進程
經過三十載的發展,從建立初期的總市值僅23.82億元人民幣,到2020年總市值近80萬億元人民幣,從單一市場結構發展到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從開放創新舉措局部試點到全面放寬,我國資本市場在持續改革開放中不斷發展。尤其是科創板和創業板注冊制改革的順利推進,標志著我國資本市場以增量帶存量的改革實驗取得了階段性成功,拉開了我國資本市場全面改革的序幕。可以說,中概股的“西游”與“東歸”貫穿了我國資本市場的改革進程,為觀察和反思我國資本市場改革開放的動因、成效與不足,提供了一個重要視角。
階段一:我國資本市場起步探索與中概股首次“西游”(1990—2000年)。在起步探索階段,我國資本市場逐步形成了中央政府對證券市場統一管理的體制,并推行審批制的股票發行制度。此后,為了進一步發掘和支持優質企業,1998年年底我國頒布《證券法》,宣布股票發行實行核準制,推動我國資本市場進入規范發展階段。但對于處于起步摸索階段的資本市場而言,審批制和和核準制之下,發行條件和監管模式等方面都存在改進的空間,例如對上市公司要求高、審批時間長等。上世紀90年代,股份制改革促使部分大型國企在美國和新加坡等海外市場上市。上世紀90年代末期,受美國互聯網發展繁榮的影響,我國掀起了一輪互聯網創業熱潮。許多互聯網企業處于快速擴張的關鍵時期,對上市融資具有迫切需求。但由于互聯網企業具有高投入、短期內難以盈利的特點,并不能滿足當時核準制下A股主板的上市要求,相對而言境外上市的條件更為寬松,融資更為便利。在此背景下,一些互聯網企業選擇赴美上市。1999年中華網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2000年網易、搜狐和新浪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
階段二:我國資本市場穩步發展與中概股第二次“西游”潮(2001—2010年)。伴隨著我國經濟強勁增長,我國資本市場也在穩步發展與積極革新。與此同時,我國企業海外上市的需求也有所增多。一是對于國內具有高成長性的初創企業而言,由于其規模小、業績優勢不明顯,難以滿足當時國內資本市場的上市要求,海外上市仍然是其獲取資本支持的首選。二是鑒于國外資本市場相對A股市場相對成熟完善,出于獲取持續發展資金、對接國際標準推動企業制度改革以及深度參與全球經濟等考慮,許多國有大型企業奔赴海外上市。2000—2010年,我國共有129家企業赴海外上市,其中既包括攜程、百度、新東方等科技互聯網公司,也包括中石油、中航油、中國人壽等大型央企。
階段三:我國資本市場不斷革新與中概股“東歸”與“西游”并行(2011—2021年)。大量企業赴海外上市伴隨的是優質企業與金融資源的流失,這也成為我國不斷進行制度創新、加快建設更加開放的資本市場的催化劑。從2014年以來滬港通、深港通、滬倫通、中日ETF相繼落地,到2019年科創板正式開板,再到新《證券法》出臺,股票發行實行注冊制,我國資本市場邁入市場化、國際化的新征程。與此同時,赴美中概股企業也面臨著新形勢與環境。一方面,由于部分中概股企業存在虛假陳述等行為,自2010年年末納斯達克上市公司大連綠諾被渾水公司出具空頭報告以來,部分赴美中概股企業遭遇做空潮與信任危機,股價受到重挫,甚至最終退市。另一方面,我國資本市場發展預期良好,信息技術等新經濟市場發展迅猛,國內對此類企業的估值也持續走高。就當時在美交易的中概股而言,其對標在我國內地資本市場的市盈率近乎美國資本市場市盈率的4倍。因此,在較大估值差異的驅動下,2015年前后,中概股迎來了首次“東歸”潮。而國內監管也關注到本次具有套利動機的回歸,為保持國內資本市場的穩定,開始嚴格把關中概股回歸企業再上市。
近期,在中美博弈逐漸升級的背景下,美國資本市場對中概股監管趨嚴,中概股赴美上市審核更加嚴格,中美資本市場呈現局部脫鉤的趨勢。在外部推力與內部資本市場建設愈發完善引力的雙重驅動下,2019年以來,中概股迎來第二次回歸潮。區別于2015年以套利為動機的“東歸”潮,本次回歸主要以國家鼓勵和支持發展的行業以及一批優質的涉及到國計民生和我國產業全球布局的公司為主。
中概股回歸的方式、現狀與影響
中概股的回歸方式:兩個路徑與兩個市場
整體而言,中概股回歸的兩個路徑是私有化退市后再上市和保留上市地位二次上市(見圖1)。而中概股在回歸過程中,客觀上面臨著回歸中國香港還是內地市場,或者是先上內地還是先上中國香港的選擇。近期,兩地市場都加強了資本市場制度改革,優化上市規則,提升發行上市環節的效率,客觀上為承接中概股回歸鋪平了道路。

圖1 中概股回歸的主要方式
中概股回歸現狀:數量與結構分析
中國香港資本市場機制體制與歐美市場體系幾乎相同,因此,中概股回歸選擇中國香港市場的成本相對更低。截至2021年3月31日,已有13只中概股赴港二次上市,新募資規模2802億港元。從回歸結構看,已經回歸的中概股中,消費、信息科技、醫療保健等新經濟龍頭占比超過90%。從結構層面看,當前已赴港二次上市的13家企業中消費類有5家、信息技術類有5家、醫療保健類有1家。消費類占該13家企業總市值的89%左右(見圖2)。其中,阿里巴巴市值規模最大,交易最為活躍。

圖2 中國香港二次上市企業數量、市值與募資金額
內地市場方面,截至2021年7月30日,A股共受理了9家紅籌企業,且申報上市板塊均為科創板。從回歸結構看,這些企業主要分布在新能源汽車產業、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生物產業、高端裝備制造產業。其中,屬于“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的公司有5家。
中概股回歸的影響
中概股的回歸,對中國香港和內地市場都會產生積極作用。對中國香港而言,可以優化其經濟結構,提供多元化的發展機遇,鞏固其作為我國新經濟企業境外融資“橋頭堡”的地位;而對內地市場而言,中概股回歸有利于帶動內地資本市場制度的改進與優化,同時也改進了資本市場的行業結構,促使其更為多元化、更有代表性。
中概股回歸在產生積極作用的同時,也存在需要對沖的影響。一方面,美國作為全球的科技中心,其吸引力仍然強勁;但面對美國資本市場監管收緊的趨勢,部分新經濟企業海外融資壓力可能增大,影響我國資本市場雙向開放的進展。另一方面,中概股的回歸在一定程度上與全球化、國際化的概念相背離,在影響我國企業赴海外上市積極性的同時,還可能影響我國企業“走出去”戰略。因此,也需要積極采取對沖舉措,進一步擴大我國金融市場的雙向開放水平。
對資本市場通過制度創新承接中概股回歸的幾點認識與思考
中概股的“西游”與“東歸”貫穿了我國資本市場改革開放的進程。通過對上述歷程的梳理可以發現,伴隨著監管部門以與國際資本市場深度接軌為目標,不斷出臺新舉措、新方案,深化境內外資本市場互聯互通,我國資本市場日益走向成熟,創新性與包容性不斷增強。面對新一輪的中概股回歸潮,既要充分利用其積極作用,深化國內資本市場改革,繼續擴大內地在岸市場的高質量開放,更要未雨綢繆,健全證券監管、加強監管部門的跨境合作,積極應對中美博弈加劇環境下中概股回歸可能帶來的不利影響。
第一,健全證券監管,優化內地資本市場環境,繼續擴大內地在岸市場的高質量開放。2021年7月6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依法從嚴打擊證券違法活動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提出要加強中概股監管,明確境內行業主管和監管部門的職責,加強跨部門監管協同。如前所述,2015年的中概股回歸潮中,套利回歸是一個重要動因。內地資本市場對新經濟企業的估值溢價,往往會使中概股企業回歸后在短期內的股價迅速上漲,加劇內地資本市場的投機氛圍。因此,從嚴打擊證券違法活動,加強中概股回歸的監管并不是阻止其回歸,而是為了構建一個“有活力、有韌性”,更有利于優質紅籌企業發展的內地資本市場,從而加大對優質中概股回歸的吸引力。因此,應貫徹落實《意見》中的具體措施,進一步明確監管部門的職責,及時完善跨部門跨機構的聯合協作機制,健全證券監管,優化內地資本市場環境,打通優質紅籌企業境內發行上市的路徑,打消優質紅籌企業的回歸顧慮,繼續擴大內地在岸資本市場的高質量開放。
第二,充分發揮中國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獨特優勢,打造我國資本市場雙向開放的“橋頭堡”。中國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具有獨特的優勢和豐富的資源。近年來,中國香港市場“新經濟”聚集地已初具規模,諸如阿里巴巴、京東、網易等新經濟企業陸續在中國香港首次公開募股(IPO)。充分利用好中國香港市場的制度優勢,是促進我國資本市場雙向開放的關鍵舉措。當前,同全球較發達的資本市場相比,中國香港在對于科技股的吸引力、規范管理、成本費率、上市資格審查等方面仍具有一定差距。因此,中國香港應進一步優化上市制度,充分發揮背靠內地巨大市場的優勢,對標高標準、高度開放的國際IPO規則,逐漸形成多樣化且層次分明的上市標準,為差異化的上市需求提供支持;同時,進一步明晰退市規則,從重處罰證券欺詐,嚴刑峻法,設置多樣化的賠償機制,打造我國資本市場雙向開放的“橋頭堡”。
第三,全面推進資本市場退市制度改革,優化資本市場資源配置功能。退市制度作為資本市場的基礎性制度,對高效實現資本市場資源配置功能意義重大。回顧以往,我國股票發行由于上市要求高、審批時間長等因素使得上市公司的名額具有稀缺性,加之退市制度的不完善,使得殼股炒作現象頻發,擾亂了各企業間的良性競爭。同時,隨著注冊制的實施,企業上市渠道更加通暢,上市公司供給將會不斷增加。對此,需要同步完善與上市規則相配套的退市制度,進一步從頂層設計進行優化,對具體實施環節要嚴格落地執行,并與上市環節形成互動,以形成“有進有出、優勝劣汰”的良好市場生態。
第四,持續推進資本市場的市場化建設,為優質中概股回歸創造條件。我國資本市場制度的不斷創新,客觀上為中概股回歸鋪平了道路,提供了新的機遇。面向未來,我國應進一步推進資本市場的市場化建設,適度加大對外開放的步伐,逐步放開創新制度的適用范圍,為更多優質中概股的回歸創造條件,也為更多具有成長潛力的企業提供實質性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