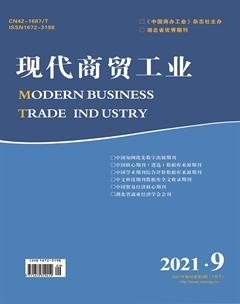共同體邏輯下網絡生態環境治理研究
張自強
摘 要:網絡輿情的治理一直都是網絡生態治理的一項重要內容。網絡輿情的產生具有相當大的社會現實因素,同時自身也具有濃厚的信息化色彩。對網絡輿情產生的社會原因進行分析,能夠為網絡治理提供借鑒思路。如今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同時,對于網絡空間治理的方式也需要發生深刻的變革。當下網絡生態治理需要拋棄傳統的單向度下政府治理模式,建立以政府、平臺和網民為主體的共同體結構,并明確和發揮各個主體的功能和作用。
關鍵詞:網絡輿情;網絡生態治理;共同體模式
中圖分類號:D9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1.09.067
0 引言
當前網絡生態環境治理需要從方法論上轉向現代社會矛盾的發現,并從源頭上認識矛盾,即契約論基礎上形成的基本共識。網絡空間作為社會治理的新興領域,對于政府行使公共權力提高政府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戰。網絡社會新契約則是伴隨網絡社會發展過程中不斷出現新問題的形勢下,由全體網絡社會的參與主體達成的行動原則和共識。網絡社會新契約旨在厘清政府、網絡平臺和網民之間的治理基礎和限度。
1 輿情學視閾下網絡輿情的結構差分
1.1 網絡輿情的社會基礎
在中國社會轉型復雜的輿論環境中,各種言論、思想和觀念相互碰撞和交融,呈現出輿論主體的分層化、內容的復雜化、表達方式的多元化以及訴求多元化的特點。社會熱點事件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不安因素。一方面是我國對于網絡空間規制的法律不夠完善。另一方面網絡虛假信息、網絡謠言、網絡水軍以及新興的自媒體讓給輿情治理的形勢更加復雜。但在中國高速發展和社會轉型的背景下,我國的社會輿論環境既符合輿情的一般規律,又具有國情下的一般特征。
網絡輿情的誘發在本質上是來源于現實社會沖突和矛盾,并通過互聯網加以宣泄的過程。現代社會中大量存在社會沖突、越軌行為等,這些因素幫助人們構成總體的社會鏡像,同時催生形形色色的輿情變化。在中國社會快速轉型的今天,不同的社會沖突和矛盾不斷地進行碰撞,為網絡輿情誘發提供了溫床。網絡輿情的產生需要能夠產生輿情的社會問題和矛盾,并且能夠激化到一定程度,這些因素就會成為輿情產生的“可燃物”。
1.2 網絡輿情偏差現象
輿情偏差現象在互聯網上體現得更加明顯,這是由于網絡社會與傳統社會相比具有更強的虛擬性、隱蔽性和滲透性等特點。曼紐爾·卡斯特認為網絡的形式將成為貫穿一切事物的形式,正如工業組織的形式時工業社會內貫穿一切的形式一樣。網絡社會是現實社會的一種新的存在,本質上是社會和個人生存和發展的利益需求場域的擴展。網絡輿情偏差出現的原因主要是互聯網傳播信息的特點所導致。
首先,互聯網規則意識缺乏。很長時間里網絡是“法外之地”的觀念先入為主占據了人們的意識理念。1996年約翰·P·巴洛在線發表的《虛擬空間獨立宣言》中稱,虛擬空間是創新、平等、公益的,永遠不受政府管轄。網絡社會完全擺脫了現實政治的困擾,摒棄傳統道德價值觀的束縛。即使當前我國網絡違法行為的法律規制已經相對完善,但事后制裁往往難以起到根本性和一勞永逸的作用,網絡守法意識的養成任重而道遠。
其次,群體極化現象在互聯網上的顯現。1961年James stone在驗證群體時發現:“如果群體內部成員意見比較保守的話,經群體討論后,決策會變得更加保守;相反,如果個人意見趨向于冒險的化,經群體討論后,決策會變得更加冒險”。這種群體極化現象則會誘發沉默螺旋機制。在互聯網上人們在表達自己的想法和觀點時,如果看到自己贊同的觀點,并且受到廣泛歡迎,就會積極參與進來,這類觀點越發大膽的發表和擴散;如果發現某一觀點無人或少有人理會,即使自己贊同也會保持沉默。那么在互聯網上決定信息傳播的往往是看對信息的贊同的多寡,這就造成了少數的真實卻難以傳播,最終淹沒在海量的互聯網信息中。
1.3 個體意識與群體意識的博弈
無論是現實社會還是網絡社會,個體和群體在進行信息傳播時都會帶有一定的主觀意識在其中。個體意識局限于個人的社會經驗與閱歷水平所共同影響的認知水平,自我意識水平越高,表達能力越成熟。在互聯網社會中“人人都是麥克風”,個體的表達自由得到前所未有地放大,但無限放大的個體意識會使得傳播信息的真實性、科學性難以保證。相反,在某些特定的網絡輿情中強大的群體意識會壓制個體意識的表達,導致個體意識的沉睡。以司法案件為例,當實現中發生的案件在網絡空間中被大量討論,那么以公共輿論為代表的群體意識和以法官、檢察官、律師為代表的個體意識,就會在司法判斷的結果上存在斷裂。
2 單向度邏輯下網絡生態治理的困境
2.1 主體的自利性
單向度思維的治理模式下,網絡空間主體存在強烈的自利性主張。作為網絡行為的施動方會最大限度的主張自己的“言論自由權”和“監督權”,而網絡行為的受動方會堅決捍衛自己的“隱私權”和“不受侵害的合法權益”甚至要求“被遺忘”的權利。網絡行為的施動方和受動方在網絡權利上存在一定的交互性,雙方的權利存在沖突和對峙。在自利性的價值導向下,雙方都對自身的權利不做出讓步,造成劍拔弩張的局面。同樣作為互聯網從業者,為減少經營成本和謀取利益而以“不代表本網立場”“海量信息無從審查”為由拒絕承擔責任。作為網絡管理者的政府部門,可能認為網絡社會秩序才是最根本,其他一切應當讓位。
2.2 糾紛解決機制虛化
單向度思維下各個主體在自身利益的驅動下,并不關注公共利益。我國在互聯網治理中對于糾紛解決機制大致可以分為三個不同層面,包括網絡用戶之間的協商、網絡平臺的監督、行政機關干預。在以往的實踐經驗中,網絡用戶之間的協商處理機制由于網絡矛盾的虛擬性,最終難以實現。網絡平臺監督也由于網絡服務經營者逐利性的特點而作用平平。同樣政府機關由于執法成本的原因,對于網絡監督難以實現常態化。格里·斯托克就指出,治理要偏重于機制并不必然依靠政府的權威,治理所要創造的結構和秩序不能從外部強加,而是需要各方主體進行有目的的互動。無論在理論還是實踐中,對于采取單向度思維進行網絡治理而形成的解決機制,無法解決網絡社會中的種種問題。
3 共同體思維下的網絡治理結構
3.1 共同體下的政府思維
控制與服務是政府在網絡空間中的雙重任務。政府作為網絡空間的管理者,能夠通過左右信息內容、信息分配等方式實現對網絡社會的控制功能。政府作為網絡空間的主要管理主體,承擔提供網絡空間良性運轉的責任。網絡空間屬于公共服務的范疇,同時也是政府網絡治理的最終目的。網絡給空間的失范現象表現為網絡犯罪、網絡侵權、網絡謠言、人身攻擊等。政府對網絡空間的控制主要是通過制定法律法規的形式實現,這種控制內容深入到網絡活動的方方面面,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網絡安全法》《互聯網生態治理規定》等。政府對于網絡空間管控的目的在于,在網絡空間的服務過程中產生一種全新的存在方式和表達方式,并且這種存在和表達方式能夠符合社會公共利益的需要,符合社會價值觀的整體方向。
服務型政府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網絡生態健康發展的必然要求。在網絡社會,減少政府管制行為,加強政府服務是網絡時代政府的職能選擇。在網絡社會里,人們對政府最大的需求就是從它那里獲得更多地服務。而政府的網絡服務功能首先體現在建立健全一個統一、公正、透明的法律制度和公共政策體系,能夠為網絡主體提供一個穩定的預期機制,為網絡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制度與政策環境。互聯網并不是“洪水猛獸”,相反是國家發展的“助推器”。
3.2 共同體下的平臺思維
網絡平臺是搭起網民與網民、網民與政府之間的橋梁,是網絡社會的基礎。從網絡平臺的性質上來說,網絡平臺是網絡服務的提供者具有很強的經濟目的。在當前的互聯網時代,網絡平臺的作用不僅僅是提供信息發布平臺,更是信息傳播者和監管者。互聯網提供了方便快捷的信息傳播,也讓網絡平臺的監管變得復雜且成本高昂。網絡平臺做到對于每一條信息進行審查,必然會使信息傳播喪失了及時性的基本要求和自身優勢。在共同體的治理模式下,網絡平臺與政府的關系變成一種合作型關系,網絡平臺建立跟帖評論服務治理機制就是以“落實主體責任,依法履行義務”的形式規定。
3.3 共同體下的網民思維
網民是網絡活動的主體,需要樹立主體意識和責任意識。網民要加強對于網絡共同體的認同感,積極配合政府進行網絡治理的各項決策。但認同感的建立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依賴于每一個網民自身素質的提升。在網絡治理中,網民永遠是治理的目的而非手段。現階段無論是作為正式性規則的國家法律制度,還是非正式下規則的公約,都是推動網絡健康發展的體現。
4 結語
網絡輿情是網絡治理的一個方面,通過網絡輿情的治理可以洞悉整個網絡治理的基本路徑。在網絡治理中單向度思維暴露出治理上的弊端,難以應對治理的需要。在網絡發展的新形勢下網絡共同體的構建對于網絡治理具有強大的理論導向作用。在網絡共同體下,國家、網絡平臺和網民作為共同體中的成員需要轉變各自的思維方式 ,發揮各自的主體作用。
參考文獻
[1]張蒙.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網絡輿情發酵機理研究[J].現代情報,2020,40(09):20-31.
[2]格里·斯托克,華夏風.作為理論的治理:五個論點[J].國際社會科學雜志(中文版),2019,36(03):23-32.
[3]趙孟營.從新契約到新秩序:社會治理的現代邏輯[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52(02):106-114.
[4]周輝.網絡平臺治理的理想類型與善治——以政府與平臺企業間關系為視角[J].法學雜志,2020,41(09):24-36.
[5]倉基武.新時代服務型政府建設路徑研究[J].攀登,2020,39(04):54-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