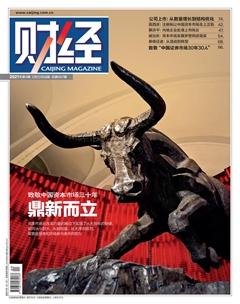闞治東:資本市場發展夢想照進現實,差距是努力方向
張欣培 祁佳妮

闞治東
在中國資本市場發展的30年間發生了太多的故事。他曾盛極一時,也曾跌入低谷。他是第一代證券公司老總中仍然活躍在資本市場上的風云人物。他就是被外界稱作“證券教父”的闞治東。
但對于“證券教父”、“證券猛人”這樣的稱呼,闞治東不以為然。他說,銀行出身的他更看重的是“穩健”,他更愿意將自己形容成“證券老兵”。
他是資本市場發展30年的見證者、親歷者,更是重要的推動者。1990年,闞治東創立申銀證券公司,后將萬國證券合并,成為申銀萬國證券公司總裁。而申銀萬國也成為當時市場上規模最大、盈利能力最強的證券公司。
而闞治東本人也創下了中國證券業歷史上的諸多第一:設立第一個證券交易柜臺;主承銷第一只A股、B股;發行第一張金融債券等。他還曾參與發起設立上海證券交易所。
但他在“陸家嘴事件”后黯然離去,此后創立了深圳市創新投資集團(簡稱“深創投”)。2002年,闞治東應深圳市政府邀請出任瀕臨破產的南方證券總裁,最后身陷牢獄之災。即便如此,闞治東依然未離開資本市場。2005年,他創辦東方匯富,再次締造資本傳奇,后者成為國內首屈一指的專業私募股權基金管理機構。
“早年資本市場的人和事已經烙印在我們這批老證券人的頭腦里,隨著時間推移,印痕越來越清晰,但我們永遠為這段歷史感到驕傲和光榮。”他說。
商場沉浮三十年,待浮華洗凈時回首往昔,闞治東對過往甚是從容;展望未來,依舊充滿期冀。在他看來,雖然中國資本市場發展早期遭遇許多坎坷與阻力,但曾推動市場發展的民間意志已轉化為了國家意志。國家這只“大手”牽引著市場走向繁榮,這是令他倍感榮幸之處。
“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必須要有強大的金融中心支撐它,才能使中國成為世界最強的國家。我希望未來世界上談起資本市場,是中國、美國和日本三大市場。”闞治東說。
證券市場能走到今天,是幾代人努力的結果,今天他們還在繼續為之努力。在資本市場建立30年之際,闞治東接受了《財經》雜志專訪,以中國資本市場改革親歷者的身份,講述了資本市場發展30年的那些歷史,以及新的期待。
市場發展從民間意志上升為國家意志
《財經》:資本市場發展30年,給您帶來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闞治東:我們通常以1990年上交所的成立作為中國資本市場改革的開端,但是在此之前,我們的資本市場已經存在了,有了證券公司、發行和交易。最早的股票飛樂音響在1984年就發行了。1986年,工商銀行上海信托投資公司靜安證券營業部就成立了。申銀證券、萬國證券和海通證券在1988年就成立了。
我感觸最深的是,大家越來越意識到資本市場在我們整個經濟發展中所起到的作用。發展資本市場已經從民間意志上升為國家意志,國家要堅定不移推動資本市場的發展,我很高興看到這個變化。

上海申銀證券公司前身——靜安信托投資分公司開設新中國第一個股票交易柜臺。
《財經》:資本市場發展30年,中國對外開放的力度越來越大,尤其是近兩年,如何看待中國對外開放的歷程?
闞治東:我們的資本市場確實取得了很大的發展,邁出了一些國際化的步伐。但是客觀來說,我們國際化的程度還有很大提升空間。即便和東京交易所相比還存在很大差距,但是差距不是壞事,差距就是我們努力的方向。我們要意識到有很多地方要學習、要反思。
當然,國際化過程也是一步步來的,不是一蹴而就。我們是當今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未來可能會成為第一大經濟體。因此,我們必須要有配套的金融市場。當然,這需要時間,需要各方面條件成熟才能去做,但是我們必須要有這樣的思想和目標。所以我認為,中國資本市場下一步的重點工作應該向加大開放力度、加快國際化進程方向發展。
《財經》:今年大家關注的一個話題是中概股回歸,美國加強了對中概股的監管,外界都在談論中概股的回歸潮,您如何看待這點?
闞治東:我相信現在很多中概股的企業是希望回來的,因為我們的市盈率和交易活躍度都很高,這是我們市場的優點,但是它們也有擔憂。比如螞蟻金服的IPO,最終被暫停,我覺得還是會給那些想要回歸的中概股企業帶來顧慮。
但是我認為,螞蟻金服暫停上市,實際上是國家對我們投資者的風險提示,我們現在用的“暫停上市”或者“暫緩上市”,不是“不能上市”。重大風險提示,要把這個道理解釋清楚,后面妥善處理,對中概股回歸負面影響可能會小一點。否則,會給那些要回歸的企業造成擔憂。當然,中概股回歸,我認為是一件好事,中國的好企業為什么不能在中國的交易所上市呢?
“我是證券市場的老兵,不是教父”
《財經》:在30年的發展歷程中,您經歷過輝煌,也跌入過深谷。您是少有的至今仍然活躍在資本市場上的早期證券人。從某種意義上講,您的經歷也是資本市場發展的縮影,您是如何看待這些經歷的?
闞治東:在資本市場,我們風光過,也做了很多值得回憶的美好的事情,當然我們也有坎坷。最重要的兩個坎坷,一是1997年我被免職。二是我本意是去南方證券救火,最終卻被誤解,遭遇牢獄之災。這些經歷確實是不愉快的經歷。但是我們更多的回憶是資本市場美好的東西。
經歷了這么多,心里肯定有落差。但是我還是比較樂觀。可能和我們這代人的經歷有關系。該讀書的時候我們上山下鄉,我當時到了東北農村,生活不僅艱苦,還會遇到很多困難。在困難面前,我總是相對樂觀一些。后來遇到的很多事情,我的心態都是不錯的。
《財經》:當時您本意是去南方證券救火,但最終南方證券還是走向破產,您也受到牽連。實際上您當時有更好的選擇,您最終還是去了南方證券,會后悔這個選擇嗎?
闞治東:這個沒什么后悔的,我們干這個事也是組織上叫我們去干的,而且組織讓我們干好了,我就覺得很榮耀。
這一觀念和現在的年輕人不一樣,年輕人可以有選擇余地,我們入黨時間比較早,大概在上世紀70年代初就入黨了,我們那時候有很強的服從組織安排的觀念。后來我的問題也得到了解決,所以我也感謝那一屆的證監會領導,沒有那一屆證監會領導極力幫我,可能我遭受的麻煩會更多。
《財經》:外界對您的稱號很多,“證券教父”、“證券猛人”,如何看待這些評價?
闞治東:這些稱呼是不同時期媒體對我的稱呼,像“猛人”、“教父”都是我們年輕時候的稱呼。“教父”這個詞在我印象中并不是個褒義詞。當年我們確實講了很多資本市場的課程,傳授我們掌握的賺錢知識,但是談不上是教父。所以到今天為止,我始終和大家說,我們就是證券市場的老兵,老證券人,老創投者,這幾個稱呼我們都能夠接受,其他的稱呼,都難以接受。
市場發展超乎想象
《財經》:您當年創辦了申銀證券,后來又合并了萬國證券,申銀萬國曾是那個時代的領軍者。證券行業發展了30多年,無論我們的券商數量、規模和實力都有了非常大的提高,有沒有超出您的預期?
闞治東:今天的資本市場發展確實超過我們預期,當年我們還把它作為一個夢,但是現在很多已經成為現實,這是超乎我們想象的。
申銀證券和萬國證券曾是上海最牛的兩家券商,彼此之間的競爭也非常激烈,兩者經常爭第一。但是如今回憶過去,我們都覺得是正面的,積極向上的,因為大家都在努力去做事情。當時我們就覺得野村證券非常厲害,所以想做中國的野村,當時對我們來說只是夢想,從來沒想到沒用多久野村的市值就被我們超過。
證券市場能走到今天是幾代人努力的結果,今天大家還在繼續為之努力。
《財經》:我們的券商數量已經百余家,頭部券商優勢十分明顯,未來中國券商的競爭格局是什么?中小券商是否也可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闞治東:首先,我認為每個行業都一樣,都有第一方陣,必然也有第二方陣和第三方陣。從很多國外的證券發展歷史可以看出,僅有少數幾家處于第一方陣,更多的都是排在后面的。所以,未來中國的證券格局也不可能全部在第一方陣,對于券商發展的模式,會有全牌照的,也會有專注某項業務的券商,不圖大,只圖精。每個券商都可以找到適合自己的生存模式。
未來,第二方陣的一定會向上努力,積蓄力量,發展壯大,躋身第一方陣。
在努力的同時,憑借合并、兼并的方式壯大。合并也是金融機構壯大的最重要的方式。
《財經》:注冊制的推出給券商帶來了新的機會,您如何看待注冊制對券商的影響?
闞治東:注冊制給兩個交易所帶來的影響是比較大的,過去交易所競爭有限,但是注冊制下,二者的競爭性會加大。我認為只要是良性競爭,就是有利的。因為只有競爭才能提高我們的效率,提高我們的服務水平,才能增加我們和世界資本市場競爭的能力,中國資本市場未來必然是和世界大的資本市場競爭的。
但是注冊制對證券公司本身來說,是加重了證券公司的責任。注冊制對中介機構的要求大大提高了。會計數據不能造假,歷史數據不能造假,證券公司做保薦人,材料要嚴格審,所以責任加大了。
《財經》:您認為創投募資越來越難,為什么募資難成為了行業普遍現象?
闞治東:募資不是越來越難,是現在募資比過去更難。我認為,首先大家對創投業的了解是不夠的,創投行業里面確實有很多誤區,造成普通投資者覺得創投業太亂,水太深,頻繁爆雷。我們過去是依靠第三方募資,現在第三方募資頻繁爆雷,導致我們很多基金難以運作。
至少目前,募資難的問題依然解決不了。我希望外界對我們可以有更清晰的認識,不要造成混淆、模糊不清的誤解。大家對于公募、私募很多東西的理念并沒有完全真正理解。從某種意義上講,我認為我們的觀念有些倒退了。
《財經》:怎么看2021年A股市場趨勢?
闞治東:我認為我們的A股市場一定是一年比一年好,但是2021年會不會特別好,我不確定,因為我并沒有看到有什么重大的事件會推動資本市場大步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