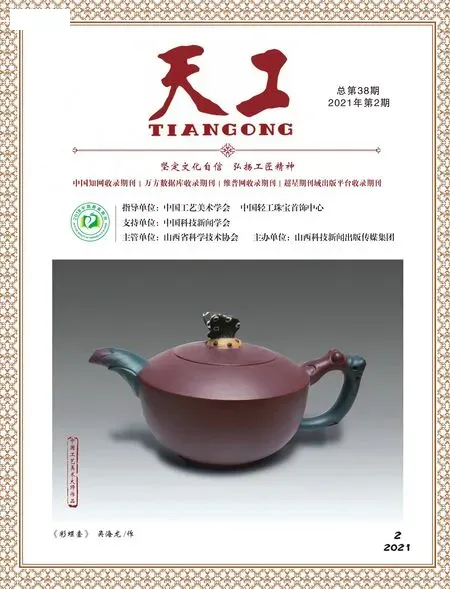中國(guó)傳統(tǒng)雕塑中“概念性特征”的表達(dá)
文 陳 輝 范曉辰
中國(guó)傳統(tǒng)雕塑是世界雕塑界中的一朵奇葩,歷史悠久、歷久彌新。
中國(guó)地域廣闊,所謂“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不同區(qū)域間文化習(xí)俗、社會(huì)風(fēng)尚難免存在差異;另外,中國(guó)朝代更迭、社會(huì)變遷導(dǎo)致社會(huì)意識(shí)形態(tài)、審美取向也各有其時(shí)代特色,由此導(dǎo)致不同時(shí)代和不同地域的雕塑在造型表達(dá)、呈現(xiàn)形式、美學(xué)追求上的豐富性,中國(guó)傳統(tǒng)雕塑的造型方式和特點(diǎn)也難以一言蔽之。但“意象表達(dá)”是中國(guó)傳統(tǒng)哲學(xué)和美學(xué)思想的共同體現(xiàn),它表現(xiàn)在中國(guó)傳統(tǒng)藝術(shù)的方方面面,也在中國(guó)傳統(tǒng)雕塑中產(chǎn)生十分深遠(yuǎn)的影響。古代匠人在創(chuàng)作過(guò)程中,造型上更加注重對(duì)客觀物象主觀認(rèn)識(shí)的“再現(xiàn)”,而對(duì)所表現(xiàn)事物的具體表象①“表象”單指事物客觀的外在形象。則不會(huì)太過(guò)深究,即所謂“妙在似與不似之間”。由此,中國(guó)傳統(tǒng)雕塑呈現(xiàn)出非常自由豐富且極具表現(xiàn)力的風(fēng)貌。對(duì)表現(xiàn)對(duì)象“概念性特征”的表達(dá)是中國(guó)傳統(tǒng)雕塑“意象表達(dá)”這一審美追求的體現(xiàn),也是傳統(tǒng)雕塑眾多造型方式中獨(dú)具特色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概念性特征”表達(dá)的概念和特點(diǎn)

圖1 象形文字“鼠”

圖2 篆書“鼠”

圖3 楷書“鼠”
在我們無(wú)法見(jiàn)到某一事物的本體而要間接認(rèn)識(shí)該事物的表象時(shí),通常有兩種途徑,一是觀看該事物的圖像資料,二是通過(guò)他人的語(yǔ)言或文字描述。但在古代,圖像信息匱乏,因此古人間接認(rèn)識(shí)事物的途徑往往是后者。這種方式帶有更強(qiáng)的主觀性,當(dāng)某一事物的形象以這種方式在眾人間廣泛傳播時(shí),人們對(duì)它的認(rèn)識(shí)變得多樣化且越來(lái)越趨向概念化,同時(shí)這種概念化的認(rèn)識(shí)也或多或少地偏離了該事物的本體。因此,對(duì)事物的概念性認(rèn)識(shí)一方面與該事物緊密關(guān)聯(lián),另一方面又與事物本體有所差異。本文將人們對(duì)某一事物較統(tǒng)一的概念性認(rèn)識(shí)稱作該事物的“概念性特征”。該“特征”不僅產(chǎn)生于人們對(duì)事物表象的間接認(rèn)識(shí),同時(shí)也存在于眾人對(duì)事物直接認(rèn)識(shí)后該事物在人腦海里形成的印象中。藝術(shù)創(chuàng)作過(guò)程中,創(chuàng)作者將眾人對(duì)所表現(xiàn)事物的“概念性特征”(而非事物本身)轉(zhuǎn)化成圖像或形體等可視內(nèi)容的創(chuàng)作方式即為“概念性特征”的表達(dá)。
創(chuàng)作者基于大眾對(duì)所表現(xiàn)對(duì)象的認(rèn)識(shí),提取和把握諸多認(rèn)識(shí)中最具代表性的“概念性特征”,并在創(chuàng)作過(guò)程中將這些特征加以突出體現(xiàn)。這種對(duì)事物“概念性特征”的把握和表達(dá)與我國(guó)象形文字的發(fā)展有著異曲同工之妙。一方面,象形文字帶有文字的符號(hào)性特征;另一方面,其又有形象圖形的影子。古人在創(chuàng)造象形文字過(guò)程中正是把握了事物最顯著的特征并加以提取和圖像化、符號(hào)化,以至于很多象形文字到現(xiàn)在我們都很容易辨認(rèn)。例如,“鼠”字最初在甲骨文中就是一個(gè)簡(jiǎn)筆畫的老鼠形象(如圖1),發(fā)展到篆文“鼠”(如圖2),字的造型跟現(xiàn)在(如圖3)已經(jīng)比較接近了。字的上半部代表鼠頭的部分,其頂端開(kāi)口,內(nèi)部?jī)山M橫線左右相對(duì),是鼠牙齒的突出表現(xiàn);字的下半部則表現(xiàn)了鼠的軀干和尾巴,其內(nèi)部橫線代表鼠爪。這即是老鼠在人們心中的形象(即它的“概念性特征”)——在古人的印象里,老鼠愛(ài)啃咬、擅打洞,因而它的爪、牙齒得以被突出表現(xiàn)。這種表達(dá)雖然不能很準(zhǔn)確地還原真實(shí)鼠的形象,但它以非常顯著甚至夸張的方式表現(xiàn)出人們普遍對(duì)鼠的概念性認(rèn)識(shí)。象形文字對(duì)事物“概念性特征”提取和夸大的表達(dá)方式與傳統(tǒng)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中“概念性特征”的表達(dá)類似,因?yàn)槲淖趾退囆g(shù)作品的不同功能屬性,藝術(shù)作品相對(duì)具象,且包含更多裝飾性造型。
二、中國(guó)傳統(tǒng)雕塑“概念性特征”的表達(dá)
(一)神獸動(dòng)物類傳統(tǒng)雕塑作品
神話傳說(shuō)是古人認(rèn)識(shí)和解釋世界的重要方式之一,在這些天馬行空的傳說(shuō)中,充滿著奇異的生物和擁有神奇力量的神怪,它們包含著古人對(duì)人類先祖的記憶和幻想、對(duì)人力所不及的自然現(xiàn)象的解讀。如此多造型奇異的生物為傳統(tǒng)雕塑的創(chuàng)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這些“人心營(yíng)構(gòu)之象”①由章學(xué)誠(chéng)說(shuō)《易》時(shí)提出。大多是一些眾人熟悉事物的解體重構(gòu)。而創(chuàng)作者對(duì)這些物象的了解最初是通過(guò)文字的概念性描述,而這些描述終成為這些物象的“概念性特征”。例如,《說(shuō)文解字》②《說(shuō)文解字》簡(jiǎn)稱《說(shuō)文》,由東漢經(jīng)學(xué)家許慎編著而成的漢語(yǔ)工具書。中對(duì)鳳的記載:“鳳,神鳥(niǎo)也。天老曰:鳳之象也,鴻前麟后,蛇頸魚尾,鸛顙鴛思,龍紋龜背,燕頷雞喙,五色備舉。”《山海經(jīng)》中對(duì)人文始祖伏羲形象的描述是“人首蛇身”,還有禺京的“鳥(niǎo)身人面”等。麒麟(如圖4、圖5、圖6)作為一種瑞獸出現(xiàn)在古人生活的許多方面,小到手把玩物大到石像生。《毛詩(shī)正義》③《毛詩(shī)正義》是唐代孔穎達(dá)所作《詩(shī)經(jīng)》的研究著作,又作《孔疏》。中對(duì)麒麟的描述是“麏身,馬足,牛尾,黃毛,圓蹄,角端有肉,音中鐘呂”,傳統(tǒng)雕塑中麒麟的造型多樣且它們之間差異較為明顯,但其基本特征都大致與此描述相吻合(不同文獻(xiàn)描述略有不同)。由此可見(jiàn),古代匠人在創(chuàng)作過(guò)程中都對(duì)文字描述的麒麟的“概念性特征”作了表達(dá),在滿足這些特征的基礎(chǔ)上,其造型的呈現(xiàn)受到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文化風(fēng)尚、個(gè)人審美、師承等因素的影響而形成各異的樣式。到今天我們對(duì)這類雕塑的辨識(shí)也是通過(guò)將這些“概念性特征”與之相對(duì)應(yīng)。
許多動(dòng)物雖然在現(xiàn)實(shí)世界中真實(shí)存在,但由于它們的生活習(xí)性或它們的活動(dòng)會(huì)對(duì)人類造成威脅等原因,使他們?cè)诠湃说纳钪须y得一見(jiàn)(如獅、虎、熊等),因此古人對(duì)它們的認(rèn)識(shí)類似于神話中的生物。

圖4 鎏金銅麒麟(東漢)河南博物院/藏

圖5 銅麒麟(清代)頤和園

圖6 石像生麒麟(明代)明十三陵神路

圖7 石獅子(隋代)洛陽(yáng)博物館/藏

圖8 掐絲琺瑯獅子(清代)故宮博物院/藏
古人常常以獅子(如圖7、圖8)的形象為基礎(chǔ)創(chuàng)作出各種各樣神獸的形象。例如,以獅子為原型的龍之五子“狻猊”,辟邪的形象也被描述為有翼的獅虎。傳統(tǒng)雕塑中,獅子的形象很多,它們的造型會(huì)因不同時(shí)代、地域甚至是不同作者而千差萬(wàn)別、大相徑庭。但它們依然可以被古人所辨識(shí)。這種可辨識(shí)性就源自古代匠人對(duì)獅子“概念性特征”的表達(dá)。獅子原產(chǎn)于非洲熱帶草原地區(qū),并非我國(guó)本土動(dòng)物,但早在西漢獅子就已被引進(jìn)中國(guó),“《東觀漢記》④《東觀漢記》是一部記載東漢光武帝至漢靈帝一段歷史的紀(jì)傳體史書。描述陽(yáng)嘉二年(133 年)疏勒國(guó)所獻(xiàn)獅子:‘獅子似虎,正黃,有髯耏,尾端絨毛大如斗。’”這是古人對(duì)獅子相對(duì)客觀的描述,但獅子在當(dāng)時(shí)的中國(guó)屬于稀罕物,連正史撰述者也未必親眼得見(jiàn)。元代文學(xué)家陶宗儀在其著作《南村輟耕錄》中說(shuō):“獅子……身材短小,絕類人家所蓄金毛猱狗。諸獸見(jiàn)之,畏懼俯伏……”⑤林移剛、楊文華:《漢民俗中獅子的形象及其內(nèi)涵》,《藝術(shù)百家》2012 年第7 期。這時(shí)獅子早已不是自然界中真實(shí)存在的動(dòng)物,而是傳說(shuō)中帶有某種神秘色彩的神物。由于不同時(shí)代古人對(duì)獅子“概念性特征”認(rèn)識(shí)不同,我們既可以看到雄壯威武的獅子造型,也可以看到獅子憨態(tài)可掬如小犬的樣子。現(xiàn)如今,獅子造型的傳統(tǒng)雕塑,有的我們辨認(rèn)起來(lái)已經(jīng)有一定困難。這是因?yàn)楠{子的真實(shí)形象我們?nèi)缃裨缫阉究找?jiàn)慣,我們對(duì)它們有更加具體、詳細(xì)的了解,在我們腦海里是非常具象的獅子形象的圖影留存,我們辨識(shí)獅子的形象也不再依靠它們的“概念性特征”,這也從側(cè)面說(shuō)明古代匠人在創(chuàng)作過(guò)程中對(duì)所表現(xiàn)對(duì)象的“概念性特征”的依賴。

圖9 食人虎卣(商晚期)日本泉屋博物館/藏

圖10 噬羊獅子石刻(唐代)美國(guó)克里夫蘭藝術(shù)博物館/藏

圖11 樂(lè)舞姬俑(部分)(西漢) 徐州博物館/藏

圖12 舞姬俑徐州博物館/藏

圖13 擊鼓說(shuō)唱俑(東漢)國(guó)家博物館/藏
《周禮·考工記·梓人》①《周禮·考工記·梓人》是中國(guó)春秋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記述官營(yíng)手工業(yè)各工種規(guī)范和制造工藝的文獻(xiàn)。中有這樣一段記載:“凡搏殺援噬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這是古代匠人表現(xiàn)捕殺噬咬他物類動(dòng)物形象(如圖9、圖10)的方法。由此可知,古代創(chuàng)作者不僅會(huì)抓住某一類動(dòng)物特有的“概念性特征”,他們還會(huì)將不同動(dòng)物的某一類相似狀態(tài)進(jìn)行“概念性特征”的總結(jié)和表現(xiàn)。
(二)人物類傳統(tǒng)雕塑作品
傳統(tǒng)雕塑對(duì)人和“神、佛”形象的表現(xiàn),古代創(chuàng)作者抓住的不僅僅是被表現(xiàn)對(duì)象作為“人”的“概念性特征”,還包括人物所扮演角色的特征。他們往往會(huì)對(duì)被表現(xiàn)角色典型的服飾和這類人物所處的典型狀態(tài)等特點(diǎn)加以概括表現(xiàn),這些特點(diǎn)即為該人物角色的“概念性特征”。這樣,作品便可以向我們傳達(dá)該人物的身份、角色等信息。
出土于江蘇徐州馱藍(lán)山楚王墓的西漢樂(lè)舞姬俑(如圖11)讓人印象深刻。它們生動(dòng)地再現(xiàn)了西漢楚王宮中舞姬伴樂(lè)舞蹈的場(chǎng)景,俑分樂(lè)俑和舞俑。樂(lè)俑有的撫琴,有的吹奏,神情專注;舞俑舞姿有的典雅含蓄,有的熱情奔放。作品將人物的神態(tài)、動(dòng)作特點(diǎn)都表現(xiàn)得生動(dòng)形象。尤其有一種形態(tài)的舞姬俑(如圖12)讓人過(guò)目難忘:舞姬軀干扁平與雙腿組成“S”形向右傾斜,被衣裙遮住的雙腿可粗略看作圓錐形,雙臂與浮動(dòng)的長(zhǎng)袖連為一體,跟軀干的上半部形成一個(gè)左邊翹起的“m”形。其造型除了頭部,其余部分都極大程度地幾何化。在人物動(dòng)態(tài)方面也完全不受人體結(jié)構(gòu)的束縛,而是在抓住人體基本結(jié)構(gòu)性特點(diǎn)的基礎(chǔ)上更加注重動(dòng)態(tài)給人的整體印象。這種抽象概括的造型靈動(dòng)而富有張力。作品抓住舞姬長(zhǎng)長(zhǎng)的衣袖、衣裙以及曼妙的舞姿等“概念性特征”加以夸張突出并盡可能地舍棄其余無(wú)關(guān)的形體,從而將舞姬的身份和所處狀態(tài)生動(dòng)地表現(xiàn)出來(lái)。此外,山東漢崖墓出土的擊鼓說(shuō)唱俑(如圖13),一手高舉鼓槌,一手將鼓抱于腰間,表情歡樂(lè)。作品以夸張的動(dòng)態(tài)和表情生動(dòng)地再現(xiàn)了當(dāng)時(shí)說(shuō)唱藝人在表演過(guò)程中歡騰跳躍的瞬間。作者很好地抓住了大眾對(duì)說(shuō)唱藝人普遍的概念性認(rèn)識(shí)(即典型的道具鼓和夸張的體態(tài)特征)并加以表現(xiàn)。
佛造像在我國(guó)歷時(shí)近2000 年的演變、發(fā)展過(guò)程中漸漸成熟,形成一套嚴(yán)格的度量與儀軌制度。古代匠人依據(jù)該“制度”對(duì)佛教中不同角色的描述和規(guī)定進(jìn)行相應(yīng)角色造像的創(chuàng)作。如此,一方面使佛造像給人以直逼內(nèi)心的震撼和神圣感,另一方面使造像所表現(xiàn)的不同角色得以被辨識(shí)。
關(guān)于佛像的肇始有兩種說(shuō)法,一說(shuō)是犍陀羅,另一說(shuō)為馬圖拉。犍陀羅的佛陀形象參考了希臘雕塑中人體的結(jié)構(gòu)特點(diǎn),而馬圖拉則以當(dāng)?shù)亟〈T、富有的中年男子為藍(lán)本。②李翎:《佛教造像度量與儀軌》,上海書店出版社,2019,第3-6 頁(yè)。二者的造型都是當(dāng)時(shí)人們對(duì)完美人體形象的概念性認(rèn)識(shí)。而佛經(jīng)對(duì)這種認(rèn)識(shí)也有頗為具體的描述,即“三十二種大人相”和“八十種隨形好”,對(duì)佛陀形象的描述小到面相、指甲蓋,大到人體比例,可謂無(wú)微不至。例如,“一孔一毛,孔毛色紺右旋相(佛身上的毫毛都是右旋的,形成‘卍’字形)”“鹿腨腸相(大腿像鹿一樣有力而健美)”“身量七肘”“頂有髻”“指甲如赤銅”“腹圓滿”③李翎:《佛教造像度量與儀軌》,上海書店出版社,2019,第7-15 頁(yè)。等。雖然這些描述無(wú)法全部在造像上得以體現(xiàn),但這些“概念性特征”仍是匠人們創(chuàng)作佛像的重要依據(jù),從而形成既與人類緊密關(guān)聯(lián),而又很大程度上區(qū)別于人的完美形象。由此,佛陀形象給人以作為神明與眾生的距離感和神圣感。
在豐富的佛教藝術(shù)中,人們往往通過(guò)佛、菩薩等的不同“手印”“法器”和“坐騎”等標(biāo)志性特征來(lái)辨認(rèn)。例如,我們熟知的文殊、普賢、觀音三尊菩薩(如圖14),坐騎分別為青獅子、六牙白象、金毛犼,當(dāng)這三尊菩薩居于同一廟堂內(nèi)時(shí),創(chuàng)作者往往會(huì)同時(shí)表現(xiàn)他們的坐騎以便于區(qū)分。《佛說(shuō)造像度量經(jīng)續(xù)補(bǔ)》對(duì)“佛像之威儀”有著很詳細(xì)的規(guī)定,威儀即為佛的顏色、手印、姿態(tài)和標(biāo)識(shí)等特征。例如,“南方寶部主寶生佛:黃色,右手施定印、左手施與愿印。摩尼寶珠至于左掌上,寶珠是寶生佛的標(biāo)識(shí)。”“大慈悲彌勒菩薩:中黃色,標(biāo)識(shí)為凈瓶。如果是‘雙標(biāo)識(shí)’,彌勒在凈瓶之外再加上龍花枝。”等等。這些對(duì)每個(gè)佛教人物的描述即為這些人物的“概念性特征”,匠人們?cè)趧?chuàng)作過(guò)程中對(duì)這些特征的表達(dá)使佛造像的角色身份得以被辨認(rèn)。①李翎:《佛教造像度量與儀軌》,上海書店出版社,2019,第35-75 頁(yè)。
雖然漢譯的《佛說(shuō)造像度量經(jīng)》到清代才出現(xiàn),但三國(guó)時(shí)期曹不興已熟練掌握了佛像的比例結(jié)構(gòu)。事實(shí)上,佛造像最初傳入我國(guó),創(chuàng)作者多是依據(jù)來(lái)自“西域”的“畫樣”進(jìn)行塑造。而我國(guó)傳統(tǒng)雕塑的傳承多是口傳心授,因而,佛造像的“創(chuàng)作要領(lǐng)(即儀軌)”和這些“粉本”得以漸漸在匠人間傳誦、傳閱。因此,佛造像“概念性特征”的表達(dá)也是我國(guó)匠人進(jìn)行佛像創(chuàng)作必不可少的內(nèi)容。②李翎:《佛教造像度量與儀軌》,上海書店出版社,2019,第18 頁(yè)。
三、中國(guó)傳統(tǒng)雕塑“概念性特征”表達(dá)的成因
著名藝術(shù)心理學(xué)家阿恩海姆曾指出:“原始藝術(shù)的目的,并不在于去產(chǎn)生愉快的形象,而是把它作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實(shí)踐工具或一種超凡的力量。”③[美]魯?shù)婪颉ぐ⒍骱D?《藝術(shù)與視知覺(jué)》,滕守堯譯,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第149 頁(yè)。因此,人類最初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是以其功能需求(這里的“功能需求”“實(shí)用功能”并非今天意義上的,而是以古人的價(jià)值取向和認(rèn)知來(lái)談)為首要目的的。中國(guó)古代一直講究“禮樂(lè)”治國(guó),“前者成為‘禮’——政刑章典,后者便是‘樂(lè)’——文學(xué)藝術(shù)”④李澤厚:《美的歷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9,第13 頁(yè)。。它與王朝、氏族的穩(wěn)定、興衰有著密不可分的聯(lián)系,這正是傳統(tǒng)藝術(shù)功能的體現(xiàn)。馮友蘭先生也認(rèn)為“儒家把藝術(shù)看作是道德教育的工具”⑤馮友蘭:《中國(guó)哲學(xué)簡(jiǎn)史》,趙復(fù)三譯,中華書局,2019,第37 頁(yè)。。由此可見(jiàn),傳統(tǒng)藝術(shù)的實(shí)用功能在我國(guó)古代社會(huì)活動(dòng)中占據(jù)著重要的地位。隨著人類社會(huì)發(fā)展、文化自覺(jué),藝術(shù)的表現(xiàn)漸漸產(chǎn)生了審美追求,有的甚至完全脫離了其原始的創(chuàng)作意圖,譬如中國(guó)的文人畫。傳統(tǒng)雕塑的造型自有其獨(dú)特的審美意趣和美學(xué)價(jià)值,但由于其創(chuàng)作者社會(huì)階層的局限等原因,它的實(shí)用功能這一特性一直或多或少地伴隨著它。

圖14 普賢、觀音、文殊菩薩泥塑(由左至右)(宋代)山西長(zhǎng)治崇慶寺羅漢殿

圖15 “大劉記印”龜鈕玉印 江西南昌漢代海昏侯劉賀墓出土
中國(guó)傳統(tǒng)雕塑正是因?yàn)檫@種實(shí)用功能特性,使其范圍主要分布在明器、禮器和宗教造像上。⑥曾齊寶:《論中國(guó)傳統(tǒng)雕塑中的塑繪一體》,博士學(xué)位論文,中國(guó)美術(shù)學(xué)院,2016,第1 頁(yè)。
明器雕塑的用途往往是作為人、物的替代陪同逝者去往另外的世界。這樣逝者便可以在離開(kāi)人世后依然享有自己生前所有的一切,即所謂“事死如事生”。明器承載著古人對(duì)逝去后所到世界的美好愿景。因此,在這里雕塑作品所傳達(dá)的理念是其被創(chuàng)作的主要目的,而這種理念的傳達(dá)與每件作品所表現(xiàn)(代表)的對(duì)象息息相關(guān)。
在中國(guó),封建社會(huì)等級(jí)制度嚴(yán)苛,正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傳統(tǒng)雕塑總是作為禮器,在政治、生活中起到彰顯和強(qiáng)調(diào)這種等級(jí)劃分的作用。例如,商周時(shí)期的青銅器、印鈕(如圖15)等。印鈕是位于印上端的雕飾物,《后漢書·輿服志》中記載:“皇帝之璽,白玉印,螭虎鈕,黃赤綬……諸侯,黃金印,橐駝鈕,文白璽,赤綬……公、候、將軍,黃金印,龜鈕……”由此可見(jiàn),印鈕所表現(xiàn)的不同對(duì)象象征著印主人不同的社會(huì)地位。
傳統(tǒng)雕塑除了在明器和禮器上發(fā)揮著一些重要作用外,它作為一種“超凡力量”的載體也體現(xiàn)在古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宮殿殿脊兩側(cè)的吞獸一般為“龍生九子”中第九子“螭吻”(如圖16),它口潤(rùn)嗓粗而好吞吐,因而有滅火祛災(zāi)的能力;“獬豸”(如圖17、圖18)因其富有智慧,辨忠奸、明是非而被立于官衙正堂兩側(cè)以求“正大光明”“清平天下”;辟邪被塑像則因其能避除兇險(xiǎn)、祛邪免害……不難發(fā)現(xiàn),不同的“神奇能力”和藝術(shù)形象間有緊密的對(duì)應(yīng)關(guān)系。
此外,宗教雕塑在傳統(tǒng)雕塑中舉足輕重。它一方面可作為宗教和政治的宣傳工具,如云岡石窟第一期,曇曜五窟、龍門石窟奉先寺中的盧舍那佛像;另一方面可作為一種超凡力量的載體,他們是神明的化身,以滿足膜拜者們求子、求福、求平安等種種訴求。
至此可知,傳統(tǒng)雕塑在實(shí)現(xiàn)各自不同功能的過(guò)程中,重點(diǎn)在于其各異的造型背后所對(duì)應(yīng)的各種意義、寓意和理念。因此,為了某種“意義”更直接、有效地被傳達(dá),雕塑造型所表現(xiàn)的對(duì)象需要容易被辨識(shí),即造型的高度“可辨識(shí)性”。既如此,為什么中國(guó)傳統(tǒng)雕塑沒(méi)有像西方雕塑那樣走向高度寫實(shí)的道路呢?首先,這與中國(guó)傳統(tǒng)美學(xué)價(jià)值取向和哲學(xué)思想有關(guān),我國(guó)傳統(tǒng)藝術(shù)普遍追求意象表達(dá),古人在藝術(shù)創(chuàng)作過(guò)程中更加注重事物內(nèi)在精氣神的表現(xiàn)。其次,傳統(tǒng)雕塑作品大多是對(duì)人已知事物的重新“再現(xiàn)”,它并非對(duì)所表現(xiàn)對(duì)象的復(fù)制,而是通過(guò)某種方法創(chuàng)造出與表現(xiàn)物象造型相似或相關(guān)聯(lián)的形式,從而使觀者能夠自然而然地將該形式與其所表現(xiàn)的對(duì)象相對(duì)應(yīng)。所以,藝術(shù)家創(chuàng)造的形式可看作是作者用以向觀者傳達(dá)某方面信息的媒介。從這種意義上說(shuō),形式與它所表現(xiàn)的對(duì)象在造型上有可能是相去甚遠(yuǎn)的。因此,古人對(duì)表現(xiàn)對(duì)象“概念性特征”的表達(dá),一方面是古人審美意趣的體現(xiàn),另一方面是為了有效地實(shí)現(xiàn)雕塑造型的“可辨識(shí)性”,從而滿足作品的功能需求。
綜上所述,中國(guó)傳統(tǒng)雕塑“概念性特征”的表達(dá)——由于以滿足作品功能需求為創(chuàng)作的首要目的,傳統(tǒng)塑者以作品最終的可辨識(shí)性為重要出發(fā)點(diǎn),不求高度還原客觀對(duì)象的實(shí)際造型,而是遵循所表現(xiàn)對(duì)象在眾人心中普遍形成的“概念性特征”。以這種特征為框架,加之以作者的想象,以及其功能要求和環(huán)境等條件的考慮,最后形成一件帶有較強(qiáng)主觀色彩的作品。傳統(tǒng)雕塑造型對(duì)物象“概念性特征”的表達(dá),是古人滿足作品功能需求的考量,也是他們智慧的凝結(jié)。這種表達(dá)為我們提供了觀察和認(rèn)識(shí)事物的新視角,啟發(fā)著我們?nèi)缃竦乃囆g(shù)創(chuàng)作。

圖16 宮殿殿脊吞獸琉璃螭吻(元代)山西博物院/藏

圖17 銅獬豸(清代)故宮御花園

圖18 陶獬豸(北周) 陜西歷史博物館/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