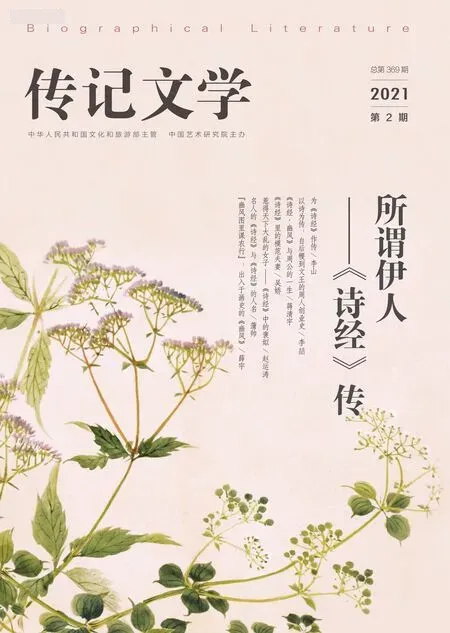名人的《詩經》與《詩經》的人名
蒲 帥
香港嶺南大學


如何選取祥瑞意象決定命名出處?傳統典籍在其中發揮了顯著的參考作用。在命名方面,中國自古便有“女《詩經》男《楚辭》,文《論語》武《周易》”之說,典籍文獻中深厚的文化精神蘊藏為命名提供了取之不竭的靈感支持,特別是在命名過程中引用《詩經》內容命名的現象,尤為引人矚目。
前人引《詩》命名,背后隱含的思考邏輯是對于《詩經》中美好詩旨的接受與重新闡釋。從《詩經》文本中選取最能夠代表自身希冀的文化符號融入命名中,意味著這些美好詩旨得到了古人的認同與接受,成為了傳遞文化信念的最佳載體。具體分析古人引用《詩經》命名的典型例證,可以看到其中包含三種迥乎不同的引用思路,也正對應了前人解讀闡釋詩旨的三個不同層面。
運用詩旨原本義,寄寓美好祝愿
首先最普遍也最常見的一種引用類型,便是嚴守“以德命為義”的本意,從《詩經》文本中選取代表祥瑞意象的字詞,直接使用其原本義,借以寄托命名者的美好祝愿。此類命名征引大多使用沒有明確指向、意蘊較為寬泛的名詞、形容詞,因而具有極強的泛用性與普適性,其中包含的文化意蘊范圍也最為廣闊。
例如北宋著名詞人周邦彥,其名字由來便是這類命名的典型代表。“邦彥”出自《鄭風·羔裘》,原句為:“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詩句中“晏”的本意為天清,引申為柔暖貌;而“三英”則指的是將豹皮鑲在袖口的三排裝飾,形容的是羔裘裝飾的華美。能穿著這樣華美服飾的,便是被稱作“邦之彥兮”的國家俊杰。《毛傳》中有“彥,士之美稱”之說,羔裘也被認為是大夫等級官員才能穿著的服裝,這都說明有一定身份地位的君子才能被稱為“邦彥”,這樣的命名顯然飽含著命名者期望后代成長為國家棟梁之才的美好希冀。
關于《羔裘》詩篇的意旨,古來便有兩種常見說法。《毛序》稱其“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認為這是一篇通過贊美古代君子表達對當朝諷喻的作品;另一種較為公允的說法見于朱熹《詩集傳》,認為詩篇“蓋美其大夫之詞,然不知其所指矣”。兩說區別在于是否相信詩篇含有諷喻之義,但均認同內容本身是借描繪羔裘表達了對國之君子的贊美、褒揚之義,因此引“邦彥”二字命名便是使用了其在詩篇中的原本含義,以此表達美好祝愿之意。
再如北宋開國名將高懷德,其名字由來也同樣借鑒了《詩經》中的美好意旨。“懷德”二字來源于《大雅·板》,原句為:“懷德維寧,宗子維城。”按照程俊英先生的解讀,此兩句意為“以德行團結賢人民眾和諸侯宗族,就是國家的安寧”。此處“德”指代“德行、品德”,而“懷”則具有“和、團結”之意,因此“懷德”便理解為“以德行團結眾人”,同樣是美好意旨的代表。
相較于風詩作品,雅頌類詩篇往往表現出更為明顯的政治內涵,這篇《大雅·板》也不例外。前人多認同《毛序》中“板,凡伯刺厲王也”的說法,將其理解為借批評同僚為名表達諷喻規勸的作品,詩篇亦因此飽含深情。作者在“價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一句中使用連串譬喻,由淺入深地述說賢人(價人)、民眾(大師)、邦國(大邦)、宗族(大宗)等均是周天子維系天下的屏障所在。而在整個邏輯鏈條中,德行無疑居于摶和一切的中心地位。周人強調“德治天下”,對于德行的追求構成禮樂制度的內在精神,因此“德”也是《詩經》文本中最為內核的文化符號。選擇征引“懷德”來命名,同樣借鑒使用了其在詩篇中表現出的原本含義,充分體現出命名者希望后代能夠成為有德之人、借德行服眾的美好愿望。
借鑒詩旨指向義,強調具體期望
《詩經》篇目中存在大量含有美好寓意的字詞。結合詩旨來看,表述美好原本義的字詞往往成為命名的熱門選擇。除此之外,另一種常見的引《詩》命名方式,則是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考慮詩篇的具體內涵,在命名時使用的是字詞特定的指向含義,以此表達命名者更為具體的期望與祝愿。
例如著有《儒林外史》的清代小說家吳敬梓,其名便是使用了字詞的特定指向意義。“敬梓”二字出自《小雅·小弁》,原句為:“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這兩句詩屬于陳述部分,意為見到父母所種植的桑樹與梓樹,一定要表現得恭恭敬敬。這種對樹木表現出的恭敬之義,背后隱藏的則是人倫禮教中的孝道要求。
詩篇中提及的桑樹與梓樹,在古代往往種植于住宅旁。這些父母親手種植的樹木,某種程度上也就成為家庭的象征,具有家宅安寧的指代意義。子女看到桑梓便難免會見物思人,進而聯想到父母的養育恩情。《毛傳》稱:“父之所樹,己尚不敢不恭敬。”子女感受體悟父母養育恩情借由日常生活中的事物表現出來,對樹木的恭敬實際代表著對父母養育之恩的感激,這正是傳統人倫孝道的鮮明體現。

[日]細井徇撰繪:《詩經名物圖解》(節選),嘉永元年(1848)

再如清代著名學者王引之,其名字由來同樣飽含命名者關于延續家族傳統的希冀。“引之”二字來源于《小雅·楚茨》結尾,原句為:“子子孫孫,勿替引之。”“替”在此處為“廢止”之意,“引”的意思是“延長、延續”,而“之”則是代詞,代指的內容是詩篇中提及的祭祀禮節。
與之前提及的《詩經》作品性質不同,《小雅·楚茨》是一首周王祭祀祖先時使用的樂歌,因此詩篇內容圍繞祭祀儀式展開。呂祖謙在《呂氏家塾讀詩記》中認為:“《楚茨》極言祭祀所以事神受福之節,致詳致備,所以推明先王致力于民者盡,則致力于神者詳。”祭祀典禮的完備寓意著生者對于死者的追念,對于前代周王施政理念的堅持與延續,因此詩篇結尾落在了對于后輩的訓誡上,希望后輩能夠將這樣的傳統代代延續下去。由此可見在命名時使用“引之”一詞,正著眼于其中繼承家族傳統的指向義。而王引之在研究領域能夠做到子承父業,學術成就不在其父王念孫之下,“引之”之名可謂是名副其實。

[宋]呂祖謙撰:《呂氏家塾讀詩記》
發揮詩旨引申義,表達深沉希冀
引《詩》命名的第三種類型,則是結合詩旨內涵對詩篇字詞進行深入闡發,在命名過程中借用其引申含義。相較于前兩者使用的原本義與指向義,借用引申義的命名往往包含著更為深沉復雜的思考與希冀,滿懷著命名者的殷切期望。
前文提及宋代名將高懷德得名取自《詩經》,而其父后唐齊王高行周的名字同樣來源于《詩經》。“行周”二字出自《小雅·都人士》,原句為:“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其中“行歸于周”若按照字面意思理解,便是“將要回歸鎬京”之意,看似并無深刻內涵,因此要理解這一命名內涵,還需對詩旨進行深入分析。
關于《都人士》的篇章主題,古來便有諸多不同意見。《毛序》稱其主旨為“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一,傷今不復見古人也”,認為這是一首充滿感傷色彩的諷喻作品。朱熹在《詩集傳》中則摒棄諷喻說只認可這是懷舊之作:“亂離之后,人不復見昔日都邑之盛,人物儀容之美,而作此詩,以嘆惜之也。”兩說的相通之處在于均認可詩篇內容的懷舊基調,因此“行歸于周,萬民所望”這句對于過去景象的描述,也就帶上了慨嘆追憶的色彩。
西周末年,統治者日益昏聵,原本起到凝聚社會作用的禮樂制度也逐步廢弛,周王朝走向了禮崩樂壞的混亂局面。黑暗的社會現實引發了人們對過往生活的集體追憶,《都人士》中稱“行歸于周”為“萬民所望”,也正基于此種懷舊情緒。在詩篇昔勝于今的回憶基調下,“行歸于周”這一符合“萬民所望”的行為,除了字面上的“返回西周故都鎬京”外,還能再讀出一層“回歸周家舊傳統,回歸禮樂制度”的深層含義。而這層更為深沉的內涵,便是引用“行周”來命名的目的所在,其中同樣蘊含著命名者對傳統禮樂精神的向往與渴望回歸之情。
再如唐代名相杜如晦,其姓名由來同樣借鑒了詩旨的引申含義。“如晦”二字來源于《鄭風·風雨》,原句為:“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單看這兩句似乎難以把握引其命名的原因,“晦”意為“昏暗”,《說文解字》稱:“晦,月盡也。”“風雨如晦”一句也就是風雨大作而導致天色昏暗之意。“已”意為“停止”,在陰晦的風雨天中雞鳴不止,原本只是風詩采用的起興手法,并無特殊的指向含義,但前人的解讀卻為這句詩注入了新的引申意義。


日本鹿鳴館
上述列舉的都是古人取名時借鑒引用《詩經》的例證,實際上類似的借鑒方式還廣泛存在于其他命名行為中。例如,在地名中也多有參考詩旨引申含義命名的實例。囿于篇幅所限,此處簡單舉兩例為證。日本明治維新后開創“鹿鳴館時代”的外交場所鹿鳴館,便由詩篇《小雅·鹿鳴》而得名,取“《鹿鳴》,燕群臣嘉賓也”之意,恰如其分地展現了鹿鳴館的外交宴會作用,寄托了借其調和交際的美好愿望。再如明治時期教育家近藤真琴于1863年創辦的攻玉塾,名稱取自《小雅·鶴鳴》中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化用其中借他人磨礪自身之意,生動形象地表現出學習的重要性,命名可謂意旨深遠,切中《詩經》意蘊之要。
以上從三個不同層面分析了引《詩》命名的不同類型。不論是擷取原本義、參考指向義還是發揮引申義,背后均反映出命名者對《詩經》文本的熟稔及對其中美好詩旨的接受。命名行為看似微小,實則是寄寓命名者殷切期望的莊重之事,以此為切入點,揣摩、觀察前人闡釋化用詩旨的具體例證,某種意義上也為我們理解前人對《詩經》意旨的接受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
注釋:
[1][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 清嘉慶刊本·七·春秋左傳正義·卷第六·六年》,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3801-3802頁。
[2]程俊英、蔣見元著:《詩經注析·十五國風·鄭風·羔裘》,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234頁。本文有關《詩經》文本的解讀均引自此書,下文注釋從略。
[3][4][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 清嘉慶刊本·三·毛詩正義·卷第四·羔裘》,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718頁。
[5][宋]朱熹撰,趙長征點校:《詩集傳·卷第四·鄭·羔裘》,中華書局2017年版,第79頁。
[6]程俊英、蔣見元著:《詩經注析·二雅·大雅·板》,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847頁。
[7][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 清嘉慶刊本·三·毛詩正義·卷第十七·板》,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1182頁。
[8][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 清嘉慶刊本·三·毛詩正義·卷第十二·小弁》,中華書局 2009年版,第971頁。
[9][清]馬瑞辰撰,陳金生點校:《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小雅·小弁》,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644頁。
[10]黃靈庚、吳戰壘主編:《呂祖謙全集·第四冊·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485頁。
[11][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 清嘉慶刊本·三·毛詩正義·卷第十五·都人士》,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1182頁。
[12][宋]朱熹撰,趙長征點校:《詩集傳·卷第十五·都人士》,中華書局2017年版,第261頁。
[13]王平、李建廷編著:《說文解字標點整理本·弟七·日部》,上海書店出版社2016年版,第168頁。
[14][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 清嘉慶刊本·三·毛詩正義·卷第四·風雨》,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729頁。
[15]程俊英、蔣見元著:《詩經注析·十五國風·鄭風·風雨》,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251頁。
[16][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 清嘉慶刊本·三·毛詩正義·卷第九·小大雅譜》,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86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