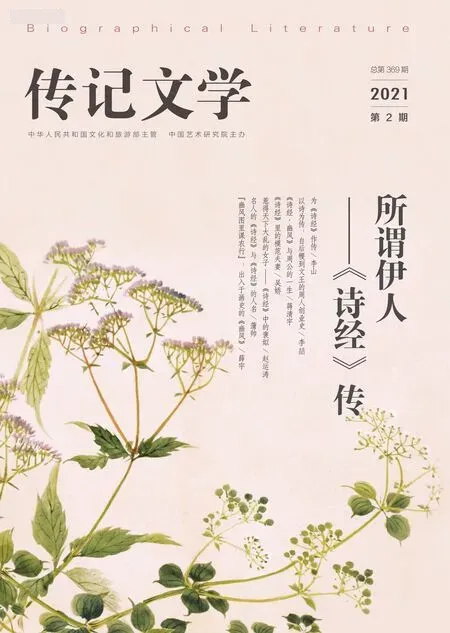『豳風圖里課農行』:出入于畫史的《豳風》
薛 宇
北京師范大學

傳[宋]馬和之:《豳風圖·七月》(局部),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



傳[宋]馬和之:《豳風圖·七月》(局部),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
宋元時期:圖解《豳風》

故宮本傳馬和之《豳風圖》卷共分7 段。畫作按照《豳風》順序依次繪出7首詩篇,左圖右書,所書內容包括《毛詩》小序與《詩》原文。畫家繪制的畫面都貼著《豳風》的文字,表現詩篇各章節內容與意象。揚之水認為“詩經圖”為“詩意圖”之屬,《豳風圖》正是別有興味的“圖解之作”。清代乾隆年間畫作收入內府,因此有乾隆御題“葦龠余風”四字卷首。《七月》一段將詩中一年的農事活動凝縮為一幅畫:右側人物錯落安置在山水農田之間,以云石、樹木分隔開觀“流火”、采桑、撲棗、筑場圃、納禾稼的農官農夫、婦人少女,忙碌中一派井然;左側則主要反映年終獻羔祭韭、朋酒斯饗、躋彼公堂的祭祀與宴樂場景,酒食與樂舞備陳,氣氛雍雅和樂。畫面筆調古樸,貼合詩意,又根據畫作的形式和表現特點對內容做出了合理的調整和安排,疏密有致的布局賦予了畫面安閑適意而又時令緊湊的節奏感。


傳[宋]李公麟:《豳風七月圖》(局部),現藏美國大都會博物館
現藏弗利爾美術館的傳馬和之《豳風七月圖》也是一幅長卷,但只繪制了《七月》一篇的詩意。卷首有文徵明題跋“豳風舊觀”四字,畫作亦左圖右書,對每一章作細致的描繪。耕種、紡織、田獵、斗蟋蟀、熏鼠等畫面被畫師一一繪制,細節完備。相比之下,這幅長卷畫面以稼穡、田獵、桑績為主,而缺失了詩篇末尾宴飲和祭祀的場景,也沒有稱引小序。不過文徵明題寫在畫面之后的《跋南宋馬和之豳風七月圖》中,卻提出“古人圖畫必有所勸戒而作”,“昔之序詩者云:周公陳王業,以告成王,謂‘民之至苦者,莫甚于農,有國有家者,宜思憫之、安之’,故作是詩,備述其艱難。今觀和之此圖,若生于周而處于豳,古風宛然也。校諸假丹青以為耳目玩者,豈可同日語哉”,備陳小序與教化之意。文徵明的題畫文字越過畫面,直達經義,并提出了畫為勸誡而作、高于娛樂耳目的觀點。這種文字在《豳風圖》成圖歷程的史書記載與題畫文字中,都最為常見。
盡管畫的是詩意,但在《詩經》經學性質的影響下,與《豳風圖》有關的史書記載、題畫詩跋等文本中,對經義的闡明卻是更為普遍的現象。經義生發多與《七月》一詩有關。從《毛序》到清乾隆的《御纂詩義折中》,歷代“隱寓”的經義大致不出周家傳統、王業肇基、民生艱難、賢王重農等。傳南宋馬和之的兩幅《豳風圖》從創作過程到題畫文字、再到后人的衍生創作,都與經義息息相關,可以說畫家雖著力于圖解《豳風》詩意,卻仍是《詩經》經學體系的附屬成分。



明清時期:對《豳風》原文的貼合和逸出

清代,乾隆帝得到了包括《豳風圖》在內的馬和之《詩經圖》殘卷,故敕令畫院畫師依馬和之《詩經圖》筆意,補足了《毛詩全圖》。隨后,乾隆又與董邦達合作臨仿了《豳風圖并書》。乾隆帝自稱“高、孝兩朝,偏安江介,無恢復之志,其有愧《雅》《頌》大旨多矣,則所謂繪圖書經,亦不過以翰墨娛情而已,豈真能學詩者乎”,強調自己的《毛詩全圖》工程與《詩經圖》繪制才是真正有“學詩”的深層含義,并不單單是為了娛樂。在大量奉旨題畫的文字中,這種深層含義得到了清晰的揭示。汪由敦《恭跋御書豳風圖》首先點明“《豳風·七月》陳王業之艱難,所言農夫紅女趨事赴時,詠歌勤苦,尤為親切有味”,體現的是追本、憫農的意思;其次言“世宗憲皇帝暨我皇上三朝睿藻,輝映冊府”與“《豳風》所述后稷、公劉、太王、文武之遺,先圣后圣有同揆焉”的映照關系,從繼承祖業、接續傳統的層面上來頌圣。張照的《石渠寶笈》中還談及乾隆一見到馬遠的《豳風圖》,聯想到的便是“姬公陳詩之意”。乾隆自己在《農器圖十詠》的解讀中表明從皇祖至今,耕織圖、豳風圖的繪制,都是為了展示、體恤生民艱辛。歷朝歷代在《豳風圖》的題畫文字上能想到的經義,都在清代這個“集大成”的時代被從頭到尾說了個遍。

[明]文徵明:《豳風圖》,現藏上海博物館
但同樣是在明清時期,在離廟堂稍遠一些的江湖之間,一些私人繪畫開始跳出馬和之的構圖與《豳風》原文的束縛,創作出在畫面上更具特色的作品。明清的《豳風圖》更傾向于在山水農家間隨意發揮,像文徵明的《豳風圖》將故宮本《豳風圖》卷的《七月》一段縱向壓縮,使左右的宴樂、農耕布局成為縱深感極強的前后布局,山水田園占據了更大的篇幅;清人唐岱、沈源合筆的《豳風圖》,畫面全然是一幅山水圖,人物散落于山水之中,呈現出悠遠的山水畫意境。至于明代周臣的《毛詩圖》立軸,因乾隆題詩中提及“豳雅”而與《豳風》密切相連,畫面中卻已然一派雞犬相聞的田園風光。山石樹木之間,幾戶茅草遮蓋的人家,忙著參與和觀賞斗雞的鄰里,水中自由的禽鳥……大量《豳風》原文、乃至《詩經》原文中都未曾涉及的關乎自然山水與鄉村田園的意象加入畫面。雖然題畫文字上還牽扯著經義,但畫作已然逸出詩篇,與原文的聯系若即若離。

回歸到詩意的“豳風圖”
從明至清,《豳風圖》的繪制被認為具有政教功能。記載繪圖史事的文字或題畫詩、賦等鑒賞文字都越過圖像對詩篇內容的直接表現,而注重點明其深遠的教化內涵。而這種政教價值,正來源于小序與歷代闡釋者重點闡發的重視傳統、傳承祖宗基業、重農、民本等經學思想。從這個角度來說,《豳風圖》為經學體系的附庸,從繪制到鑒賞都依附于經義體系、服務于政教功能。《豳風圖》很少被鑒賞者單純地從審美上看待,而是被看作經學體系的一部分,或者說它的審美價值本身就體現在教化上。
對于《豳風圖》的藝術鑒賞,因此也多側重彰明其雅正的風格,比如《書畫跋跋》評價林子奐《豳風圖》時引用了沈瑞伯的話,認為林畫“雅”;張照評價馬遠繪制的《豳風圖》,便說此畫“婦女容態,自有國有家者,以至田野紡織,莫不端莊靜雅,無一毫邪辟意思,望之令人肅然起敬”。這種強調雅正、不邪辟的審美的傾向,在其他詩文主題的繪畫中并不多見。但是《豳風圖》貼合詩意的畫面,尤其是明清之后大量私人作品的出現,到底還是為《豳風》、為《七月》逸出經義提供了一條路徑。在不關乎題畫或記畫的詩文作品中,“豳風圖”反而逐漸成為如詩如畫的田園風光、其樂融融的鄉野生活的代名詞,成為了一個整體視覺意象,與外部鄉村田野景色對接,引發詩文或烘托意蘊,為作者抒發私人情感服務。

[明]周臣:《毛詩圖》,現藏普林斯頓大學美術館
元代王逢有《閻立本職貢圖為章修齊題》一詩,全詩因閻立本的《職貢圖》而發,落腳于回歸田園的志趣,即“名園良疇繞柘湖,篤志好在豳風圖”。這種抒情十分私人化,并不涉及任何經義,只將“豳風圖”作為田園生活的形象化表達。可見,作者已經將“豳風圖”看作一個象征著山水、田園、農家生活的意象。
清人涉及“豳風圖”意象的詩作數量繁多,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乾隆帝的詩作。前文已經提及,這位君主在繪制《豳風圖》方面顯示出了巨大的熱情,此時對于《詩經》的官方解讀和受到認可的《豳風圖》題畫文字也都帶有明顯的附庸經義的特點。在這種經典闡釋取向中,乾隆帝創作出一系列使用“豳風圖”意象的詩,就很值得關注。在《御制詩初集》中有《麥苗》一詩,寫“新苗”“春雨”等鄉野化的風物景色,以“何異豳風圖里看”收尾。“何異”的說法正是將前文所見“麥苗”帶出的田園鄉村景色定義為“豳風圖”的主要內容,以“豳風圖”作為田園鄉村景色的形象化總結。再如《仲春雨景》“豳風圖畫北村便,一覽春耕倍適然”等,“豳風圖”的用例亦是如此。此外林則徐所寫的“此二十里間,棗樹最多,其實已纂纂矣,桑林亦蔥蔥彌望,誠一幅豳風圖也”,也是以桑棗蔥郁擬作“豳風圖”。
在帶有“豳風圖”意象的文學作品中,如清人錢大昕說的“起看四野間,耄稚共欣笑。戴笠出耘鋤,著屐踏泥淖。村村歸犢臥,處處鳴蛙鬧。饟黍趁晴初,提壺或醉倒。一幅豳風圖,神理都曲肖。”(《題筠浦中丞甘雨應祈圖卷》),笠、屐、犢、蛙等不見于《豳風》詩的意象,以及將整個鄉野圖景與“豳風圖”對等的行為,說明“豳風圖”已經成為一個獨立的意象,用以指代平和美好的鄉村農耕生活和與農業密切相關的自然風物。這種意象內涵與《豳風·七月》詩的詩意密切相關,而與《毛序》提示的傳統、王業、憫農等內涵明顯脫節。至于許兆椿的“繪得豳風七月圖,濕云潑墨尚模糊”,與江南竹枝清歌連寫,對應的早已不是周家的西土風物,而是一派南方水墨融融的自然風情了。
當然,“豳風圖”這個意象并不是在所有詩文中都不與經義掛鉤。在許多詩文中,仍可見到經義系統長久而深厚的影響力。但相較于提到《豳風》詩,則提起稼穡艱難,則離開自己詩文描繪的畫面而數說經義,“豳風圖”這個意象為貫通《豳風》的田園詩意和私人抒情詩文對歸隱、鄉野等的圖景描繪,提供了特殊的路徑。“豳風圖”這種說法及歷來《豳風圖》詩意畫的典型特點,顯然為《豳風》詩篇呈現的“如詩如畫”的田園詩意進入文學開辟了一方小天地。《豳風》尤其是《七月》文本本身明媚和諧的農業情調是這種貫通的基礎,“豳風圖”以這種呈現詩意的方式的出現,則是《豳風》詩意在文學領域擺脫累積的經義、融入更廣闊的私人抒情創作的階梯。雖然歷來《豳風圖》的制作與對其的鑒賞都離不開經義和政教,但圖像一旦畫就,或者說“豳風圖”這個概念一旦形成,其作為一個概念、一個意象的獨特內涵也就隨之生成,得以進入其他領域的創作。在經學闡釋方式以正統、官方的形式支配著漫長的經典文本闡釋史、形成了一套影響力巨大的經學闡釋體系的背景下,在經典文本突破經義、進入經學以外的其他領域的嘗試中,載體的轉變是一條值得關注的有效途徑。
“豳風圖里課農行”(《西直門外》),《豳風》在入畫又返歸詩文的漫長歷史里,出入于經義之中,生發于詩意之外,將美麗的山水農田、恬靜的鄉野勞作、漫長的農耕歷史都一筆一劃地繪進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畫卷之中。直至今日,泛黃的一幅幅畫作仍能令觀者眷眷想起古老的《豳風》與周家文化,以及心向往之的原野故鄉。
注釋:
[1]唐代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載錄明帝司馬紹《豳詩七月圖》。參見[唐]張彥遠撰,俞劍華注釋:《歷代名畫記》,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64年版,第92頁。
[2][清]王原祁、孫岳頒等纂輯:《佩文齋書畫譜》卷五一“馬和之”條,清康熙四十七年內府刻本,第28b頁。
[3][元]夏文彥編纂:《圖繪寶鑒》卷四,民國三年上虞羅氏宸翰樓據元至正本影刻本,第5a頁。
[4]參見揚之水:《馬和之詩經圖》,《中國典籍與文化》2012年第1 期,第115-121頁。
[5][明]宋濂等撰:《元史》,中華書局1976年版,第3615頁。
[6]參見[元]趙孟頫撰:《農桑圖序》。任道斌編校:《趙孟頫文集》,上海書畫出版社2010年版,第201頁。
[7][清]王原祁、孫岳頒等纂輯:《佩文齋書畫譜》卷八十三“宋李公麟孝經圖”條,清康熙四十七年內府刻本,第1a-1b頁。
[8]見朱彝尊《經義考》中吳寬提到解縉總題林子奐《豳風圖》時的議論。[清]朱彝尊撰:《經義考》卷一一九“林氏《豳風圖》”條,清光緒二十三年浙江書局刻本,第6b頁。
[9][明]陳建撰:《皇明通紀》,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583頁。
[10][清]王原祁、孫岳頒等纂輯:《佩文齋書畫譜》卷八十五“元趙孟頫畫豳風圖”條,清康熙四十七年內府刻本,第1a-1b頁。
[11]參見《學詩堂記》。[清]清高宗撰:《御制文二集》卷十一,《清代詩文集匯編》第330 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50頁。
[12][清]汪由敦撰,張秀玉、陳才點校:《松泉集》卷十六跋一,黃山書社2016年版,第784頁。
[13][17][清]張照、梁詩正等編纂:《石渠寶笈》卷三十二“宋馬遠豳風圖”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05頁。
[14][明]倪元璐撰:《倪文貞集(外四種)》卷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06-207頁。
[15][明]王世貞撰:《弇州續稿》卷九,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4a頁。
[16][明]孫鑛撰:《書畫跋跋》續卷三“豳風圖”條,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9b頁。
[18]楊鐮主編:《全元詩》第59 冊,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223頁。
[19][清]清高宗撰:《御制詩集》初集卷八,《清代詩文集匯編》第319 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72頁。
[20][清]清高宗撰:《御制詩集》初集卷五,《清代詩文集匯編》第319 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36頁。
[21][清]林則徐撰:《林則徐全集》第9 冊,海峽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467頁。
[22][清]錢大昕撰:《潛研堂詩續集》,陳文和主編:《嘉定錢大昕全集》第十冊,鳳凰出版社2016年版,第374頁。
[23][清]許兆椿撰:《秋水閣詩集》卷六《題甘雨應祈圖為費蕓浦中丞作》,《續修四庫全書》第1472 冊,第608頁。
[24][清]清高宗撰:《御制詩集》三集卷六十六,《清代詩文集匯編》第323 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5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