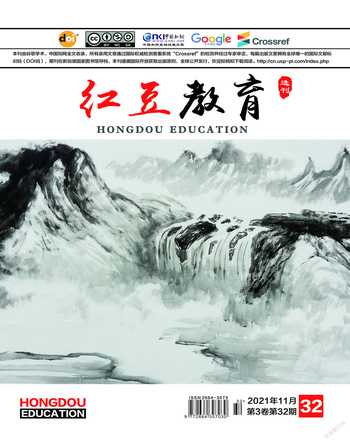兩峰對峙,釵黛合一
熊鑫
【摘要】林黛玉和薛寶釵是《紅樓夢》的兩個女主角,她們的才情智慧,可謂是難分仲伯,各有千秋,天真浪漫的林黛玉與溫柔端莊的薛寶釵分別寄托了作者曹雪芹不同的審美追求,二者都是作者欣賞與推崇的女性形象,并且在人物塑造的過程當中漸漸將其合二為一。而釵黛兩人的人物形象以及關系一直都是飽受爭議的話題,“釵黛合一”的觀點歷來爭執不斷,脂硯齋明白無誤地旁批到“釵、玉名雖兩個,人卻一身”。本文對“釵黛合一”的意象展開論述,對黛釵二人各自的形象特色以及兩位理想女性在曹雪芹筆下是如何走向融合等方面做進一步分析。
【關鍵詞】林黛玉;薛寶釵;對立;融合
一、“釵黛合一”觀點提出和論證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庚辰本)》是《紅樓夢》較早的一種版本,存世僅前八十回,帶有脂硯齋的大量批語,是紅學研究的重要依據,在這個版本的第五回和第四十二回中,脂批都透漏出二美合一的傾向[1]。
《紅樓夢》第五回賈寶玉夢游太虛仙境,翻閱了十二釵的判詞,而判詞也是“釵黛合一”最直接的證據,其中十二釵除薛寶釵和林黛玉以外都一人一畫、一人一詩,由此來暗示各位女子的命運和結局,而開卷的釵黛兩人在金陵十二釵的畫冊上是合并的,同詩同畫,兩人的判詞《終身誤》也是合并的,由此可知曹公深意。賈寶玉在太虛仙境中遇到了他的夢中情人,警幻仙姑的妹妹,乳名兼美,此人兼具黛玉寶釵之美:其鮮艷嫵媚神似于寶釵,風流婀娜則又似黛玉。寶玉、黛玉和寶釵三人名字也是頗有深意的,寶玉,“至貴者寶,至賢者玉”,而寶釵之寶,貴在其人品端正大方,黛玉之“玉”,得其堅貞,與之相對的是黛玉的性情。
《紅樓夢》第四十二回的總評中明確寫出二者合而為一,“釵、玉名雖兩個,人卻一身……,使二者合而為一……”。俞平伯先生由此提出“二美合一”,先生認為釵黛兩人雙秀雙絕,二者是一種并列、對稱的關系,不分上下,釵黛合并才是作者心中所追求的理想女性形象。但“釵黛合一”其實是作者曹雪芹在《紅樓夢》中塑造極致之美的意象的兩面,而俞平伯先生是最早發現“釵黛合一”這一意象的。“釵黛合一”是受“天人合一”思想的影響,寶釵是山中高士,而黛玉則是天上仙品,二中關系并非對立存在,而是可以和諧共處的。從寶釵和黛玉兩個角色在書中的定位來看,黛玉是完美愛情的化身,她風流婉轉情致纏綿,與寶玉志同道合;寶釵則是理想婚姻的化身,嫻熟美麗端莊高潔,能與寶玉相濡以沫,可謂大方之家,而萬艷同悲,美好的事物總是易碎的,歸于大悲劇的結局,兩者最終都逃不過“玉帶林中掛,金簪雪里埋”。
二、兩峰對峙:釵、黛人物形象的不同
《紅樓夢》中人物塑造是其一大亮點,莎士比亞幾十部戲劇創造了兩百多個成功人物,曹雪芹一部未完成的《紅樓夢》就創造了兩百多個經典人物形象,其中女性形象頗為出彩,占據了較大篇幅,曹雪芹用細致的語言對人物進行了刻畫,將人物塑造得惟妙惟肖,出神入化。林黛玉和薛寶釵作為作品的兩大女主角在前世便是情場冤家,曹雪芹對她倆的描繪注入的筆墨最多,也是塑造得最為成功的角色,各大家對她們的評論也眾說紛紜,關于兩者評論,自紅樓建夢以來就沒有停止過,由此成為紅樓的第一大公案。黛玉和寶釵雖說具有著很高的相似性,但二者作為曹公筆下的兩個精心刻畫的人物,也各具其特色,在來歷、出場、外貌、性格等方面有著顯著的差異。
(一)來歷
黛玉前世為絳珠仙子,為了還淚而入世。她人未出場,讀者便從賈雨村對黛玉的贊嘆得出其“言語舉止另是一樣,不與近日女子相同”的過人之處,之后賈府眾人眼觀黛玉“年貌雖小,其舉止言談不俗,身體面龐雖怯弱不勝,卻有一段自然的風流態度”,黛玉的不同凡響之處再次得到烘托;到了寶黛二人見面,黛玉“大吃一驚”[2],感覺“倒是像在哪里見過(寶玉)一般”,寶玉則是一笑,說:“這個妹妹我曾見過。”黛玉的亮相,由于“木石前緣”,形成了一種詩意、哲學、神話式的氣氛,她是攜帶超越世俗的超然之氣來到世間的。
寶釵的來歷被作者隱去,籠統地交代其幼年時便喪父,出身于“百萬之富”的“皇商”家庭,各省均有買賣承局。寶釵一出場便跟隨其兄薛蟠的“殺人官司”,為躲禍來依附賈府,但她個人的真正使命是“待選”秀女,作者有意強化了寶釵的世俗氣。
(二)出場
首先從出場時間來看,雖然釵黛進賈府安排在相連的兩回書中,但時間已間隔了將近一年。黛玉進府是省親前三年,對應書外是雍正十一年,而寶釵則是雍正十二年,雖然都是冬天,但寶釵比黛玉早一些時間,釵是初冬,黛是殘冬。
其次是進府次數不同。之所以黛玉進府比寶釵隆重熱烈,因為黛玉是第一次來江南,而寶釵則是第二次了。她第一次來府是雍正五年,雍正七年離開,是為了進京待選。兩人的身份地位是相等的,因為寶釵已是第二次了,歡迎程度略有不同。
(三)外貌
釵黛的不同是肉眼可見,是直觀的。在十二釵中,寶釵和黛玉的美色是旁人不可及的,曹公借用其他人的三兩言語生動地將兩位美人的美貌呈現在讀者眼前。第三回黛玉初入賈府時,曹公以他人的眼光來描繪黛玉的容貌,“見黛玉年貌雖小,其舉止言談不俗,身體面龐雖怯弱不勝,卻有一段自然的風流態度,便知他有不足之癥。”由此可見黛玉雖美,但是顯露不足之癥,黛玉的美是病態美。在第五回中,如此描述寶釵:不想如今忽然來了一個薛寶釵,年歲雖大不多,然品格端方,容貌豐美,人多謂黛玉不可及。由此可見,寶釵的美是容貌豐滿、端莊大方。兩人一個環肥,一個燕瘦,黛玉是清新脫俗之美,而寶釵是富貴之美。
(四)性格
林黛玉和薛寶釵在性格上存在著本質的區別,二者性格的對立是情與禮的對抗。從天性來看,曹公在塑造人物時,賦予林黛玉的特性是“才”,賦予薛寶釵的特性是“德”,才學靈氣是林黛玉所特有的人設,品德修養則是薛寶釵的典型特征。
黛玉是感性自由的化身,寶釵則是理智禮教的化身。無論是在詩才、樣貌、品格,寶釵都在十二釵之列的前端。而相比于黛玉,寶釵在詩作方面要稍遜一籌,少有黛玉的靈氣,只要求“主意清新,措辭不俗”,黛玉在行酒令道出《牡丹亭》的戲文“良辰美景奈何天”時告訴黛玉:“諸如這《西廂》《琵琶》以及《元人百種》,無所不有,他們是偷背著我們看,我們也卻偷背著他們看。”,由此可見寶釵對于這一類禁書也是有所了解,而她單從黛玉的兩句酒令便聽出其典故,我們可以猜想她的知識面可能遠遠比我們了解得更廣,熟知文章的內容才知道什么是禁忌,什么應該回避,這種種都是寶釵為了迎合封建社會的禮教,她所讀之物也是符合封建社會審美的,即使讀過禁書,為了維護她的大家閨秀的形象,是不會展露在外人面前的。賈寶玉前往梨香院探望病中的薛寶釵,薛姨媽留飯留酒。賈寶玉道:“酒不必燙熱了,我只愛吃冷的。”薛寶釵卻笑道:“寶兄弟,虧你每日家雜學旁收的,難道就不知道酒性最熱?若熱吃下去,發散的就快;若冷吃下去,便凝結在內,以五臟去暖他,豈不受害!從此還不快不要吃那冷的呢。”[3]賈寶玉聽這話說得有情理,便乖乖聽話放下冷的,命人暖來方飲。因為她見多識廣、生活習慣良好、注重日常保養,會生活。相比于林黛玉的才氣,寶釵的才更多的是在管理上,對于生活中的細枝末節了如指掌,能打理好賈府上上下下,是個當家的好手。
林黛玉認為看書學習只是個人閑情雅致,反對寶玉參加科舉,而寶釵支持寶玉走讀書做官之路,參加科舉考試,投入于仕途經濟做賈府的接班人。寶釵用怕熱推辭寶玉不去看戲,寶玉調侃道:“怪不得他們拿姐姐當楊妃,原來也體豐怯熱”,寶釵面對寶玉這番唐突的話,雖心里也有怒氣,但卻只是冷笑兩聲,依然坦然答道:“我倒像楊妃,只沒有個好哥哥好兄弟可以作得楊國忠的”,這背后就是在諷刺寶玉作為她和賈元春的弟弟,卻只知道在閨中“廝混”、不學無術,連個楊國忠都不如,倘若是黛玉,定是不會這般直接拆穿黛玉,對他如此苛求。寶釵的父親去世之后,家庭變故對她造成較大打擊,但見哥哥不成器為了體貼母親,便停書料理家務,家庭的變故并未使得她消沉或是放棄生存,相比于黛玉她更是堅韌地承擔起家庭里的部分責任,而這些早年間的經歷雖已讓她變得八面玲瓏、深知人情冷暖,可她卻并沒有因此而悲觀厭世、孤高自許,還是那個“腹有詩書氣自華”的女子,而且更加熱愛生活。
三、靈與肉的兩面:釵、黛的統一
從寶玉夢游太虛仙境中“兼美”人物形象的設定,以及《終身誤》的唱詞,我們都可以看出寶玉心中理想的形象是黛玉的性情美與寶釵的世俗美相融合的“兼美”形象。寶玉和黛玉同樣是封建社會的叛逆者,是黑暗中彼此的守望者,只有黛玉懂得寶玉的任性與自由,寶玉眼中的黛玉是心靈層面可遇不可求的精神伴侶;而寶玉對寶釵的感情僅僅是浮于表面的,和眾人一樣認為寶釵是個艷壓群芳端莊大方的大家閨秀,但是卻少了對于黛玉的那種偏愛,在寶玉眼里寶釵就是一具凡俗女性的軀體[4]。
釵黛兩個人的對立更像是靈與肉的對立。曹雪芹在刻畫林黛玉的美貌時,描寫的筆法刻意虛化,是一種主觀感受的美:心較比干多一竅,病如西子勝三分。寶玉初見黛玉,也是感受到似曾相識,而在《紅樓夢》中曹雪芹對于薛寶釵五官的刻畫細致入微,且寶釵從不化妝,她的美是健康典雅的,寶玉看見寶釵的酥臂時恨不得摸一摸,他眼中的寶釵就是一具凡俗女性的軀體。黛玉象征著人類作為人本身與生俱來的天然屬性,她追求自然、自由,會直率表達自己的喜好,天性敏感而靈動的她能夠敏銳地察覺到人情世態,但她依舊不會為了迎合世事而矯飾自己。寶釵則象征著人作為社會人所具有的世俗屬性,她端莊得體,與社會相處時內斂圓通,博學多才、溫柔嫻靜、世事洞明使得她虛美和偽善。但是寶釵對待并非完全虛偽,他是真心勸告寶玉要在仕途經濟上用心思,寶玉挨打時也是真的為寶玉傷心難過,但是與黛玉相比,寶釵這一切的本源都是基于功利的,這也是作為人在社會上生存必須要作出的改變。
結論
《紅樓夢》這本書塑造了許許多多鮮活的人物形象,以賈寶玉與林黛玉、薛寶釵的愛情婚姻悲劇為主線,展現了真正的人性美和悲劇美。眾多人物形象中,十二釵是最為人稱道的,不同人物有著不同的命運,而十二釵唯獨釵黛二人同用一判詞也寄寓了作者曹雪芹的獨特審美追求。
釵黛兩人形象象征著人的天然屬性與世俗屬性,也是每個人在生存意義、生存方式所選擇是所面臨的矛盾,本身并沒有所謂的對與錯,人生來向往著自由自在、無拘無束,倘若想要保持它就必須要付出代價;同時,一個人想要很好地融入于社會當中就必須做出改變,讓自己的個性變得更加合群,這個過程雖然痛苦但是倘若能夠機敏地處理人與社會的關系,最終卻能夠獲得世俗意義上的成就。這種兩難的矛盾是人處在社會當中必須經歷的,人人都有自己的理想但又不得不顧及現實,人人都力圖兼顧而又難以兼顧,因而“兼美”的形象只能出現在賈寶玉的夢里。
參考文獻:
[1]郭征南.《紅樓夢》六十七回考辯[D].曲阜師范大學,2010.
[2]曹雪芹,高鶚.紅樓夢[M].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10.
[3]楊真真.“任是無情也動人”——試析薛寶釵與牡丹[J].湖北科技學院學報,2013,33(10):88-90.
[4]林柳生,郭聯發.《牡丹亭》和《紅樓夢》中情與理的比較研究[J].南昌教育學院學報,2005(04):2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