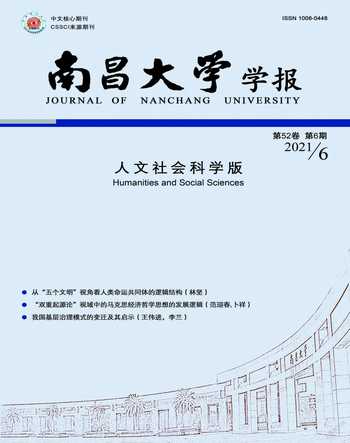論事件的內(nèi)涵、屬性及多樣化關(guān)系
杜軍 劉利民
摘 要:事件是認(rèn)知語義學(xué)的關(guān)鍵概念之一。按照戴維森的異態(tài)一元論,客觀事件是物理事件,物理事件引發(fā)的心理事件是人們運(yùn)用不同層面的心理語言描述同一物理事件。物理事件與心理事件之間不是決定論的因果關(guān)系,而是心理事件附隨于物理事件,且心理事件涌現(xiàn)出超越物理事件的新意義。“事件”實(shí)際上應(yīng)分為實(shí)存事件、原生事件、次生事件三個(gè)不同層面。實(shí)存事件是客觀存在的事件,原生事件指人們使用普通心理語言描述的原發(fā)性心理事件,次生事件是指原生事件與其他心理事件相互作用而生成的復(fù)雜心理事件。
關(guān)鍵詞:認(rèn)知語義學(xué);異態(tài)一元論;心理-物理隨附性;實(shí)存事件;原生事件;次生事件
中圖分類號(hào):H030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1006-0448(2021)06-0120-08
自20世紀(jì)中期以來,“事件”成為哲學(xué)、語言學(xué)領(lǐng)域的熱點(diǎn)話題;然而,既有研究未能清晰地界定事件的概念、內(nèi)涵與屬性,模糊化事件與事物、行動(dòng)的界限,故對(duì)后續(xù)以事件為研究對(duì)象的認(rèn)知語義學(xué)及語言類型學(xué)的發(fā)展不利。其實(shí),事件的本質(zhì)與屬性這一問題是一個(gè)長(zhǎng)期困擾哲學(xué)家、語言學(xué)家、心理學(xué)家的疑難問題。綜觀兩千多年的事件研究史,最初由柏拉圖提出“事件是發(fā)生的事情”[1](P35),到事件與事實(shí)、事物、行動(dòng)的辨析[2](P1-19),再到事件的整合性、規(guī)約性、層級(jí)性的探討[3],又到事件的空間及時(shí)間屬性的探析[4],關(guān)于事件的內(nèi)涵與本體性的討論從未停止。美國語言哲學(xué)家戴維森(D.Davidson)在1967年就在《行為句的邏輯式》一文中,采用形式邏輯分析的方法論證了事件論元的存在及其個(gè)體化;但他的觀點(diǎn)未在語言學(xué)中引起注意和討論,以至于相關(guān)討論至今仍停留在“事件不是一個(gè)基本概念,只能由時(shí)間這一概念進(jìn)行間接刻畫”[5](P17)的認(rèn)識(shí)上。
從邏輯上來講,人們認(rèn)知客觀存在的同一事件理當(dāng)相同,反映人類認(rèn)知思維的語言表達(dá)也應(yīng)相同;然而,實(shí)際日常使用中的語言表達(dá)卻多樣化,進(jìn)而生成語言內(nèi)差異和語際類型學(xué)差異[6](P287)。如是,多樣化的語言表達(dá)是否表征多樣化的事件、事件的多樣化表征是否具有共核引起筆者關(guān)注,進(jìn)而提出本文的研究問題:(1)在本體論層面,事件的內(nèi)涵和屬性是什么,從而解答事件的多樣化表征是否有共核;(2)在認(rèn)識(shí)論層面解構(gòu)事件的內(nèi)涵,確認(rèn)認(rèn)知視域下事件的屬性,是心理事件還是物理事件,兩者的關(guān)系如何;(3)在語言表達(dá)層面,分析多樣化的語言表征與事件的多樣化之間的關(guān)系,進(jìn)而構(gòu)建識(shí)解復(fù)雜事件的認(rèn)知模型,最終形成在本體、認(rèn)知和語言表征三個(gè)維度探究事件的研究范式。
基于以上研究問題,本文擬在本體論層面,通過對(duì)比分析戴維森與奎因(Quine)的事件哲學(xué)思想之異同,探討事件的本體論屬性;在認(rèn)識(shí)論層面,基于戴維森的異態(tài)一元論,論證心理事件存在的合法性和事件的心理-物理隨附性,從而闡釋事件的內(nèi)涵,明確認(rèn)知視域下事件的屬性;在語言表達(dá)層面,基于美國認(rèn)知語義學(xué)家倫納德·泰爾米的宏事件理論,通過對(duì)比分析英漢語狀態(tài)變化事件語料,解釋多樣化的語言表征與多樣化的事件之間的關(guān)系,借用生物學(xué)術(shù)語構(gòu)建實(shí)存—原生—次生事件識(shí)解模型。
一、事件的本體性質(zhì)
事件是否具有本體論屬性關(guān)乎事件能否被個(gè)體化,使事件成為獨(dú)立的對(duì)象;奎因在專著《對(duì)話中的奎因》中論及,事件的類別十分廣泛,內(nèi)涵很難界定,如何獲得事件個(gè)體性是一個(gè)不容易妥善解決的難題[7](P137)。奎因認(rèn)為,每一個(gè)事件總是宇宙中的事件的一部分,如果孤立地認(rèn)知一個(gè)事件,便無法確定其意義。按此,事件無法被個(gè)體化。然而,戴維森認(rèn)為事件構(gòu)成一個(gè)基本的本體論范疇,有充分理由將事件視為實(shí)體,由此事件獲得個(gè)體性[8](P139)。戴維森承認(rèn),每一個(gè)事件的確是宇宙中的事件的一部分,一個(gè)事件的變化極有可能引發(fā)另一個(gè)事件的變化[8](P145);為識(shí)解事件,人們有可能將復(fù)雜事件簡(jiǎn)單化割裂成兩個(gè)甚至更多的子事件,而忽略子事件之間的因果鏈,從而錯(cuò)誤地個(gè)體化事件。因此,戴維森的事件的個(gè)體化不是將事件割裂,而是與事件的同一性相關(guān)。他巧妙地運(yùn)用語言哲學(xué)的方法,將事件實(shí)體與事件描述分開。他認(rèn)為,對(duì)于客觀世界存在的“同一事件”,當(dāng)人們用嚴(yán)格的物理語言描述該事件時(shí),該語言表達(dá)式表征的是物理事件;反之,當(dāng)人們出于不同的意圖,用心理語言進(jìn)行描述時(shí),該事件被表征為心理事件[9](P108)。如對(duì)“天下雨”這一客觀世界存在的事件,如果將其描述為“因?yàn)樗魵庥隼涠夯癁樗畯奶炜章湎隆保@是物理事件;如果將其描述為“下大雨了、落點(diǎn)了、下毛毛雨了、天上落下生命之泉”等,這些是心理事件。不論是物理事件還是心理事件,兩者都有相同的因果聯(lián)系,是“同一個(gè)”事件的不同實(shí)現(xiàn)。這就是“天下雨”這一事件可個(gè)體化的依據(jù)。
關(guān)于事件的本體屬性,奎因又提出了另一個(gè)命題:基于事件描述句的因果關(guān)系或者基于事件實(shí)例之間的相似性的分析談?wù)撌录鲆暱赡艽嬖诘氖录漠愘|(zhì)性[7](P135)。異質(zhì)性論說認(rèn)為以因果關(guān)系作為事件個(gè)體化的標(biāo)準(zhǔn)行不通。因?yàn)樵S多事件是物質(zhì)的變化,變化的事件至少涉及兩個(gè)位置或兩種狀態(tài);相應(yīng)地,我們可以用多個(gè)不同的句子描述此事件,每個(gè)句子可能只描述客觀存在的“同一事件”的一部分,具體哪一部分取決于人們的意向性態(tài)度。即是說,事件描述句可能僅是不同的“部分事件描述句”,凸顯的是事件的異質(zhì)性,忽略事件的整體性;如此,不可能個(gè)體化事件[7](P136)。奎因的論述貌似很合理,如翻譯界對(duì)古詩“月落烏啼霜滿天”中“月落”的翻譯存在極大的爭(zhēng)議:此句中的“月落”是指掛在西邊天空中的月亮正在向下落去,還是已經(jīng)落下[10](P215)?日落具有時(shí)間進(jìn)程屬性:起始、持續(xù)、結(jié)果,而這些屬性可能被人們單一化地聚焦,形成“開始……、正在……、已經(jīng)……”等割裂式的描述,而不能形成整個(gè)事件的個(gè)體化。可是,戴維森僅接受了奎因的部分意見。他遵循唯物主義的觀點(diǎn),提出一切實(shí)體與事件都是物理的,可以用時(shí)空特性界定“個(gè)體化事件”;但當(dāng)論及包含人的意圖等心理因素的事件時(shí),他主張采用區(qū)分事件及事件描述語的方法將其個(gè)體化。這是因?yàn)樵谌粘I钪校藗儾惶赡芤矝]有必要從科學(xué)或形而上學(xué)的角度識(shí)解事件;人們?cè)诰唧w情境中通常以自我感知認(rèn)知事件,從而生成多樣化的事件表征。由此觀之,按照戴維森的觀點(diǎn),客觀世界中的事件只有一個(gè),以物理定律描述的事件稱為物理事件;基于物理事件,賦予人類理性原則(如命題態(tài)度、意圖)等描述的事件是心理事件。物理事件與心理事件具有不同的性質(zhì),其差異性由描述事件使用的語言決定;就此而言,事件的描述比事件本身更為重要。
二、事件的心理認(rèn)知屬性
(一)事件的異態(tài)一元性
既然客觀世界存在的是同一事件,人類認(rèn)知是對(duì)客觀世界的反映,那么從邏輯上來講,不同的人對(duì)同一事件的認(rèn)知理應(yīng)相同,反映人類認(rèn)知思維的語言表達(dá)也應(yīng)相同;然而實(shí)際上,當(dāng)人們使用語言表達(dá)個(gè)體事件時(shí),事件表征卻是多樣化的。究其原因,在于不同的人將客觀存在的同一事件表征為不同的心理事件,故在語言表達(dá)上就會(huì)出現(xiàn)語言內(nèi)差異及語際間的類型學(xué)差異。如是,物理事件與心理事件兩者的關(guān)系如何值得探究。
對(duì)于這樣的問題,戴維森在《心理事件》中就同一事件中的物理事件及與之相對(duì)應(yīng)的心理事件之間的對(duì)接定律提出“異態(tài)一元論”三原則:第一條,因果相互作用原則,心理事件以因果方式與物理事件互相作用;第二條,因果法則即決定性規(guī)律法則;第三條,基于因果法則的心理事件不由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嚴(yán)格規(guī)律預(yù)測(cè)或解釋,而是由屬于心理事件的非嚴(yán)格的心理-物理規(guī)律解釋[9](P105-121)[11](P128)。三條原則看似矛盾,其實(shí)不然,它們從不同的視角解析物理事件與心理事件的性質(zhì)以及兩者之間的關(guān)系。
第一條原則從本體論層面指出,一切事件都是物理事件;但是由于人類心理的復(fù)雜性,故人類心智可能對(duì)此事件賦予兩種甚至多種解釋。當(dāng)人們對(duì)同一事件賦予不同的認(rèn)知焦點(diǎn)與背景或者給予不同的注意力視窗時(shí),人們對(duì)該事件的語言描述就會(huì)呈現(xiàn)多樣化。簡(jiǎn)言之,描述的事件對(duì)象的外延相同,但描述的方式不同。據(jù)此,人們?cè)趯?duì)客觀世界的“同一事件”進(jìn)行具體描述時(shí),用的是物理語言還是心理語言描述,就會(huì)相應(yīng)地生成物理事件或心理事件,盡管兩者在本體層面是“同一”的。心理事件由物理事件引起,但兩者的性質(zhì)不同。“引起”不是說物理事件是因,心理事件是果,而是說可描述為物理事件的同一客觀事件引發(fā)了心理語言的描述。
第二條原則從認(rèn)識(shí)論層面出發(fā),僅適用于闡釋物理事件。事件有多種描述方式;用遵循嚴(yán)格因果法則的物理學(xué)語言描述的事件就是物理事件。物理事件的變化可能導(dǎo)致心理事件的變化,也可能不引發(fā)變化。用物理學(xué)語言可以表述一個(gè)對(duì)象主體的行為以及主體與環(huán)境之間的關(guān)系,但不能描述心理事件。因?yàn)樾睦硎录惓?fù)雜,具有整體性、層級(jí)性等特點(diǎn),并且一個(gè)心理事件可能引發(fā)一個(gè)或一系列心理事件;故對(duì)它的描述需要其他心理謂詞參與。同時(shí),用心理謂詞刻畫的意向性狀態(tài)不能還原為物理謂詞所表達(dá)的意義。例如,“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中“蛇咬”導(dǎo)致流血,引發(fā)心理描述,如“疼痛、恐懼”等;而10年后,被“蛇咬”的物理事件已經(jīng)不存在,可是恐懼的心理描述依然存在。
第三條原則從語言論層面出發(fā),稱為心理異態(tài)性原則。任何心理事件都不是獨(dú)立自存的,總是與個(gè)體的其他心理事件相互作用,所以決定性意義的嚴(yán)格規(guī)律不適用于闡釋心理事件。描述心理事件的心理謂詞不僅隨附于物理謂詞,還有賴于其他心理謂詞。同時(shí),因?yàn)樾睦淼恼w性特征,一個(gè)命題態(tài)度的內(nèi)容總是由另一個(gè)(些)命題態(tài)度的內(nèi)容所導(dǎo)出,且又可以導(dǎo)出別的命題態(tài)度。例如就“A red,red rose”的意義而言,可能因個(gè)人經(jīng)歷而導(dǎo)出“某人正在表達(dá)愛情”等命題[12](P204)。這一思想與奎因的語義整體論相符。由此,我們?cè)诮缍ㄕJ(rèn)知視域下的“事件”時(shí)要明確心理事件存在的合法性;要考量心理和物理事件之間既相互依賴又各自獨(dú)立、既相互依存又不完全決定的因果關(guān)系,即戴維森的心理對(duì)物理的“隨附性”。
(二)事件的心理-物理隨附性
戴維森認(rèn)為,事件的心理-物理隨附性最清晰的形式是用物理事件識(shí)別心理事件[8](P139)。如大雪融化或是凍結(jié)一段時(shí)間后,可能發(fā)生雪崩。通常情況下,雪崩的原因和它所波及的范圍是我們關(guān)注的焦點(diǎn)。此時(shí),雪崩事件的原因和結(jié)果在人類認(rèn)知概念系統(tǒng)中被凸顯,即雪崩事件的因果關(guān)系得以凸顯。這樣,通過語言對(duì)雪崩進(jìn)行描述或者重復(fù)描述才具有意義。然而,奎因就此表達(dá)相反觀點(diǎn):“(我)不會(huì)將事件簡(jiǎn)單地看作物理對(duì)象,事件來自句子而非實(shí)體”[7](P135),因此需要重視語言中的單稱詞項(xiàng)(singular terms),因?yàn)閱畏Q詞項(xiàng)確認(rèn)事件的身份。顯然,奎因認(rèn)為只有指稱對(duì)象才能個(gè)體化事件。由于單稱詞項(xiàng)就是具體指實(shí)在的某個(gè)人或物的名詞或短語,因此我們只能說某人做了某事,而不能說某事如何。戴維森則不同意。他認(rèn)為,句子就是普通的句子,是否包含單稱詞項(xiàng),絲毫不影響該句的指稱事件[11](P121)。即便一個(gè)句子不是以單稱詞項(xiàng)為主語,我們?nèi)匀豢梢酝ㄟ^描述事件的句中成分之間的關(guān)系將某個(gè)事件理解為一個(gè)個(gè)體事件,無須以一句話中的單稱詞項(xiàng)作為標(biāo)準(zhǔn),如下[9](P95):
例1:Doris’s capsizing of the canoe occurred yesterday.
例2:Doris capsized the canoe yesterday.
以上兩句的意義從實(shí)在的物理事件角度來看沒有差異,不論是例1“多麗絲昨天(至少有一次)船翻了”,還是例2“多麗絲的(一次)船翻發(fā)生在昨天”,客觀事件即是有一個(gè)名為Doris的人經(jīng)歷了船翻事件。不論是例1聚焦船翻這一事件,還是例2聚焦經(jīng)受者Doris;雖然兩個(gè)語言表達(dá)式的焦點(diǎn)不同,但是兩者的基本含義沒有本質(zhì)區(qū)別。因此,戴維森認(rèn)為即便一個(gè)沒有單稱詞項(xiàng)的普通句子也可以表達(dá)和指稱一個(gè)事件。這意味著有可能從句子本身的結(jié)構(gòu)和成分考慮它是否以及如何與物理事件相關(guān)聯(lián)。然而,事件描述語卻無法與心理事件直接關(guān)聯(lián)。一句話與一個(gè)心理事件關(guān)聯(lián)另有因素決定,無法直接從這句話中尋找這種因素[11](P123)。據(jù)此,句子是“以某種方式描述事件”;然而,句子僅是句子而已,無論句中是否包含單稱詞項(xiàng),都能保持句子與事件的關(guān)聯(lián)。單稱詞項(xiàng)可能與指稱物理事件相關(guān),而不一定與附隨于物理事件的心理事件相關(guān),因?yàn)槲锢硎录⑹录枋稣Z視角、事件描述語意圖等都可能作用于心理事件,這些因素統(tǒng)一于事件的心理-物理隨附性之中。
任何心理事件都隨附于物理事件,但又涌現(xiàn)(emergence)出新的特征[8][13]。如是,心靈是命題態(tài)度的集合,當(dāng)具有不同經(jīng)歷因而心理狀態(tài)不同的語言使用者處于特定的意向性狀態(tài)時(shí),采用意向性的謂詞,表達(dá)特定的信念、愿望,就會(huì)生成語言學(xué)層面特定的意義。換言之,當(dāng)語言使用者對(duì)客觀世界的同一事件進(jìn)行描述時(shí),客觀世界存在的物理事件及與之對(duì)應(yīng)隨附的心理事件、人們選取的描述事件的意向性態(tài)度等都會(huì)作用于語言表征,就會(huì)生成“整體意義不等于部分意義之和”的語言意義。
三、狀態(tài)變化事件的同一與異質(zhì)問題分析
按照異態(tài)一元論推理,作為語言學(xué)研究對(duì)象的事件主要是心理事件。心理事件具有看似矛盾的整合性和異質(zhì)性。本節(jié)基于美國認(rèn)知語義學(xué)家倫納德·泰爾米的宏事件對(duì)心理事件進(jìn)行闡釋。宏事件由泰爾米于1972年首次提出,是指由復(fù)雜句或簡(jiǎn)單句表征的復(fù)雜事件[6](P213);其中,主要事件稱為框架事件(framing event),次要事件稱為副事件(co-event)。框架事件構(gòu)建宏事件的結(jié)構(gòu),是抽象的圖式;副事件為宏事件提供背景、原因、方式等,起著充實(shí)、細(xì)化框架事件的作用[6](P217-218)。宏事件是上層概念,包括五種類型:運(yùn)動(dòng)、體相、狀態(tài)變化、行動(dòng)關(guān)聯(lián)和實(shí)現(xiàn)事件[6](P213)。五種事件具有高度相似的語義、句法結(jié)構(gòu)和相同的概念化模式[6](P213)。本文僅以狀態(tài)變化事件作為分析對(duì)象。
狀態(tài)變化事件是指“事物的狀態(tài)改變或是原狀態(tài)的保持不變”[6](P236),“改變”與“保持不變”可類比運(yùn)動(dòng)事件中的“運(yùn)動(dòng)”與“靜止”兩種狀態(tài)。事物的“改變”,即事物通過轉(zhuǎn)換(transition,類似運(yùn)動(dòng)事件中的“move”)達(dá)到狀態(tài)的改變。這一事件的核心是“狀態(tài)變化”,即“完成轉(zhuǎn)變,成為新的狀態(tài)”,相當(dāng)于運(yùn)動(dòng)事件中的“移動(dòng)到達(dá)目的地”。以狀態(tài)變化事件的界限狀態(tài)和離散狀態(tài)的相互作用為依據(jù),將其分為兩大類、五小類[14](P70)。有界連續(xù)狀態(tài)(bounded gradient transition type)是指物體或情景在有界范圍內(nèi)的連續(xù)的漸變過程;有界離散狀態(tài)(bounded discrete transition type)是指物體或情景在有界范圍內(nèi)的分離且完全實(shí)現(xiàn)的狀態(tài)變化;無界連續(xù)狀態(tài)(unbounded gradient transition type)是指物體或情景在無界范圍內(nèi)的連續(xù)的漸變過程;無界離散狀態(tài)(unbounded discrete transition type)是指物體或情景在無界范圍內(nèi)的分離且完全實(shí)現(xiàn)的狀態(tài)變化;靜止?fàn)顟B(tài)(change within or with a state)是指物體或情景長(zhǎng)期停止于某種狀態(tài)。如下[14](P71):
例3:I xeroxed his original letters.
例4:The meat rotted away.
“I xeroxed his original letters”描述的是無界離散狀態(tài)變化事件“我復(fù)印他的原信件”。這一事件被不斷地重復(fù),從整體上來看,“我復(fù)印他的原信件”這個(gè)事件一直沒有任何改變。然而,“我”的每一次復(fù)印的結(jié)果卻是不同的,即每一次復(fù)印可被切分成不同的事件片段,如對(duì)每一頁的復(fù)印操作;即是說,“復(fù)印”這一整體事件可以被切分成N個(gè)不同的小事件。換言之,“我復(fù)印他的原信件”這一整體事件是N次相似事件的整合。故此例表明事件具有異質(zhì)性,這符合奎因的觀點(diǎn)。然而,依據(jù)戴維森的觀點(diǎn),不論多少次“單次間隔式”的復(fù)印都只是整體“復(fù)印”事件的一個(gè)隱性的片段。通常情況下,人類識(shí)解事件時(shí)首要遵循格式塔原則,將其識(shí)解為一個(gè)心理事件表征,該表征從事件的“整體性”出發(fā),而不必單稱化地表征每一次復(fù)印活動(dòng)。
“The meat rotted away”描述的是無界連續(xù)狀態(tài)變化事件“肉腐爛了”。“肉腐爛”這一事件如果在某一時(shí)刻用肉眼觀察,通常很難看出腐爛程度的不同;然而,在相對(duì)長(zhǎng)的時(shí)間段內(nèi)持續(xù)觀察,實(shí)際上經(jīng)過一定時(shí)間后,肉腐爛的程度是不一樣的,故此時(shí)“肉腐爛”事件合理化地被切割為N段異質(zhì)性“腐爛”事件。例4也表征事件的異質(zhì)性。然而,不論多少次“單次漸變式”的腐爛都只是整體“肉腐爛”事件的一個(gè)隱性的片段。因?yàn)槿藗冏R(shí)解事件時(shí)通常都以事件的“整體性”感知為出發(fā)點(diǎn),故語言表征事件的方式采用個(gè)體化表征。從例4可以看出,心理事件表征既可實(shí)顯物理事件的細(xì)節(jié),也可舍去細(xì)節(jié)表征態(tài)體。
心理事件的異質(zhì)性與整合性之辯,不光表現(xiàn)在無界狀態(tài)變化事件中,在有界狀態(tài)變化事件中更為突出,如下[14](P71):
例5:He choked to death on a bone.
例6:The log burned up in one hour.
“He choked to death on a bone”描述的是有界連續(xù)狀態(tài)變化事件“他被骨頭噎死了”。從事件的因果性出發(fā),因?yàn)樗裕校┕穷^,呼吸道被阻塞,導(dǎo)致他死亡。從事件的時(shí)間屬性分析,在(他)被噎住的整個(gè)過程中,從噎住—大口呼吸—粗聲呼吸—呼吸困難—窒息—死亡,整個(gè)過程表現(xiàn)呼吸道被阻塞后不同程度的呼吸困難的異質(zhì)性變化,直到(他)呼吸的終結(jié)。不同程度的呼吸困難癥狀貌似體現(xiàn)事件的異質(zhì)性。然而,從人類認(rèn)知心理在線構(gòu)建過程來看,無論呼吸困難程度差異如何,都被整合為“窒息至噎死”這一個(gè)體化事件。
“The log burned up in one hour”描述的是有界離散狀態(tài)變化事件“原木在1小時(shí)內(nèi)燒盡”。此句由時(shí)間詞“1小時(shí)”凸顯事件的整體性,因?yàn)榛鸪掷m(xù)燃燒1小時(shí),故原木被燒盡(成灰)。不論在整個(gè)燃燒過程中,原木的“被燃燒”狀態(tài)被切分成多少個(gè)具有異質(zhì)性變化的階段,N個(gè)具有異質(zhì)性變化的階段都會(huì)被整合為“原木在1小時(shí)內(nèi)燒盡”這一事件。
從事件的異質(zhì)性和整合性的闡釋,不難推導(dǎo)出日常使用語中的事件描述語必然呈現(xiàn)多樣化的趨勢(shì),從而生成語際內(nèi)和語際間類型學(xué)差異。然而,異態(tài)一元論指出,多樣化事件表征必然具有共核;故對(duì)客觀存在的同一事件的不同描述語可能具有相同的深層語義結(jié)構(gòu),這一點(diǎn)對(duì)語言類型學(xué)劃分具有重要的指導(dǎo)意義。
狀態(tài)變化事件可概念化為一個(gè)認(rèn)知域,內(nèi)含四個(gè)語義成分:焦點(diǎn)實(shí)體(figure entity)、背景實(shí)體(ground entity)、激活過程(activating process)和系聯(lián)功能(association function)。系聯(lián)功能獨(dú)自或與背景實(shí)體一起構(gòu)成“核心圖式”,是劃分語言類型的重要標(biāo)志[6](P237-238)。焦點(diǎn)實(shí)體(figure entity)是指句中當(dāng)前最受關(guān)注的焦點(diǎn),它的境況如何常由語境決定,是句子要表達(dá)的主題。背景實(shí)體(ground entity)是指表述與焦點(diǎn)實(shí)體成分相對(duì)的事物,常被認(rèn)為是焦點(diǎn)實(shí)體成分的參照。激活過程(activating process)是指表述焦點(diǎn)實(shí)體與背景實(shí)體之間的動(dòng)作過程,表示事件發(fā)生的動(dòng)力(dynamism),具有轉(zhuǎn)變與守恒(transition and fixity)兩種意義。系聯(lián)功能(association function)是指表述焦點(diǎn)實(shí)體與背景實(shí)體之間的關(guān)系。狀態(tài)變化事件的深層語義結(jié)構(gòu)如下[6](P238):
例7:I blew the candle out.
(我把蠟燭吹滅了。)
深層語義結(jié)構(gòu):[I “A MOVED”the candle TO EXTINGUISHMENT]WITH-THE-CAUSE-OF[I blew on /it]。
例8:The candle blew out.
(蠟燭熄滅了。)
深層語義結(jié)構(gòu):[the candle“MOVED” TO EXTINGUISHMENT]WITH-THE-CAUSE-OF[SOMETHING blew on it]。
“I blew the candle out”表達(dá)的是施事性狀態(tài)變化事件,因?yàn)椤拔掖迪灎T”導(dǎo)致“蠟燭熄滅”。“我吹蠟燭”是原因,“蠟燭熄滅”是結(jié)果。“The candle blew out”表達(dá)的是非施事性狀態(tài)變化事件,因?yàn)椤癝OMETHING blew on the candle”導(dǎo)致“the candle“MOVED” TO EXTINGUISHMENT”。兩例的語義結(jié)構(gòu)既凸顯事件的因果性,又凸顯事件的過程性;甚至從狀態(tài)變化事件實(shí)現(xiàn)的“結(jié)果”來看,兩例中“因?yàn)椋吃颍灎T熄滅了”,凸顯事件的同一性。
例8中,“蠟燭”是焦點(diǎn);“熄”(副事件)融合于動(dòng)詞“熄”之中,身兼二職,既表達(dá)了激活過程(狀態(tài)改變),又表達(dá)了該事件的原因;“滅”表示路徑,即“蠟燭”的狀態(tài)變化;“了”表示背景,表示狀態(tài)變化的完成。核心圖式由路徑“滅”和虛化的背景“了”(表示事件完成的時(shí)體標(biāo)記)構(gòu)成。例8中,“the candle”是焦點(diǎn),“blew”表示除狀態(tài)變化外詞化并入事件的原因,“out”表示路徑,背景實(shí)體缺失。
分析例9發(fā)現(xiàn),客觀世界中的同一事件是“蠟燭熄滅了”。如果用物理謂詞描述,即是“由于氣體流動(dòng),導(dǎo)致蠟燭四周溫度降低,氧化反應(yīng)中止進(jìn)行,因而‘蠟燭熄滅了’”。
例9:蠟燭熄滅了。/The candle blew out.
然而,除非是在遵循嚴(yán)格定律的科學(xué)范疇中,否則一般人的認(rèn)知識(shí)解并非如此,而是基于感知的心理事件表征,這樣的表征通常用心理謂詞予以描述。如果用心理謂詞描述同一事件,由于人類心理的復(fù)雜性,該句極有可能被賦予不同的施動(dòng)、焦點(diǎn)等,故有相同因果關(guān)系的同一事件在英漢語中有不同的表征方式。如例9中英語的核心圖式由衛(wèi)星語素“out”表征,而漢語的核心圖式由路徑“滅”和虛化的背景“了”表征,體現(xiàn)出語言類型學(xué)差異。簡(jiǎn)言之,使用不同的心理謂詞,可生成不同的心理事件描述語;然而,由于同一事件具有相同的邏輯因果關(guān)系,故而即使是不同的事件,描述語表征的仍然是同一事件。
雖然客觀世界僅存在“同一事件”,卻因?yàn)槿祟愋睦淼膹?fù)雜性,人們基于不同的意向性態(tài)度、情感等心理內(nèi)容和機(jī)制,遵循嚴(yán)格或非嚴(yán)格的因果法則,對(duì)同一事件進(jìn)行物理或心理語言描述,從而生成日常使用語言中異態(tài)化的語言表達(dá),凸顯事件的心理-物理隨附性。同時(shí),因?yàn)槿祟愓J(rèn)知概念系統(tǒng)中的概念整合識(shí)解方式,具有因果關(guān)系的物理事件與心理事件也可被個(gè)體化為同一事件,又因?yàn)樾睦硎录g關(guān)系鏈的存在,心理事件描述語涌現(xiàn)出超物理事件描述語的信息,故生成“整體意義不等于部分意義之和”的意義。
四、事件的認(rèn)知識(shí)解
基于前述分析,本文在此借用生物學(xué)術(shù)語,進(jìn)一步提出識(shí)解復(fù)雜事件的認(rèn)知模型,即實(shí)存—原生—次生事件識(shí)解層面的觀點(diǎn)。
實(shí)存事件是指在時(shí)空中實(shí)際發(fā)生的自然事件本身,也是前述中提及的客觀事件,其顯著性特征是同一性和可感知性。實(shí)存事件用物理語言描述,如科學(xué)家對(duì)日食的概念界定:“當(dāng)月球運(yùn)動(dòng)到太陽和地球中間,如果三者正好處于一條直線時(shí),月球就會(huì)擋住太陽射向地球的光,月球身后的黑影正好落到地球上,就發(fā)生日食”;又如植物學(xué)家對(duì)秋天楓葉變紅的界定:“因?yàn)闂魅~片中有花青素,它在酸性液中呈紅色。當(dāng)進(jìn)入深秋季節(jié)后,氣溫降低,光照減少,楓葉片細(xì)胞液此時(shí)呈酸性,整個(gè)葉片便呈現(xiàn)紅色。”
參見百度百科官網(wǎng),https://baike.so.com/doc/5335835-5571274.html.
原生事件是指原發(fā)性心理事件,人們通常基于對(duì)事件的直觀感知,使用普通心理語言描述,最接近物理性描述語言。原發(fā)性心理事件分為兩個(gè)層面:第一層面的原發(fā)性心理事件凸顯現(xiàn)象性特征,遵循規(guī)則,可預(yù)測(cè),忠實(shí)于個(gè)體主觀感知,如“棉衣給你溫暖或者你穿上棉衣就暖和了”;第二層面的原發(fā)性心理事件凸顯人類感知事件的共性,客觀世界中的事件紛繁多樣,我們不一定能把握其本質(zhì),只能以語言方式操作實(shí)際感知,即語言所按住的共性感知。因?yàn)閺倪壿嬌蟻碇v,所有人的生理結(jié)構(gòu)、神經(jīng)結(jié)構(gòu)都是一樣的,所以事件給我們的感知應(yīng)是一樣的[15](P36),因此,第二層面的原發(fā)性心理事件具有普遍性、可驗(yàn)證性和規(guī)約性。通常使用接近于物理性語言的事件表達(dá)式,如“由于棉花的松散結(jié)構(gòu),因而棉衣具有保溫的作用”。
次生事件是指原發(fā)性心理事件與另一個(gè)(或一些)心理事件相互發(fā)生作用而生成的復(fù)雜心理事件。次生事件較之原發(fā)性心理事件更加依賴人對(duì)客觀外在世界的主觀感知及認(rèn)知識(shí)解方式。次生事件基于人們對(duì)客觀外在世界的直觀感知,但又凸顯其涌現(xiàn)性意義(包括但不限于人類的情感、記憶、意向性等心理因素)的介入。次生事件被賦予不可預(yù)測(cè)性和可派生性,在語言層面表現(xiàn)為多樣化、異態(tài)化的心理事件描述語,如日食也可被描述為“天狗食日”。在此以例10為考察點(diǎn),具體闡釋事件的認(rèn)知識(shí)解模型。
例10: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
例10中“紅入桃花嫩”的實(shí)存事件的描述語可能是“因?yàn)樘一ㄊ遣煌该鞯奈镔|(zhì),當(dāng)桃花表面吸收可見光段中紅光(605—700 nm)以外的其他波長(zhǎng)的光線,只有紅光被桃花反射而被人眼捕捉到,因此桃花看上去是紅的”;“青歸柳葉新”的實(shí)存事件的描述語可能是“因?yàn)闃淙~中有一種葉綠素的物質(zhì),當(dāng)葉綠素足夠時(shí),柳葉就綠了”。不難看出,以上兩個(gè)描述句的實(shí)存事件是時(shí)空中發(fā)生的自然事件本身,是宇宙中客觀存在的人類可感知的事件。然而,在日常語言表達(dá)中,人們依據(jù)自身直觀感知經(jīng)驗(yàn)將以上實(shí)存事件通常描述為“桃花紅了,柳葉綠了”。這兩個(gè)小句反映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中人們的普遍、直觀感知,具有感知的共性,屬于原發(fā)性心理事件描述語。
更進(jìn)一步,當(dāng)人們關(guān)注“已經(jīng)變紅的桃花”和“已經(jīng)變綠的柳樹”時(shí),人們基于各自不同的社會(huì)實(shí)踐,引發(fā)各自認(rèn)知概念系統(tǒng)中的背景網(wǎng)絡(luò)
此處的“背景網(wǎng)絡(luò)”由美國著名語言哲學(xué)家約翰·塞爾(John Searle)于1983年提出,是指人類具有的、來自社會(huì)實(shí)踐的豐富而復(fù)雜的能力,包括技能、能力、前意向性前提斷言、假定、立場(chǎng)以及非表征性的態(tài)度等。背景以浸潤(rùn)的方式滲透在整個(gè)意向性狀態(tài)網(wǎng)絡(luò)之中,從而引發(fā)人們對(duì)同一事物或事件的多樣化的表征。
,為人們識(shí)解原發(fā)性心理事件提供多樣化的意向性視角和狀態(tài),導(dǎo)致“桃花紅了,柳葉綠了”與不同的心理事件相互發(fā)生作用,生成次生事件。如例10中,若將“紅”變?yōu)檎J(rèn)知的焦點(diǎn),引發(fā)人們憑借已有的情感、意向等心理因素再次識(shí)解“桃花紅了”的是新發(fā)的花蕊。此時(shí),人類認(rèn)知概念系統(tǒng)中的認(rèn)知隱喻可能被啟動(dòng),故派生出兩個(gè)次生事件“紅入桃花”和“桃花蕊嫩”以識(shí)解春天的美好;或者依據(jù)人類認(rèn)知概念系統(tǒng)中的認(rèn)知轉(zhuǎn)喻識(shí)解機(jī)制,將春天的美好轉(zhuǎn)喻化為其他美好的事物或事件。以此推論,可衍生出更多的心理事件。但是,人類又要遵循認(rèn)知的格式塔原則和語言經(jīng)濟(jì)學(xué)原則,故將兩個(gè)及兩個(gè)以上的次生事件在語言結(jié)構(gòu)層面詞化并入為“紅入桃花嫩”的語言表達(dá)式中。同理,若以“青”作為認(rèn)知焦點(diǎn),人們基于已有的個(gè)人社會(huì)實(shí)踐,引發(fā)不同的情感、意向等心理因素再次識(shí)解“柳葉綠了”的是新芽,故派生出兩個(gè)次生事件“青歸柳葉”和“柳葉新芽青”。同樣,為遵循人類認(rèn)知的格式塔原則和語言經(jīng)濟(jì)學(xué)原則,兩個(gè)及兩個(gè)以上的次生事件在語言結(jié)構(gòu)層面詞化并入為“青歸柳葉新”的語言表征以表達(dá)對(duì)春天新生事物的稱頌。簡(jiǎn)言之,人類認(rèn)知概念系統(tǒng)對(duì)客觀世界中存在的同一物理事件(即實(shí)存事件)進(jìn)行識(shí)解,生成具有共性的原發(fā)性心理事件;基于背景網(wǎng)絡(luò),該原發(fā)性心理事件與另一個(gè)(或一些)心理事件相互發(fā)生作用,經(jīng)由人類認(rèn)知概念系統(tǒng)中的概念整合、注意力視窗、概念隱喻、轉(zhuǎn)喻等認(rèn)知識(shí)解方式,引發(fā)多樣化的次生事件,從而生成多樣化的事件表達(dá)式。
五、結(jié)語
實(shí)存事件是客觀世界發(fā)生的物理事件,它本身并無多樣化的意義,而是使得心理事件附隨于其上的事實(shí)性存在。物理事件的發(fā)生和進(jìn)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zhuǎn)移,但人可以用精確定義、無歧義、不模糊的語言對(duì)其進(jìn)行描述。當(dāng)然,物理語言也是人們的認(rèn)知在語言層面的表征,但其標(biāo)準(zhǔn)是與客觀事實(shí)高度吻合的,且表達(dá)的語義內(nèi)容具有可預(yù)測(cè)性。換言之,物理語言的意義就是語句的真值,遵循亞里士多德的真理符合論。此類表達(dá)幾乎只存在于純科學(xué)研究之中。
對(duì)于同一客觀物理事件,日常語言的表達(dá)豐富得多。在通常情況下,人們也不可能用純粹客觀的事實(shí)來確定日常語言表達(dá)的真值。作為貼近物理事件的原發(fā)性心理事件,由于其表達(dá)的是語言使用者對(duì)事件的感知,因而語句的意義不再是與客觀事實(shí)的高度吻合,而是與語言使用者的感知相吻合。因此,原生事件表達(dá)式不一定完全符合客觀事實(shí),而是符合客觀事實(shí)引起的說話人和聽話人的感知和理解。于是,日常語言表達(dá)的客觀性也就在于人們的感知共識(shí)。在次生事件層面,由于涉及的心理因素(如記憶、情感、意向性等)更多,多樣性就更為明顯,主觀性也更強(qiáng),相互理解也就更需要交際雙方具有更多相似的認(rèn)知背景,共識(shí)就更需要通過相互交流而建立。
總之,實(shí)存事件及其變化是認(rèn)知語義學(xué)中“事件”的誘因,其引發(fā)的心理事件無論是原生還是次生,都不再忠實(shí)于實(shí)存事件,而因不同的心理因素參與,呈現(xiàn)出無限的新意和多樣性。
參考文獻(xiàn):
[1]
Barbara L T.Events as They Are[G]//Piotr Stalmaszczyk,Ed.Turning Points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Frankfurt:Peter Lang Publishing Group,2011.
[2]Hacker P M S.Events and Objects in Space and Time[J].Mind,1982,91.
[3]Langacker R W.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M].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4]Jonathan B.What Events Are[G]//Richard M Gale,Ed.The Blackwell Guide to Metaphysics.Backwell:Blackwell Publishing Company,2002.
[5]吳平,郝向麗.事件語義學(xué)引論[M].北京: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出版社,2017.
[6]Talmy L.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Typology and Process in Concept Structuring:Vol.2[M].Cambridge,MA:MIT Press,2000.
[7]Quine W V O.Quine in Dialogue[M].Harvard: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8.
[8]Davidson D.Essays on Actions and Event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9]Davidson D.The Essential Davidson[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10]王寅.認(rèn)知語言學(xué)的“體驗(yàn)性概念化”對(duì)翻譯主客觀性的解釋力——一項(xiàng)基于古詩《楓橋夜泊》40篇英語譯文的研究[J].外語教學(xué)與研究,2008(3).
[11]劉陽.事件思想的分析維度——以蒯因與戴維森之爭(zhēng)為考察起點(diǎn)[J].福建論壇(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20(7).
[12]劉炳善.英國文學(xué)簡(jiǎn)史[M].新增訂本.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
[13]Lycan W G.Philosophy of Language:A Contemporary Introduction[M].Third Edition.New York:Taylor & Francis Group,2018.
[14]杜軍.狀態(tài)變化事件認(rèn)知機(jī)制探究[J].外國語文,2016(3).
[15]劉利民.在語言中盤旋——先秦名家“詭辯”命題的純語言思辨理性研究[M].成都:四川大學(xué)出版社,2007.
A Study on Connotation,Attribute and Multiple Stratification of Event
DU Jun,LIU Li-m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 610207,China)
Abstract:
Event is one of the key concepts of cognitive semantics.According to Davidson’s theory of anomalous monism,only the objective event has an ontological oneness,and the causal link between physical event and mental event should be understood as the physical event having caused the description in mental language,in which sense the mental event supervenes on the physical event and new meanings emerge in the mental event,which transcends the physical phenomenon.In this way,event actually shows a triple level model:the real event,the primary mental event and the secondary mental event.The real events are those that exist objectively in the world.The primary mental events refer to events described by people using universal mental language.And the secondary mental events refer to the complex mental events which generated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primary mental events and other mental events.
Key words:
cognitive semantics;anomalous monism;supervenience;real event;primary mental event;secondary mental event
(責(zé)任編輯
胡海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