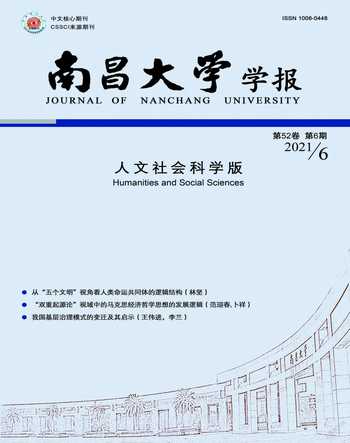“鄉村再造”:政黨引領鄉村治理的理論邏輯與歷史經驗
張巖 周明明
摘 要:政黨引領鄉村治理主要通過黨的組織體系、領導體系和意識形態等,實現“鄉村再造”,在建構現代國家基層政權、推進鄉村治理現代化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基于“政黨中心主義”的分析視角,探究百年大黨引領鄉村治理的演變規律,可以透視政黨使命的自覺性、政黨組織的協調性、政黨功能的服務性和政黨治理的多元性四個特性,準確把握政黨引領鄉村治理在革命、建設、改革、復興等不同時期的邏輯導向。推動政黨引領鄉村治理實現鄉村振興的戰略目標,需要從治理使命、治理系統、治理功能、治理主體四個維度,提升農村基層黨組織的組織力,推進鄉村治理體系現代化,滿足農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協同共建鄉村治理共同體。
關鍵詞:政黨引領;鄉村治理;政黨中心主義;歷史演進;實踐經驗
中圖分類號:C91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448(2021)06-0092-10
在傳統中國向現代中國的治理轉型中,鄉村治理始終是黨和國家工作的重中之重,是關系到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大議題。當前學界關于鄉村治理研究的理論邏輯主要有兩個層面:一是從“國家—社會”或“政黨—國家”的權力結構關系出發,提出“政黨下鄉”“資源下鄉”“服務下鄉”,以應對鄉村治理中的資源短缺、能力不足等問題;二是從新公共管理理論出發,提出了“整體性治理”“多元治理”“總體性治理”“政黨整合治理”等概念,以解決鄉村治理中的碎片化、一元化等問題。在鄉村治理的歷史變遷研究中,呂德文從鄉村治理體制的角度認為鄉村治理的制度化和規范化程度迅速提高[1](P78),趙樹凱從國家治理的角度將鄉村治理的百年變遷劃分為六個時期[2](P11),周文、劉少陽[3](P47)按照改革開放前、改革開放后以及新時代三個時期對鄉村治理的歷史變遷進行梳理,主要關注鄉村治理變遷本身。在政黨與鄉村治理的研究中,既有以組織嵌入為特征的基層黨組織功能建設研究,又有關于農村基層黨組織干部隊伍建設和組織力建設的研究,更多地側重于基層黨組織建設的問題與對策研究。中國共產黨作為使命型政黨,不僅可以通過農村基層黨組織的自身建設引領鄉村治理,發揮戰斗堡壘的作用,而且可以運用政黨的意識形態和組織體系領導鄉村治理,推進鄉村善治,實現“鄉村再造”。
一、“鄉村再造”:基于“政黨中心主義”的解釋框架
“政黨中心主義”在某種程度上源于“國家—社會”關系的中國實踐,是對“國家中心主義”和“社會中心主義”的積極回應。“將政黨帶進來”明確提出了“政黨、政府與社會關系三分法”[4](P92),把政黨視為推進國家治理和制度變遷的關鍵因素。中國共產黨遠遠超越了西方政治將政黨視為“國家與社會的中介”的定義,“不僅成為國家建設和社會改造的領導力量,而且成為國家建設和社會改造的組織基礎。”[5](P39)中國共產黨作為領導黨和執政黨,在對國家進行全面滲透的同時,仍然保持組織、功能上的相對獨立性,可以不依賴國家權力和制度體系,“而擁有實際的政治力量”[6](P10),這是政黨引領鄉村治理、實現“鄉村再造”的理論依據和政治前提。“鄉村再造”既是百年來我們黨基于“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是農民問題”的認知邏輯,把為農民謀幸福作為重要使命、實現鄉村社會組織化、不斷解放和發展農村生產力的歷史過程;又是基于“民族要復興鄉村必振興”的價值邏輯,在黨的堅強領導之下,以黨組織嵌入鄉村治理全過程,實現政治吸納,凸顯政治功能,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推動鄉村社會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滿足農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偉大實踐。“鄉村再造”強調的是鄉村治理的過程和目標,其標識是實現“農業高質高效、鄉村宜居宜業、農民富裕富足”;鄉村治理強調的是“鄉村再造”的方法和路徑,其標識是實現“黨組織引領下的農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政黨引領鄉村治理是政黨對鄉村社會的整體性和系統性的再造。基于“政黨中心主義”的分析框架,政黨引領鄉村治理具有以下四個特性:
(一)政黨使命的自覺性
政黨使命的自覺性指中國共產黨肩負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具有堅定的政黨意志和明確的奮斗目標,能夠自覺地進行鄉村治理。政黨引領鄉村治理的自覺性是對“政黨自主性”的集中詮釋,作為無產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不僅可以按照自己的意識形態形塑自身的階級基礎,而且可以能動地改造社會,以鞏固政黨的政治基礎,實現政黨的政治目標。中國共產黨通過組織建設,構建起極具組織性和紀律性的政黨組織結構,依托強大的組織體系和先進的黨員個人,滲透到鄉村社會的每個角落,落實鄉村治理的具體舉措。政黨引領鄉村治理并不是隨心所欲的,需要通過“自我調適”以適應鄉村治理環境,明確“鄉村再造”的政治方向。具體來講:一方面,中國共產黨繼續通過“滲透式”的組織拓展模式,變革鄉村治理機制,重構鄉村社會的組織形態,優化鄉村治理的政治生態,實現了政黨權力向家庭、個人的延伸。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始終保持自身的純潔性和先進性,既能夠通過宣傳教育強化階級意識,“使無產階級形成為階級”[7](P44),解決農民階級的階級意識弱化問題,又可以通過建立良好的黨群關系,踐行黨的初心和使命,堅守全心全意為人民群眾服務的宗旨。
(二)政黨組織的協調性
政黨組織的協調性是指政黨引領鄉村治理應該置于國家治理體系之中,既加強治理系統之間的協調,又注重治理系統內部的整合,提升鄉村治理的整體效能。中國共產黨以消滅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為奮斗目標,作為無產階級政黨稟賦的先進性,使其能夠代表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這意味著政黨引領鄉村治理不會局限于狹隘的農民階級思想,不會困惑于鄉村發展中的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而是關注鄉村社會的整體性和結構性變遷。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作為“長期執政”的政黨,不會陷于黨派輪替、相互傾軋的惡性競爭之中,能夠匯聚民心、凝聚力量,編制鄉村治理與鄉村振興的長遠規劃,實現“鄉村再造”的最終目標。在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史進程中,中國共產黨從未忽視鄉村問題,始終將“鄉村再造”與黨和國家在各階段的歷史任務緊密銜接,政黨引領鄉村治理是中國共產黨實現對國家全方位領導的重要基石。政黨引領鄉村治理是極其復雜而龐大的系統性工程,需要農業與其他產業之間、農民群體與非農群體之間、農村與城鎮之間的協調配合,進而實現鄉村社會的整體性發展。理解政黨引領鄉村治理,不能陷入“剝削農民”“掠奪農業”“忽視農村”等片面誤讀之中,而應該用發展眼光、整體視野來看待鄉村治理問題。
(三)政黨功能的服務性
政黨功能的服務性是指政黨引領鄉村治理延續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內在邏輯,代表農民階級的利益訴求,關注鄉村社會的現實需要。它不同于其他社會組織的服務性功能,具有明確的政治立場和政治方向。政黨引領鄉村治理始終堅持人民立場,發揮政治整合和社會服務功能,引領鄉村社會的整體性發展,實現“鄉村再造”。
一方面,政黨引領鄉村社會,實現經濟變革。準確把握鄉村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變革與之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調動鄉村社會生產要素的積極性,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政黨引領經濟變革的基本目標。在傳統的農業社會之中,政黨引領鄉村治理必須要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這直接關系到農民對農村基層黨組織的支持度和認可度,以及鄉村治理的有效性。另一方面,政黨引領鄉村社會,實現社會變革。政黨引領鄉村治理不能僅僅依靠自上而下的組織滲透和社會控制,還需要提供優質的公共服務和有效的社會管理,激發農民自上而下的政治參與。同時,政黨引領鄉村治理必須要關注鄉村社會需求的多元性和多樣性,不僅要滿足農民對于經濟生活的基本訴求,而且要滿足農民的個性化需求,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和幸福感。
(四)政黨治理的多元性
政黨治理的多元性是指政黨引領鄉村治理不能僅僅依靠單一的政黨主體,需要動員農民個體和其他鄉村社會治理組織參與其中。在國家與社會的結構關系中,鄉村社會構成了具有相對自主性的政治空間,需要多元治理主體的合作共治。中國共產黨擁有強大而完整的組織網絡,但是作為政黨組織并不能尋求替代其他形式的社會主體,而應該引導和培育其他的治理主體參與到鄉村治理之中,以更好地發揮黨的領導力和組織力。隨著社會分工日趨精細化,僅僅依靠政黨組織難以滿足鄉村社會多元化差異化的需求,需要有效的外部規制和激勵示范,吸納社會組織、經濟組織等治理主體參與到鄉村社會治理之中,充分發揮各自的主體優勢,實現鄉村治理效能的最大化。農村基層黨組織動員多元治理主體參與鄉村治理,不僅需要物質激勵和資源供給,而且需要政治覺悟、道德約束、社會責任等多方面的精神支撐,營造積極健康的鄉村文化,克服傳統鄉村社會的惰性以及小農經濟的自我封閉性,形成“一核多元、協調共治”的治理格局,增強鄉村治理的韌性和彈性。
二、百年政黨引領鄉村治理的歷史演進與邏輯導向
政黨引領鄉村治理需要從“政黨中心主義”的理論視角,探究鄉村治理變遷的全過程。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中國共產黨并引領鄉村治理的著力點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以執政黨身份領導國家和政府有效實現“鄉村再造”。
(一)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以分配土地、革命動員為導向的鄉村治理
近代以來,隨著國家稅賦攤派加重、土地兼并加深、政治道德倫理瓦解,部分鄉紳精英出現了劣紳化、土豪化,鄉村治理日趨混亂,傳統“皇權不下縣”的鄉村治理模式受到嚴重沖擊,鄉村發展出現嚴重“內卷化”。中國共產黨在成立之初便認識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農民階級的特殊性,明確了工農聯盟的革命主體地位。面對受教育狀況普遍較低的現實,中國共產黨嘗試通過“補習學校、通俗講習所、消費合作社”[8](P479)等方式對農民進行階級教育,開展農民干部培訓,但這種做法顯然難以滿足革命發展需要。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明確提到“組織起來”[9](P110)的號召,認為農民是革命先鋒,應該通過組織農會、普及政治宣傳、發展文化運動等方式把農民組織動員起來。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基于政治經濟發展極不平衡的國情,明確提出“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將革命的重心由城市轉移到農村,這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次重大嘗試,也是政黨引領鄉村治理的重要開端。中國共產黨早在1923年便成立第一個農村黨支部,開啟政黨引領鄉村治理的具體實踐,以保障中國共產黨對農村革命的領導權。在以支部為中心的農村黨組織建設中,明確提出“黨的發展要以質量為原則,吸收雇農、貧農的積極分子組建農村支部,并健全支部生活”[10](P543),通過重塑黨員身份和階級認同,保持黨組織的先進性和純潔性,領導農民進行土地革命戰爭,引領鄉村治理。
土地問題是政黨引領鄉村治理的首要問題,從土地革命時期的“打土豪、分田地”,到抗日戰爭時期的“減租減息”,再到解放戰爭時期的“耕者有其田”,中國共產黨適時調整土地政策,重點在于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確立了廢除封建剝削土地所有制、實現人民解放的革命道路。在土地改革運動中,農村黨組織按照貧農、雇農、中農、富農、地主等階級成分來進行土地分配,既避免了平均主義思想,又強化了農民階級的階級意識。各地區組建土改工作隊深入到農村地區指導土改工作,開展極具魅力的意識形態宣傳,通過“算賬”“訴苦”等方式闡述階級剝削的故事,進一步喚醒了農民的階級身份和革命斗志,形成了強大的政治動員能力。解決農民土地問題,不僅實現了鄉村社會組織結構和階級結構的變革,而且為革命軍隊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后勤保障,使農村革命根據地成為“銅墻鐵壁”。為了滿足生產力低下的農業生產需要,農民創造性地舉辦了犁牛合作社、生產互助組等農業生產性組織,在農村黨組織的引領下得到普遍認可和積極推廣。為保衛農村革命根據地,農村黨組織積極組建民兵、農會、婦聯、兒童團等自治組織,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鄉村治理的早期群眾組織。為了鞏固農村革命政權建設,從建立工農聯盟的蘇維埃政權到“三三制”的民主政權建設,中國共產黨團結鄉村社會中的積極因素參與到鄉村治理之中,推動全國范圍內革命戰爭的勝利。
這一時期,政黨引領鄉村治理的邏輯起點是革命斗爭,“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是關系到革命事業發展的全局性問題。“鄉村再造”的核心在于政治解放,使鄉村社會擺脫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使農民成為鄉村社會的主人。中國共產黨不僅明確了農民階級在中國革命中的角色,而且認識到鄉村貧困落后的根源,并提出解決鄉村治理難題的改革措施。農村黨組織往往采取強制措施和階級斗爭的方式實現鄉村治理結構的重塑,但也會采取統一戰線的辦法將以少數富農、開明鄉紳為代表的鄉村精英吸納到鄉村治理體系之中。在革命戰爭中,農村黨組織所采取的包括土地政策在內的改革舉措、包括群眾路線在內的工作方法,成為政黨引領鄉村治理的重要“路徑依賴”。
(二)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時期:以組織生產、發展經濟為導向的鄉村治理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政黨引領鄉村治理的核心議題是如何擺脫農村貧困落后的面貌,推動社會主義工業化。全國范圍內的土地改革進一步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增強了農民對國家和政黨的政治認同。農村黨組織通過改革封建社會的倫理宗法觀念,掃除舊社會痼疾,推進移風易俗,使鄉村治理得到明顯改善。但是分散的小農經濟并不利于農村生產力的持續提升,而且“農村階層中新的分化現象開始出現”[11](P127),這顯然不符合中國共產黨對于“消滅階級對立”的意識形態和“鄉村再造”的價值目標,也難以適應國家工業化的發展需要。“組織起來,是由窮變富的必由之路”[12](P29),以互助組、合作社為主要形式的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實現了農業生產資料的集體化和規模化。1958年成立的人民公社已經不局限于經濟組織,而是“政社合一”“黨政合一”的組織,實現了政黨對鄉村社會的組織和整合,“基本完成了農村社會的再造。”[13](P119)這種一元化的黨政領導體系徹底結束了近代中國“一盤散沙”的狀態,分散性的鄉村社會被改造成為具有廣泛階級聯系的整體性社會,形成了強大的組織力和動員力,滿足了在生產力極其低下的情況下國家工業化建設的現實需要。盡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中國共產黨為了增加工人階級的黨員比重,曾提出“今后對農民黨員的發展,應加以限制”[14](P210),但是隨著鄉村治理的不斷深入,以黨支部和黨小組為組織形式的農村黨組織進一步向鄉村社會延伸,明確了農村黨組織在鄉村治理中的核心地位。
在生產資料所有制變革完成后,政黨引領鄉村治理繼續延續革命的方式進行鄉村改造。一方面,采取“劃成分”“戴帽子”的方式來確認鄉村社會成員的身份,而且“身份一經獲得不僅不容易隨著經濟地位的改變而改變,而且會延續到自己的后代”[15](P172)。在人民公社體制之下,不僅吸納貧下中農出身的鄉村精英擔任基層干部,而且通過“憶苦思甜”、貧下中農再教育的方式喚醒他們的階級記憶,以保持無產階級的純潔性和階級內部的凝聚力,使階級關系可以超越血緣、地緣和業緣等關系及其邊界。另一方面,加強鄉村地區的宣傳教育活動,用階級斗爭的思想改造鄉村文化。比如:通過“破四舊”運動,破除封建的、剝削的思想和習俗;通過“農業學大寨”運動,宣傳集體主義精神和無私奉獻精神。這些運動式的鄉村治理模式由于忽視了農民現實需求,并未取得預期效果。更為重要的是,以“組織軍事化、行動戰斗化、生活集體化”[16](P384)為特征的人民公社,加劇了農村黨組織行政化,削弱了農村黨組織在鄉村治理中的權威。以生產隊為單位的生產組織方式和以“工分制”為基礎的產品分配方式,片面強調“一大二公”的平均主義,難以激發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更不符合農業發展的實際狀況,農業生產經營體制陷入困局。
這一時期,政黨引領鄉村治理的邏輯起點是政治掛帥,表現為延續革命時期的階級斗爭模式,采取運動式方式進行鄉村治理。“鄉村再造”的重心在于發展生產,鄉村社會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和階級關系發生了根本性變革,雖然鄉村治理具有一定的“左傾”錯誤,但并不能否定“全國農業發展總體上仍處于不斷增長”[17](P54)的客觀事實。這一時期鄉村為城鎮提供了較為充足的生產生活資料供給,為工業發展輸送勞動力和原材料,承擔著為國家工業化提供原始積累的任務,為我國建立較為完備的工業體系做出了貢獻。全能主義的鄉村治理模式帶來了國家對鄉村社會的過度干預和全面控制,不僅需要承擔極高的治理成本,而且農民的主體意識受到嚴重削弱,其他社會主體參與鄉村治理的政治空間被壓縮。
(三)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以引入市場、激發活力為導向的鄉村治理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拉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序幕,中國共產黨將發展生產力、改革同生產力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視為“一場廣泛、深刻的革命”[18](P4)。中國共產黨采取“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方法,選擇“先農村,后城市”的改革次序,鄉村治理仍然是關系到改革開放的全局性問題。中國共產黨再次以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為突破口,確立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通過土地所有權與承包權的分離,使農民獲得土地生產經營權,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大大提升。個人從原來的“單位人”向“社會人”轉變,淡化并消除了階級身份,開啟了“鄉政村治”的基層治理格局。村民自治不僅改變著鄉村治理的社會結構,使鄉村治理保持一定的自主性,而且發揮著政治訓練和政治啟蒙作用。國家權力從鄉村社會中退出并不意味著政黨權力的退出,中國共產黨明確提出要進一步“搞好以黨支部為核心的村級組織建設”[19](P70),通過組織建設和制度建設,加強農村基層黨組織在鄉村社會的政治領導力。
國家對鄉村控制的緩解,使鄉村社會獲得了一個相對寬松的治理空間。“放權讓利”的改革浪潮激發了自下而上的制度創新,形成了強大的“邊緣革命”。鄉村地區的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出現了以集體經濟為代表的“蘇南模式”和以個體經濟、民營企業為代表的“溫州模式”,形成了“離土不離鄉”的中國特色工業化道路。在市場經濟和城市化推動之下,大量資源和人口由農村涌向城市,農民工群體持續涌向城鎮和發達地區,出現了“離土又離鄉”的人口大遷移,深刻改變著鄉村社會的人口結構和社會關系網絡,也深刻影響著政黨引領鄉村治理的模式與路徑。
鄉村治理的改善并不意味著鄉村社會矛盾的消解,城鄉之間、鄉村社會內部圍繞公共資源的爭奪從未停止,鄉村社會一度出現“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治理困境。中國共產黨意識到市場和城鎮對鄉村資源的無限制汲取,不僅有可能會削弱黨的執政基礎,而且背離了“鄉村再造”的發展目標,必須要增強國家資源調控權力,縮小城鄉發展差距。2005年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2006年國家全面取消農業稅,開啟了“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新時期。中國共產黨運用國家權力和制度體系,加大對農業農村的公共投入,推出一系列支農惠農政策,包括“新農合”、農村義務教育、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等社會福利制度,以及農機、良種、化肥等農業生產性補貼補助措施,著力解決“三農”問題,鄉村治理環境得到明顯改善。
在加強農村公共資源輸入的過程中,為避免平均主義以及各級政府的挪用,國家往往以項目制的形式為鄉村發展提供專項資金和政策支持,但是由于農村基層黨組織的弱化虛化,難以有效承接國家資源,鄉村治理再次面臨資源分配不均和治理效能低下的困境。一方面,權力尋租者、地方富人與灰黑社會勢力借助“錦標賽體制”之下的“爭資跑項”工作,通過各種方式蠶食國家資源。另一方面,缺乏必要道德和責任約束的謀利性釘子戶和上訪戶等機會主義者,借助“壓力型體制”之下的“維穩”工作,通過利益博弈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由此產生的“分利秩序”[20](P95),不僅造成公共資源的私人化,資源有效使用效率偏低,而且造成鄉村治理秩序混亂,弱化了鄉村治理的公共性。“烏坎事件”是這一時期鄉村治理困境的典型案例,“其主要原因和表現是治理主體有效性不足。”[21](P173)
在這一時期,政黨引領鄉村治理的邏輯起點是以經濟為中心,通過引入市場機制發展農業生產,改善農民生活,激發農村社會活力。“鄉村再造”的核心在于人民富裕,通過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變鄉村社會貧困落后的面貌,提升鄉村社會的生產力水平,創造出豐富的物質生活資料。政黨引領鄉村治理形成了相對成熟的理論體系,主要依托制度化和法治化途徑,通過改進程序和技術管理來規范行使權力,借助國家和政府的制度體系實現鄉村治理。但農村黨建工作也存在諸多問題,比如:農村基層黨組織的社會整合能力和宣傳動員能力不足,部分地區“兩委”關系不協調導致農村基層黨組織軟弱渙散、缺乏凝聚力和組織力。高度市場化和人口快速流動造成鄉村精英因外出務工逐漸脫離鄉村社會,“空巢老人”“留守兒童”等社會問題日益突出,造成鄉村治理主體缺失,導致鄉村治理空心化。現代觀念對傳統鄉土觀念的沖擊,使得基于土地聯結的鄉村共同體理念逐漸瓦解,鄉村社會呈現出離散性特征,鄉村治理的公共價值被侵蝕。
(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黨建引領、鄉村振興為導向的鄉村治理
進入新時代以來,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深刻變化,全面深化改革進入深水區和攻堅期,鄉村治理在治國理政中占據著重要地位。中國共產黨將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基于“保持農村穩定”和“促進發展”的雙重目的[22](P97),繼續以土地政策為重點,推進鄉村社會變革,引領鄉村治理。農業生產的機械化和專業化,不僅提升了農業生產效率,釋放了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而且使得傳統農業生產經營方式難以適應現代農業生產技術的發展需求。2014年《關于引導農村土地經營權有序流轉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意見》以制度化的形式規范土地經營權流轉,形成了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的“三權分置”。在新一輪土地流轉和規模經營改革中,農村基層黨組織發揮著政策指引和市場服務功能,不僅農村黨員干部發揮“領頭雁”“排頭兵”的作用,而且創新出以煙臺“黨支部領辦合作社”[23](P13)為代表的經濟模式,壯大農村集體經濟,推進農業產業化發展。
農村基層黨組織體系日趨完善,不僅在鄉村社會的經濟組織和社會組織中建立黨組織,實現農村基層黨組織全覆蓋,而且通過財政投入保證農村基層黨組織的有效運作,解決鄉村治理中存在的組織虛化弱化問題。尤其是在“兩委”關系上,進一步梳理黨支部與村委會的關系,強調“黨務”與“政務”的分工而不是對立,明確提出“村黨組織書記應當通過法定程序擔任村民委員會主任和村級集體經濟組織、合作經濟組織負責人,村‘兩委’班子成員應當交叉任職”[24](P12),實現了鄉村干部隊伍的有機整合。同時,通過健全紀檢監察工作,加強農村基層黨組織的紀律建設和作風建設,嚴厲打擊鄉村地區的“微腐敗”、涉黑涉惡勢力,“整治群眾身邊腐敗和不正之風工作”[25],有效增強了人民群眾對農村基層黨組織的信任和認可。
“脫貧摘帽”已經不再是階級斗爭的政治術語,而是中國共產黨消除絕對貧困的重大戰略。在脫貧攻堅戰中,中國共產黨展示出強大的政治組織力和社會動員力,通過對口支援、干部下沉、網格化管理等方式,選派“第一書記”和駐村干部,引導多元社會力量參與鄉村治理。脫貧攻堅并不是不計成本的資源投入,而是將“輸血”與“造血”相結合、“扶貧”與“扶智”相結合,由農村基層黨組織落實脫貧標準和扶貧政策,做好農村精準扶貧管理。打贏脫貧攻堅戰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標志性任務,不僅僅是在解決城鄉差距、地區差距等現實性問題,而且是在兌現中國共產黨對“先富帶后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政治承諾,更是“鄉村再造”的階段性目標。2017年黨的十九大明確提出從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五個方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并制定了一系列的方案、規劃、法律等文件,推進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有序銜接,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與實現共同富裕的協同推進,進一步縮小貧富差距,朝著城鄉共同富裕的目標邁進。
在這一時期,政黨引領鄉村治理的邏輯起點是治國必先治黨,管黨治黨是關系到鄉村治理的根本性問題,是實現鄉村振興戰略的政治保障。中國共產黨以“自我革命”的魄力加強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依靠強大的組織體系,發揮黨員干部“關鍵少數”的模范帶頭作用,落實責任主體意識,持續推進資源下沉和人員投入,實現自上而下的政治動員。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如期實現,鄉村社會的生活水平和公共服務有效改善,鄉村治理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現實中仍然存在諸多問題,比如:在國家資源投入有限的條件下如何保持鄉村治理的內生動力?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如何避免貧富分化和城鄉二元對立?如何解決鄉村治理主體越位和缺位問題?在實現“鄉村再造”的進程中,仍然需要充分發揮政黨引領鄉村治理的政治優勢和組織優勢,推進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三、鄉村振興背景下政黨引領鄉村治理的實踐進路
新時代,“鄉村振興”戰略是中國共產黨實現“鄉村再造”的關鍵步驟,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重大舉措。政黨引領鄉村治理仍然需要遵循“政黨中心主義”的理論邏輯和歷史邏輯,持續深化鄉村治理體系變革,需要充分發揮政黨引領鄉村治理的自覺性、協調性、服務性和動員性。
(一)增強治理使命的自覺性,提升農村基層黨組織的組織力
中國共產黨肩負著實現鄉村振興的重大使命,堅持黨的領導是貫徹落實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維護鄉村治理秩序、保障農村資源供給、將黨的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的政治前提。首先,明確鄉村治理的政治方向。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將黨的領導貫穿于鄉村治理的全過程,充分發揮黨組織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其次,保障鄉村振興的制度供給。要創新政黨引領鄉村治理的領導機制和決策機制,規范重大事項、重大問題的民主協商和集體決策程序,健全黨組織領導的民主監督機制和社會參與機制。最后,營造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要以政治建設為統領,增強黨性修養,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增強黨員干部的責任感和使命感,破除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作風,永遠保持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政治本色和先進品格。
以提升組織力為核心,加強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提供堅強組織保障。一要創新組織設置形式,優化農村基層黨組織結構。在擴大農村基層黨組織的有形覆蓋和有效覆蓋的同時,堅持“一村一策”的精細化管理,通過談心談話、批評與自我批評、民主懇談等方式,構建系統完備、運作高效的農村基層黨組織運行機制。二要切實抓好“關鍵少數”,加強鄉村黨員干部隊伍建設。“選好配強村級領導班子,突出抓好村黨組織帶頭人隊伍建設,”[26](P30)通過選拔教育培訓,建設一支政治過硬、本領過硬、作風過硬的鄉村振興干部隊伍。三要嚴密黨的組織紀律,突出政治意識和政治標準。提升黨組織的凝聚力和戰斗力,以黨群身份構建組織網絡,打破血緣、親緣、地緣等農村傳統宗族關系,使政黨引領能夠超越狹隘利益關系,防止出現謀利集團。四要密切聯系人民群眾,建立良好的黨群關系。人民群眾是黨的力量之源、執政之基,要將維護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全面貫徹落實群眾路線,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
(二)注重治理系統的協調性,推進鄉村治理體系現代化
政黨引領鄉村治理必須要置于國家治理體系之中,立足于鄉村振興的改革目標,協調鄉村治理系統之間的內在關系,“根據不同的權力特點和治理對象之間的契合度有針對性地發揮各自的優勢,”[27](P98)發揮鄉村治理結構的整體效能,協同推進鄉村治理體系現代化。首先,政黨引領鄉村治理與城市治理的有效銜接,實現城鄉融合發展。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不是與城鎮化相對立,而是尊重鄉村社會的流動性和開放性,以城市治理帶來鄉村治理,構建現代治理體系。中國共產黨通過城鄉黨組織的有效銜接,促進城鄉黨建資源的深度整合,能夠帶動城鄉之間的人才、政策、產業、文化等各領域的交流融合,加強城鄉治理體系的有機結合,推進城鄉社會協同發展。
其次,政黨引領市場機制與政府機制的有效銜接,實現鄉村資源優化配置。市場機制能夠促進生產要素和生活資料的區域間自由流通,政府機制能夠通過政策傾斜和資源扶持帶動鄉村公共資源的再次分配,中國共產黨則能夠發揮政治引領功能,彌補市場機制的自發性缺陷,克服政府機制的官僚主義弊端,實現鄉村社會資源的有效整合。政黨引領鄉村治理還可以通過區域化黨建的組織形式,吸納不同組織中的黨員代表,打破了組織之間的封閉與割裂狀態,構建農村基層黨組織與各類治理系統的廣泛聯系,促進黨建公共資源的共建共享。
最后,政黨引領自治、德治、法治之間的有效銜接,完善鄉村治理的頂層設計。自治建立在中國鄉村自治悠久的歷史傳統和黨領導鄉村自治四十余年的實踐經驗基礎之上,中國共產黨通過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引領,創建村民自治管理平臺,激發了鄉村自治活力。法治是黨領導依法治國在鄉村治理中的具體體現,農村基層黨組織不僅通過法治化、制度化的方式,形成約束鄉村治理主體的正式規則,而且通過營造學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圍,增強村民的法治意識和法治能力。德治則是通過道德文化、風俗習慣等鄉村文化,形成對鄉村社會的道德約束。農村基層黨組織要積極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正面引導人們的價值取向和思想觀念,構建鄉村內生的社會秩序。
(三)增強治理功能的服務性,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
當前我國仍然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是實現鄉村有效治理、維護人民根本利益、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關鍵所在,需要通過政黨領導鄉村治理改革,促進鄉村經濟社會發展,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
政黨引領鄉村治理要持續推進經濟變革,轉變農業農民農村的弱勢地位。土地制度改革是變革鄉村生產關系的重中之重,是實現共同富裕、鄉村振興的重要基礎。中國共產黨具有前瞻性和預見性,主動變革傳統分散經營方式,加快發展新型農業集體經濟,走出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農業現代化道路。一方面,要將土地視為一種生產要素,積極推進以明晰產權為導向的土地確權工作,構建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政黨引領鄉村治理,不僅通過股權設置、收益分配等方面的公平分配,保障農民的合法權益,實現農民增收,而且通過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有序流轉,促進農村內部產業分工,滿足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需要,實現現代農業的優化升級。另一方面,將農民視為一種社會行業分工中的職業身份,而不只是政治身份,培育以農業為職業并掌握專業技能的新型職業農民。政黨引領鄉村治理,需要進一步將農村勞動力從土地的束縛中解脫出來,引導農民積極參與社會分工和市場競爭,自由選擇生活方式,激發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內在推動力。
政黨引領鄉村治理要持續推進社會變革,補齊農村民生和公共服務短板。農村基層黨組織要積極推進服務型黨組織建設,靈活運用“四議兩公開”等方式聽取群眾意見,增強農村基層黨組織服務群眾意識,確保黨組織能夠為群眾辦實事。圍繞鄉村社會的教育、就業、醫療等民生問題,組建村民服務中心,構建便民服務的長效機制,促進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與此同時,農村基層黨組織要積極構建“互聯網+農村黨建”鄉村治理模式,加快農村網絡基礎設施建設,促進互聯網技術與鄉村治理相結合,提升鄉村治理效率,降低鄉村治理的成本。推進政黨引領鄉村治理信息化,不僅可以通過加強黨的自身建設,疏通黨群聯系渠道,提升農村基層黨組織的服務能力,而且可以通過網絡平臺及時掌握農民的現實訴求,了解鄉村社會的發展困境,提供更加便捷精準的公共服務。
(四)規范治理主體的多元性,協同共建鄉村治理共同體
政黨引領鄉村治理需要規范多元社會主體參與鄉村治理的運行機制,釋放其他社會主體參與鄉村治理的政治空間,共同打造“一核多元、協調共治”的治理格局。就個體而言,要充分重視農民在鄉村治理中的主體地位。將個體化、原子化、流動性的農民“重新組織起來”,發揮農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要使鄉村振興的戰略目標能夠得到廣大農民的支持和認可,使農民成為鄉村經濟發展的主要獲益者,充分滿足農民的個性化和差異化需求。就組織而言,要充分發揮農村基層黨組織的組織“孵化器”功能。一是政黨引領鄉村政治性組織建設。適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要求,健全村委會的組織機制和運行程序,吸納鄉村社會精英參與農村自治組織,破解鄉村社會權力碎片化的難題。二是政黨引領鄉村經濟性組織建設。適應現代農業發展的要求,需要吸納致富能人、職業農民加入農業經濟合作社,促進生產技術知識和市場經驗方法的傳播與培訓,改善農業生產經營和農村產業發展。三是政黨引領鄉村社會性組織建設。適應鄉村社會多樣化發展趨勢,引導社會公益慈善組織和志愿服務組織參與農村幫扶共建活動,改善社會保障和民生工作,豐富鄉村社會生活。
政黨引領鄉村治理要培育鄉村社會的公共精神,強化鄉村生活的公共性,避免社會主體盲目追逐自身利益而引發鄉村治理的失序。農村基層黨組織要“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28],深入挖掘傳統中國鄉村治理的文化資源,改善鄉村社會的文明程度和精神風貌。首先,延續“熟人社會”的治理優勢。農村基層黨組織要通過鄉土人情、民俗活動等方式,培育蘊含鄉村特色的優秀傳統文化,喚醒鄉村文化記憶,重新構建鄉村社會的信任關系,增強對鄉村社會的價值認同和情感認同,將內在道德轉化為人們的行為自覺。其次,構建鄉村社會的非制度約束。農村基層黨組織要通過村規民約、道德規范等方式,倡導文明風尚,弘揚清正家風,培育家國情懷,激發人們認知層面的“利他”因素,強化鄉村公共輿論和道德監督,增進政治共識。最后,營造良好的鄉村社會風氣。農村基層黨組織要積極推動移風易俗,增強鄉村主體的責任意識,消除“等靠要”的消極思想,約束“搭便車”的投機心理,遏制鄉村社會的“圈子文化”和“裙帶風氣”,增強鄉村共同體意識。
四、結語
政黨引領鄉村治理,實現“鄉村再造”,遵循著“政黨中心主義”的理論邏輯,將政黨的意識形態和組織體系滲透到鄉村治理實踐中,直接關系到鄉村治理的方式、秩序和目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后,政黨引領鄉村治理要朝著鄉村振興的戰略目標繼續前進,為最終實現共同富裕而不懈努力。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核心要義,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保證,亦是“鄉村再造”的最終目的。政黨引領鄉村治理,實現“鄉村再造”,必須要立足于中國鄉村社會的客觀實際,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根本立場,加強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組織并動員農民進行廣泛的政治參與,吸納多元社會主體參與到鄉村治理之中,增強鄉村治理的主體活力,“合理規劃與布局”[29](P156),營造良好的鄉村治理生態,推進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參考文獻:
[1]
呂德文.鄉村振興背景下鄉村工作共同體的建構邏輯[J].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1(5).
[2]趙樹凱.鄉村治理的百年探索:理念與體系[J].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4).
[3]周文,劉少陽.鄉村治理與鄉村振興:歷史變遷,問題與改革深化[J].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21(7).
[4]景躍進.將政黨帶進來——國家與社會關系范疇的反思與重構[J].探索與爭鳴,2019(8).
[5]林尚立.領導與執政:黨、國家與社會關系轉型的政治學分析[J].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01(6).
[6]景躍進.黨、國家與社會:三者維度的關系——從基層實踐看中國政治的特點[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5(2).
[7]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中央檔案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
[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中央檔案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4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
[1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中央檔案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6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
[11]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2卷(1949-1978)[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
[1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
[13]賀雪峰,董磊明,陳柏峰.鄉村治理研究的現狀與前瞻[J].學習與實踐,2007(8).
[1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
[15]徐勇.階級、集體、社區:國家對鄉村的社會整合[J].社會科學戰線,2012(2).
[1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1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
[17]陸益龍.百年中國農村發展的社會學回眸[J].中國社會科學,2021(7).
[1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
[19]江澤民.論黨的建設[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
[20]陳鋒.分利秩序與基層治理內卷化——資源輸入背景下的鄉村治理邏輯[J].社會,2015(3).
[21]黃韜,王雙喜.產權視角下鄉村治理主體有效性的困境和出路[J].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3(2).
[22]祝天智.農村土地承包政策中的效率與公平張力及其消解[J].求實,2020(6).
[23]江宇.“煙臺經驗”的普遍意義[J].開放時代,2020(6).
[24]中共中央辦公廳 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加強和改進鄉村治理的指導意見》[R],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2019(19).
[25]整治群眾身邊腐敗和不正之風工作取得明顯成效[N].中國紀檢監察報,2021-10-11(1).
[26]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27]辛璄怡,于水.主體多元、權力交織與鄉村適應性治理[J].求實,2020(2).
[28]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2021-07-02(2).
[29]姜玉欣.大數據驅動下社會治理面臨的困境與策略選擇[J].東岳論叢,2020(7)
“Rural Reconstruction”:The Theoretical Logic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Rural Governance Led by Political Parties
ZHANG Yan1,ZHOU Ming-ming2
(1.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Shandong Youth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Jinan 250103,China;
2.School of? Marxism,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250100,China)
Abstract:
Rural governance led by political parties mainly “reconstruct the rural” through the party’s organizational system,leadership system and ideology,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building a modern national grass-roots political power and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Based on the analytical perspective of “party centrism”,we explore the evolution law of rural governance led by the Centennial party,which can perspective the four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party’s mission,the coordination of the party organization,the service of the party’s function and the diversity of Party governance,and accurately grasp the logical guidance of the party’s leading rural governance in different periods such as revolution,construction,reform and rejuvenation.To promote political parties to lead rural governance and achieve the strategic goa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we need to improve the organizational strength of rural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from the four dimensions of governance mission,governance system,governance function and governance subject,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system,meet the rural people’s yearning for a better life,and jointly build a rural governance community.
Key words:
party leadership;rural governance;party centrism;historical evolution;practical experience
(責任編輯
陳世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