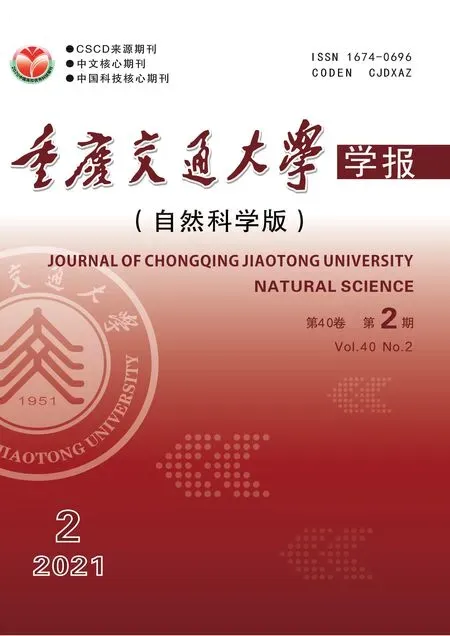飽和砂層泥水平衡盾構隧道開挖面穩定研究
蔣加兵,陳子龍,徐 濤
(1.中建四局第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廣東 深圳 518000;2.航天江南集團有限公司,貴州 貴陽 550009;3.澳門大學 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澳門 999078)
0 引 言
盾構技術已被廣泛應用于城市,特別是城市歷史街區和建筑密集區等需要嚴格控制地面變形區域的地鐵隧道建設中。當盾構隧道位于高水壓、高應力環境下的飽和砂層中時,如越江、越河和跨海隧道,開挖面的穩定性尤其重要。開挖面支護壓力過小可能導致地下水涌入壓力倉,導致開挖面傾塌;支護壓力過大會造成地面擠出破壞。開挖面支護壓力設計或控制不當造成的安全事故時有發生,特別是隧道開挖面失穩造成的地面結構物破壞、路面塌陷等事故屢見不鮮。2018年2月7日佛山市地鐵二號線隧道透水事故,造成11人死亡;2018年1月25日廣州市軌道交通21號線突發坍塌事故,死亡3人。在這種地層條件下,壓力泥漿通常用來平衡盾構隧道開挖面上的水土壓力,以穩定開挖面。壓力倉中的壓力高于地層中的靜水壓力,泥漿會向地層中入滲。在這種情況下,部分有效支護力轉化為超孔隙水壓力,使開挖面上有效支護壓力減小,降低開挖面穩定性。在一些隧道的掘進過程中,超孔隙水壓力已被監測到,例如荷蘭第二Heinenoord隧道、綠心隧道、阿姆斯特丹南北線隧道、上海中環穿越黃浦江隧道等[1-4]。因此,合理的壓力設計對開挖面穩定至關重要。
N.HORN[5]首次提出了的盾構隧道開挖面穩定的倉筒理論,如圖1。隨后,這一極限平衡法被很多學者采用并發展[6-8]。最近,黃阜等[9]、呂璽林等[10]、P.PERAZZELLI等[11]采用極限平衡法分析了開放式盾構隧道開挖面滲流對支護壓力的影響,并提出了支護壓力的上限解。但是,泥水平衡或土壓力平衡盾構隧道,掘進產生的地下水流方向和掘進方向相同,這和開放式盾構隧道掘進產生的地下水流方向相反。另外,地層條件(如均質含水承壓層和半封閉含水承壓層)也會影響開挖面上的水力梯度并影響滲流。另據試驗表明,在掘進過程中,由于泥漿和開挖土體的混合物填充盾構機和開挖面之間的間隙,開挖面上沒有泥膜形成[12]。泥漿的入滲距離隨混合物中土顆粒的含量增加而增加,開挖面上的有效支護壓力和有泥膜形成的情況有所不同。
筆者采用極限平衡法和超孔隙水壓力計算模型,并結合室內泥漿入滲試驗結果,分別分析土體強度、地層條件和泥漿入滲對開挖面支護壓力和微觀穩定的影響。
1 計算模型
1.1 模型建立
楔形體模型的基本框架如圖1。楔形體力學平衡示意如圖2。

圖1 楔形體模型

圖2 楔形體力學平衡
1.1.1 支護力E(θ)
支護力E(θ)按式(1)計算[13]:

(1)
式中:G為楔形土體A′B′C′D′E′F′自重,kN;Pv為楔形土體上方塊體C′D′E′F′K′L′M′N′自重產生的豎向均布荷載,kN;θ為楔形土體傾斜面與水平面的夾角,(°);φ′為開挖面區域土體的有效內摩擦角,(°);c為開挖面區域土體的黏聚力,kPa;T為作用在楔形土體傾斜面上的剪切抵抗力,kN;D為隧道直徑,m。


圖3 臨界傾斜角確定
1.1.2 楔形體重力G
(2)
式中:γ2,av隧道開挖面土體平均重度,kN/m3。
1.1.3 楔形體上方土塊豎向荷載Pv
(3)
式中:σv, crown隧道頂部總豎向應力,kPa。
1)當隧道頂部深度tcrown≤ 2D時[13]
σv(z)=γ1,av·z
(4)
式中:γ1,av隧道底部土體的平均重度,kN/m3;z為深度,m。
2)當tcrown>2D時[13]
(5)
式中:A為倉筒C′D′E′F′K′L′M′N′橫截面積,m2;U為倉筒橫截面邊長,m;K1為倉筒橫截面積范圍內的側向土壓力系數。
1.1.4 楔形體A′B′C′D′E′F′三角平面上的抵抗力T[13]
(6)
(7)
式中:K0為楔形土體上方塊體頂部的側向土壓力系數;Ka為朗肯側向土壓力系數。
1.2 案例分析
以一個直徑D=10 m,上覆土層C=20 m,支護壓力E=50 kPa,水位線位于地下3 m,有效重度γ′=11 kN/m3,干重度γd=17 kN/m3,飽和重度γs=21 kN/m3,黏聚力c=0 kPa,有效內摩擦角φ′=36°的現場為例,根據圖4開挖面E、θcr和φ′的相關關系可知:模型預測的支護壓力E隨土體有效內摩擦角φ′的增大而變小;臨界傾斜角θcr隨內摩擦角φ′的增大而增大。表明:對于無黏性土而言,土體強度越高,所需支護壓力越小;開挖面臨界傾斜角越大,作用在開挖面上的土壓力也越小,所需支護壓力也會減小。

圖4 開挖面E、θcr和φ′的關系
2 泥漿入滲影響
一般認為泥水平衡盾構開挖過程中,會在開挖面上形成不透水的泥膜,泥漿壓力完全轉換為作用在土體骨架上的有效支護壓力。但室內試驗證明,當開挖的土體和泥漿混合物填充盾構機和開挖面之間的間隙時,將沒有泥膜形成[12]。這種情況可能出現在掘進速度大于泥漿入滲速度的掘進過程中。另外,從荷蘭第二Heinenoord隧道的現場實測來看,壓力倉內的泥漿實為開挖土體和泥漿的混合物的密度在1 260~1 470 kg/m3[14]。在這種情況下,泥漿入滲后土體的滲透系數為:
(8)
式中:ks為土體的滲透系數,m/s;t為入滲時間,s。
式(8)計算所得滲透系數值和細砂中的泥漿入滲試驗測得的滲透系數值的對比結果如圖5。由圖5可知,計算結果和試驗結果吻合。開挖面土體的滲透系數在初期下降迅速,然后趨于緩慢。開挖面滲透系數可以很短時間內滿足開挖要求。需要注意的是,被泥漿入滲的土體滲透性會迅速降低。由于不同土體中泥漿的入滲距離和入滲速度不同,可能導致距開挖面不同距離土體滲透性隨時間的變化也會不同。文獻[15]的泥漿入滲距離如式(9):

圖5 泥漿入滲土體的滲透系數變化
(9)
式中:emax為泥漿入滲的最大距離,m;α為影響因子(2 ≤α≤ 4);Δp為壓力倉內壓力和地層靜水壓力的壓力差,Pa;τy為泥漿的屈服強度,Pa;d10為過篩重量占10%的粒徑,m。
泥漿的入滲速度如式(10):
(10)
式中:e為任意時間點的入滲距離,m;a為入滲距離達到最大入滲距離一半時的時間,s;t為時間,s。
公式(9)對t求導可得泥漿入滲速度如式(11):
(11)
從式(8)、(9)可以看出,泥漿入滲距離和速度與壓力倉內壓力、地層靜水壓力、泥漿屈服強度和土體d10值有關。因此,設定一個固定的支護壓力對不同工程而言過于簡單。
3 開挖面微觀穩定
地層條件會影響到盾構掘進產生的地下水流(超孔隙水壓力)和開挖面的穩定性。兩種不同的地層條件如圖6[16]:圖6(a)盾構隧道位于是均質含水承壓層中,圖6(b)盾構隧道位于半封閉含水承壓層中。均質含水承壓層中,地下水流會向四周流動的球形水流;但對于半封閉含水承壓層而言,在水平面內地下水流可以看成是一個一維水流,超孔隙水壓力不隨深度變化。
對于均質含水承壓層,盾構隧道開挖面上的水頭可以近似計算[17],如式(12):
(12)
將式(12)對x求導得:
(13)
在開挖面上(x=0)有:
(14)
對于半封閉含水承壓層,開挖面上的水頭如式(15)[18]:
(15)
式(15)對x求導得:
(16)
在開挖面上(x=0)有:
(17)
為維持開挖面的微觀穩定,即穩定開挖面上的單個無黏土顆粒,必須維持一個由恒定水力梯度(i≥2)提供的拖曳力[19]。對于均質含水承壓層中一個直徑為5 m或者更小的隧道而言,支護壓力50 kPa(開挖面上的水頭為5 m)可以滿足穩定開挖面微觀穩定的最小水力梯度的要求。但是對于直徑大或等于10 m的隧道,同樣條件下水力梯度為i≤1。這個水力梯度難以保證開挖面上單個土顆粒的穩定。同樣的,對于半封閉含水承壓層中一個直徑大于等于10 m的隧道,假設滲漏因子為100 m,50 kPa的支護壓力可以實現水力梯度i=0.05,不能滿足開挖面微觀穩定的最小水力梯度的要求。總體而言,在沒有泥漿支護的情況下,開挖面上的水力梯度很難維持開挖面穩定,因此建議壓力泥漿用于飽和砂層盾構隧道開挖面支護。
除了微觀穩定外,地層分層還在其他方面影響開挖面的穩定。A.BEZUIJEN 等[20]研究表明盾構掘進在半封閉含水承壓層時,會在盾構隧道周圍產生更高的超孔隙水壓力。從而降低開挖面的穩定性。相較均質含水水承壓層而言,需要更大的開挖面支護壓力。同時,當掘進在半封閉含水承壓層時,超孔隙水壓力會的影響范圍更廣,這將可能導致地面擠出破壞。另外,在半封閉含水承壓層中泥漿的入滲速度更慢。更大的孔隙水壓力范圍和更低的入滲速度將降低開挖面的穩定性。
水力梯度也會影響土體的受力狀態,這里不做具體展開。
4 結 語
考慮泥漿入滲和超孔隙水壓力的分析,微觀穩定泥水平衡盾構隧道被檢視用宏微觀模型。基于分析和試驗結果分析,得出以下結論:
1)在設計支護壓力時必須考慮泥漿入滲和超孔隙水壓力的影響,附加額外壓力以彌補泥漿入滲過程中有效支護壓力損失。
2)開挖面的滲透性是一個動態變化過程,而且不同土體中泥漿的入滲距離和入滲速度不同,可能導致距開挖面不同距離的土體的滲透性隨時間的變化也會不同。盾構機掘進和停止(維養和管片安裝)兩個階段的入滲狀態也不同。因此簡單的設定一個固定的支護壓力對不同工程并不適用。
3)相較均質承壓含水層而言,盾構隧道在半封閉承壓含水層中掘進時開挖面更加穩定。在沒有泥漿支護的情況下,開挖面上的水力梯度很難維持開挖面穩定,因此建議壓力泥漿用于飽和砂層盾構隧道開挖面支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