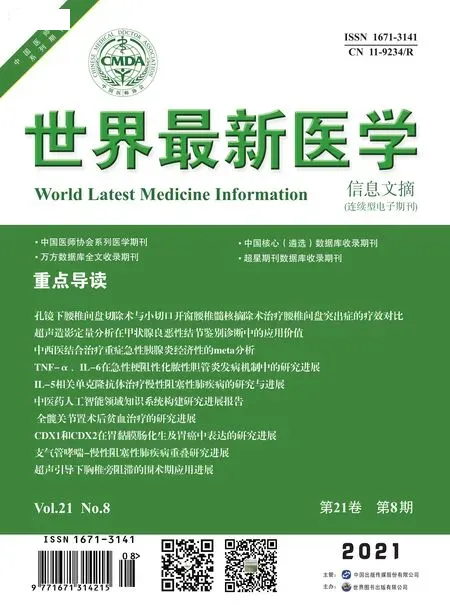扶正祛邪治法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恢復期的應用探討
唐家禾,黃葉芳,黃淑潔,唐健元,謝春光
(成都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四川 成都 610075)
0 引言
2019 年12 中旬以來,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爆發,現已證實為一種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傳染病。截至2020 年8 月1 日,累計確診85775 例,死亡4651 例,治愈80476 例,此次疫情波及廣泛,且目前尚無確切有效的防治藥物。據一線情況反饋,發現患者于恢復期CT 多提示肺部遺留纖維條索灶,提示肺纖維化,肺功能下降[1]。
1 COVID-19 患者恢復期狀況
1.1 臨床表現
COVID-19 患者恢復期的臨床表現多為進行性氣促、倦怠乏力、納差嘔惡、痞滿等,或有低熱,舌干少津或白膩,脈細或無力,其發熱、干咳、咽痛、肌痛、腹瀉、呼吸困難等癥狀消退。體溫恢復正常3 天以上,呼吸道癥狀明顯好轉[2-3]。
1.2 體格檢查
COVID-19 患者恢復期間,對其主要進行肺相關體格檢查,表現為進行性氣急、干咳,部分患者可出現杵狀指,叩診為濁音或實音,聽診可聞及吸氣性Velcro 啰音[5]。
1.3 實驗室檢查
COVID-19 患者治療期間,可出現外周血白細胞總數正常或減少,淋巴細胞計數減少,肝酶、乳酸脫氫酶、肌酶、肌紅蛋白增高,肌鈣蛋白增高,C 反應蛋白(CRP)和血沉升高,降鈣素原正常,嚴重者D-二聚體升高、外周血淋巴細胞進行性減少,常有炎癥因子升高。經規范治療后,恢復期間患者各項實驗室檢測指標多恢復正常[4-5]。
1.4 胸部影像學
COVID-19 患者治療期間約92.3%存在肺部影像學改變,其肺部CT 均不同程度地出現毛玻璃陰影,典型改變彌漫性線條狀,小葉間隔增粗,嚴重者出現兩肺彌漫性實變伴間質增厚(Fig 1 D~F),恢復期間患者肺內GGO 病變逐漸減少,急性滲出性病變明顯改善,纖維索條影逐漸增多,提示肺纖維化,肺功能下降[6-7]。
1.5 特殊檢查
連續兩次呼吸道標本核酸檢測呈陰性(采樣時間至少間隔24 小時),其準確度為痰標本最高,鼻拭子相對較低,咽拭子最低[5]。
2 扶正祛邪法理論源流
扶正,意為培補正氣,使用扶助正氣的藥物或配合其他療法,從而增強體質,提高機體抗邪能力,得以戰勝疾病、恢復健康,如補氣、壯陽、滋陰、養血等。祛邪,意為祛除病邪,通過藥物或其他療法祛除或削弱病邪,減少邪氣侵襲和損害,達到邪去正安的目的,如汗法、吐法、下法、清熱、利濕等[8]。
2.1 初現于先秦
早在先秦時期,便有醫書提及過相關概念。醫家之宗《黃帝內經》云“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正氣存內,邪不可干”,“不相染者,正氣存內,邪氣可干,避其毒氣”。由此可見,早在當時便已意識到正氣虛弱與邪氣侵體是機體發病的兩大關鍵因素,若正氣旺盛,加之防護措施到位,則能有效御外,以防邪氣趁虛而入[9]。
2.2 明確于東漢
傳至東漢時期,扶正祛邪理論正式提出,體系得以充實與完善。醫圣張仲景延沿傳《內經》的思想,于《傷寒論》中指出“四季脾王不受邪”、“五臟元真通暢,人即安和”的理論,強調正邪相爭是影響疾病轉歸和預后的關鍵,且在臨床治療時需注意“扶正不留邪,祛邪謹傷正”的原則。《金匱要略·血痹虛勞病脈證并治第六》亦有“薯蕷丸”一方,為氣血陰陽俱虛、外邪趁虛侵犯人體的一類病癥,為經方中扶正祛邪的代表方,體現仲景“扶正祛邪”一法的臨床實踐運用[10]。
2.3 成熟于唐宋
唐宋時期,扶正祛邪[11]理論運用趨于鼎盛,為當時治療疫病之首要法則。徐琪玥等經大量數據研究核實,縱觀唐宋時期治療疫病常用方藥中,補氣類使用頻率最高,可見扶正祛邪為其主要治則。如許叔微著有《普濟本事方續集》,指出“何謂須用有胃氣緣胃受谷氣,谷氣生則能生氣血,氣血壯則榮衛不衰,榮衛不衰則病自去矣”認為脾胃維持機體氣血正常生理功能,從而榮衛得以固全,可達抵御外邪之功。
2.4 相傳于金元
金元時期,扶正祛邪理論得以傳承。朱丹溪提出“凡治病,必先固正氣”,李東垣提出“既脾胃有傷,則中氣不足,中氣不足,則六腑陽氣皆絕于外……故榮衛失守,諸病生焉”。醫家們用藥注重補益和中,強調扶正祛邪之治療要法。誠如“善用兵者,必先屯糧,善治邪者,必先養正”[12]。
2.5 發展于明清
明清時期,扶正祛邪理論得以進一步發展。吳鞠通《溫病條辨》論述到“留得一分正氣,便有一分生理”[13],張介賓于《景岳全書·瘟疫》中提出“傷寒瘟疫,俱外侮之證,惟內實者能拒之”,王肯堂指出“時疫者,乃天行暴厲之氣流行,法當辟散疫氣,扶正氣為主”,均為扶正祛邪理論之傳承和發展。
綜上所述,運用扶正祛邪治法時需注意以下幾點:(1)扶正是為了祛邪,祛邪亦是為了扶正,二者相輔相成,并駕齊驅。(2)分清主次緩急,遣方用藥靈活。扶正多用于虛證,祛邪多用于實證,虛實交雜時扶正與祛邪并用,需辨明輕重緩急,攻補兼施,隨證治之。(3)注意“扶正不留邪,祛邪謹傷正”的治療原則[14]。
3 COVID-19 恢復期的中醫病因病機分析
3.1 病因為“感受疫戾之氣”
武漢地區水多濕重,去年下半年久旱成伏燥,12 月陰雨連綿半月形成濕寒之氣,伏燥與寒濕邪氣相合,從而形成疫毒邪氣,即瘟疫[15]。《疫證治例》云“風寒暑濕燥火六氣失時,是為六沴。沴,惡氣,亦毒氣也。中其毒者,率由口鼻入……稽留氣道,蘊蓄軀殼,病發為疫,證類傷寒。”《傷寒指掌》亦云“天久陰雨,濕北風行,脾土受傷,故多寒疫寒濕”[7]。國家衛健委、中管局及各省市衛健委分析其病因總體可概括為“感受疫戾之氣”,但具體分析各略有不同,其中提及最多的病因為“濕邪疫毒”、其次為“寒濕疫毒”,最末為“濕熱犯肺”[16-17]。
3.2 主要病機為余邪未盡,正氣虧虛
肺居胸中,上通喉嚨,開竅于鼻,外合皮毛,且為嬌臟,是臟腑之華蓋,故邪疫之氣極易直犯肺臟,患者外感此非時之氣,肺臟宣發肅降、主氣司呼吸等功能失調,肺為邪客,氣機壅滯,升降失司,累及他臟。此次疫情治療參考《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七版)》,[18]西醫學納入抗病毒治療、抗菌藥物治療、免疫治療等,中醫學主要包括宣散、調和、清解、通下以及酌用中藥注射液等治法,因重用開表清里之法,故而邪雖已大去,但正氣已傷,同時可能留有余邪,正如葉天士言“恐爐煙雖熄,灰中有火”,需及時跟進治療。
3.2.1 余邪未盡
(1)余熱未清
疫邪去之大半,余邪未盡,氣陰已傷,故仍可見低熱,熱邪灼傷津液,口干咽燥;氣隨陰傷,故見乏力,自汗出;氣推動無力,聚濕為痰,則見納差腹脹等癥狀。
(2)瘀血阻滯
目前臨床顯示,COVID-19 恢復期患者多提示肺纖維化,此癥可歸類于中醫學的肺痹、肺痿、喘證、肺脹、痰飲等肺系疾病中[19],此類病多夾有瘀,因肺朝百脈,通調水道,當肺痿不用時,則調布津血不暢,推動無力,積為瘀血。此外,病程遷延,久病入絡,引起臟腑經絡氣血瘀滯,《素問》云“久病入深,榮衛之行澀,經絡時疏,故不通”。
(3)痰濁壅盛
邪犯機體,臟腑功能受損,致使脾失健運,痰濁內生,形成新的病理產物,進一步影響機體功能,濁陰壅擾中焦,則可見痞滿、納差嘔惡等癥狀。
3.2.2 正氣虧虛
(1)氣陰兩虧
熱病后期,熱盛傷津,真陰虧損,氣隨津脫。氣虛則神疲乏力,倦怠懶言;氣行無力,濕聚為痰,則納差腹脹便溏等;陰虛則虛火內生,肺氣失宣,發為咳嗽、氣促;虛熱內生,則口渴咽干。
(2)肺脾氣虛
疫邪客肺,大病去后,耗傷肺氣,子病及母,脾失健運。故而肺失宣降,咳嗽氣短;脾失健運,納差腹脹;脾肺氣虛,津液失布,聚濕成痰;氣虛則推動無力,機能活動減退,則神疲乏力,聲低懶言。
4 扶正祛邪治法對COVID-19 恢復期的應用探討[20-30]
4.1 扶正治法
4.1.1 益氣養陰
熱病過后,多見傷津耗氣之癥,可見氣短乏力,自汗出,口干,舌質紅或淡,舌苔白或少,脈細數。肺為嬌臟,極易傷陰,可用麥門冬、黨參、甘草等藥物以益氣生津,取其甘潤之效;佐以粳米、大棗益養胃陰,則津液可上歸于肺;再配伍半夏,以其溫燥之力使滋而不膩。
4.1.2 健脾補肺
邪去大半,脾胃受損,運化失司,可見氣短,倦怠乏力,納差嘔惡,便溏,舌質淡胖,苔白膩,脈弱滑。可選用黨參、黃芪、甘草等補益脾肺之藥以益氣固元;白術、茯苓等淡滲祛濕藥物以健脾助運;佐以枳殼、陳皮等行氣消痞藥物,補而不滯。
4.2 祛邪治法
4.2.1 清瀉余熱
熱病后期,高熱雖除,但余熱留戀氣分,可見或有低熱,乏力,心慌,口干,自汗出,腹脹,舌質紅,苔少,脈虛數。可選用竹葉、石膏等涼潤藥物以清瀉余熱;配伍麥冬等甘味微苦寒之藥物以養陰生津,助清余熱;佐以半夏,其性溫燥削弱,但可助麥冬補而不滯,石膏清而不寒。
4.2.2 活血化瘀
多用于體內存瘀的恢復期患者,可見氣短,胸悶,乏力,舌質紅,或舌有瘀點,苔薄白,脈沉酌用桃仁、紅花等活血化瘀之品,佐以芍藥養血合營,川芎活血行氣,需隨證加減,主要達到化瘀生新之功效。
4.2.3 祛痰泌濁
熱病過后,脾胃受損,運化失司,易生痰濕,且肺中病灶炎性滲出易凝聚為飲,可見納呆少食,時欲吐痰,氣短多喘,汗出不暢,舌淡或白,苔厚膩,脈沉滑。需健脾助運,如選用黨參、茯苓、黃芪、白術等藥物,而避免使用芳香化濕類過于辛燥之品以進一步耗氣傷津。
4.3 扶正與祛邪當二者同施
綜上所述,“正已虛而邪未盡”是COVID-19 恢復期的主要病機,而扶正祛邪治法為歷代醫家所推崇,也同樣適用于此次疫情恢復期的臨床治療指導,在臨床時需注意隨證加減治之。現將各個省市指南中記載的恢復期用藥總結如下。

表1 COVID-19 恢復期中醫藥治療方案
5 其他中醫療法
5.1 中醫外治法
可采用艾灸療法、艾灸聯合刺血療法、中藥穴位貼敷、穴位埋線法等[31]。艾灸肺俞、膏肓可升高肺纖維化大鼠干擾素-γ 的含量,從而發揮有效防治肺纖維化目的[32]。徐慧卿[33]以中藥湯劑、艾灸、點刺放血等聯合治療方法治療肺纖維化患者42 例,與對照組相比,治療組患者肺功能改善明顯。燕金芳[34]以四一散(自擬方)對51 例患者進行穴位貼敷,發現穴位貼敷能有效促進肺間質炎癥吸收,促進肺功能升高。王步青[35]等人發現,特定穴位埋線治療可有助于改善輕度肺纖維化患者肺功能,有效提升患者生活質量,且便捷、安全、無不良反應。綜上所述,在臨床醫師辨證指導下進行中醫外治法,可有效改善COVID-19 恢復期肺功能下降患者的生活質量。
5.2 傳統保健運動
傳統保健運動[36]是利用中醫理論指導中醫養生的理論和實踐成果,包括太極拳(每次30 分鐘左右,每日1 次)、八段錦(每次15 分鐘左右,每日1-2 次)、五禽戲等,通過軀體的調節,意念的運用,在中醫理論指導下[37],來調節和增強人體各部分機能,從而起到固護正氣、強身益智、防治疾病等作用。
6 小結
自我國防控救治此次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近2 月以來,中醫藥參與疫情防控救治的全過程,包括潛伏期、發病期、恢復期等,但目前有效防治藥物仍有待研發,且確診、治愈人數不斷劇增,越來越多的恢復期患者出現機體免疫力低下及肺部纖維化等后果,故而患者恢復期的治療以助其盡快恢復健康尤為重要,以保證患者恢復期有效恢復機體正氣且不再復感癘氣而發作,希望此篇探討對于臨床治療恢復期的新冠肺炎患者時能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