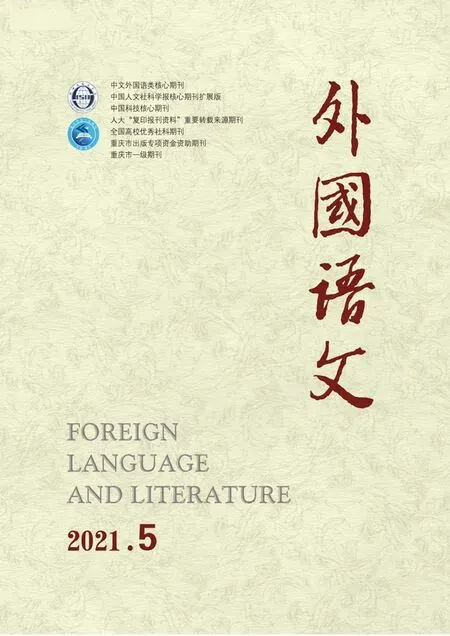高厄的七罪書寫和道德選擇
——以《人類之鏡》為例
張亞婷
(陜西師范大學 外國語學院,陜西 西安 710062)
0 引言
中世紀英國詩人約翰·高厄(John Gower, 1330—1408)像許多中世紀歐洲詩人一樣深受基督教影響,在詩作中進行宗教教義闡釋和道德說教。從14世紀70年代起,他用三種語言先后創作了三首長詩:盎格魯-諾曼語的《人類之鏡》(Mirourdel’Omme),拉丁語的《吶喊聲》(VoxClamantis)和中世紀英語的《情人的坦白》(ConfessioAmantis)。高厄研究大多集中在《情人的坦白》上,但為其他兩首長詩提供寫作框架的《人類之鏡》未引起太多關注。關于《人類之鏡》,麥考利認為,高厄在想象力和技法上優于以前的盎格魯-諾曼語作家(Macaulay, 1899:li-lvi)。這首詩的標題采用了中世紀作品題目廣泛采用的“鏡子”一詞,屬“典范和訓誡之鏡”,旨在進行道德說教。“英語文學之父”杰弗里·喬叟(Geoffrey Chaucer, 1343—1400)把詩歌《特洛伊羅斯和克麗西達》(TroilusandCriseyde)獻給高厄時稱他為“道德家高厄”(moral Gower),這為高厄研究奠定了基調。事實上,高厄在這首長達近三萬行的詩歌中,把中世紀歐洲流行的擬人化寓言、等級諷刺文和訓誡文等形式融合在一起,全詩以界定善惡寓意、揭示社會罪惡行為和表明道德選擇布局,既口誅筆伐,又諄諄教導。因此,本文旨在分析高厄如何以擬人化寓言形式繪制出罪惡與美德之“樹”,通過等級諷刺文再現社會不同人群的邪惡行為,最后以訓誡文的形式說明提升人們精神追求的力量之源。
1 提出問題:罪惡與美德之戰
中世紀時期,人們通常以樹的視覺化效果來展示善惡之戰。12世紀中期,德國的說教手冊《童貞女之鏡》(SpeculumVirginum)就配有“美德之樹”和“罪惡之樹”的插圖,樹葉分別代表七種美德和七種罪惡,其樹根分別是謙卑和傲慢。14世紀“美德之樹”的果實代表七種神圣美德,每種美德又分為七種附屬美德,而樹根代表著謙卑。羅伯遜對此進行評價時指出,中世紀時期,人們一般把罪惡分為七種,美德之所以采用七分法是因為它們和圣靈的饋贈有關(Robertson, 1970: 6-8)。這種分法與14世紀由法語譯為英語并在英國頗為流行的《罪惡與美德之書》(TheBookofVicesandVirtues)中的分法頗為相似。值得注意的是,高厄在《人類之鏡》中正好以文字為媒介“繪”出了“罪惡之樹”和“美德之樹”,并通過擬人化寓言展示了魔鬼家族和上帝家族譜系的建立過程和特點。
高厄在詩歌開頭講述了大天使路西法如何背叛上帝以及亞當和夏娃如何受蛇的引誘失去伊甸園的故事,指出罪惡無處不在。他以譴責“罪惡”開始,“聽聽這個吧,每位渴望,/‘罪惡’的戀人,/她的愛是虛假的”(1-3行)(1)John Gower, “Mirour de L’Omme.” in The Complete Works of John Gower:The French Works.Ed. G.C. Macaulay.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899:1-334.全文原作引文只注出詩行,不再另注。詩中出現的擬人化寓言人物在論文第一部分用雙引號標出。。魔鬼從天堂跌入地獄之后想盡辦法行惡,生育了丑陋邪惡的女兒“罪惡”并給她傳授最奸詐的伎倆,又與她一起生育了兒子“死亡”。“罪惡”和“死亡”生育了七個女兒,即“傲慢”“嫉妒”“憤怒”“貪婪”“懶散”“貪吃”和“縱欲”。顯然,高厄不像英國詩人羅伯特·曼寧(Robert Mannyng, 1275—1338)那樣稱她們為“地獄的女兒”,也不同于英國神秘主義者沃爾特·希爾頓(Walter Hilton, 1340—1396)把泉水比作罪惡之源,用七條河和人體的七個部位來比喻七罪。如上所見,他反而以神學和基督教教義中的七宗罪為她們命名,同當時的教會人士、世俗藝術家和作家采用這些概念的做法一樣,屬于典型的七罪書寫傳統。
詩歌中,魔鬼召開會議,目的是如何把人類帶到地獄。“罪惡”說道:“父親,我向您保證,/我會和我養大的七個女兒一起/欺騙人的肉體:/如果人和她們為伴,/他逃不過厄運,/最終會變壞。”(367-373行)與魔鬼屬于同一社群的“世界”“死亡”“誘惑”和其他成員乃一丘之貉,他們想盡辦法引誘人類,使人的“靈魂”和“肉體”爭辯并產生分歧,但“肉體”看到“死亡”后迅速回歸到“靈魂”身邊。失敗后的魔鬼找來“罪惡”和“世界”商量對策,而“世界”和“罪惡”的七個女兒的婚姻實際上是幫助魔鬼實現愿望的聯袂。她們婚后每人又生育五個女兒,共計35個女孩。這些女孩長相奇怪,騙術高超,目的就是欺騙人的靈魂。麥考利指出:“在《人類之鏡》中關于罪惡的這一部分,每宗罪被均勻地分為五個,或者,正如作者所寫,有五個女兒。就我所知而言,這種五分法沒有向以前的任何作家借用。當然,道德論著中把七罪再進行細分很常見,通常細分的數字不規律,我還沒有發現把每宗罪系統地分為五個的權威做法。”(Macaulay, 1899:xxxvi-xxxvii)筆者認為,五分法也許和高厄在《情人的坦白》中認為人的罪惡來自五官感覺有關(Macaulay, 1901:295-302行)。“罪惡”的女兒們騎著不同動物參加婚禮,手棲有寓意符合各自身份和特點的不同鳥類或家禽,她們的嫁妝是地獄。婚禮在五月舉行,自然女神重新裝點世界,冥王和冥后應邀出席,“世界”和“罪惡”就位,酒神巴科克斯管理大廳,愛神維納斯負責賓館住房,吟游詩人演繹自然之妙曲。可以看到,這些人物多是希臘神話中的人物。高厄似乎有意表明,上帝和魔鬼之戰又是基督教與異教之間的斗爭。
高厄竭盡筆墨來描述魔鬼家族建立過程,而上帝家族是為反擊七罪出現。上帝把代表美德的七個女兒“謙卑”“仁愛”“忍耐”“英勇”“慷慨”“適度”和“貞潔”嫁給“理性”先生。婚禮舉行當天,“理性”身著白色條紋深藍色長袍,藍色意味著對上帝忠誠,白色是純潔的符號。他打開了“罪惡”永遠無法征服的三角旗,選擇了“好思”“好句”和“好事”三位吟游詩人奏樂助興。牧師“上帝的恩典”主持婚禮,“良知”把上帝的女兒們帶到教堂,“靈魂”做擔保人。這說明,上帝和“理性”正式向魔鬼和“世界”宣戰。通常人們認為上帝有四個女兒,比如在圣維克特的休(Hugh of St. Victor, 1096—1141)、克雷沃的伯納德(Bernard of Claivaux, 1090—1153)、格羅塞特斯特(Robert Grossetest, 1175—1253)和詩人蘭格倫(William Langland, 1332—1386)的寫作中,這四個女兒分別是“仁愛”“正義”“真理”和“和平”。但是,高厄進行了創新,采用了七分法代表美德,又和基督教通常認定的七大神圣美德(即信仰、希望、仁愛、謹慎、正義、勇氣和克己)不同。值得注意的是,高厄筆下的七罪與七種美德都以女性形象出現。費蘭特指出,因為表述概念的詞語多是陰性,因此通常也會讓女性人物來再現。這種手法是修辭需要和心理需要的綜合(Ferrante, 1985:42-43)。高厄在擬人化寓言中彰顯二元對立的善惡世界,首先從寓意上表明人的內在沖突。
從展開方式來看,高厄對罪惡的書寫以1(魔鬼)-1(罪惡)-1(死亡)-7(七罪)-35(七罪每人生育五個女兒)的產生模式展開,美德以1(上帝)-7(七種美德)-35(美德每人生育五個女兒)布局,比如“傲慢”的五個女兒分別是“虛偽”“自負”“自大”“炫耀”和“違抗”,其對抗者“謙卑”的五個女兒是“虔誠”“畏懼”“謙虛”“謹慎”和“順從”。從字面意義來看,這些寓言人物的名字是同一詞的衍生詞,且罪惡和美德各自女兒的名字互為反義詞,罪惡及其女兒是魔鬼的后代,美德及其女兒均是上帝的后世。由此可見,她們的對抗性存在恰好證明上帝與魔鬼處于完全對立的二元世界。我們很難確定高厄是否了解羅馬基督教詩人普魯登修斯(Prudentius,348-413)在《靈魂之戰》(Psychomachia)中通過寓言展示罪惡與美德的博弈,但高厄以七分法和五分法的方式“繪”出了罪惡與美德的“樹”狀視覺圖。
如前所述,喬叟視高厄為道德家,這可能和高厄當時在倫敦為人熟知的詩歌名氣有關,即他堅持改良主義,思想上擁護古典主義,保持了質疑善惡問題的連續性(Yeager, 1984:97)。在《人類之鏡》中,高厄的道德立場得到大量文獻的支撐。筆者的統計顯示,他主要引用《圣經》中的人物故事(比如以賽亞、約伯、大衛、所羅門、該隱、亞伯、拉結、摩西、丹尼爾、亞當等)和歐洲大陸的教父、哲學家、歷史學家或詩人等人的話語佐證(比如圣格列高利、圣哲羅姆、圣奧古斯丁、圣安布洛斯、塞內加、圣馬克、波愛修斯、伊索多、索利努斯、賀拉斯、西塞羅、亞里士多德、奧維德、加圖等),還以愷撒、亞歷山大和康斯坦丁等人的事跡為例證,并引用希臘神話人物、大量諺語和自然史等方面的知識進行說明。他的寫作表明,這首詩歌中的許多東西源于知識積累,而非個人經驗本身。這種百科全書式的寫作使高厄以讀者、觀察者、審判者和“繪畫者”的角色出現,把不同來源的材料縫合起來,以擬人化寓言的形式立意,通過文字繪出“罪惡”與“美德”兩棵“樹”,成為把百科全書式寫作和懺悔文學結合在一起的寫作大潮中的優秀詩人,為進行社會批判奠定了基礎。
2 再現問題:現實社會中不同人群的罪惡行為
在以擬人化寓言形式書寫了上帝和魔鬼譜系的建立之后,高厄隨即轉向社會空間,因為罪惡已經蔓延到了宗教界和世俗社會不同階層。這和當時的社會背景及高厄的個人經歷有一定關系。蘭格指出,英國在英法百年戰爭期間發的戰爭橫財改變了薪水和價格結構,引發經濟和社會危機,戰爭橫財使一些人突然過上奢侈生活,整個社會底層處于騷動之中。教會和政府嚴重腐敗,導致整個社會奢靡之風盛行(Langer, 1972:288-289)。我們知道,高厄寫作《人類之鏡》時已從肯特郡搬到倫敦居住(Bennett, 2018:258-282),對出現在倫敦不同階層或人群中的各種社會亂象頗為了解,因而進行諷刺和說教。這屬于典型的等級諷刺文(estate satire)或等級文學(estates literature)。事實上,他對不同階層人物的再現對喬叟寫作《坎特伯雷故事》產生了一定的影響(Mann, 1973:207-208; Correale et al., 2005:2-3)。高厄指出,他寫作的動機不僅僅來自個人想法,而是來自所有基督徒的牢騷、抱怨和吶喊,“西蒙用金和銀/統治羅馬宮廷,/盡管喧嚷,但窮人的聲音聽不到:/那些沒有帶金質禮物去的人,/不會獲得正義,/不會獲得寬容和仁慈”(18451-18456行)。他用羅馬教會貪財的腐敗行為譴責英國人拜金的現狀,用西蒙的例子譴責社會中存在的傲慢和貪婪之風,為處于他者或附屬位置的群體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發聲,表現出道德憤怒和反拜金主義思想,而這種憤怒是人們看到某個人或某個機構觸犯道德原則之后表現出的一種怒氣。高厄詳細描述了現實社會中的七罪行為,并對此進行了強烈譴責,而罪惡出現在不同群體的思想和行為之中。
教會各級人員(包括主教、高級教士、領班神父、教區牧師、學生、修士和托缽士)和不同修會的貪財或不作為行為使高厄感到不滿和失望。主教剝奪信徒的錢財建立起自己的財富王國,專欺窮人,包庇貴族。高級教士搶奪下屬,兜售贖罪券換取錢財。領班神父和主任牧師作惡不斷,一心斂財,主任牧師甚至開妓院獲利。教區牧師不是花神圣教會的錢去學校和宮廷謀職,就是在教區聲色犬馬。年度彌撒牧師吃喝玩樂,耽于肉欲。高厄責問道:“當你在誦經臺上/唱彌撒曲的時候,/你說實話,/你想著上帝,還是其他誰?/上帝聽到了你的聲音,但那個愚蠢的女孩/卻占據著你的心。”(20681-20686行)文中多處有這樣的質疑。他認為學生去教堂不是為靈魂尋求力量,而是學壞。壞孩子長大成為壞人,壞學生變為壞牧師。他還指出,過去居住在山洞中修行的修士現在也過著奢侈生活,“天啦!恥辱啊!/今天的修士住宿如同國王/住在大廳/他們尋歡作樂:/人數眾多,但我沒發現幾個/愿意遵守/修會奠基者的戒律”(21114-21120行)。他的一聲“恥辱啊”表明他對教會體制、現狀和未來的極度絕望,在批判中擴大了罪惡揭示和說教的范圍。勒平指出,高厄把學生和修士這些沒有圣俸但不常出現在等級諷刺文中的人包括進來,最大限度地實現這種體裁的目的,即通過糾正罪惡達到道德改善的目的(Lepine, 2019: 267)。
高厄對國王和騎士這一群體進行了譴責和批判。國王不履行保護神圣教會和法律的義務,在其位不謀其政。高厄力勸國王禁欲,不要貪杯愛財,應熱愛正義和真理,摒除雜念、無知和傲慢,保持謙卑和理性。他還譴責尸位素餐的騎士,因為他們對戰爭不感興趣,期待的是錢財、面包和紅酒。這當然和13世紀起就已經出現危機的騎士制度有關。高厄以英勇善戰、富有美德的查爾斯國王、戈弗雷和亞瑟王為例鼓勵他們為了上帝、勇氣和愛情去海外戰斗,發揚騎士精神。高厄認為英吉利海峽兩岸有不同頭銜的權貴們(比如王子、公爵、伯爵和侯爵等)掠奪窮人,使人們深受其害,但無人找到良方,他奉勸貴族們學會懺悔。羅斯的研究顯示,當時的申訴案中,被告人主要是騎士、紳士和權貴,上流社會人士比例占到一半(Rose, 2017:195-200)。顯然,高厄的指責具備很強的現實維度。
高厄還批判法律界人士,尤其是高級律師、法官、治安官和陪審員等,因為法律受到金錢的腐蝕而失去正義。以高級律師為例,他們為了錢財歪曲法律,壓榨窮人,拖延案子以獲得更多錢財,“(他們)總是雙手攤開/只要給金子,/四面八方的來人,/都受歡迎”(24429-24432行)。高厄可能受13世紀古法語寓言詩《玫瑰傳奇》(RomandelaRose)中律師形象塑造的影響,在諷刺高級律師方面又和同時代詩人蘭格倫不謀而合,“賄賂,求情,關系,嚇唬,/這些是法官的/伎倆,他們因此墮落:/據說,我相信這些說法,/正義現在受黃金掌控/它威力很大”(24625-24630行)。治安官發誓向國王和大眾效力,但不送禮案件就石沉大海,杳無音信,送了禮的人即便沒理最后都會贏了官司,而陪審員的謊言和歪曲讓小錯變大錯。從高厄詳細的描述和表現出的厭惡情緒來看,這些人以送禮多寡論正義。羅斯指出,英國國王愛德華一世和愛德華二世時期的政治歌就是控訴法律的無效和金錢對法律體系的腐蝕(Rose, 2017:150-151)。因此,這種趨勢發展到高厄創作時期不足為奇,而他的批判和這些詩歌達成互文,進一步說明金錢在14世紀英國法律執行中的破壞作用。
高厄還表現出極其強烈的反商情緒。加斯特認為,14世紀50年代到14世紀末,英國的商業活動不穩定,商人權力崛起,在政治和文化中發揮著重要作用(Gaste, 2018:128)。因此,高厄以弗羅德(其名Freud意為“冒牌貨”)為例,認為他富可敵國,卻誑時惑眾,弄虛作假,表里不一,追逐利潤。他還諷刺金匠、珠寶商、藥劑師、醫生、馬具匠、鞋匠、酒商、家禽小販和零售店主等其他行業的從業者。這些人的普遍特點是絞盡腦汁騙人,弄虛作假,移花接木,無惡不作,和客戶或消費者的交換關系失衡,在信仰體系中表現出道德責任感缺失,但高厄并沒有具體描寫消費者對此的反應。他再現的這種欺騙行為和蘭格倫在《農夫皮爾斯》(PiersPlowman)中寓言人物“貪婪”向“懺悔”坦白自己和妻子的欺騙行為相似。在某種程度上,高厄的觀點和立場和他對商業發展中出現的這些罪惡行為的憎惡和不滿有關。高厄寫道,人們過去舉止得體,買賣誠實,但現在一切徹底改變,“因此,現在人們可以看到/事事正在變壞,/(包括)生意和商品。”(25810-25812行)高厄在揭示和批判中的懷舊情緒表明了古今之差,雖然商業在14世紀的社會發展方面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但商業活動在運行中同時伴有許多罪惡行為。貝爾托萊認為,從現實層面看,不排斥當時倫敦檢察官有腐敗行為,弱者通過欺騙行為獲得通向權力的機會,糾正這種行為的權力處于缺場狀態(Bertolet, 2013:43)。
需要注意的是,本是同情底層勞動者的高厄卻把他們比作是正在蔓延的蕁麻,“在它帶來正義之前,/會突然刺痛我們。”(26495-26496行)他認為洪水、野火和揭竿而起的小人物一旦占了上風就會摧毀一切。這也許是高厄在14世紀70年代已感受到英國的政治氣候和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社會壓力。編年史家佛華薩(Jean Froissart,1337—1405)的記載顯示,1381年英國農民起義的本意是擺脫農奴身份以獲自由,但最后卻演變為殺富劫財(Froissart,1978:211-230)。事實上,1358年法國北部就爆發了反對戰爭稅的農民暴動,史稱扎克雷起義,但最終被鎮壓。海峽兩岸先后出現的相似情況說明當時由于戰爭和勞動力結構的改變出現了社會危機。顯然,高厄在這方面對時代脈搏有足夠到位的把握。他在控訴和勸告之余反復呼吁人們要同情窮人,這種訴求具備14世紀頗為流行的控訴文學(literature of complaint)的特點,但這可能只是他意念上對窮人的刻板印象或理解。中世紀經濟理論學家認為,貧窮具有積極的道德價值,但非自愿貧窮并不是罪惡或美德,而是不幸,教會法庭會幫助他們,但世俗法庭卻視窮人為“看不見的人”(Colish, 1997:326-327)。雖然高厄同情窮人,卻認為所有階層變得更壞,窮人也不例外,“沒人對自己的階層滿意”(26560行),“現在地球每個地方都充滿壓迫/貧窮和痛苦”(26580-26582行),但人人都說“這個時代壞了,這個時代壞了!”(26591行)這些感慨表達出他對時代的幻滅感,而這種幻滅感來自社會不同等級之間的不平等關系和人們在物質和精神層面的貧乏。因此,科爾曼指出,“高厄是那個世紀在揭示政治和社會動蕩方面最優秀的詩人”(Coleman,1981:135)。由上可見,高厄再現了社會不同等級、不同職業人群的罪惡行為,展示出對信仰滑坡的焦慮與憤怒情緒,但在詩歌最后指出了解救良方。
3 解決問題:效仿圣母
詩歌最后,高厄質疑和反思罪惡之源。在他看來,世界的組成部分土、水、空氣和火都對人類有益,太陽、月亮、星辰、樹木和動物不是罪惡之源。他仔細分析后認為是人類自己造就了這些罪惡,因為人有自由意志,可選擇棄惡從善,通過善行來改變世界。他意識到自己過去沉迷于世俗之樂,驚愕中自覺被七罪毀滅,在自我反思和懺悔中指出進行自我內控的必要性。他準備全心服務于上帝,深信圣母會給他的靈魂開出療法以治愈他的傷口。這也許可以從高厄妻子的墓碑上看到他改變自己的原因和目標,因他自稱為“謙卑的高厄”,而謙卑被看作是圣母瑪利亞的美德,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也是所有美德的根基。在一首中世紀英語布道詞中,圣母被看作是天堂之花百合的根,具備所有美德,她能為人的罪惡找到療法,使有罪之人獲得新生(Ross, 1940:189)。高厄認為有必要講述圣母的經歷,以讓人們知道她的偉大之處。他的這種意愿表達使他的道德圈擴大至他人。事實上,高厄的書寫處于中世紀流行的訓誡文學傳統之中,因為這種類型的詩歌或布道詞一般遵循一定模式展開:界定罪惡或描述現實生活中人的罪惡行為,敘事者決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或意識到自己的罪惡,最后在禱告中祈求圣母作為調停人從中周旋,讓人們得到基督的寬恕和祝福,以便在死后進入天堂。這種想法其實在高厄的盎格魯-諾曼語詩集《五十首歌謠》(CinkanteBalades)的最后一首歌頌圣母的詩中得到充分體現。
高厄在《人類之鏡》的最后部分細述了圣母的出生故事和圣母五喜。他不同于同時代其他詩人,后者多以歌頌、祈求或贊美圣母為主,而高厄強調上帝對她的偏愛和她對童貞的堅守,用太陽光穿過玻璃但玻璃沒有受損來說明瑪利亞是童貞女母親。他還講述了圣母五喜,即圣母領報、耶穌誕生、耶穌復活、圣母升天和圣母獲得榮光。弗雷立克指出,對中世紀基督徒來說,純潔是能夠反映真理的典范之鏡,是反思、冥想和智慧的源頭,是人們了解自我和模仿的理想之鏡(Frelick, 2016:7-8)。凱利認為,早期教父在寫作中強調童貞之身和精神貞潔的完整性和一致性,認為童貞/貞潔就是一種精神特質(Kelly, 2000:3-7)。伊赫納特指出,諾曼征服之后,英國在禮拜儀式、神學闡釋和瑪利亞神跡故事講述方面推進了瑪利亞崇拜的進程(Ihnat, 2016:16-137)。高厄遵循文學傳統和時代信仰,采用不同頭銜(母親、童貞女、謙卑的創造物)或物體(百合花、清泉、橄欖樹、海洋之星、明月、無刺的玫瑰、鳳仙花的香味、沒藥)贊美圣母。他強調圣母身心純潔,暗示她身上具備其他人沒有的美德。達納韋認為,高厄書寫圣母的生平和展示她的歡喜與悲痛的目的就是進行教導,以矯正“罪惡”(Donavin,2012:36-45)。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罪惡”女士竭力行惡,企圖把人帶入地獄,而圣母以美德感召信徒,以使人類得以獲得救贖。顯然,高厄倡導人們放棄一切導致罪惡的行為,追求富有美德和更高境界的精神生活,借此表達對美好、純潔的社會秩序和精神家園的向往和建立一種完整有序的社會的道德愿景。這從他對魔鬼家族和上帝之家的布局的對稱性上也可見一斑。
值得注意的是,高厄沒有忘記目標讀者和聽眾,他在寫作中把瑪利亞崇拜和中世紀典雅愛情糅合在一起,具備世俗化特點。他指出,圣母有女性的溫柔之心,頭戴高貴王冠,成為神圣宮廷的統治者,獲得無數榮譽。他對基督和圣母性別角色進行交替書寫,這增強了他們形象的世俗化特點。基督富有騎士的所有美德,他貼心、強壯、富有、英俊、禮貌、慷慨,在相貌、品德和財富方面無人比肩,天堂、大地、海洋和天空都屬于他,他打敗了死亡并摧毀了地獄之門,查理曼大帝都無法與他媲美。高厄認為這樣的勇士值得被愛和回報,沒有哪位女皇有這么富有的情人,“您(圣母)的情人比任何人/都彬彬有禮;/因為他在宮廷長大,/那里任何壞人或邪惡之人不曾進入。”(29487-29491行)顯然,高厄強調圣母和基督出身貴族,完美無瑕,富有美德。伯恩利指出,基督以騎士和靈魂的情人的形象第一次出現在13世紀隱修讀物《修女指南》(AncrenRiwle)之中,但這主要在抒情詩中得到充分發掘。因為宗教體驗和典雅愛情有著相似的心理基礎,即以儒雅之心為特征,而這種溫柔情感也是情感虔誠的基礎(Burnley, 1998:186)。在一些盎格魯-諾曼語抒情詩中,基督就以靈魂的戀人或以出身高貴、英俊無比且溫文爾雅的情人的形象出現。14世紀早期的盎格魯-諾曼語詩人尼克拉斯·鮑宗(Nicholas Bozon)在展示基督身上具備的騎士精神時把他比作勇敢無畏的騎士。可見,高厄身處文學傳統,把瑪利亞崇拜和典雅愛情結合起來,使她既顯得神圣,又沒有脫離中世紀宮廷文化對理想女性形象的期待視野,使基督的形象和騎士文學或抒情詩中的男主角相似。對于貴族聽眾或讀者來說,這更能讓他們產生心理共鳴和身份認同。對于旨在說教的高厄來說,這自然有助于達到訓誡、布道、共情的作用和目的。
高厄的說教與訓誡和14世紀的文化語境密不可分。科爾曼指出,14世紀的經院哲學關注個人道德和天堂回報的關系,這個話題波及具備識字能力且更關注個人救贖的大眾那里,明顯地出現在以喬叟、蘭格倫、高厄和“高文”詩人為代表的文學黃金期,說教文學從神學、政治和倫理方面教育大眾。他們采用人物歷史化手法,但這些人物也是14世紀語境下活生生的人(Coleman, 1981:15-16)。正如喬叟翻譯的短詩《圣母的禱告詞》(AnABC)具有同樣的訴求一樣,處于這種語境下的高厄的寫作自然具有現實主義色彩和說教目的,而詩歌結尾的禱告詞也表明了他做出的道德選擇。顯然,他以自我反思為基礎,以富有美德的“百合花之根”的圣母形象呼吁建立純凈、和諧和有序的社會風氣,希冀美德戰勝破壞秩序的各種罪惡行為。
4 結語
高厄在寫作中既遵循中世紀文化語境下的文學書寫模式,同時又在借鑒的基礎上有所創新。《人類之鏡》在擬人化寓言中從理論層面探討善惡世界的博弈,又深入再現社會各階層有違于道德準則的罪惡行為,以純潔的神圣家庭成員故事結尾。高厄結合自身經歷緊緊把握時代脈搏,在道德關注中敏銳地捕捉到社會問題并進行揭露,挖掘罪惡根源所在,在說教中由己及人,指出美德具備的積極作用。在14世紀70年代英國面臨內憂外患的狀況下,他以“繪畫者”和“道德審判者”的角色出現,在控訴現狀和表達希冀之余,揭露英國社會潛藏的運行模式,在詩歌創作中起到說教和糾錯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