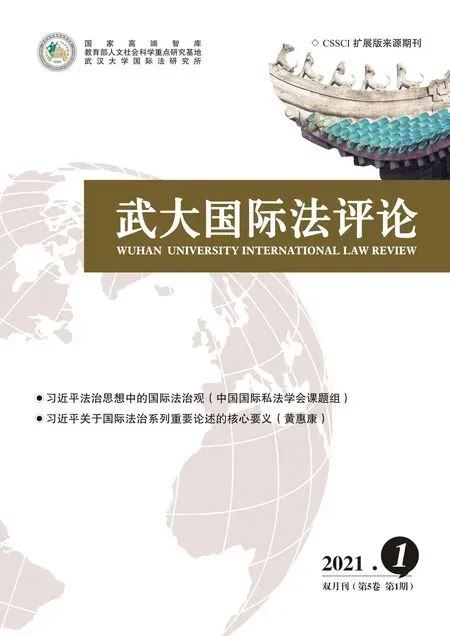歐盟投資法院裁決執行規定的合法性問題
連俊雅
近年來,以專設仲裁制度為核心的投資者與國家間爭端解決機制(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以下稱“ISDS 機制”)在運行中逐漸暴露出諸多問題,如仲裁裁決缺乏一致性和糾錯機制,仲裁員缺乏獨立性、公正性和多元性,仲裁程序過于昂貴和冗長以及第三方資助導致當事人權利的不平衡等。①See UNCITRAL, Possible Reform of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Submission from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LTD/V19/073/86/PDF/V1907386.pdf?OpenElement, visited on 4 December 2020.這些問題導致ISDS 機制遭遇合法性危機。在此背景下,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以下稱“UNCITRAL”)于2017 年成立第三工作組推動以國家為主導的ISDS 機制改革。建立投資仲裁上訴機制已成為ISDS 機制改革的核心內容,但建立何種上訴機制以及如何建設上訴機制成為焦點問題。其中,我國主張建立常設投資仲裁上訴機構,①See UNCITRAL, Possible Reform of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Submission from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LTD/V19/073/86/PDF/V1907386.pdf?OpenElement, visited on 4 December 2020.而歐盟建議建立包含初審法庭和上訴法庭的常設投資法院機制以取代國際投資仲裁機制。②See UNCITRAL, Possible Reform of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Submission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ts Member States,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LTD/V19/004/19/PDF/V1900419.pdf?OpenElement, visited on 4 December 2020.在歐盟的強力推動下,一些國際投資協定已納入該機制,并排除了東道國國內法院、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以下稱“ICSID”)和專設投資仲裁庭的救濟。目前,歐盟正不遺余力地將該機制推廣至其正在談判的其他投資協定中,包括中國—歐盟雙邊投資協定。③參見黃世席:《歐盟國際投資法庭制度的緣起與因應》,《法商研究》2016年第4期,第162頁。歐盟設立投資法院機制的目的在于取代國際投資仲裁機制,但這導致其裁決能否依據現有的投資仲裁裁決執行機制存在爭議。國際投資仲裁機制在過去60 年間取得成功的核心在于投資仲裁裁決可依據《解決國家與他國國民間投資爭議公約》(以下稱《華盛頓公約》)和《承認及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以下稱《紐約公約》)實現在全球范圍內的自由流動。因此,投資法院機制要取代投資仲裁機制就必須解決投資法院裁決④為便于與投資仲裁裁決和法院判決相區分,本文將投資法院作出的爭端解決結果稱為“投資法院裁決”。的執行問題。為解決執行困境,歐盟在部分國際投資協定中規定投資法院裁決屬于《華盛頓公約》和《紐約公約》下的投資仲裁裁決,但其合法性問題已引起國內外學者的熱切關注。然而,僅有個別國內學者對投資仲裁裁決可否依據這兩個公約獲得執行問題進行了簡單分析,并未探討歐盟相關投資協定規定的合法性問題,也未涉及歐盟倡導的投資法院裁決專門執行機制。⑤參見秦曉靜:《歐盟投資法院機制的不確定性及我國的應對策略》,《山東社會科學》2020年第1期;黃世席:《歐盟國際投資法庭制度的緣起與因應》,《法商研究》2016年第4期。
為此,本文首先分析歐盟投資法院裁決的性質和歐盟對投資法院裁決執行路徑的設計,然后重點討論投資法院裁決依據《華盛頓公約》和《紐約公約》執行的規定的合法性問題,最后分析歐盟關于建立專門投資法院裁決機制倡議的可行性并提出我國的應對建議。
一、歐盟對投資法院裁決執行路徑的設計
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早在2013 年就提出建立一個常設投資仲裁法院的設想。①參見黃世席:《歐盟國際投資法庭制度的緣起與因應》,《法商研究》2016年第4期,第164頁。歐盟在《里斯本條約》于2009 年12 月生效后獲得國際投資協定的締結權,②參見肖軍:《歐盟TTIP 建議中的常設投資法院制度評析》,《武大國際法評論》2016年第2期,第453頁。并于2011 年開始考慮將這一設想付諸實踐。歐盟及其成員國認為ISDS機制存在的問題是相互關聯且呈系統性的,通過單一的、碎片化的改革方案無法全面解決,但常設投資法院機制可一并解決上述問題。③See UNCITRAL, Possible Reform of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Submission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ts Member States,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LTD/V19/004/19/PDF/V1900419.pdf?OpenElement, visited on 4 December 2020.為回應歐洲議會對ISDS 機制的批評和貫徹歐盟關于國家規制權與投資保護之間平衡的投資政策,④參見王少棠:《合法性危機的解除?歐盟投資爭端解決機制改革再議》,《法商研究》2018年第2期,第164頁。歐盟委員會于2015 年11 月首次將投資法院機制納入《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伙伴協議》(以下稱“TTIP 協定”)的投資章節。隨后,歐盟將該機制適用于其商簽的一系列國際投資協定中,如《歐盟—加拿大全面經濟和貿易協定》(以下稱“CETA”)、《歐盟—越南自由貿易協定》《歐盟—越南投資保護協定》(以下稱“歐盟—越南IPA”)、《歐盟—新加坡投資保護協定》(以下稱“歐盟—新加坡IPA”)以及《歐盟—墨西哥全面經濟伙伴協定》。目前,這些投資協定有待歐洲議會和歐盟成員國的批準,尚未生效。⑤參見秦曉靜:《歐盟投資法院機制的不確定性及我國的應對策略》,《山東社會科學》2020年第1期,第182頁。2018 年3 月20 日,歐盟對外公布了《制定一個建立解決投資爭端的投資法院國際公約的協商指令》(以下稱《投資法院國際公約協商指令》)⑥See EU, Negotiating Directives for a Convention Establishing a Multilateral Court for the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https://data.consilium.europa.eu/doc/document/ST-12981-2017-ADD-1-DCL-1/en/pdf, visited on 4 December 2020.,允許締約國選擇性加入,將投資法院機制從雙邊層面推向多邊層面。2019 年1 月,歐盟正式向UNCITRAL 第三工作組提交建設多邊常設投資法院機制的具體建議。⑦See UNCITRAL, Possible Reform of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SDS):Note by the Secretariat,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LTD/V19/081/95/PDF/V1908195.pdf?OpenElement, visited on 4 December 2020.目前,歐盟關于投資法院機制的建設已經較為完善。
(一)投資法院裁決的性質
投資法院屬于常設爭端解決機構,共有兩個審級,包括初審法庭和上訴法庭,并由全職裁判員組成。初審法庭與一般投資仲裁庭的功能相同,負責查明事實、正確適用法律①適用的法律為國際法而非某一國的國內法。并審理上訴法庭駁回的案件。②See UNCITRAL, Possible Reform of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Submission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ts Member States,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LTD/V19/004/19/PDF/V1900419.pdf?OpenElement, visited on 4 December 2020.上訴法庭受理當事人以法律適用錯誤或嚴重的事實認定錯誤為由對初審裁決提起的上訴案件,但不對案件事實進行全面的審理。③See UNCITRAL, Possible Reform of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Submission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ts Member States,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LTD/V19/004/19/PDF/V1900419.pdf?OpenElement, visited on 4 December 2020.投資法院的初審法庭和上訴法庭均由國際投資協定締約國聘任的全職裁判員組成,且這些裁判員有固定的任職期限和薪酬。④See UNCITRAL, Possible Reform of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Submission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ts Member States,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LTD/V19/004/19/PDF/V1900419.pdf?OpenElement, visited on 4 December 2020.裁判員不僅應具有較高的道德品質,還應具備其他國際法院法官的專業能力,尤其是具有國際投資法知識、國際貿易法以及國際投資或貿易爭端解決的專業知識。⑤See UNCITRAL, Possible Reform of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Submission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ts Member States,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LTD/V19/004/19/PDF/V1900419.pdf?OpenElement, visited on 4 December 2020.在初審階段,投資法庭主席從九名全職裁判員中隨機選出三名組成審判法庭,但須確保這三名裁判員分別來自東道國、投資者母國和第三國,如歐盟—新加坡IPA第3.38.6條和第3.38.7條即如此規定。類似地,在上訴階段,上訴法庭主席從六名全職裁判員中隨機選出三名裁判員組成審查法庭。可見,無論是在初審階段還是在上訴階段,投資爭端方均沒有選擇裁判員的權利。此外,投資法院裁決具有終局性,締約國應像執行本國法院判決那樣執行該裁決且不得對其進行上訴、審查、撤銷或其他救濟,如歐盟—新加坡IPA 第3.57 條即如此規定。因此,投資法院裁決是由常設投資法院的全職裁判者依據國際法⑥包括國際投資協定、國際法以及國際法律原則,如歐盟—墨西哥FTA 投資章節第15.2條規定,投資法院作出裁決的依據為本投資協定以及適用于當事人的其他國際法規定和法律原則。作出的裁決,與某一具體國家的法律或領土無關,不具有國籍。那么,投資法院裁決是屬于法院判決還是國際投資仲裁裁決?
投資法院的性質直接決定其裁決的執行路徑。然而,投資法院的屬性兼具法院和仲裁機構的二元特征,即既具備國際法院的特征,如采用上訴機制、全職裁判員、當事人不得選任裁判者,又具備國際投資仲裁庭的特征,如采用投資仲裁規則作為程序規則、允許當事人選擇仲裁規則。值得注意的是,歐盟起初強調投資法院的司法特征,但隨后逐漸弱化該特征并凸顯其仲裁特征。具體而言,歐盟早在2015 年的TTIP 協定文本草案中使用“投資法院”(investment court)和“法官”(judges)。①See European Union, Draft Proposal for Investment Protection and Resolution of Investment Disputes,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15/november/tradoc_153955.pdf, vis ited on 4 December 2020.但歐盟在隨后的《投資法院國際公約協商指令》以及其與加拿大、新加坡、越南和墨西哥商簽的國際投資協定以及向UNCITRAL 第三工作組提交的建議案②See UNCITRAL, Possible Reform of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Submission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ts Member States,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LTD/V19/004/19/PDF/V1900419.pdf?OpenElement, visited on 4 December 2020.中不再使用“法官”(judges)一詞,而是使用“仲裁庭成員”(members),并規定投資法院裁決等同于針對商事爭議作出的仲裁裁決,如歐盟—新加坡IPA 第3.57 條即如此規定。歐盟強調投資法院具備仲裁機構特征的主要目的在于希望依據現有的國際投資仲裁裁決機制來確保投資法院裁決的執行。③See Zareen Qayyum, The Enforceability of Proposed Reforms to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CSID Review 8 (2020), https://doi.org/10.1093/icsidreview/siaa016, visited on 4 December 2020.歐盟近期商簽的國際投資協定就直接明確了上述目的。例如,TTIP 協定投資章節第30.6 條、CETA 投資章節第8.41 條、歐盟—新加坡IPA 第3.22 條、歐盟—越南IPA 第3.57條、歐盟—墨西哥FTA 投資章節第31 條均規定,為了實現通過《紐約公約》執行的目的,投資法院裁決應被視為針對商事爭議作出的仲裁裁決。因此,投資法院的二元屬性使其執行問題涉及復雜的法律問題。
(二)歐盟設計的三種執行路徑
對于投資法院裁決的執行,歐盟設計了外國法院判決執行機制、國際投資仲裁裁決執行機制、專門的國際投資法院裁決執行機制三種路徑。其中,對于依據外國法院判決執行機制執行的路徑,2019 年《承認與執行外國民商事判決公約》(以下稱《海牙判決公約》)曾為投資法院裁決的執行提供了法律可能性。歐盟曾于2017年2月率先提出要在《海牙判決公約》草案中引入共同法院,以期歐盟境內的共同法院判決能夠依據該公約在歐盟成員國以外的國家得到執行。盡管各國關于共同法院的討論均立足于現有的共同法院④據我國學者統計,世界范圍內存在八個符合共同法院的國際法院或超國家法院,包括非洲商法協調組織內設的司法與仲裁共同法院、安第斯共同體法院、歐洲聯盟法院、樞密院司法委員會、加勒比海法院、東加勒比海最高法院、比荷盧法院和統一專利法院。參見錢振球:《〈海牙判決公約草案〉中共同法院條款研究》,《武大國際法評論》2019年第1期,第62頁。,但并不排除未來設立的共同法院,尤其是歐盟倡導的常設投資法院。①參見錢振球:《〈海牙判決公約草案〉中共同法院條款研究》,《武大國際法評論》2019年第1期,第70頁。實際上,投資法院不屬于某一國家國內的法院,具備國際法院的要素,如基于國家間簽訂的國際條約而設立、永久性的機構、獨立的法官、涉國家爭端的解決以及裁決具備的拘束力。因此,投資法院符合2017 年《海牙判決公約》草案第22 條第1 款關于共同法院的規定。該提議得到美國、瑞士、澳大利亞等國家的支持,但遭到尚未有共同法院的國家的反對,如中國、俄羅斯、以色利和日本。最終,由于共同法院規則涉及面過廣且各國間分歧過大,2019年7月2日由海牙國際私法會議通過的《海牙判決公約》最終文本中未對共同法院進行規定,將共同法院判決的執行問題交由締約國自由裁量。②參見張春良、黃姍:《論海牙判決公約視閾下的共同法院規則——兼論“一帶一路”倡議下司法協助的中國進路》,《河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20年第5期,第110頁。在缺乏公約明確規定的情況下,投資法院裁決難以在歐盟成員國以外的國家得到執行。這也導致歐盟放棄通過《海牙判決公約》執行投資法院裁決,轉向國際投資仲裁裁決執行路徑。
歐盟在向UNCITRAL 提交的建議案中指出投資法院裁決的三個執行路徑,即依據專門的投資法院裁決執行機制執行、依據《華盛頓公約》執行和依據《紐約公約》執行。③See UNCITRAL, Possible Reform of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Submission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ts Member States,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LTD/V19/004/19/PDF/V1900419.pdf?OpenElement, visited on 4 December 2020.首先,歐盟意在建立專門的投資法院裁決執行機制。考慮到投資法院機制與投資仲裁機制的較大差異性以及《華盛頓公約》在促進ICSID 仲裁裁決執行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設立專門的投資法院裁決執行機制能夠切實解決投資法院裁決的執行問題。為此,歐盟在《投資法院國際公約協商指令》中指出要制定一個關于投資法院的國際公約(以下稱“投資法院國際公約”),并在該公約中建立投資法院裁決執行機制。④See UNCITRAL, Possible Reform of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Submission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ts Member States,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LTD/V19/004/19/PDF/V1900419.pdf?OpenElement, visited on 4 December 2020.另外,鑒于上訴法庭可以法律適用錯誤和事實認定存在重大錯誤為由對投資法院裁決進行審查,歐盟主張投資法院裁決在執行階段不應再進行審查,并強調排除撤銷機制的適用。⑤See UNCITRAL, Possible Reform of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Submission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ts Member States,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LTD/V19/004/19/PDF/V1900419.pdf?OpenElement, visited on 4 December 2020.因此,該專門執行機制將比《華盛頓公約》下的執行機制更具強制性。其次,歐盟提出將《紐約公約》作為上述執行機制的重要補充,以促進投資法院裁決在第三國的執行。①See UNCITRAL, Possible Reform of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Submission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ts Member States,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LTD/V19/004/19/PDF/V1900419.pdf?OpenElement, visited on 4 December 2020.歐盟主張“投資法院國際公約”將采用與《聯合國投資人與國家間基于條約仲裁透明度公約》類似的“選擇加入”模式,②See UNCITRAL, Possible Reform of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Submission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ts Member States,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LTD/V19/004/19/PDF/V1900419.pdf?OpenElement, visited on 4 December 2020.即一國可通過加入“投資法院國際公約”的方式將投資爭端提交投資法院管轄,并在國際投資協定中聲明與其相關的投資爭端可提交投資法院。③See Zareen Qayyum, The Enforceability of Proposed Reforms to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CSID Review 7 (2020), https://doi.org/10.1093/icsidreview/siaa016, visited on 4 December 2020.然而,考慮到短時間內不會有太多國家加入“投資法院國際公約”從而使投資法院裁決無法在廣大第三國執行的情況,歐盟主張利用《紐約公約》來滿足投資法院裁決在第三國執行的需求。再次,歐盟還主張投資法院依據《華盛頓公約》的仲裁規則作出的裁決屬于ICSID 仲裁裁決,可直接依據該公約得到執行。由于《華盛頓公約》的投資仲裁裁決執行機制近乎自動執行機制,所以投資法院裁決依據該公約能夠得到強有力的執行。
在專門的投資法院裁決執行機制建立前,歐盟希望利用現有的國際投資仲裁裁決執行機制來執行投資法院裁決。目前,歐盟已將后兩個執行路徑在其商簽的國際投資協定(以下稱“歐盟投資法院投資協定”)中進行了規定,如TTIP 協定中投資章節第30.6 條、CETA 投資章節第8.41 條、歐盟—新加坡IPA 第3.22 條、歐盟—越南IPA第3.57條、歐盟—墨西哥FTA投資章節第31條的規定。④這些規定內容基本相同,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投資法院的終局裁決對當事人具有拘束力,不得再進行上訴、司法審查、撤銷或其他形式的救濟;(2)各方當事人應像承認和執行本國終審法院裁決那樣執行投資法院裁決;(3)投資法院裁決的執行所適用的法律為執行地的法律;(4)其他章節中關于自然人或法人的權利義務的規定不得妨礙投資法院裁決的承認和執行;(5)投資法院裁決應被視為針對商事爭議作出的仲裁裁決;(6)依據《華盛頓公約》中仲裁規則作出的裁決應被視為該公約第四章第六節中的仲裁裁決。然而,上述規定實質上構成對《華盛頓公約》和《紐約公約》的修改,并將給這些公約的其他締約國帶來額外的義務,⑤參見秦曉靜:《歐盟投資法院機制的不確定性及我國的應對策略》,《山東社會科學》2020年第1期,第184頁。存在合法性問題。
二、依《華盛頓公約》執行的規定的合法性問題
1966 年《華盛頓公約》是在世界銀行倡導下締結的一項多邊條約。依據該公約設立的ICSID 已成為解決投資者與國家間投資爭端的最具影響力的國際性機構。ICSID為每個在ICSID登記的投資爭端案件組建臨時性調解委員會或仲裁庭提供制度性和程序性框架。①ICSID 行政理事會對《華盛頓公約》的基本程序框架進行了補充,制定了詳細的規章和規則,如《世界銀行執行董事會關于ICSID 公約的報告》《行政和財務規章》《關于發起調解和仲裁程序的程序規則》《關于調解程序的程序規則》。參見左海聰主編:《國際經濟法》,武漢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54-55頁。然而,由于歐盟自身尚不是《華盛頓公約》的成員,歐盟無法成為ICSID 仲裁程序中的適格被申請人,且針對其作出的投資法院裁決也無法依據《華盛頓公約》予以執行。②參見秦曉靜:《歐盟投資法院機制的不確定性及我國的應對策略》,《山東社會科學》2020年第1期,第184頁。因此,本部分只討論涉及歐盟成員國的投資法院裁決的執行問題。
(一)歐盟投資法院投資協定對《華盛頓公約》的修改
針對ICSID 受理的國際投資爭端案件作出的仲裁裁決分為ICSID 仲裁裁決③截至2019 年年底,在ICSID 登記的案件中,667 個案件以ICSID 仲裁裁決方式解決,占比高達89.5%。See ICSID, The ICSID Caseload—Statistics (Issue 2020-1), https://icsid.worldbank.org/en/Documents/resources/The% 20ICSID% 20Caseload% 20Statistics% 202020-1%20Edition-ENG.pdf, visited on 4 December 2020.和非ICSID仲裁裁決④依據其他仲裁規則,如《ICSID 附加便利規則》《UNCITRAL 仲裁規則》《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仲裁規則》《香港國際仲裁院仲裁規則》作出的投資仲裁裁決被稱為非ICSID仲裁裁決。此類仲裁裁決無法通過《華盛頓公約》得到執行,但在司法實踐中可通過《紐約公約》得到執行。。《華盛頓公約》第54條明確定,只有ICSID仲裁裁決才可依據該公約的執行機制得到執行。要成為ICSID 仲裁裁決就必須符合該公約關于仲裁庭的組成、仲裁程序規則、仲裁裁決的救濟等的規定。然而,投資法院裁決因其作出主體的獨特性和上訴機制的存在而難以被認定為ICSID 仲裁裁決。首先,《華盛頓公約》只適用于由ICSID 組建的臨時仲裁庭作出的仲裁裁決。而投資法院裁決是由常設投資法院作出的裁決,所以不屬于ICSID仲裁裁決。其次,ICSID仲裁裁決所依據的仲裁規則局限于《華盛頓公約》及ICSID 制定的《關于發起調解和仲裁程序的程序規則》。而投資法院裁決所依據的仲裁規則可由投資爭端當事人選擇,包括上述仲裁規則和其他仲裁規則。依據其他仲裁規則作出的投資法院裁決顯然不屬于ICSID 仲裁裁決。再次,《華盛頓公約》禁止對ICSID 仲裁裁決提起上訴或采取其他的救濟措施。然而,投資法院包含了上訴機制,能夠針對初審法庭裁決進行上訴,與《華盛頓公約》的規定不符。
為達到使投資法院裁決依據《華盛頓公約》得到執行的目的,歐盟投資法院投資協定對《華盛頓公約》進行了修改。具體而言,CETA 投資章節第8.41 條、歐盟—新加坡IPA 第13 章第3.22 條、歐盟—越南IPA 第3.57 條以及歐盟—墨西哥FTA投資章節第31 條規定,投資法院依據《華盛頓公約》的仲裁規則作出的裁決應被視為ICSID 仲裁裁決。這些規定在上述締約國間修改了《華盛頓公約》第54.1 條的規定。那么,此種修改是否符合《維也納條約法公約》①《維也納條約法公約》于1969年5月23日開放簽署,并于1980年1月27日生效。第41 條的規定仍值得探討。
(二)修改《華盛頓公約》的規定不合法
《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41.1 條允許國際公約的部分締約國對該公約進行修改,只要此種修改不被該公約所禁止。第41.1條規定:“多邊條約兩個以上當事國得于下列情形下締結協定僅在彼此間修改條約:(甲)條約規定有作此種修改之可能者;或(乙)有關之修改非為條約所禁止,且:(一)不影響其他當事國享有條約上之權利或履行其義務者;(二)不關涉任何如予損抑即與有效實行整個條約之目的及宗旨不合之規定者。”盡管《維也納條約法公約》并不適用于早于其生效的《華盛頓公約》,但大多數學者認為《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41 條中所包含的修改條約的法律原則已成為習慣國際法。②See August Reinisch, Will the EU’s Proposal Concerning an Investment Court System for CETA and TTIP Lead to Enforceable Awards? 19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772 (2016).因此,第41 條的規定仍可用于解決締約國之間對《華盛頓公約》進行的修改是否合法的問題。③See Calamita N. Jansen, The (In)Compatibility of Appellate Mechanisms with Existing Instruments of the Investment Treaty Regime, 18 Journal of World Investment &Trade 606 (2017).然而,《華盛頓公約》未明確規定締約國可對其進行修改。④See August Reinisch, Will the EU’s Proposal Concerning an Investment Court System for CETA and TTIP Lead to Enforceable Awards? 19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772 (2016).需要探討的問題是歐盟投資法院投資協定對《華盛頓公約》所作的修改是否被《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41.1.2 條所禁止。在國際法實踐中,依據《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41.1.2 條對國際公約成功修改的案例很少,所以可從文義上對該條進行理解。⑤See Calamita N. Jansen, The (In)Compatibility of Appellate Mechanisms with Existing Instruments of the Investment Treaty Regime, 18 Journal of World Investment &Trade 609 (2017).目前,學者們對《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41.1.2 條中的“禁止”一詞存在不同的理解。有觀點認為,該條只適用于國際條約中“明文禁止”的情形。⑥See Zareen Qayyum, The Enforceability of Proposed Reforms to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CSID Review 11 (2020), https://doi.org/10.1093/icsidreview/siaa016, visited on 4 December 2020.還有觀點認為,《維也納條約法公約》刪除了起草文本中“明文或默示禁止”的用語,所以從《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41.1.2 條中可得出“默示禁止”的結論。①See Brian McGarry & Josef Osansky, Is the Law of Treaties an Obstacle or a Conduit for the Reform of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32 Emory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1009 (2017).然而,上述兩種理解均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未結合第41.1.2 條整個條文進行解釋。基于該條的文義理解,對國際公約所作的修改不僅不應被該公約所禁止,還不得產生兩種法律后果,包括影響其他締約國享有的在此條約上的權利或義務和違反該條約的目的和宗旨。由此可推斷出,若對第41.1.2 條作狹義理解,認為其僅適用于國際公約明文禁止修改的情形,那么締約國對國際條約的修改即使不違反明文禁止的規定,也可能產生減損其他締約國在此公約上的權利或增加其他締約國的相關義務,或者違反該公約的目的和宗旨的法律后果。若對第41.1.2 條作廣義理解,認為其適用于該公約所默示禁止修改的情形,那么締約國違反默示禁止修改的情形通常也產生了所禁止的上述兩種法律后果。因此,采用“默示禁止”的標準來衡量歐盟投資法院投資協定是否違反《華盛頓公約》第41.1.2條的規定較為合適。
首先,歐盟投資法院投資協定對《華盛頓公約》的修改違反了該公約默示規定的情形。盡管《華盛頓公約》未明確規定其締約國可對其進行修改,但《華盛頓公約》第53.1 條規定,ICSID 仲裁裁決不應受上訴機制的審查。歐盟投資法院投資協定規定投資法院裁決等同于ICSID 仲裁裁決,但其設有針對投資法院裁決的上訴機制。這意味著存在針對ICSID 仲裁裁決的上訴救濟方式,且這種救濟是在ICSID 之外進行的。因此,此種修改產生了對《華盛頓公約》整體修改的法律后果,屬于該公約所禁止的情形。其次,歐盟投資法院投資協定對《華盛頓公約》的修改與該公約的目標和宗旨不符。《華盛頓公約》第1.2 條體現了該公約的目的和宗旨,即由ICSID 依據本公約的規定為一締約國和另一締約國國民之間調解和仲裁投資爭端提供便利。這意味著由ICSID 管理的投資調解和仲裁程序必須符合《華盛頓公約》的條文規定,例如采用專設仲裁形式、一審終審制、當事人指定仲裁員的權利以及禁止對ICSID 仲裁裁決提起上訴等。然而,歐盟投資法院投資協定中的投資法院并不屬于ICSID 組建的仲裁庭,采用兩審終審制,聘任常設裁判員并排除當事人選擇裁判員的權利以及設立上訴法庭。因此,歐盟投資法院投資協定中關于投資法院裁決屬于ICSID 仲裁裁決的規定,也與《華盛頓公約》的目標和宗旨不相符,違反了《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41.1.2條的規定。
總體而言,盡管《華盛頓公約》的執行機制有助于投資法院裁決得到便捷、高效地執行,但該公約的執行機制具有較強的閉合性。歐盟投資法院投資協定關于投資法院的裁決等同于ICSID 仲裁裁決的規定構成對《華盛頓公約》的修改。盡管《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41.1條允許《華盛頓公約》締約國間對該公約進行修改,但歐盟投資法院投資協定對《華盛頓公約》的修改違反了該公約的默示規定,并產生了違反該公約目的和宗旨的法律后果,屬于《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41.1.2條所禁止修改的情形。因此,CETA投資章節第8.41條、歐盟—新加坡IPA第13章第3.22條、歐盟—越南IPA第3.57條以及歐盟—墨西哥FTA投資章節第31條規定均存在不合法的法律問題,難以實現投資法院裁決依據《華盛頓公約》在第三國執行的目的。
三、依《紐約公約》執行的規定的合法性問題
《紐約公約》是由UNCITRAL 于1958 年制定的,其目的在于為國際商事仲裁裁決的執行提供國際法框架。截至目前,《紐約公約》已有166 個締約方,①UNCITRAL, Contracting States of New York Convention, http://www.newyorkconvention.org/list+of+contracting+states, visited on 4 December 2020.在促進國際商事仲裁裁決在全球范圍內的自由流動上取得重大成功。該公約只適用于國際商事爭議,但《UNCITRAL 國際商事仲裁示范法》(1985 年)對“商事”的定義作廣義理解,將投資也包含在內。即使投資爭端涉及主權國家的立法或規制行為,也仍被認為屬于《紐約公約》下的“商事爭議”。例如,不少國際投資協定明確規定其協定下的投資爭端屬于商事爭議,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第1136.7 條和《能源憲章條約》第26.5.2 條。另外,司法實踐也表明針對投資爭端作出的仲裁裁決可通過《紐約公約》執行,且《紐約公約》締約國作出的“商事”保留也不構成投資仲裁裁決執行的障礙。②See Bungenberg Marc & Reinisch August, From Bilateral Arbitral Tribunals and Investment Courts to a Multilateral Investment Court 162-163 (Springer Nature Switzerland AG 2018).
投資法院裁決能否通過《紐約公約》得到執行?有學者認為,盡管投資法院使用“法院”一詞且具備一些司法性特征,但投資法院主要采用仲裁形式,其裁決可通過《紐約公約》執行。③See August Reinisch, Will the EU’s Proposal Concerning an Investment Court System for CETA and TTIP Lead to Enforceable Awards? 19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783 (2016).歐盟向UNCITRAL 第三工作組提交的建議案中主張投資法院裁決屬于《紐約公約》第1.2 條中由常設仲裁機構作出的仲裁裁決,所以可依據該公約得到執行。④See UNCITRAL, Possible Reform of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Submission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ts Member States,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LTD/V19/004/19/PDF/V1900419.pdf?OpenElement, visited on 4 December 2020.然而,上述關于《紐約公約》適用于投資法院裁決的討論均不夠深入,說理也不夠充分。盡管如此,歐盟投資法院投資協定直接規定投資法院裁決可通過《紐約公約》得到執行,如CETA 投資章節第8.41 條、歐盟—新加坡IPA 第13 章第3.22 條、歐盟—越南IPA 第3.57 條以及歐盟—墨西哥FTA 投資章節第31 條的規定。這些規定實際上對《紐約公約》作出了修改。這些修改是否合法以及能否在第三國得到執行?這涉及《紐約公約》相關條文的解釋問題。
按照《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31.1條的規定,《紐約公約》的解釋應按照該公約的目的和宗旨對該條約進行善意的文義解釋。另外,《紐約公約》賦予締約方在國際商事仲裁裁決承認和執行上很大的靈活性,所以締約方國內法院適用該公約的司法實踐也屬于《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31.3 條規定的情形。研究締約方的司法實踐對判斷投資法院裁決是否屬于《紐約公約》下的仲裁裁決和投資法院裁決能否在這些國家得到執行十分重要。此外,《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32 條規定,可依據《紐約公約》的起草文件、談判記錄等輔助材料來解釋該公約。本部分結合《紐約公約》的條文規定分析投資法院裁決是否符合《紐約公約》的規定,從而判斷歐盟投資法院投資協定規定的合法性問題。
(一)不違反《紐約公約》規定之處
首先,投資法院裁判庭的組成不違反《紐約公約》中仲裁庭組成的規定。《紐約公約》第5.1.4 條要求其組成必須符合當事人之間的協議。那么,由初審法庭或上訴法庭的主席從全職裁判員中隨機選取三名組成裁判庭而非由投資爭端當事人選擇的裁判員組成裁判庭,是否符合《紐約公約》的要求?實際上,第5.1.4 條并未要求仲裁庭必須由當事人指定的仲裁員組成,只要仲裁庭的組成不違反當事人的協議即可。投資爭端當事人選擇將投資爭端提交投資法院解決,意味著其同意未來投資法院裁判庭的組成。另外,類似的司法實踐表明,裁判庭組成過程中排除投資爭端當事人選擇裁判員的權利通常不構成違反《紐約公約》的規定。例如,在Iran v. Gould 案①See Ministry of Defense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v. Gould Inc., 887 F.2d 1357 (9th Cir. 1989).和Dallal v. Bank Mellat 案②See Dallal v. Bank Mellat [1986] 2 WLR 745.中,盡管伊朗—美國索賠仲裁庭③美國—伊朗索賠仲裁庭是美國和伊朗兩國根據1981 年1 月19 日《阿爾及爾共識》設立的國際仲裁法庭,是為了解決與伊朗人質危機有關的索賠的專門常設國際性仲裁庭。該仲裁庭位于荷蘭海牙,設有九名“仲裁員”,伊朗任命三名,美國任命三名,其余三名由上述六名任命。其適用的規則是《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仲裁規則》。中的仲裁員是由締約國預先選定且投資爭端方無選擇的權利,但美國和英國法院認為該仲裁庭的組成仍符合《紐約公約》的規定并予以執行。另外,很多體育仲裁機構的仲裁規則不允許當事人指定仲裁員,如《國際籃聯仲裁機構仲裁規則》第8條規定仲裁員由仲裁庭主席從仲裁員名單中輪流隨機選定,但其作出的仲裁裁決仍通過《紐約公約》得到執行。①參見黃世席:《歐盟國際投資仲裁法庭制度的緣起與因應》,《法商研究》2016 年第4期,第169頁。我國大連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18 年8 月依據《紐約公約》承認和執行了國際體育仲裁院作出的仲裁裁決。②參見張春良:《國際體育仲裁院仲裁裁決在中國的承認與執行——基于我國承認與執行CAS裁決第一案的實證考察》,《天津體育學院學報》2019年第2期,第113頁。
其次,投資法院裁決滿足《紐約公約》中拘束力的要求。《紐約公約》第5.1.5 條規定,締約國法院有權在仲裁裁決未對當事人產生拘束力的條件下拒絕執行該裁決。由于投資法院存在上訴機構,投資法院裁決是否滿足《紐約公約》對“拘束力”的要求?有學者指出,當事人選擇仲裁程序就是源自對由中立第三方作出拘束力的裁決結果的期待,且投資法院是常設性的,采用兩審終審制,并聘任全職裁判員,具有準司法性質,所以其作出的裁決具有拘束力。③See Bungenberg Marc & Reinisch August, From Bilateral Arbitral Tribunals and Investment Courts to a Multilateral Investment Court 156-157 (Springer Nature Switzerland AG 2018).還有學者主張,仲裁裁決的拘束力與其終局性密切相關,即仲裁裁決的終局性使仲裁裁決立即具有拘束力。④See Zareen Qayyum, The Enforceability of Proposed Reforms to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CSID Review 18 (2020), https://doi.org/10.1093/icsidreview/siaa016, visited on 4 December 2020.例如,《UNCITRAL 仲裁規則》規定所有的仲裁裁決都應是終局的且對當事人具有拘束力,當事人應立即執行仲裁裁決。為明確投資法院裁決的拘束力,CETA 投資章節第8.41 條、歐盟—新加坡IPA 第3.22 條、歐盟—越南IPA 第3.57 條以及歐盟—墨西哥FTA 投資章節第31 條規定,在投資法院裁決作出后若無上訴情況則裁決作出90 日后具有拘束力,以及若提起上訴但被駁回或經上訴法庭審理后的裁決具有拘束力。這種規定可防止締約國法院以投資法院裁決不具有拘束力為由而拒絕執行。因此,《紐約公約》對仲裁裁決拘束力的要求并不會對投資法院裁決的執行產生障礙。
(二)違反《紐約公約》規定之處
首先,投資法院裁決不屬于《紐約公約》中的仲裁裁決。《紐約公約》第1.1條將其適用范圍限制在“仲裁裁決”。《紐約公約》及其配套的《UNCITRAL 國際商事仲裁示范法》均未對“仲裁裁決”的法律含義作出具體界定,但依據“仲裁裁決作出地”標準和“非內國裁決”標準將該公約的適用范圍限制在兩種仲裁裁決。⑤一種是外國仲裁裁決,即在申請承認和執行地國家之外的國家領土內作出的仲裁裁決。另一種是非內國裁決,即被申請承認和執行的國家不認為是國內裁決的仲裁裁決。參見楊弘磊:《中國內地司法實踐視角下的〈紐約公約〉問題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 年版,第82-83頁。這兩種類型的仲裁裁決均與仲裁裁決作出地存在法律聯系,也是多數《紐約公約》締約國進行司法審查的重點之一。①僅有極個別的締約國執行了與仲裁地沒有法律聯系的仲裁裁決,如Société Européenne d’Etudes et d’Entreprises (S.E.E.E.) v. République Socialiste Fédérale de Yougoslavie et autres, Case 982/82, Judgement of 1984.然而,投資法院裁決是依據國際法作出的裁決,與某一特定國家法律不存在聯系。可見,投資法院裁決屬于“浮動的裁決”,不屬于《紐約公約》下的兩類仲裁裁決。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在Iran v. Gould 案和Dallal v. Bank Mellat案中,美國和英國法院認為伊朗—美國索賠仲裁庭依據國際法作出的裁決可根據《紐約公約》得到執行,但均未對該裁決是否屬于浮動的裁決以及裁決地所在國荷蘭的法律是否適用的法律問題予以解決。目前,締約國法院關于“仲裁裁決”的司法實踐也未達成一致,所以作為浮動的裁決的投資法院裁決能否像伊朗—美國索賠仲裁庭的裁決那樣依據《紐約公約》執行,仍存在法律不確定性。因此,歐盟投資法院投資協定規定作為浮動的裁決的投資法院裁決屬于《紐約公約》下的仲裁裁決。這一規定擴大了該公約的適用范圍,違反了該公約的規定。
其次,投資法院裁決不符合《紐約公約》中提交仲裁的自愿性和合意的要求。《紐約公約》第2條和第5.1.1條規定,依據該公約執行的仲裁裁決必須是基于當事人自愿提交的書面仲裁協議而作出的仲裁裁決。其中,當事人提交仲裁的自愿性和合意對于有效仲裁協議的判斷至關重要。國際投資協定中的投資仲裁條款意味著東道國事先同意仲裁并在投資者提起仲裁申請時達成提交仲裁的合意。加之,傳統的國際投資協定為投資爭端方提供多種救濟路徑,包括友好磋商、調解、東道國的國內救濟、專設仲裁庭以及國際投資爭端解決機構的仲裁等,所以投資者提交投資仲裁是基于其自愿作出的決定。目前,司法實踐中關于條約投資仲裁滿足提交仲裁的自愿性和合意的要求基本不存在爭議,如Republic of Ecuador v. Chevron Corp 案②See Republic of Ecuador v. Chevron Corp, 638 F 3d 384 (2nd Cir. 2011).。然而,除了友好磋商和調解外,歐盟投資法院投資協定只允許投資爭端當事人將投資爭端提交投資法院,排除了東道國的國內救濟、專設仲裁庭以及其他國際投資爭端解決機構的救濟。這種強制將投資爭端提交投資法院的規定是否違反了《紐約公約》中提交仲裁的自愿性和合意要求?在Iran v.Gould 案和Dallal v. Bank Mellat 案中,《阿爾及爾共識》規定伊朗或美國的投資者只能向伊朗—美國索賠仲裁庭申請仲裁而不得訴諸國內法院,但美國和英國審理法院認為該機制仍滿足《紐約公約》對提交仲裁自愿性的要求。③See Bungenberg Marc & Reinisch August, From Bilateral Arbitral Tribunals and Investment Courts to a Multilateral Investment Court 155 (Springer Nature Switzerland AG 2018).考慮到伊朗—美國索賠仲裁庭與投資法院之間的重大差異,不少理論界和實務界人士認為歐盟投資法院投資協定的規定有損提交仲裁的自愿性,且這將成為依據《紐約公約》執行投資法院裁決最主要的法律障礙。①See G. Kaufmann-Kohler & M. Potestà, Can the Mauritius Convention Serve as a Model for the Reform of Investor-State Arbitration in Connection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a Permanent Investment Tribunal or an Appeal Mechanism?-Analysis and Roadmap, https://www.uncitral.org/pdf/english/ CIDS_Research_Paper_Mauritius.pdf, visited on 4 December 2020.因此,歐盟投資法院投資協定在滿足《紐約公約》關于有效仲裁協議的要求上存在一定的法律困境。
總體而言,《紐約公約》的執行機制具有較強的靈活性和一定的開放性,為投資法院裁決依據該公約得到執行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然而,作為“浮動的裁決”的投資法院裁決并不屬于《紐約公約》下的仲裁裁決和難以滿足提交仲裁的自愿性和合意的要求。因此,投資法院裁決依據《紐約公約》在歐盟投資法院投資協定締約國外的第三國執行存在合法性問題。
四、建立專門執行機制的可行性及我國的因應
自2003 年《歐洲安全戰略》開始,歐洲就積極推動“有效多邊主義”作為自身的戰略目標。②參見陳志敏、吉磊:《歐洲的國際秩序觀:“有效的多邊主義”?》,《復旦國際關系評論》2014年第1期,第165頁。在國際投資仲裁領域,歐盟一直積極維護自己的奠基人地位,③參見黃世席:《歐盟國際投資仲裁法庭制度的緣起與因應》,《法商研究》2016 年第4期,第165頁。積極引領此領域的改革。歐盟主導建立去仲裁化的多邊常設投資法院機制以取代國際投資仲裁機制。然而,為了解決制約投資法院機制有效運行的核心問題——投資法院裁決的執行,歐盟將投資法院裁決定性為投資仲裁裁決,以便利用《華盛頓公約》和《紐約公約》的仲裁裁決執行機制。鑒于投資法院機制的特殊性,要實現投資法院裁決在上述公約締約國執行的目的將不可避免地對上述兩個公約進行修訂。公約的修訂涉及一系列復雜的法律問題,其難度并不比制定一個新公約小。這也是歐盟倡導建立專門的投資法院裁決執行機制的主要原因。盡管歐盟當前積極追求依據《華盛頓公約》和《紐約公約》執行投資法院裁決,但建立專門的投資法院裁決執行機制才是歐盟的長遠之計。目前,歐盟尚未在投資法院國際公約中對該專門的機制作出具體的條文設計,但根據歐盟對該機制的設想以及歐盟投資法院投資協定的相關條文的分析,該專門機制與《華盛頓公約》下的執行機制相似,但因其排除了后者的撤銷機制將比后者具有更強的執行力。
(一)建立專門執行機制的可行性
投資法院裁決執行機制的建立與國際投資仲裁機制向公法方向發展的趨勢相契合。投資法院機制意在消除國際商事仲裁制度在解決投資者與東道國間爭端上的不足,注重對東道國公共利益的保護,實現投資者與東道國利益保護的平衡。①參見張慶麟:《歐盟投資者—國家爭端解決機制改革實踐評析》,《法商研究》2016 年第3期,第144頁。而ICSID 起初參照國際商事仲裁機制設計國際投資仲裁機制,存在理念上的錯位。具體而言,與ICSID 的預期不同,當前的國際投資仲裁案件主要依據國際投資協定而非國際投資合同提起。例如,ICSID 受理的絕大多數投資爭端案件主要依據雙邊投資協定提起,占比高達60%,而依據國際投資合同提起的僅占16%。②See ICSID, The ICSID Caseload—Statistics (Issue 2020-1), https://icsid.worldbank.org/en/Documents/resources/The% 20ICSID% 20Case-load% 20Statis-tics% 202020-1% 20Edition-ENG.pdf, visited on 4 December 2020.目前,國際投資仲裁機制的改革過程是一個不斷糾偏的過程,逐漸從私法領域向公法領域發展,并形成一個獨特的法律體系。③See Anthea Roberts, Clash of Paradigms: Actors and Analogies Shaping the Investment Treaty System, 107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49 (2013).例如,投資仲裁裁決的作出主體已不局限于專設仲裁庭,開始擴展至依據國際投資協定設立的常設投資爭端法院或仲裁庭;上訴機制開始嵌入投資仲裁裁決機制,打破一裁終局制度;投資仲裁裁決作出的法律依據為國際法而非某一特定國家的法律,且仲裁地和國籍的概念被弱化。在此背景下,根植于商事仲裁的《紐約公約》和《華盛頓公約》已經難以迎合國際投資仲裁機制的發展潮流。為此,歐盟提出在“投資法院國際公約”中設立一個專門的投資法院裁決執行機制。這個執行機制反映了國際投資仲裁機制的公法性質,順應了國際投資仲裁機制的發展趨勢。隨著歐盟與越來越多的國家簽署投資法院投資協定,專門的投資法院裁決執行機制的建設也將得到越來越多國家的支持,所以該機制具有可行性。可以預見,專門的投資法院裁決執行機制的建設將推動國際投資仲裁裁決執行機制的變革。
按照歐盟的設想,投資法院裁決執行機制的建立需要依托“投資法院國際公約”。目前,“投資法院國際公約”的制定尚處于萌芽階段。對于歐盟而言,其首要目標在于將投資法院機制納入其正在商談的所有國際投資協定中,再逐步制定一個多邊投資法院國際公約讓更多的國家加入從而實現在全球范圍內構建投資法院機制的目的,最后通過該公約所創設的專門的投資法院裁決執行機制來實現該裁決在全球的自由流動。因此,在短期內建立專門的投資法院裁決執行機制存在較大的法律難度。考慮到這個現實問題,歐盟決定先采用將投資法院裁決認定為仲裁裁決并依據《華盛頓公約》和《紐約公約》來執行的策略。作為這兩個公約的締約國,我國將面臨投資法院裁決在我國執行的問題。
(二)我國對投資法院裁決執行問題的因應
盡管我國不是歐盟投資法院投資協定的締約國,但仍存在投資法院裁決在我國執行的現實可能性。例如,上述投資協定締約國的投資者向我國申請執行針對上述國家的投資法院裁決,或上述締約國向我國申請執行針對上述投資者的投資法院裁決。目前,歐盟自身尚不是《紐約公約》和《華盛頓公約》的成員。我國在批準加入《紐約公約》時作出了互惠保留和商事保留,意味著我國只承認和執行在該公約締約方領土內作出的仲裁裁決和針對商事爭議作出的仲裁裁決。因此,根據互惠保留,我國有權拒絕執行針對歐盟作出的投資法院裁決,且根據商事保留,我國有權依據該公約拒絕執行所有的投資法院裁決。另外,如前文所述,由于針對歐盟作出的投資法院裁決無法依據《華盛頓公約》予以執行,所以我國有權依據《華盛頓公約》拒絕執行。但是,我國可能面臨涉歐盟成員國①波蘭不是《華盛頓公約》的締約國。、加拿大、新加坡、越南、墨西哥的投資法院裁決依據《華盛頓公約》在我國執行的問題。根據前文分析,歐盟投資法院投資協定關于投資法院裁決等同于ICSID 仲裁裁決的規定與《華盛頓公約》相沖突,存在合法性問題,所以我國可拒絕執行涉上述國家的投資法院裁決。
值得注意的是,歷時七年35 輪談判,我國于2020 年12 月30 日與歐盟完成了《中歐全面投資協定》的談判。然而,現有的協定尚未納入有關ISDS 機制的具體規定,而只是規定雙方有義務在該協定簽署后兩年內就投資爭端解決條款簽訂補充協定。究其原因在于,我國與歐盟在關于ISDS 機制的條款設計上存在較大的分歧。我國認為ISDS 機制是一個總體上值得維護的機制,倡導通過設立常設上訴機制、維護當事人指定仲裁員的權利、完善與仲裁員有關的規則、促進投資調解的使用、納入仲裁前磋商程序和制定第三方資助透明度規則來解決ISDS 機制中存在的問題。②See UNCITRAL, Possible Reform of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Submission from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LTD/V19/073/86/PDF/V1907386.pdf?OpenElement, visited on 4 December 2020.目前,我國已在個別國際投資協定中采用了投資仲裁上訴審查機制和仲裁員名單制度,如2015 年簽署的《中國—澳大利亞自由貿易協定》。可以預見,我國極有可能在《中歐全面投資協定》中保留ISDS機制。與此同時,投資法院機制已經成為歐盟簽署國際投資協定的“標配”。在歐盟對投資法院機制的強力推行下,該機制被納入《中歐全面投資協定》的投資爭端解決條款中也具有極大的可能性。我國既應認識到投資法院機制整體上能夠有效彌補ISDS機制的諸多缺陷,③參見鄧婷婷:《歐盟多邊投資法院:動因、可行性及挑戰》,《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4期,第68頁。也要注意投資法院機制存在的諸多問題,如上訴法庭成員的選拔方式不明確、法官薪酬過低、上訴范圍與發回重審范圍界限模糊等。①參見汪梅清、吳嵐:《歐盟主導的投資法庭上訴機制及其對中歐投資爭端解決機制的借鑒意義》,《國際商務研究》2019年第6期,第71頁。由此可推測,《中歐全面投資協定》的投資爭端解決條款將兼采投資法院機制和包含常設上訴機構的投資仲裁機制。其中,關于投資法院裁決執行的規定將不可避免受到前文所提及的歐盟投資法院投資協定中相關條文的影響,如CETA 投資章節第8.41 條的規定。這同樣會導致《中歐全面投資協定》因違反《紐約公約》和《華盛頓公約》規定而存在合法性問題,進而產生投資法院裁決難以在第三國得到執行的法律困境。為了維護我國政府和我國投資者的合法權益,我國應重視投資法院裁決的執行問題。另外,我國所倡導建立的常設投資仲裁上訴機制也面臨難以依據《華盛頓公約》和《紐約公約》執行的法律難題。因此,我國應借此機會積極參與國際投資仲裁裁決執行機制的改革。究竟是對《華盛頓公約》和《紐約公約》進行修訂使其適用范圍擴展至投資法院裁決和投資仲裁上訴機構的裁決,還是制定一個專門適用于國際投資仲裁裁決執行的新公約,我國應盡快形成自己的方案。
五、結 語
在ISDS機制遭遇合法性危機的背景下,歐盟倡導建立投資法院機制,旨在取代國際投資仲裁機制,推動國際投資爭端解決的司法化。該機制的主要特色在于包含常設的投資法院、上訴機制、全職裁判員以及由締約國保留指定裁判員的權利。該機制將有助于解決ISDS 機制中存在的缺乏糾錯機制、裁決間不一致性和仲裁員缺乏專業性和獨立性等問題,也有助于實現東道國監管權和投資者合法權益保護之間的平衡。歐盟正在全球范圍內強力推進投資法院機制,維持其在國際投資體系中的主導作用。該機制也將不可避免地納入《中歐全面投資協定》的投資爭端解決條款中。投資法院機制設計的初衷是去仲裁化,導致其裁決執行的問題成為富有爭議的問題。考慮到短期內建立專門投資法院裁決執行機制的法律難度較大,歐盟采用在國際投資協定中規定投資法院裁決屬于投資仲裁裁決的策略,以達到依據《華盛頓公約》和《紐約公約》執行的目的。然而,這些規定均在不同程度上違反《華盛頓公約》和《紐約公約》的規定,存在合法性問題,導致投資法院裁決很難在第三國得到執行。制定專門的投資法院裁決執行機制是歐盟的長久之計,迎合了國際投資仲裁機制向公法方向發展的趨勢,將推動國際投資仲裁裁決執行機制的變革。在中歐著手就《中歐全面投資協定》中投資爭端解決條款進行談判的背景下,我國應重視歐盟投資法院裁決的執行問題。另外,我國所倡導建立的常設投資仲裁上訴機制與歐盟倡導的投資法院機制均面臨難以依據《華盛頓公約》和《紐約公約》執行的法律難題。因此,我國應把握此契機積極參與國際投資仲裁裁決執行機制的改革工作。究竟是對《華盛頓公約》和《紐約公約》進行修訂,還是建立一個全新的國際投資仲裁裁決執行公約,我國應盡快形成自己的方案,掌握國際投資仲裁裁決執行機制改革的話語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