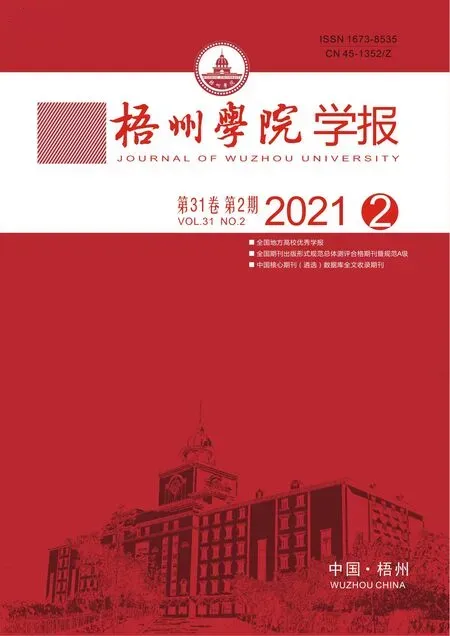桂東民間戲劇的傳承問題及創新發展路徑
陳啟權
(梧州學院 文學與傳媒學院,廣西 梧州 543002)
中國戲曲源遠流長,從先秦儺戲開始,歷代民間戲劇適應著各個歷史時期的文化生態變遷,低調而頑強地向前邁進。今天,廣西的“桂東北、桂東與桂東南、桂南、桂中、桂西南、桂西與桂西北等6個文化帶”[1]都有著多種獨具特色的民間小戲。其中,以梧州為中心的桂東與桂東南文化帶主要有岑溪牛娘戲、藤縣牛歌戲、龍圩鹿兒劇、蒼梧采茶戲以及岑溪、藤縣的杖頭木偶戲等5個地方小戲劇種。它們在其發展史上都曾多次面臨生存危機,但在最近幾年隨著文化惠民送戲下鄉、戲曲進校園等活動的開展以及鄉村振興計劃的實施,又都重新煥發出勃勃生機,發展形勢喜人。然而,作為一種非物質文化遺產,這些民間戲劇的真實生存處境如何?在表面繁榮、前景看好的情況下又出現了哪些突出問題?各種社會主體力量又該怎樣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提出的文化創新精神,共同推動其創新發展呢?對于這些問題,筆者在深入調研的基礎上,嘗試作一些梳理和深度思考,藉此希望在新時代背景下能為更好地保護、傳承民間戲劇并推動它們持續健康發展作出一點貢獻。
一、桂東民間戲劇傳承和發展現狀及其成因
與國內其他民間戲劇一樣,桂東地方小戲長期以來基本上靠的是師徒傳授、民間藝人自學成才和專業人士輔導等傳承方式代代相傳下來。縱觀其歷史,從局部來看,某些藝人會退出,某些劇團會解散,但總體上這些戲劇只在某些時期迫于政治壓力而顯得沉寂,卻從來都沒有退出過歷史舞臺。這彰顯著其生命韌性。最近幾年,桂東地區民間小戲傳承和發展態勢良好,表現為傳承人積極性增強,新劇團紛紛涌現,演出場次逐漸增多,文化部門支持力度不斷加大,戲劇展演和交流日見頻繁。同時,在鄉村市集售賣戲劇唱本、音像制品、內存卡、唱碟機等相關商品的生意越發紅火,形成了小規模的文化產業。這種盛況出現,究其原因不外乎有以下幾方面。
(一)需求增長與報酬增加
在廣大農村,人們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促使他們的精神需求也變得旺盛起來。越來越多的人特別是學識修養稍高的中老年人不再滿足于玩撲克、打麻將、出圩入市、閑坐聊天等娛樂活動,他們更希望利用閑暇時間去讀報、看書、練字、聽音樂、觀看戲劇表演等,因為這些活動體驗能讓他們的內心更加充實。因此,觀看歷史氛圍濃厚、精神內涵豐富的傳統戲劇便成為了他們強烈的心理傾向。村民觀劇意愿增強,自然會促使新老劇團紛紛行動起來,各顯神通。其中的動機不排除有些人純粹出于興趣,但更多的是基于有一份不錯的報酬收入。這是老百姓一種樸實的想法,無可厚非,不應從道德角度妄加非議。據了解,在桂東地區,一個劇團多數為8人左右的規模,一天演出一場約2~3h,報酬為1 000~3 000元,這樣算下來一天人均收入少則一兩百元,多則三四百元,近兩年好的劇團收入還逐漸看漲。一個劇團若年均演出場次超250場,其年總收入還是較為可觀的,所以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從業余愛好者轉變為專職表演藝人。
(二)政策推動與政府引導
首先,《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的頒布實施對民間戲劇的復蘇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據了解,最近10幾年桂東地區各縣市地方政府每年都有約20萬元的預算支出,作為戲劇創作和表演的活動經費,另有5 000~8 000元不等的傳承經費提供給各級傳承人。其次,近年來我國文化惠民活動、戲曲進校園、鄉村振興計劃等大大小小的政策、措施出臺,也給更多劇團帶來了發展機遇。他們的演出場次增加了,收入增多了,影響也擴大了。像岑溪綠云牛娘隊、龍井聯合牛娘隊、五星牛娘隊、六豐牛娘隊、藤縣民間牛歌隊、春花牛歌隊、翡翠牛歌隊等20幾個名聲在外的劇團每年演出場次均增加到近300場。個別劇團甚至是從年初唱到年終,一年四季演出幾乎沒有間斷,仿佛成為了專業演出團隊。這些劇團影響擴大以后,經文化部門牽線搭橋,當地政府、公安局、衛生局、教育局、扶貧辦、交警大隊、鐵路管理部門等機關、單位也常會邀請他們去進行廉政建設、交通安全、守法護法、環境衛生、扶貧脫困等演出宣傳活動。同時,在這些活動過程中,自然少不了當地媒體的積極介入助勢,如“據了解,大坡鎮通過文藝演出宣傳生態鄉村建設,提高了群眾的認識,也調動了大家的積極性”[2]。機關、團體、企事業單位與傳媒的介入,客觀上促進了各地民間戲劇的繁榮發展。
(三)注重宣傳與科技助力
在走訪民間劇團時,筆者發現很多新組建的民間劇團為了打開局面,都會有自己一些獨到的宣傳推廣方法。有的劇團成立初期會先設法通過拜訪一些有威望的老藝人、文化部門的管理者等方式去獲得經驗傳授和專業指導,順帶拓展人脈,同時不計報酬積極主動地參加當地包括廟會在內的一切演出活動,從而打響名聲。有的建隊伊始會通過租借圩鎮空地免費表演幾個月,吸引周邊村鎮群眾觀看,期間主動邀請熱心專業人士指導,同時通過QQ、微信朋友圈、抖音、快手、優酷視頻等網絡平臺發布相關信息及演出視頻。像岑溪糯洞高塘牛娘隊、岑城鎮龍井聯合牛娘隊、天平翡翠牛歌隊等好幾個劇團都在一兩年之內以此方式闖出了一片新天地。新冠疫情爆發前一年他們幾個劇團的演出場次均已達300場,有的在2020年春節前預定演出檔期已安排到了農歷二月底且大部分交了定金,可見其受歡迎程度。成功的新建劇團其開拓創新之舉還有很多,都充分展現了民間智慧及一定的創新精神,令人欣喜。
(四)精神追求與美好愿景
中老年人為什么會喜歡聽戲曲?在采訪中,筆者就此問題曾問過多個年紀較大的民間藝人,他們的答案竟然出奇地相似,即普遍認同于“對于民間戲劇,年輕人即使不反感也不容易喜歡,而老年人則相反,即使不喜歡也不大會反感”這一觀點。這種說法其實道出了一種心理科學:年輕人富有夢想,喜歡憧憬;老年人滿懷回憶,更愛懷舊。而民間戲曲大多數為傳統劇目,基本上是由歷史演義小說、民間傳說、民間故事改編而成,這些歷史題材敘事充滿濃厚的歷史氣息和世俗韻味,很容易讓老年人融情入景并在回味人生滄桑過程中獲得很好的精神撫慰,從中收獲一份寧靜、欣悅及對社會人生的成熟思考。中老年人不約而同地喜歡觀劇,又或者如當代學者所說:“對傳統文化的緬懷飽含著民族凝聚的情感,企盼傳統的復歸,實際上是對傳統異化的一種抗爭”[3]。
二、桂東民間戲劇傳承與發展存在的問題
新時代新氣象,新機遇,民間戲劇迎來了發展良機。但作為一種非物質文化遺產,其天然自帶豐富內涵、傳統韻味、高雅氣質等審美要素,自然會在偏愛快感的當代社會顯得不合時宜。而一旦其被商業同化又缺乏必要的引導和資金扶持時,便會矛盾叢生,問題迭出,對此我們應保持一種清醒的認識。當前桂東民間小戲在發展過程中主要還存在以下3個方面的突出問題。
(一)劇團人數偏少,年齡結構普遍不合理
近幾年筆者走訪過的幾十個劇團,多數或為了“減員增效”或因難招新人而顯得人數不足,其中8人劇團居多,且其成員大多是50歲以上的中老年人,年衰力竭。這樣的規模和年齡結構帶來了3個方面的負面效應:一是由于人數少因此常常出現一人飾多角的情況;二是缺少年輕成員,無奈只好讓老人反串小生或花旦,極不協調;三是因老人居多,青黃不接,劇團面臨傳承危機。這個問題也是最大的問題。傳承危機的出現還跟個別劇團傳承人的狹隘意識或“小心眼”有關。有人至今還有“肥水不流外人田”“教會徒弟餓死師傅”的陳舊觀念,所以技藝不輕易外傳。如果血親或家族范圍內暫時無合適人選,“招新”工作就會擱置,劇團常年就靠幾個六七十歲的老人硬撐著運轉。這樣常常導致有的劇團最后不得不無奈解散。
(二)劇作創新不足,缺乏吸引力
一般而言,當前民間戲劇表演腳本的來源大致有3個方面:第一類是古傳劇本或民間藝人將自己收藏于樓閣塑料袋或箱子里破損的劇本一字不落地重新謄抄而形成的劇本。第二類是經過稍有才學的藝人改編過的劇本。這兩類劇本占了民間戲劇唱本的絕大多數,其內容大多以傳統故事為主,封建倫理道德和政治教化思想明顯,因而往往不太符合當代價值觀,而其藝術手法也較粗糙,別字別詞較多,情感不夠細膩,邏輯力量普遍較弱。第三類為新創作的劇本。這類作品倒是較有時代感,但總體數量不多。總之,由于創新能力不足,部分民間劇團只會反復搬演諸如《牛郞與織女》《梁山伯與祝英臺》《貍貓換太子》《高文舉》《秦香蓮》《玉堂春》《橫紋柴》《睇鴨妹》等熱門劇目,情節沒有創新,表演沒有特色,所以過程會顯得乏味,令觀眾難以自始至終投入觀看。采訪時常有老藝人自嘲,以往我們演出到深夜時,臺下一般只有兩個人還在堅守:一個是出租自家油燈的,另一個是睡著了的。顯然,沒有新意的創作和表演是難以吸引年輕觀眾甚至是“口味叼”的老年觀眾。
(三)培訓或扶持力度不均衡,劇團發展分化嚴重
當前,桂東民間劇團雖不斷涌現,但他們大多靠團內“傳幫帶”的方式進行經驗和技藝傳授,長期缺乏專業指導,總體水平較低,再加上常有臨時拉人湊角現象,所以時有較拙劣甚至粗俗表演,令觀眾反感。更重要的是,不少劇團由于“授徒傳藝和演出活動都局限在山區農村中”[4],往往在出外參訓、參演方面信息不暢、熱情不高或條件受限,得到的指導和交流的機會不多,因此長期以來很難走出低迷狀態。相反,好的劇團在人氣、人脈和來自各方的資金幫助及政策傾斜方面要遠優于基礎薄弱的新建劇團,所以形成有的劇團一年到頭有忙不完的活兒,熱熱鬧鬧,而有的一年半載的演出卻沒幾場,冷冷清清,最終劇團會不歡而散。總之,由于各民間劇團得到的幫扶力度差別很大,因此發展很不均衡,這樣的狀況是不利于民間戲劇遍地開花、繁榮發展的。
總而言之,基于思想觀念、政治經濟、社會心理、文化藝術等多個方面因素,當前桂東民間戲劇發展存在的問題還有很多,制約了其總體繁榮發展,因而有必要進行更大力度的改革創新。
三、桂東民間戲劇的創新發展路徑
新時代須有開拓創新精神,民間戲劇也應如此。近年有學者提議,“要實現戲曲的復興,必須從政策、宣傳、編創、表演等各方面入手,大膽創新,調動人民群眾看戲的熱情,使戲曲成為人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5]。因此,桂東民間戲劇藝人作為創新主體應更新觀念,努力在劇本創編、戲劇表演、劇團發展等多個方面作出更多大膽的創新嘗試,而各地政府部門也應結合地方經濟發展、政治環境、科技水平等多方面因素,負責擔當,為桂東民間戲劇的創新發展出謀劃策,保駕護航。
(一)觀念更新
民間戲曲要想在新時代獲得繁榮發展,各劇團首先應消除“保守、自私、狹隘”等陳舊觀念,要以當代“分享交流”“團隊合作”“互利共贏”的思想意識代替長期以來的“單打獨斗”“固步自封”“家族圈子”等保守想法和做法。要本著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原則,大力培植新人,不論親疏遠近、學識深淺。各劇團要在創作和表演方面多加交流,取長補短,而不應抱有“同行如仇家”的不良俗見。其次是各劇團都應有危機感和與時俱進的強烈意識,應該認識到恪守古風,一成不變終會被時代淘汰。相反,只有因時因地因俗地對劇本、表演還有服飾、道具等作出一些大膽合理的改動,才能永葆活力。當然,引導劇團觀念更新,地方政府責無旁貸。各地政府應增加預算,一方面通過發放補貼促使劇團愿意招新與合作交流,另一方面通過各種培訓開展思想“扶貧”,從中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植入,讓民間藝人多一些責任感,少一些目光短淺或急功近利。
(二)劇本創新
首先是內容的創新。創編劇本時既要傳承傳統,又要充滿當代生活氣息和生活情趣,能引起觀眾的情感共鳴。如近年創作的一首牛娘戲敬酒小調便體現這一特點。“一杯酒,敬阿公,祝福阿公健如龍,壽比南山不老松;二杯酒,敬阿公,祝福阿公樂融融,日日臉上滿笑容;三杯酒,敬阿公,祝福阿公冇憂宗,兒孫尊老育家風。”這劇作在“福如東海,壽比南山”的傳統思想觀念基礎上融入了“尊老愛幼,傳承好家風”的新時代倡議。當然,要說到內容創新,岑溪“爆肚戲”應該是做得最好的,因為它采用的是一種無形劇本即“口頭劇本”,創新是隨時隨地發生的,是內在于其演唱要求和特點的。所謂“爆肚”,是指“唱詞在肚里,即興演唱,見人唱人,見物唱物”[6]。比如賀春時見人抽煙,則能即時唱出“哥在廳堂抽香煙,煙香飄到妹身邊;煙香連著哥情意,妹聞煙香喜連連”。見大姑娘關門,則爆出“賀了一重又一重,睇見姑娘關門攏,姑娘好心開我入,配夫定是大富翁”。見主人家擺設,則脫口而出“石上種竹石下蔭,海底種松萬仗深,八仙臺上放盞燈,只換油來不換心。”這些唱詞雖為即興發揮,卻工整對仗,講究押韻,朗朗上口,富有感染力。其次是形式創新,比如唱詞、對白都可以或穿插、或補充非劇情內容以作情緒情感的調節。如有的桂東民間戲劇唱本詞句會穿插粵曲歌詞如《分飛燕》中的“知你送君忍淚還,哎呀,難!難!難!”或山歌《花好月圓》等大眾喜聞樂見的腔調,有的會增加謝幕詞作為祝福語如“吾唱了,今晚劇情又唱完。六月飛霜唱到此,萬古流傳竇娥冤”《竇娥冤》;“吾唱了,多謝大家來觀看。患難相扶度時光,祝福大家永安康”《乞兒中狀元》等。這些都是很好的創新手段,不妨大膽嘗試。最后是創作現代戲劇,這是創新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雞籠》《親家》《百行孝為先》《嫌貧愛富》《巧媳婦》等地方知名劇目推出,表明戲劇創新工作取得了不俗的成績。另外,還要指出的是,要想讓深受普通話影響的年輕一代的桂東人能夠喜歡民間戲劇,像“黃蟮走過沙灘地,吾死總之脫曾殘(脫層皮的意思)”中的“曾殘”,這些不常見的方言土語應棄之不用,而像“今日游街去紛紛,街頭巷尾咁多人,前呼后擁伴我去,打游金街幾精神”中的“咁”,完全可用“真”置換,這樣才更通俗易懂。
(三)表演創新
據記載,其實早在20世紀20年代“牛娘戲便吸收了廣戲的表演程式及服飾裝扮,向更成熟階段發展”[7]。同樣地,桂東其他民間小戲也都有類似的借鑒創新表演,從而一定程度上使它們走出狹隘的小天地,獲得更廣泛的歡迎。因此,在戲劇舞臺上,唱、念、做、打等多個方面其實都可以既效仿古人,又適度融入時代元素,大膽創新。第一,在角色創新方面,可進行性別角色反串,男扮女裝或女扮男裝等。當然,若化妝技術不好,演員與角色年齡還是要大致相仿,否則會出現上述所說的不協調情況。第二,在表演形式方面,可在整個表演過程中增加相關歌舞表演或其他劇種唱科動作。像岑溪糯洞唐坡牛娘隊常有以下創新做法:一是演出之前先歌舞熱身,吸引觀眾圍觀;二是白天免費吹八音,晚上再演戲;三是努力融進京劇、粵劇等大戲的一些表演動作。第三,在表演地點方面,可變換表演場景。如適當時候可以暫離固定舞臺,將表演空間擴展到觀眾中去,以模仿真實情景的方式演戲。如藤縣同心鎮牛歌隊演出《狀元兒乞丐父》劇目時,便多次嘗試利用白天時間在村邊街角按劇情要求進行逼真演繹,結果均引來觀眾圍觀、叫好或積極參與某一角色表演,讓他們有了一種別樣的觀戲體驗。這種表演已經很接近西方的“浸沒”戲劇風格了,它能收到德國戲劇家和戲劇理論家布萊希特所提倡的“間離效果”,即“讓觀眾清醒地意識到自己是在看戲而非現實情境”[8]。
(四)保護創新
當代民間戲劇無疑是很大程度上受益于科學技術的進步的,至少在交通工具、燈光使用、服飾加工、舞臺布置等多方面都提高了效率或增強了視覺效果。但這顯然不夠,各地政府和文化部門首先還應引導民間藝人學會利用電腦進行劇本創編,利用網絡開展合作編劇,利用新媒體平臺開展更多表演交流等。其次,桂東幾個縣近年來都獲得了文化藝術之鄉的榮譽稱號,所以應考慮圍繞牛娘戲、牛歌戲、鹿兒劇等劇種打造文化品牌,拓寬旅游途徑,反過來也促使這些地方戲劇以更精美更具新意的形式走向觀眾。再次,各地不妨多舉辦群眾性文藝活動如戲劇匯演或展演活動,在活動中提出創新要求,從而引導戲劇走向新時代。最后,各地應通過戲曲進校園、進鄉村的活動引導各劇團在創作和表演過程中融進更多行業故事或內容,加快其創新速度。當然,在創新保護的過程中,各地要成立民間戲劇管理辦公室和民間戲劇協會,既要為其創新提供環境與機會,又要通過旅游開發、戲曲下鄉、戲曲進校、戲曲上線等提供技術和資金支持。
四、結語
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和文化生態環境的急劇變遷,使不少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逐漸被邊緣化。而“在文化的非領土擴張趨勢下,傳統地方文化在外來強勢文化的沖擊下發生文化變遷,逐漸失去了其地方性”[9]。與此同時,商業傾向明顯和娛樂色彩濃厚的大眾文化迅速崛起,又不斷擠壓著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生存空間。在外來文化的沖擊下,文化要進行本土重建;在時尚文化的包圍下,傳統文化要創新發展,努力突圍。近幾年來桂東民間戲劇傳承與發展現狀表明,雖然民間戲劇在當今不可避免地會遇到發展難題,但是它們有著頑強的生命力,也能通過一些創新舉措,通過自身調整去適應文化生態環境,迎來發展的春天,所以對其生存發展大可不必持過于悲觀的態度。我們相信,只要民間劇團、政府、企事業單位、學者及其他社會有識之士都本著創新的原則,共同努力去推進對它們的創新保護與傳承發展,新時代的民間戲劇一定能夠順利地走向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