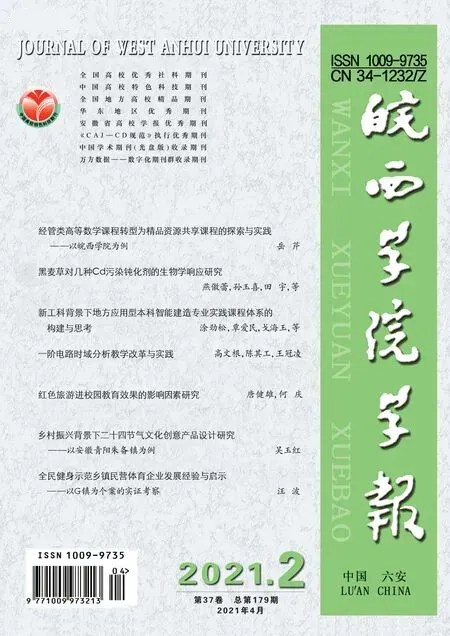中國油畫“徽式語境”新圖式的當代路徑探尋
薛 峰
(蚌埠學院 藝術設計學院,安徽 蚌埠 233030)
21世紀以來,西方當代藝術的主流已經被影像、裝置等觀念藝術為主的藝術形態所占據,而在國內架上繪畫依然是中國當代美術中的中堅力量,油畫創作作為架上繪畫的一種表現形式,在其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當下隨著互聯網時代的來臨,信息爆炸帶來了圖像的泛濫,“讀圖時代”的到來正在改變人們觀照世界、認知世界的行為方式,同時它也在消解著傳統藝術的純粹性。油畫創作也不可避免地陷入圖像化的陷阱,這種傾向導致作品中的繪畫性遭到破壞,創作者的想象力、繪畫語言的獨特性以及客觀物象的表現力都無一例外地遭受消解,油畫創作最終演變成為復制或拼接圖像繪畫的過程。這種建立在影像語言基礎上的繪畫手段常以具象繪畫的形式出現且沒有實現由圖像語言向繪畫語言的轉換,這就使創作者的油畫創作過程中無法發揮其藝術創造性,等于用一種繪畫手段去描繪不同的畫面場景,作品最后呈現的面貌缺乏鮮活的生命力。當使用油畫材料去表達創作者的審美觀念與文化立場時,單一的繪畫語言顯然是蒼白無力的,具象寫實手段僅僅是其中的一種表現形式而已,而且具象表現這一手法因其多用于現實主義題材而逐漸沒落。隨著東西方文化彼此間不斷地碰撞、融合,中國傳統文化介入當代繪畫創作已成為一種趨勢,像國內風起云涌的新水墨、新文人畫、意象油畫等繪畫樣式不斷呈現,復活傳統、探尋和吸收中國傳統繪畫精髓已成為當下藝術創作者的共同追求。
在中國傳統繪畫的理念中“筆墨”的意義遠高于客觀物象的再現,中國畫里的筆墨講究“筆為主導、墨隨筆出”,兩者相互依存,在描繪物象的過程中表現意境,達到形神兼備的藝術效果。實際上這一理念同時對應著油畫創作過程中強調以筆觸和油彩諧調配合所形成的繪畫語言,因此,以寫意的表現性弱化寫實的刻板與拘謹的意象表現這一油畫樣式具有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特征,并且符合中國人的文化審美心理,在油畫創作中主張把對意象表現的研究放在首要位置,將中國傳統繪畫中的意境和品格作為主要線索納入到整個作品創作的流程之中,不斷激發創作者在油畫創作過程中的表現力和創造力,從而創作出兼具精神高度與獨特審美情趣的好作品。
1 “徽式語境”溯源
自古以來徽州地區山川秀麗、人文薈萃,徽州地域文化的內涵豐富多彩、影響深遠。明清時期的徽商以雄厚的經濟實力聞名天下,他們在積累財富的同時也促進了當地文化的繁榮與發展,徽州人民在文化藝術領域里創造出很多流派,這些流派涉及當時文化的眾多層面并且特色鮮明,在全國都產生了巨大影響,徽州人民在文學、繪畫、戲劇、醫學、建筑、飲食等方面逐漸形成自己獨特的語言風格,最終沉淀為獨樹一幟的徽派文化。像徽派建筑、徽州民俗、徽派篆刻、徽州版畫、徽州雕刻、徽劇、徽派盆景等文化至今仍深刻地影響著人們的生活。一種地域文化能夠涉及如此眾多領域。足以見證其存在的重要價值,研究和傳播徽州文化,對于弘揚中國傳統文化,樹立文化自信都具有深遠的現實和歷史意義。
在璀璨的徽州歷史文化長河中,新安畫派是一個極具代表性的文化現象。他們是活躍在明末清初時期的著名山水畫派。在此群體中以歙縣人弘仁、休寧人查示標、孫逸、汪之瑞為主要代表人物,歙縣、休寧縣古屬“新安郡”管轄,因此,被稱之為“新安四家 ”,再加上后期的安徽籍畫家黃賓虹、汪采白、江兆申等人一起被統稱為“新安畫派”;他們在藝術創作過程中主張師法自然、寄情筆墨,作品多以描繪黃山地區的山川河流為主題來表達自我,宣泄心中的苦悶之情。繪畫從形式到風格都大膽創新,給明末清初畫壇的陳舊畫風帶來了新的生機。尤其是其中的兩位代表人物弘仁和黃賓虹各具貢獻,弘仁是“新安畫派”的早期開拓者,其畫風冷峻、用筆簡潔,雖然學習宋元各家之長,但又深入自然,創新求變,其山水畫構圖別具匠心、筆墨蒼勁,常以黃山的奇松怪石為描繪主體,畫面以幾何形體來歸納怪石嶙峋的山峰,作品傳遞出高遠深邃的空寂之美,“在筆墨的處理上,沒有大片的墨,沒有粗崛躍動的線,山石上基本沒有繁復的皴筆和過多的點染”[1](P95),可以說他所取得的成就在當時是超越前賢的。而黃賓虹的繪畫與弘仁有所不同,他用筆繁重且多以濕筆點皴,畫面山川雄渾,草木蔥蘢,尤其中年以后,其作品已形成自己獨特的個人風格,云山相疊、水煙蒼茫,逐漸突破早期“新安畫派”清淡高逸的繪畫語言,在繼承宋元山水的優良傳統后創造性地把山水畫推向一個嶄新的高度,因此,可以說黃賓虹先生是“新安畫派”的集大成者,他對山水畫的探索至今仍影響著當代畫家的繪畫創作。由此可見,“新安畫派”眾多大師們的作品給今天的藝術創作者帶來諸多清新的啟示,我們應當深刻研讀其作品中所傳達出的山水精神,把山水圖式與當下繪畫創作做一個有效的融合,打破畫種界限、從他們的文化遺存中尋找適合自身需要的視覺語言加以提煉,塑造出當代藝術情境中“意象表現”這一重要語匯。
2 國內油畫創作的現狀與困境
油畫藝術作為起源于西方的繪畫種類,傳入中國已有百余年時間,中國人真正系統學習油畫技藝是從新中國成立以后開始的。當時學習和參照的對象主要是蘇聯的現實主義繪畫體系,這種情形一直延續到20世紀80年代初期。在此期間的油畫創作主要圍繞意識形態,藝術創作逐漸蛻變為政治宣傳的工具與手段,尤其在“文革”時期,油畫作品的題材和樣式主要以“紅、光、亮”和“高、大、全”為主要特征,脫離了正常的審美趣味。改革開放以后,重溫了歐洲幾個世紀以來所形成的繪畫流派以及風格特點,從文藝復興、印象主義、現代主義直至后現代繪畫都擁有數量眾多的追隨者。然而,這種看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熱鬧場景實則暗藏危機,其結果就是簡單的模仿與拷貝西方現成的藝術圖式,挪用拼湊各種油畫流派的語言風格,一度形成和制造了一波又一波藝術繁榮的假象。例如,從20世紀80年代的“傷痕美術”開始,國內油畫界不斷變換流行趣味,從“八五新潮”到“政治波普”,從“艷俗藝術”到“卡通一代”,直至今天流行的“壞畫藝術”,無不顯示出群體性的焦躁與急功近利。其次自九十年代開始,商業與市場的介入使油畫創作領域更加無所適從,“流水線作業”“復制抄襲”等有悖于學術道德的現象都時有發生。隨著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開始,藝術市場隨之迅速萎縮,導致近年來油畫創作一蹶不振。另外由于歷史及觀念的原因,中國油畫藝術的主流創作手法依舊以寫實性的客觀再現為表達方式,這種傳統的寫實油畫表現技法在西方當代藝術體系中已經徹底的邊緣化,同時油畫藝術歷史歷經幾百年的發展演變在繪畫觀念以及觀看角度上都已發生了實質性的改變,因此,我們必須靜下心來,另辟蹊徑,探索出一條適合自身發展規律,并且具有獨立文化立場的創新之路。
3 借鑒傳統是當代油畫創新發展的必由之路
當今的世界在科技文明與物質文明高速發展的同時,也給人類帶來了新的困惑。由于城市的快速擴張割裂了人與自然的紐帶關系,互聯網的虛擬化特征加劇了人群的情感異化,以消費至上為市場準則的娛樂文化成為大眾生活的主流,藝術在當下正面臨著全新的文化經驗,必須及時改變觀察世界的角度,調整自身的文化立場。而繪畫作為視覺藝術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需要更新語言系統,以一種新的視覺經驗來反映客觀現實。今天的繪畫藝術在完成了對西方藝術的借鑒與模仿后已陷入困頓狀態,急需找到新的出口。文化的魅力就在于它的多樣性、兼容性和對立性,不能無視傳統文化、地域文化發展的歷史脈絡,要靜下心來完成對傳統的梳理。“在精神層面上重拾傳統文化的魂魄,在文化層面上深刻思考東西方之間文化上的交流與轉換。將工作的重心放在更廣泛的藝術視野中重新認識傳統、理解傳統、激活傳統。”[3](P9)
山水畫作為中國傳統藝術中的一塊精神高地,自兩宋以來一直是文人墨客的表現主體,在中國傳統繪畫里沒有風景繪畫的概念,對于中國人來講表現自然山川所蘊含的意義遠比西方單純的風景繪畫深刻的多。他們認為,從自然中獲得的啟示與感悟比客觀地再現更為重要,因此將對自然的感悟轉化為內在的意向,通過繪畫的形式完成由物象到心象的升華。從山水畫的歷史上看,由宋代山水講究“外師造化”演化為明代山水講究“中得心源”,凸顯出這一現象的發展軌跡。這種由水、墨、紙、筆等幾種簡單工具生發出的氤氳之氣,實際上包含了自然中的物理空間和藝術家內心的意象空間,共同營造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空靈之境,“空靈其實是一種意境,而意境可謂是藝術作品中精神內涵的棲息之地。”[4](P276)
“新安畫派”大師們筆下的黃山就以禪宗般的靈境來體現畫家們超凡塵世的人生境界,其清淡高逸的藝術品格、云山煙水的表現技巧,創造性地發揚了中國傳統繪畫中的山水精神。以弘仁為代表的新安畫家群體生活在明末清初的朝代更迭時期,但他們仍然堅守儒家的人格思想,在繪畫創作中深入研習北宋及元代畫家的繪畫技巧,筆墨簡潔枯淡、冷峻剛毅,與當時江南畫學日漸甜俗的畫風有著本質的不同。“新安畫派”在為山水寫照的同時更為在意精神層面的表達,作品呈現出一種內省的思想深度。他們的繪畫超越了明清文人畫的流行趣味,其審美境界與人格高度都是其他傳統山水畫派所無法企及的。我們通過對“新安畫派”大師作品的梳理研讀,從他們的文化遺存中提煉出適合未來發展的視覺元素,把山水精神、山水圖式與當下的繪畫語言進行轉譯與融合,打破畫種界限,在架上繪畫以及其他視覺藝術領域中大膽探索,以一種全新的語言模式展現在當代藝術的潮流之中。
4 油畫創作對“新安畫派”山水圖式的借鑒與突破
當下許多油畫創作者都把回望傳統作為繪畫實踐的切入點,中國傳統繪畫里水墨、宣紙與西方繪畫里的油彩、畫布在材料美感上雖各有特點,但在媒介的使用上實際上有著天然的聯系。水和墨對應著油和彩,在承托材料上,宣紙對應著亞麻布,水墨、油彩同時都通過毛筆和油畫筆來實現對主觀、客觀物象的塑造。因此在繪畫研究中通過對彼此材料特性的梳理借鑒,是完全可以實現繪畫語言的轉化與突破的。“新安畫派”后期的代表人物黃賓虹在繪畫中常常使用細密的點與皴的筆墨交織技法,使畫面產生了近看抽象、遠觀意象的畫面效果,與西方油畫中的印象派畫風有著異曲同工的藝術表現手段。可以說“新安畫派”的發展歷程就是一段對藝術語言不斷挖掘、創新的探索過程,他們為今天的藝術創作樹立了鮮明的路標。通過對“新安畫派”的深入研習,學習他們深入生活、師法自然、對筆墨創新的探索精神,從而達到在油畫創作中實現超越物象的審美高度。
西方的油畫技術傳入中國已有百年歷史了,如何用油畫語言來表達中國人的情感一直是中國幾代油畫創作者共同探尋的命題。像早年留學法國的趙無極、朱德群、林風眠、吳冠中等老一輩油畫家以及今天活躍在國內畫壇的洪凌、尹朝陽。曹吉岡、彭斯等中青年油畫家,他們共同之處在于將東方意象借助油畫媒材融入作品創作之中,將自然風景轉化為山水圖式。他們的作品不僅僅是對中國傳統方式的簡單復制,而是將山水精神通過語言轉換來實現對當代油畫的改造。趙無極先生的繪畫,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書法,水墨與西方繪畫中的光線、色彩巧妙地融合于一體,畫面呈現出氣勢磅礴的廣闊場景,他的繪畫過程依舊沿用西方抽象繪畫的創作手法,不起草圖,對作品沒有預設效果,強調繪制過程中的偶發性,借用中國畫里的潑墨技法。使畫面產生不可預知的肌理效果,并在此基礎上生發意象元素,它成功地將水墨繪畫語言拓展到油畫創作領域,可以說,趙無極先生是少數成功進入西方藝術史的華人藝術家,他開創性的繪畫實驗為后繼藝術家搭建起連接東西方藝術的橋梁。
在國內眾多油畫家中,洪凌先生是一位充滿著東方智慧的藝術家,他的藝術植根于深厚的山水文化之中,并從中國山水畫的文化積淀中提煉出“天人合一”的宇宙觀,結合西方抽象繪畫的表現技巧,作品呈現出澎湃潮涌的視覺張力和對自然與生命的深層次思考。同時他也是與徽州文化關系最為緊密的畫家之一,20世紀90年代,他就把工作室建在黃山市郊外的新安江畔,常年游走和感悟徽州大地的山水文脈,真正做到了把藝術和生命投射到自然之中,在繪畫創作中他普遍采用大尺寸畫幅平置于地面,顏料中添加大量的稀釋劑在畫面上潑灑滴濺,不同色域碰撞生發出意象的輪廓,大小疏密的色點匯聚成不同的畫面空間層層遞進,以書寫性運筆構成的線條支撐起畫面的主體結構,率性揮灑的筆觸與斑駁流淌的色彩讓觀者體會到強烈的視覺沖擊,正如他在文中敘述的:“一直以來,我努力把油畫媒材和油畫的優長與東方山水自然文化的核心精神融合到一起,啟動一個新的可能性。”[5]可以說洪凌先生繼承和發揚了“新安畫派”從弘仁到黃賓虹的“枯寒冷峻”和“草木華滋”的繪畫思想,創造性地將美國抽象表現主義,揮灑流淌的繪畫技藝和中國傳統繪畫的沷彩技法融為一體,以油畫材料作為媒介進入到了傳統山水文化的核心深處,形成了自己獨樹一幟的語言風格,為我們打開了另一條觀看自然的通道。目前,國內還有眾多的油畫家像洪凌先生一樣的都在研究利用油畫媒材介入中國傳統的繪畫實驗,如曹吉岡先生用墨化坦培拉材料的技法描繪山水,尹朝陽先生用表現主義手法賦予油畫風景以新的定義,彭斯先生借用長卷的形式創作的古意山水油畫等等,可以說借助油畫材料敘述中國故事的創作思路已成為當下藝術家的一個共同追求。
5 結語
現代油畫的創作必須在中國當代的文化現實中通過回望傳統來尋找中國油畫的當代路徑。回歸傳統的過程實際上是重新認識自己的過程,傳統帶給我們的不是束縛,而且另辟蹊徑的自由。東方繪畫的傳統常常與人的禪悟、修行有關,因此注重自身的文化積累,保持平和心態,不斷提升自我的品格與境界,在精神上回歸傳統文化顯得至關重要。
藝術創作的過程實際也是一次系統的思考過程,我們要回避油畫創作中出現的圖像化傾向,更多分析、探討中國繪畫的歷史,尤其是兩宋至明清時期的山水畫史,著重研究“新安畫派”大師弘仁、黃賓虹繪畫的主要特征,從他們的構圖、筆墨中體會山水精神的豐富內涵,把中國畫里的寫意性和油畫語言中的厚重感做一個有機的調和,把中國山水畫里的意象元素和寫意筆法與油畫技法里書寫性筆觸對應起來,構建新的語言系統。將繪畫修養的提升放在繪畫技能的訓練之上,把意象表達作為油畫創作的基本語匯,從“新安畫派”敢于創新的繪畫理念中得到啟示,將中國傳統繪畫元素融入油畫創作之中,重塑當代情境中的“徽式語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