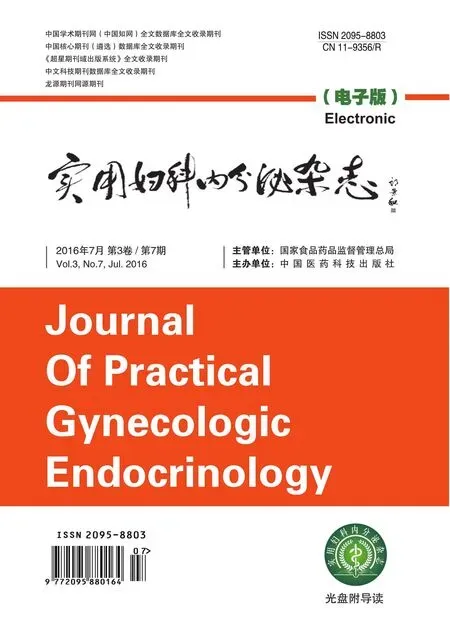超聲彈性成像與常規超聲診斷乳腺良惡性腫瘤的應用價值研究
梁 志
(重慶市北碚中醫院超聲科,重慶 400700)
超聲彈性成像與常規超聲診斷乳腺良惡性腫瘤的應用價值研究
梁 志
(重慶市北碚中醫院超聲科,重慶 400700)
目的 對超聲彈性成像與常規超聲在乳腺良惡性腫瘤中的診斷價值進行研究、調查。方法選取2014年2月~2016年2月我院收治的乳腺腫瘤患者80例,入院后均進行常規超聲檢查,而后再進行超聲彈性成像檢查,并對腫瘤良惡性進行鑒別,比較兩種檢查方式的診斷結果。結果常規超聲診斷良性腫瘤為48例,診斷率為94.1%(48/51),與病理診斷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惡性腫瘤診斷21例,診斷率為72.4%(21/29),與病理診斷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 超聲彈性成像診斷良性腫瘤為50例,診斷率為98.03%,惡性腫瘤27例,診斷率為93.10%,與病理診斷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結論 超聲彈性成像能夠對乳腺腫瘤的良惡性進行鑒別,其診斷準確率更高,效果更為理想。
超聲彈性成像;常規超聲;乳腺腫瘤
乳腺腫瘤在女性中的發病率非常高,近年來,隨著女性承擔的社會壓力、家庭壓力越來越大,乳腺癌的發生率也越來越高,對女性的健康和生活有著非常嚴重的影響。對于患者來說,盡早明確診斷才能接受治療。本病在臨床中主要采用影像診斷,超聲是最常用的影像診斷手段,但不同類型的超聲對疾病的診斷準確度也不同[1]。超聲彈性成像是在原有超聲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一種檢查方式,有研究顯示,超聲彈性成像在乳腺癌腫瘤良惡性鑒別中的準確率非常高,為進一步證實上述觀點,我院選取乳腺腫瘤患者80例,對超聲彈性成像與常規超聲在乳腺良惡性腫瘤中的診斷價值進行研究、調查,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4年2月 ~2016年2月我院收治的乳腺腫瘤患者80例,年齡35~62歲,平均年齡(50.4±13.2)歲,平均病程(8.9±5.4)個月,平均腫瘤直徑(2.8±1.7)cm,均經過手術病理證實腫瘤性質,且知情同意參與調查。
1.2 一般方法
1.2.1 儀器。采用日立彩色多普勒超聲診斷儀進行診斷,超聲儀具有彈性成像技術。
1.2.2 檢查方法。患者首先進行常規超聲診斷,頻率在5~13 MHz,患者仰臥位,在雙乳涂抹耦合劑,而后進行掃描,記錄患者腫塊位置、大小、數量、質地,同時記錄腫塊內部、周圍回聲、鈣化狀況和血流信號,對患者疾病進行分級診斷。而后采用彈性成像技術進行檢查,探頭頻率為5~12 MHz,以雙幅實施顯示功能對SR進行測定,觀察二維超聲圖像和彈性圖像,對疑似部位勻速輕輕按壓,目的在于獲得完整的曲線圖,在測量的圖像中選擇一張標準曲線進行分析,計算SR平均值,以平均值為最終檢查結果。
1.3 診斷指標
1.3.1 采用BI-RADS-US對患者疾病進行分級診斷,患者疾病診斷共分為五級。
一級:患者乳腺組織正常,無異常。
二級:患者乳腺腫瘤呈現良性病變,單純性囊腫,隨訪過程中纖維腺瘤并無改變,術后疤痕改變。二級患者建議每年隨訪一次。
三級:良性病變,可能存在惡性病變。囊腫與皮膚平行或高于皮膚,囊腫呈現橢圓、圓形,周緣窄且尖銳,觸診邊界清晰,囊腫存在鈣化表現,鈣化超過0.5 mm,兩側邊緣存在規整的后方聲像,或兩側邊緣銳利。患者腫瘤后方回聲無變化或增強表現,腫瘤內部無血流信號。診斷為三級的患者建議每個季度或每半年進行一次隨訪。
四級:患者不符合一級、二級、三級診斷者則為四級診斷,若患者疑似惡性病變要進行活檢穿刺。
五級:患者為惡性病變,惡變率超過95%,囊腫形態不規則邊緣模糊,囊腫高于皮膚表面,周圍組織改變,皮膚凹陷。腫瘤呈現強回聲暈征,鈣化程度低于0.5 mm,腫瘤內部存在血流信號。
二級、三級為良性病變,四級、五級為惡性病變。
1.3.2 SR診斷。以3.08為臨界值,超過3.08則為惡性腫瘤。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19.0統計學軟件對數據進行分析,計數資料以例數(n)、百分數(%)表示,采用x2檢驗,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 果
2.1 常規超聲診斷結果與病理診斷結果比較
常規超聲診斷良性腫瘤為48例,診斷率為94.1%(4 8/5 1),與病理診斷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惡性腫瘤診斷21例,診斷率為72.4%(2 1/2 9),與病理診斷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2.2 超聲彈性成像診斷結果與病理診斷結果比較
超聲彈性成像診斷良性腫瘤為50例,診斷率為98.03%,惡性腫瘤27例,診斷率為93.10%,與病理診斷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1 常規超聲診斷結果與病理診斷結果比較 [n(%)]

表2 常規超聲診斷結果與病理診斷(n,%)
3 討 論
乳腺腫瘤在臨床中分為良性和惡性兩種,良性腫瘤、惡性腫瘤聲像特點有不同之處也有相似之處,因此診斷中常常會出現誤診、漏診狀況,嚴重影響患者疾病的治療和診斷[2]。常規超聲診斷具有無創、快捷等有點,但由于腫瘤聲像特征不明顯,因此,診斷也不理想。
常規超聲成像機理與超聲彈性成像不同,常規超聲是假設聲速在不同介質中直線傳播,若介質均勻程度相同聲像也會相同[3]。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聲像圖像會因為位置、亮度等干擾出現失真,導致疾病診斷存在誤差,影響疾病診斷率。超聲彈性成像的成像機理為測量探頭軸與壓縮組織間的位移分布,并預測其彈性系數,當組織的彈性系數增加時,應變量會減小,彈性分數也會升高[4]。在研究的過程中發現,導管浸潤癌的彈性系數最大,而脂肪組織的彈性系數最小。
常規超聲能夠通過乳腺腫瘤的回聲、形態、血流信息進行分析,由于良性腫瘤和惡性腫瘤在二維超聲、圖像中的表現非常類似,因此,診斷過程中容易出現誤診[5-6]。例如乳腺導管內癌患者導管內的結構非常紊亂,在未形成腫瘤時容易與正常組織、癌變組織混淆[7-8]。在本次研究結果中顯示:常規超聲診斷良性腫瘤診斷率為94.1%,與病理診斷比較無明顯差異,惡性腫瘤診斷率為72.4%,與病理診斷存在明顯差異,而超聲彈性成像診斷良性腫瘤為診斷率為98.03%,惡性腫瘤診斷率為93.10%,與病理診斷比較無明顯差異。結果證明,超聲彈性成像能夠更好的疾病良惡性進行鑒別,診斷率更高。對我院的結果進行分析后我們認為,針對存在乳腺病變的患者來說,可在常規超聲的基礎上聯合超聲彈性成像檢查,此種方式能夠更好的對疾病進行診斷,避免誤診、漏診發生。
綜上所述,超聲彈性成像在乳腺良性、惡性疾病診斷中效果更為理想,患者疾病診斷率更高,但針對病情復雜的患者來說,可采用超聲彈性成像聯合常規超聲進行診斷,以明確診斷。
[1] 趙 青,翟 虹,趙獻萍.超聲彈性成像與常規超聲診斷乳腺腫瘤良惡性的應用價值[J].重慶醫學,2013,42(13):1468-1470.
[2] 張韻華,劉利民,俞 清,夏罕生,黃備建.超聲彈性成像聯合常規超聲在乳腺良惡性病變鑒別診斷中的價值[J].中國臨床醫學,2013,24(04):565-567.
[3] 馮慶藝.超聲彈性成像技術在鑒別乳腺腫塊良惡性中的應用價值探討[J].當代醫學,2012,18(16):9-10.
[4] 孔祥海.超聲彈性成像與常規超聲診斷100例乳腺良惡性的應用價值[J].影像技術,2014,2(04):38-40.
[5] 倪梁紅,張新書,彭 梅.常規超聲結合彈性成像對乳腺腫塊良惡性的鑒別診斷價值[J].臨床超聲醫學雜志,2014,16(08):555-557.
[6] 于 蕾,李建國,楊 力.超聲彈性成像比值法與面積比法在鑒別乳腺良惡性腫塊中的應用價值[J].中國全科醫學,2014,17(24): 2904-2906.
[7] 杜新峰,張 浩,李偉漢.超聲彈性成像與常規超聲診斷乳腺腫瘤良惡性的應用價值[J].醫藥論壇雜志,2015,36(05):166-167.
[8] 肖 芳.超聲彈性成像與常規超聲診斷乳腺腫瘤良惡性的應用價值[J].當代醫學,2015,21(31):82-83.
本文編輯:張 鈺
R445.1;R737.9
B
ISSN.2095-8803.2016.07.13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