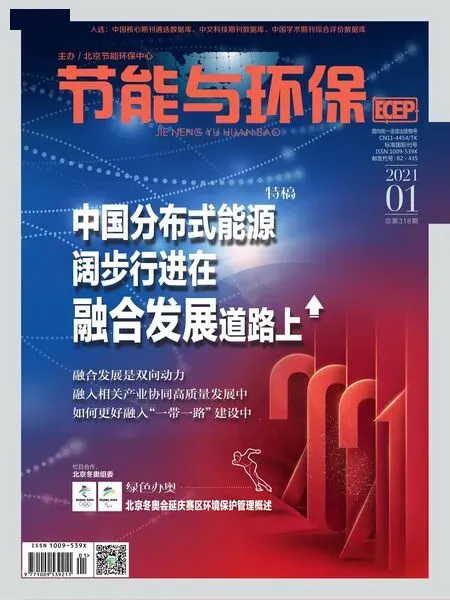如何更好融入“一帶一路”建設中

自我國政府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后,在我國政府的倡議下,國內企業積極在帶路國家投資興業。這其中就包括新能源、可再生能源企業。廖爽給出的數據很是亮眼,“根據商務部的最新統計,2020年1~10月,我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對57個國家非金融類直接投資983.4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24.8%,占同期總額的16.3%,較上年同期提升3.6個百分點,一批綠色、低碳、可持續的合作項目持續推進,我國清潔能源企業在參與國際清潔能源產業鏈體系分工合作方面具有非常廣闊的發展空間。”那么,如何更好地融入“帶路”建設之中?廖爽給出了如下建議。
宏觀、中觀重分析,微觀重“架構”
“我們建議企業在‘走出去’過程中應主要從宏觀政策環境分析、中觀產業環境分析及微觀具體項目的可行性分析入手,綜合判斷特定國別、特定市場的投資價值、合作模式及潛在風險等。”廖爽說。
“宏觀政策環境分析即考慮東道國政局及社會整體是否穩定,是否有因政策變化引起項目的暫停或終止,是否已充分了解東道國的宗教信仰、民族風俗、勞工標準及環境保護等各個有可能帶來潛在風險的宏觀因素。”廖爽說。在以上方面做好了充分準備以后下一步怎么做?廖爽建議,企業可以建立自身的國際市場風險評估體系,從東道國政治、社會及經濟風險等各環節進行科學合理的評估,相信可以從很大程度上規避很多棘手的硬性問題。
“中觀產業環境分析主要是指適用于當地支持清潔能源產業發展的多邊政策及國內的相關產業支持政策是否完善。”廖爽以東盟國家市場為例給予分析說明。之所以選擇東盟市場為例,是因為“我們一直視東盟為周邊外交優先方向和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重點地區”。要做好東盟市場中觀產業環境分析,其一,要清楚兩個重量級區域合作文件。一是2020年11月《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即RCEP的簽署對進一步推動我國與東盟國家實現區域內開放合作,穩定產業鏈供應鏈、暢通貿易、促進投資具有重要意義;二是《2016-2025年東盟合作行動計劃(APAEC)》,要對其內容了然于胸。該行動計劃提出到2025年可再生能源在東盟區域一次能源消費占比達23%,加之東盟相關國家在光伏、風電領域的資源稟賦等,東盟市場無疑成為我國清潔能源產業對外投資合作的關注重點。其二,洞悉國內外融資渠道。一是要關注雙邊合作基金,如中國歐亞經濟合作基金、中非發展基金等,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以財務投資人身份參與相關地區清潔能源領域項目投資,為企業提供金融、市場和管理等方面的增值服務,在一定程度上對沖財務風險,解決融資手段單一,融資成本高等問題。二是多關注其他多雙邊合作機制及對外援助項目等,真正在大的機制框架下實現“抱團出海”。
“對于東道國本身的中觀環境,我們通常關注如FIT、稅收政策(包括外資企業投資相關稅收、設備進口、購售電、企業所得稅、預提稅等)、利潤回收政策(很多項目建成后運營期長達20-30年)。”廖爽說。
微觀項目層面關鍵看“架構”。“首先是融資架構,因為這直接決定了項目的資金安全和內部收益。第二,融資模式應與稅收籌劃相結合的架構。”廖爽分析道,隨著境內企業的國際化視野越來越開闊,運用的市場化手段也越來越豐富:包括境內貸款直接支付、全球授信、內保外貸、境外發債等模式紛紛出現。他認為,一個有效的投資架構應該將融資模式和稅收籌劃做到有機統一,企業應綜合考慮我國、投資東道國以及中間控股公司所在國的相關稅務影響并貫穿于架構搭建的始終。比如,在投資東道國為印度的情況下,基于印度與毛里求斯簽訂的稅收協定,中國企業通常可以選擇設立位于毛里求斯的中間控股公司,間接控股印度子公司的股權架構,從而享受退出階段的稅收利益。
利用工作機制、平臺助力企業更好“走出去”
廖爽表示,商務部投資促進事務局作為國家級的雙向投資促進機構,在清潔能源產業的投資促進工作方面將充分發揮我局的外向型工作職能,利用我局現在負責的中國—中東歐國家投資促進機構聯系機制、中英地方聯合工作組、中墨企業家高級別工作組、中國—東盟合作圓桌會、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投資工作小組及等多雙邊機制及與54個國家和地區的94家投資促進機構建立戰略合作伙伴關系和我局負責的境外中資企業商會聯席會議機制等工作渠道,不斷為國內清潔能源領域企業有針對性的投資促進工作,促進國內企業深入了解重點國別宏觀市場,中觀產業發展情況并適時推薦投資項目信息。同時,也將積極引導國際國內相關投融資、法律稅務規劃及其他第三方服務機構加入支持清潔能源企業“走出去”的隊伍中來,為我國清潔能源產業與其他國家更好開展互利合作做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