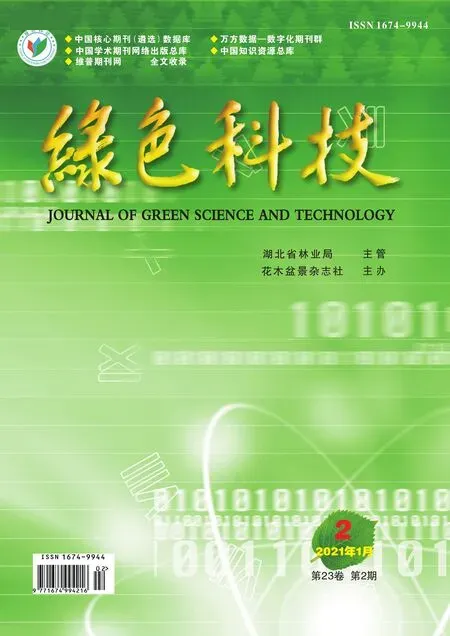武漢城市生活垃圾分類及減量現狀及治理對策
萬秦娟,楊 鵬
(華中師范大學,武漢 湖北 430079)
1 生活垃圾分類現狀
生活垃圾分類是從源頭減少生活垃圾總量的重要途徑,也是全民參與的關鍵環節。通過垃圾分類處理系統可以更高效快速的實現生活垃圾資源化、無害化、減量化。隨者城市化的進展,大城市的生活垃圾總量呈穩步增加的態勢,“垃圾圍城”問題是多數城市亟待解決的難題。
武漢市中心城區當前生活垃圾產量平均為每天8348 t,年產量12274萬t,人均日產量為1.21 kg。生活垃圾中有機物含量隨著城市居民經濟收入的提高和生活條件的改善不斷增加,武漢市生活垃圾中餐廚等有機垃圾增至30%、可回收垃圾約占25%、灰渣等無機物約占10%,其他類約占35%,生活垃圾的年均增長率為14.7%。在新冠疫情期間,武漢市生活垃圾每天的處理量為6000 t左右,且無害化處理率100%(常住人口有所減少,人均生活垃圾產出量下降,生活垃圾的清運量與往年同期相比明顯減少,特別是采取封閉管理措施以后,公共區域餐飲企業產生的餐廚垃圾減少很多)。隨著全面復工復產和正常生產生活秩序的恢復,生活垃圾的產量、清運量大幅上升,目前大部分城市已與往年同期水平基本持平,武漢市生活垃圾清運量由前期最低的每天5400 t,回升到目前的9500 t,基本上與往年同期的每天處理量1.1萬t持平。
武漢城市生活垃圾的源頭包括:居民的日常生活,飯店的運營垃圾,城市街道及公共設施的維護垃圾等。根據武漢人們生活習慣的差異,生活垃圾的主要成分覆蓋了煤灰、紙張、塑料、廚渣、玻璃、毛骨、橡膠皮革、果皮、陶瓷磚石、金屬、紡織纖維及木質雜草等,并可將其分為幾大類:可回收成分(紙張、塑料、橡膠皮革、纖紡、玻璃、金屬);宜燃成份(紙張木質雜草);宜發酵成分(廚渣、果皮、毛骨);現未對有害垃圾做出明確的定義。
目前武漢市生活垃圾主要采用填埋方式處理,因堆肥處理運行費用高、肥料銷售難而沒有采用;焚燒發電正處在建設期且是武漢市垃圾處理的發展方向。就目前的技術而言,各種處理方式均有二次污染的風險,而且處理量遠遠跟不上垃圾的增長速度。武漢市自2006年以來生活垃圾的產量和無害化處理的狀況如表1所示。

表1 武漢市生活垃圾產量及處理率
垃圾分類是達成垃圾減量化必不可少的關鍵環節[1]。在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的前提下,生活垃圾的減量化和資源化更是當務之急。生活垃圾的減量化和資源化的前提是垃圾源頭的有效分類。城市生活垃圾分類回收能更好地實現垃圾資源化,隨者生活垃圾處理技術的進步,武漢市的垃圾資源化效率超過了50%。將可循環利用的資源從垃圾中分離出來循環利用,最終可以減少垃圾量70%。隨著物質資源的豐富,生活垃圾的成分變得越來越復雜,其中部分有害的成分可能與其他垃圾發生化學反應,最終對環境造成更深層次的危害。生活垃圾分類有助于減少垃圾處理的成本和危險。當前,生活垃圾分類處于一種較為原始的狀態,主要依靠拾荒者、居民、環衛工人對廢品進行分散收集。居民將可回收物單獨存放;拾荒者從垃圾容器中分揀出部分可回收物;環衛工人在作業過程中分揀出部分可回收物。
武漢市政府早在1996年就開始關注城市垃圾問題。關鍵的時間節點和政策包括:1996年,武漢市引進2000余個垃圾分類箱;2000年,武漢市環衛局前往我國其他垃圾分類試點地區學習,在洪山廣場推行垃圾分類;2001,推行效果不理想而取消;2005年底,武漢市主次干道垃圾分類箱20000個,垃圾分類回收率不足5%,民營企業試行末端垃圾分類處理。全市首條垃圾分選線在二妃山垃圾場啟用;2008年,武漢市圈獲“兩型社會”試驗區。武漢市決定青山區試行垃圾分類收集處理,將鋼都花園地區作為試點,整體推行。青山區鋼都花園8個社區共放置了100組共300個垃圾桶,將生活垃圾分為可回收物,不可回收物和有毒垃圾三類進行收集處理,但未能實施下去;2013年10月,武漢市東西湖區城管部門擬用4年時間,基本形成覆蓋全區城鄉的居民生活垃圾分類體系;2014年5月,正式下達相關文件,博大城市星座小區成為第一個東西湖區進行垃圾分類處理的小區;2018年1月19日,從武漢市城管委獲悉,即日起武漢市將全面推行生活垃圾分類,即以干濕分類為基礎,將生活垃圾分為有害垃圾、餐廚垃圾(濕垃圾)、可回收物、其他垃圾(干垃圾)四類,并分類投放至收集容器,再通過專業運輸車分別運往專業機構負責處理、回收或再利用。2018年,在全市87個街道、220個社區、811個居民小區等區域開展試點工作。2019年9月,武漢市司法局、武漢市政府法制信息網公布《武漢市生活垃圾分類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該意見稿明確了生活垃圾分類責任,在分類標準、具體要求等方面,作出了明確規定。此辦法一旦通過,意味著江城將由生活垃圾分類試點進入生活垃圾強制分類階段。武漢強制垃圾分類來臨。2020年5月11日,經武漢市政府常務會審議通過《武漢市生活垃圾分類管理辦法》,計劃7月1日起施行。記者通讀了解到,該辦法明確了該市生活垃圾分類責任,在建立生活垃圾分類標準、規定生活垃圾分類具體要求、推行生活垃圾分類智慧化管理制度等方面,作出了明確規定。這意味著江城將由生活垃圾分類試點邁進生活垃圾強制分類階段。據了解,對單位和個人,也作出了獎懲規定。對違規單位,最高罰5萬元,對不分類的個人,將處50~200元以內處罰。
武漢市推行的垃圾分類方法經歷了3個階段,第一階段是2005年提出的可回收和不可回收的“二分法”。2008年進入第二階段,分為可回收垃圾、不可回收垃圾和有毒垃圾。2018年武漢全面推行生活垃圾四分法,分為有害垃圾、廚余垃圾、可回收垃圾和其他垃圾。2020年7月1日《武漢市生活垃圾分類管理辦法》開始正式實施,這標志著武漢市生活垃圾進入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廚余垃圾、及其他垃圾四大類的強制分類階段。《辦法》對單位和個人的垃圾分類行為做出了具體的獎懲規定。如,對違規的單位最高處罰5萬元;對違規的個人處以50~200元以內處罰。2020年7月1日,武漢再次強調垃圾分類的重要性,需根據不同區的特點設立試點,待條件成熟再進行大面積推廣。2020年9月1起施行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明確指出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應當加快建立分類投放、分類收集、分類運輸、分類處理的生活垃圾管理系統,實現垃圾分類制度有效覆蓋。
生活垃圾源頭分類與生活垃圾末端處理是相輔相成的,為了改進生活垃圾源頭分類政策的效果,武漢市嚴格執行分類清運的標準規范。一方面,繼續做好城市公共區域清掃保潔,加強對企業園區、公交站點、商貿中心、交通樞紐等人群密集區域的清掃保潔和消殺。此外,武漢市為了實現垃圾集中處理全覆蓋,繼續嚴格執行生活垃圾全程監管,實現及時收集、清運、處理,并確保生活垃圾日產日清。自1980年以來,武漢市垃圾處理的主要方式是將垃圾填埋到城鄉結合部的湖塘和洼地,如東西湖金口、漢口岱山、漢陽紫霞觀等。2003年和2007年,二妃山和陳家沖垃圾衛生填埋場相繼建成并投入使用。2008年,4個中心城區和6個遠城區中心城鎮的生活垃圾基本實現了集中處理,集中處理率達到90%以上。陳家沖衛生填埋場與荷蘭億碳公司合作開發填埋氣體CDM(清潔能源機制)項目,利用垃圾填埋場產生的填埋氣體發電。盡管武漢市在1996年就開始了垃圾分類,但由于各種原因未能得到堅持。2020年7月1日,武漢再次強調垃圾分類的重要性,需根據不同區的特點設立試點,待條件成熟再進行大面積推廣。
2 存在問題及優勢
2.1 存在問題
(1)人口增長導致垃圾產量上升。武漢市統計年鑒顯示武漢市人口規模持續擴大,常住人口每年以1%增長。人口的增長必然導致武漢市居民生活垃圾總量的增加,而傳統的混合收集、運輸、處理的方式降低了垃圾的回收率,減弱了末端處理效率,嚴重阻礙了循環經濟的發展。
(2)居民環境意識薄弱。城市生活垃圾分類的問題并不是個體行為問題而是一個集體行為問題[2]。居民作為生活垃圾的生產主體,了解其垃圾分類態度和分類行為,對生活垃圾源頭減量化和資源化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根據問卷調查結果發現有89.71%的居民贊同垃圾分類的觀點,6.71%認為垃圾分類可有可無,甚至有3.58%的居民反對垃圾分類。從居民垃圾分類行為來看,44.07%的居民僅偶爾采取垃圾分類,有36.47%的居民從未進行垃圾分類,僅有19.46%的居民有垃圾分類的習慣[2]。由此可見,武漢市居民的環境意識不強,提高居民垃圾分類的意識迫在眉睫。
(3)專業知識欠缺。垃圾收集、分揀人員的相關專業知識相對欠缺,缺少對黨員干部、志愿者、物業管理人員在居民垃圾分類集中處理方面的培訓。專業知識的欠缺導致分揀員工作效率較低,缺少生活垃圾分類知識交流平臺不利于信息資源分享和行為規范培養。生活垃圾成分差異和分類人員素質差異要求高水平的專業培訓機構。
(4)處理技術落后。政府資金投入不足,而且多數資金用于垃圾基礎設施建設和維護、收集、清運、處理環節,使得對垃圾處置技術的科研投入較少,缺少對高效專業智能分類模式企業的扶持,這直接限制了武漢市生活垃圾處理技術、管理水平的發展[3],進而對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投放的積極性產生消極影響。
(5)垃圾處理體系建設有待加強。生活垃圾分類投放、分類收集、分類運輸和分類處置及監督管理構成完整生活垃圾治理體系,其中環節缺一不可。當前城市生活垃圾治理體系存在以下問題:沒有及時改善基礎配套設備;未對投放時間和地點做出明確規定;依然采用混合運輸方式未做到分類運輸;并未采用相應有效的監管制度,居民隨意傾倒垃圾、無人收集、無人管理的現象比較普遍。
2.2 基礎優勢分析
(1)良好城市基礎。武漢2000年獲得“中國優秀旅游城市”和“優秀旅游”、2004~2006年均獲得“國家園林城市”的城市榮譽、2010年獲得“國家森林城市”榮譽、2015年被評為“全球最具活力城市”(第八位)、“全國文明城市”和“國家衛生城市”。說明武漢市各個方面都在不斷的取得進步,主要表現為城市環境優化,市民生活水平提高,基礎設施建設不斷改善,市民的環境行為規范逐漸形成。
(2)政府支持。到2020年為止,全市現有的各類垃圾容器約為22萬個,干垃圾收運車1742臺、濕垃圾收運車658臺,垃圾中轉站13座[3]。武漢市實行以社區為主、街道為基礎的環境衛生管理體制。市城管執法局全面負責全市市容環境衛生行業的業務指導和發展規劃等工作,區城管局負責本區域市容環境衛生的管理工作,街道環境衛生管理所負責街道區域內的環境衛生管理和日常打掃作業。市城管執法局環衛處是環境衛生管理的業務處,負責環境衛生的打掃和保潔,以及垃圾的分類和轉運;建設處負責垃圾終端處理設施的建設和維護,對垃圾進行焚燒或填埋等處理。做到分工明確,將責任落實到各級政府,完成層層抓落實,協調各類資源,使資源配合效率達到最大化。
(3)無害化水平。相比于生活垃圾的“減量化”和“資源化”,武漢市的垃圾“無害化”處理水平相對較高。2020年已經保障了城市生活垃圾100%無害化處理率。特別是在新冠疫情期間,武漢市生活垃圾做到了日產日清,每日的生活垃圾的處置量為6000 t左右,且做到了100%無害化處理。尤其對醫療機構和隔離點的廢棄物處理,做到了專人專車單獨收集,通過焚燒避免二次污染。
(4)非政府組織積極參與。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會和萬科公益基金會支持了“2019年壹起分社區計劃”,通過建立示范社區和行動經驗,探索因地制宜的社區垃圾分類模式,提升社區垃圾分類的有效性。武漢市江漢區花仙子社區是其中一個試點,并將廚余堆肥循環利用實踐方案推進到武漢市的其他四個社區,并取得了顯著的成績。這些社區的共同優勢有,一方面社區有較多的可供綠化的公共區域,另一方面小區中的園藝愛好者及時將廚余垃圾轉化為肥料。社區居民可以全程參與,使得居民間的義務宣傳大大提升了試點的宣導效果。同時,也通過親子活動吸引了25~40歲的志愿者,促進了活動開展的可持續性。
3 國內外垃圾治理經驗分析
日本、美國和德國等發達國家均是較早實行垃圾分類的國家,結合各國國情,總結各國先進經驗,大體分為4個階段:①從源頭的產品設計、制造和包裝等方面入手進行改造。如,德國秉持“避免產生-循環利用-末端處理”的理念,根據產品產生的廢棄物的種類、是否可回收對生產商收取費用[4]。同時施行押金制,即在購買產品時需支付包裝押金,退還包裝時再返還押金。②增加回收設備及增加分類回收方式,常用的集中分揀包括中心分類回收方式、商業網點分類回收方式和街頭大型集裝箱分類回收方式。③通過健全和完善的法規體系推動全體居民的環保行為。如,日本從幼兒時期就進行垃圾分類教育,采用分類管理的教育引導系統將產品垃圾歸類、整理和投放,并依靠健全的法律規章體系規制居民的環保和資源回收行為。④采用補貼和稅金的方法激勵引導市民的環保行為[5]。如英國以家庭為單位按垃圾重量征收費用,通過稅收手段減少廢棄物的產生,遏制垃圾傾倒量的增長,并提高了垃圾分類的回收率。⑤嚴格執行分類末端處置規定。如德國采取以生物堆肥為先、焚燒為輔、及衛生填埋補充的活垃圾處置方法。
相較于全球垃圾分類較為成功的城市,我國城市仍處于生活垃圾治理的起步階段。2000年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將上海、北京、深圳、廣州等8大城市做為我國垃圾分類的試點城市,各城市均有對垃圾分類的地方法律法規[4],效果各有千秋,積累了大量值得武漢學習的經驗。第一,從是否可回收的二分類法改進為以焚燒和是否有害區分的四分類法,且施行分類的試點不斷擴張包括了居住區、學校及各類公共場所等。第二,就北京市600個社區試點的城市生活垃圾分類實況為例,生活垃圾的分類率和正確投放率均不理想。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是居民對垃圾分類的知曉深度不夠。雖然聘用了5000多名垃圾分類指導員,但并未調動居民一次分揀的積極性,基本仍然依靠保潔人員的二次分揀(76%),且存在監督力度不足和考察指標模糊的問題[6]。第三,2019年以來上海、杭州等市均強調了強制實施垃圾分類的必要性,采取了嚴格的城市生活垃圾治理制度,且獲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實際上,制度激勵的短期有效性導致垃圾回收率及分類投放率并不理想。第四,重視社區作為城市運行基本單位的重要作用,利用社區治理推進生活垃圾治理是解決城市環境問題的重要手段。北京和上海推行的社區實施積分兌換禮品的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為武漢市的城市生活垃圾治理提供了良好的借鑒素材。
4 治理對策
4.1 完善配套設施
為了調動居民進行垃圾分類的積極性,政府可以向居民免費提供分類收集專用的垃圾袋或垃圾箱,將當前普遍使用的是否可回收的二類垃圾容器更換為精細分類的四類垃圾容器。此外,優化垃圾分類設施的位置和性能,確保垃圾分類設施的充足和一定的標識性,以滿足居民的分類投放垃圾的需求。
4.2 加強宣傳和教育引導
環境知識儲備是影響環境行為的重要原因[7]。政府的宣導政策對垃圾分類行為的影響是積極的[8],應該發揮主導作用,將社會力量,基層社區納入到輿論宣傳體系中來,通過包括微信、電臺廣播、海報、宣傳欄在內的多種渠道來開展宣傳教育,普及垃圾分類的知識,培養居民的環境道德責任感。將垃圾分類知識的考核引入學校德育建設之中,培養中小學生良好的意識習慣,為將來社會整體形成垃圾分類的氛圍打下堅實的基礎;可以通過在基層社區開展垃圾分類的各類評比,從而提高居民垃圾分類的行為意識。
4.3市場化治理
生活垃圾處理系統有待形成一個完備的產業鏈,引導社會資本進入,加強工作人員及流程專業化,以提高城市垃圾回收和處理的能力。將垃圾分類和垃圾處理進行整合,減少因分離而產生的政策實施難度。推動生活垃圾私有化及垃圾處理服務化,依據居民垃圾的產量和垃圾處理的成本進行收費,通過引入市場經濟因素影響居民的行為策略,從垃圾分類行為的主體切入來實現垃圾減量化。
4.4 社會集體自治
社會集體自治是指通過在內部達成協議約定來對集體內的個體進行約束和指導,其包括行為準則和對行為準則的監管制度。集體自治有助于政府在公共服務方面的政策的貫徹實施,補充政府在公共服務方面的缺失,減輕政府的財務負擔,提高公共服務效率。
5 結語
武漢市應在借鑒國內外科學高效的治理經驗的基礎上,綜合考慮文化差異、城市發展水平差異、生活習慣差異、各類生活垃圾占比差異、自身城市生活垃圾處理現狀,以循環經濟理念為核心,切忌生搬硬套的全盤模仿。從生活垃圾處理的源頭為治理起點,認真貫徹相關政策,切實執行相關制度規則,鼓勵全民參與垃圾分類,以達到生活垃圾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的目標。
致謝:本文在華中師范大學鄧紅平教授的指導及學院的支持下完成,在此表示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