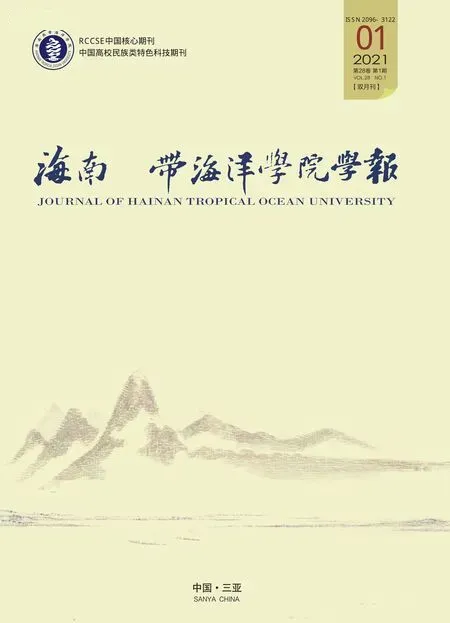海南黎族文身習俗的地理學詮釋
許桂靈,司徒尚紀
(1.中共廣東省委黨校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所,廣州 510053;2.中山大學 地理科學與規劃學院,廣州 510275)
文身被譽為“刻在身體上的敦煌壁畫”[1],“刻在人體上的文化遺產”[2],為古代世界各民族一種較為普遍的文化形態,近年來一直為中外矚目,也是學界研究的一個熱點。黎族是我國最突出的有文身習俗的民族之一,也是世界上有著最為豐富多彩的文身圖式的民族。海南黎族文身之由來,各家各說,見仁見智。概括起來主要有刀耕火種說、生態環境說、民族標志說、圖騰崇拜說、抗婚說、區域標志說、審美說等。無論是哪一說,都離不開海南特定的地理環境基礎。正如費孝通先生所言,“任何民族的生息繁殖都有其具體的生存空間”[3]1,“民族格局似乎總是反映著地理的生態結構”[3]2。本文擬從人與環境關系的維度,考察黎族文身之根源。
一、 文化傳承說
海南黎族古代是嶺南百越族的一支,廣泛分布在河海地區。按照張壽祺[4]的解釋,“越人”就是生活在水濱的居民,即水居部族;之一。晉代皇甫謐撰《逸周書·王會解》稱:“東越海蛤。歐人蟬蛇,蟬蛇順,食之美。于越納,姑妹珍。且甌文蜃。共人玄貝。”[5]可知南方越人以水生生物為食。《史記》中說:“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6]唐代學者張守節《史記正義》云:“楚越水鄉,足螺魚鱉,民多采捕積聚,鲏疊包裹,煮而食之。”[7]反映了古代南方越人所處之水鄉環境。《淮南子·原道訓》稱:“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眾,于是民人被發文身,以像鱗蟲,短綣不绔,以便涉游。”[8]《漢書》稱:“越人常在水中,故斷其發,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9]顧野王《輿地志》云:“交趾周時為駱越,秦時曰西甌,文身斷發避龍。”[10]可見,文身是適應水鄉澤國的炎熱天氣而產生的文化現象。1982年在廣州柳園崗數十座南越國墓葬出土了文身的木俑,高52厘米,圓目高鼻,身體肥胖,前胸印有墨繪的卷云紋,無發,箕踞而坐[11]567。這一考古發現說明古越人有文身的風俗是不爭的事實。海南黎族前身屬駱越人,有文身之俗是很自然的。
漢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平南越國后,旋即收復海南,設儋耳、朱崖2郡16縣。漢朝官吏殘酷掠奪黎族民眾的物產,如廣幅布等,多次引起黎族人民的反抗。《后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載:“武帝末(前87),珠崖太守會稽孫幸調廣幅布獻之,蠻不堪役,遂攻郡殺幸。”[12]被鎮壓后,大部分黎族被迫從沿海移居五指山區,由水居變成陸居,從平原進入山區。1873年10月,美國傳教士香便文(Benjamin Couch Henry,1850—1901)到海南旅行,在漢黎交界地區的“未知山谷”考察“海南土著人”,認為“漢人把他們從沿海以及島北大部分低地平原趕回來,那里與中部和南部山區一樣,都曾經是黎人的領地”[13]54。1951年,華南師范大學曾昭璇先生隨廣東民族考察團入五指山黎區調研后指出,“美孚即傳說被漢族地主所迫,由感恩遷入山區,今天感恩還有美孚人遺址可查云云。侾族亦有由海岸遷入山地的傳說,如三差黎由八所海岸遷入千家(樂東)的說法,四差黎亦同樣由崖縣海岸遷入山區的傳說。從歷史上看,統治者的征剿迫使黎族放棄肥美的沿海地區,遷入山地,都有記錄”[11]555-556。另在黎族族譜中還記有因遭受自然災害而遷入山區的,如岐人《族譜》中即:“因遭臺風和海潮的襲擊,沿著昌化江兩岸尋找高地安家,群遷俄查或尖峰高地居住。”[14]394
民族學者認為保留至今的黎族船形屋,就是黎族這種居住方式轉變的物證。船形屋是古越人“干欄式”房屋的變種,保留昔日船蓬狀的屋頂和海濱木樁的支撐結構,是黎族先人曾居住在海濱的一個有力的佐證[11]555-556。這種船形屋廣見于五指山地區。光緒十三年(1887)胡傳(胡適之父)《游歷瓊州黎峒行程日記》中記載其所見儋州自南豐至凡陽一帶,“生黎所居之茅棚,上圓如船之篷,下以木架之,或高尺許,或高二三尺,用竹片或小竹排而編之。坐臥于其上,其下透空,犬豕可入,兩頭或一頭為門,亦如船”[15]。曾昭璇先生實地考察的白沙本地黎、通什(今五指山市)、番陽等地岐黎、樂東一帶侾黎、島西南海岸地區美孚黎等,都保留有船形屋,形制大同小異,皆反映他們昔日是海岸居民,被迫遷入山區后殘留下來的文化遺存。曾氏認為:“黎人的船形屋正是反映他們當日是海岸居民,其后被迫遷入山地殘留下來的文化遺跡。”[11]556
由此推論黎族文身這種本來是適應水環境的生活文化方式,像船形屋一樣,隨黎族入內地上山,也隨而轉移到新居地,作為一種文化形態,傳承下來。
二、 文身適應熱帶雨林環境
在五指山區熱帶雨林環境下,森林茂密,水汽蒸騰,濕度非常大;加之毒蛇猛獸呼吸的氣體以及動植物尸體腐爛產生的有毒氣體彌漫,所謂山嵐瘴氣籠罩各個角落,形成一個非常惡劣的生存空間。香便文在黎母山地區考察,所見“層峰疊嶂,竹林叢深,水中的毒氣和山中的霧嵐交織,濃重的氣霧遮蔽四面八方,外人并不總能進入村中,于是各部落可以憑借這種天險作惡為患”[13]61。甚至香便文快結束行程、抵達瓊海萬泉河下游(今瓊海市西南部的東大農場)仍擺脫不了瘴毒侵襲,“夜晚的涼風吹過這條敞篷船,升騰在水面上的瘴毒濕氣包裹著我們,在我們疲憊的身上播下發燒的種子,我們太疲倦了,無法抵抗它的侵襲”[13]152。胡傳在黎峒旅行,說到此前政府曾對黎族人民用兵,“東西二路殺賊不過三百余名,而官軍勇丁瘴故者三千余人之多,可嘆也哉”[15]。在這種環境下,黎族人民文身的各種圖案可起到保護色的作用,類似今日軍隊迷彩服,有助于避免被各種有害動物傷害。20世紀50年代初,曾昭璇入五指山考察時發現,“常近距離仍不易發現黎婦,即因面、手、足文成圖案,與陽光透入林中所成疏影景象相似之故,即確有保護作用”[14]399。關于文身這一適應環境方式的記載多見于古籍。郭璞注《山海經·海內南經》云:(雕題國)“畫體為麟采,即鮫人也。”[16]《漢書·地理志》亦記“文身斷發,以避蛟龍之害”[16]。
三、 文身圖案源于天文地理要素
地理環境是存在于人類周圍的自然、人文要素的總和。就海南黎族文身而言,主要是自然地理要素,包括天文、氣象、地形、動植物等。這些要素納入文身圖案之列,既是作為自己的保護神,也反映出黎族人對這些地理環境的認識,折射黎族人民生態文明思想的光輝。

以地形要素而言,文身圖案中有山脈、河流等,都符合海南多山多水地理環境以及它們與黎族生產生活的關系。山是狩獵的場所,要想有收獲,須得到山鬼允許,崇拜由此而生。水里有水鬼,可致人喪命或生病,故江河湖海也享受崇拜而被納入文身圖案之列。例如白沙本地黎族由大腿至小腿的文身以波浪紋為主,這與他們居住的船形屋的形式相類似,反映了近水的居住環境[11]518。
以植物要素而言,黎族認為它們也有靈。海南島森林植被茂密,種屬繁多,形成不同群落和多種生態環境。黎族文身也采取不同圖案與此相匹配,以期有效地與大自然協調,保護自己。1934年,人類學家劉咸到海南黎區進行人類學考察,收集到黎族文身圖記有61種之多,包括面文37種,手文14種,腿文10種,計有斜文、橫文、圈文、字文等4類圖案式樣[11]516。這些圖案屬于植物的數量最大,出現頻率最高,其中主要有樹林類、草地類和谷粒類,很多圖案用簡練的筆畫表達了這種環境景觀。
“黎族原始先民……長年生活在莽莽林海之中,青山綠樹是他們的棲息之地,成為他們索取生活物資的源泉。”[19]森林是游耕方式的最主要資源,由此形成對森林的崇拜,率而發展為文身圖案。1965—1976年,僅在原自治州境內,刀耕火種面積達49萬畝,占自治州耕地面積的7.4%。20世紀80年代平均每年仍然有4萬畝之多[20]201。故有論者認為,刀耕火種是黎族文身的來源之一[21],也不無道理。
植物圖案主要有花、葉、藤條、檳榔、椰子樹、谷物,既有野生的,也有栽培的,一起構成黎族生產、生活環境的一部分。黎族文身中還有草叢的圖案,而草叢也是燎荒對象。黎族認為稻谷也有靈魂,俗稱“稻公”“稻母”,黎語稱為祖先,備受崇拜。文身中大量出現的點狀圖案,可理解為山欄稻谷粒(一說為青蛙卵的象征),是刀耕火種的成果[18]。
以動物要素而言,黎族除了游耕農業,狩獵也是他們最主要生產方式。這些動物也是黎族食物的一個主要來源。舉凡牛、蛇、猴、豬、鼠、蟲、龍、魚、蚊、雞、狗、羊等都有靈魂,都是鬼,一律受到崇拜,尤以對牛魂的崇拜最篤[22]。黎族家家戶戶都珍藏有一塊稱為“牛魂”的寶石[23]。在東方市黎區,有起于元朝的“牛節”,每年農歷九月的第一個“牛日”,定為“牛節”。是日,在外地工作的人也回鄉一同慶賀這一節日。大家對歌、喝酒,歡聚一堂,以示對牛的崇敬和感激。當今,文身成為一些青少年的時尚,牛的各種圖案在文身行業被視為最“牛”的一種文身符號,這與牛在黎族歷史上的地位不無關系。在黎族的觀念中,鹿是瑞獸,是美好、吉祥的象征。膾炙人口的《鹿回頭》傳說和雕刻,風靡海內外。而蛙可感知雨水的到來,與水稻生產豐歉關系甚大。又蛙在母系社會象征生育繁衍,反映古代增加人口的愿望。所以蛙和鹿一樣,無論在黎錦還是文身圖案中都占有最崇高、最普遍的地位。如“昌江王下三派村的村民頸上所文的點群,即為青蛙卵的象征,祝福多姿多孫的意愿,因其時黎族嬰兒死亡率高”[11]539。這些類別圖案的原型都是海南熱帶環境生長、活動的物種,受到黎族的崇敬而納入文身圖式中。
四、 文身色彩與森林環境相協調
海南熱帶森林郁閉度很大。明清時,“自儋州至崖州千里間,木多雜樹,又多樹上生樹。……巨且合抱,或枝柯伏地下,連理而生”[24]。在崖州,“行半日不見天日”[20]186。為達到保護自身的目的,黎族在文身色彩上也做了獨到的選擇。黎族傳統服飾以深藍色、黑色為主,采用靛藍草發酵后,經反復多次染色而成。其文身亦以藍、黑色為主,同時加炭,一旦文身成功,永久不掉色。另外,黎族在耕山勞動中,所及之處多是燒荒的灰燼、黑土,故多穿耐臟的藍、藍黑色衣服。這類顏色在叢林中不顯眼,能有效地隱蔽自己。黑色在壯侗語族各民族中,被視為萬色之母,為吉祥、永久、莊重之標志,得到廣泛崇尚。如同為百越人一支的廣西那坡縣的“黑衣壯”,其所有服飾為清一色黑衣,與森林的色調和環境相一致或協調。海南黎族使用的語言同樣屬壯侗語黎語支,具有相同的審美觀,以黑為美,主要是在高山密林中活動,其文身色彩離不開黑森林背景。
五、 文身部位與環境融成一體
黎族的文身部位都為身體的暴露部分,是符合海南氣候環境和人類愛美追求的。熱帶地區,穿衣服本來就不方便,也不利于散熱,故南越各族中有稱“裸國”的,如《史記·南越列傳》稱:“南方卑濕,蠻夷中間,其東閩越千人眾號稱王,其西甌、駱裸國亦稱王。”[25]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黎族男性仍不喜歡多穿衣服,黎族女性露出的身體部分也比較多。女性文身可彌補衣服花邊的花紋,擴大衣邊的美觀部位的面積。再者,文身可模擬衣服花紋、鐲子、戒指、項鏈等飾物,增加美感。
據曾昭璇收集的文身圖式,各支系文身部位不一。如白沙本地黎潤黎的文身普遍在臉、胸、背、手、足、大腿等處,以女子居多。男人的文式簡單,分布于前胳膊、腹背。本地黎為島上的土著居民。東漢楊孚《異物志》已記其“儋耳,南方夷,生則鏤其頰皮,連耳匡,分為數支,狀似雞腸,累累下垂至肩”[26]。直至今日,潤黎的文身圖式仍如此,面、胸、手、足等處皆有,后又演化為美化裝飾,改為文鳥、獸等圖式,部位也有所擴大,包括面部斜面、下頜、脖子、胸至腹之間、手部交叉處、手背、臂部、手腕、小腿、腳后跟、足面、膝蓋、大腿、小腿等處。王國全《黎族婦女的文身習俗》一文所記潤黎的文身部位有“臉上、脖子、胸脯、腹部、脊背、臂部、小腿……以方塊紋和樹葉紋組成文身圖案”[27];分布在昌化江一帶的美孚黎,以女子文身最多,圖案也有“青蛙”和“蛇”等,且后者常以黑白兩色相間,被稱為“南蛇人”,更凸顯了與森林的色調關系。分布在五指山深處的岐黎,舊稱生鐵黎,見于新中國成立前合畝制地區,如保亭、樂東等地,其文身在胸上、臉上、唇下、腕上、足上,具有線條較粗、圓點大等特點。分布在平原、谷地的侾黎,又稱“平地黎族”,漢化程度深,如崖州(三亞)、樂東盆地的黎族等,這里地形開闊,環境不及深山惡劣,文身部位以頭部為主,族群識別功能要明顯一些,計有文手、頸、下頜、足、腳、環耳、胸、掌背、小腿,而在嘴的周圍則文“刺嘴箍(俗稱‘烏鴉嘴’)”[11]517-534,說明嘴巴最易暴露,需要遮掩保護[11]539。宋代周去非《嶺外代答·蠻俗門·繡面》也早記海南黎女以繡面為飾:
蓋黎女多美,昔嘗為外人所竊。黎女有節者,涅面以礪俗,至今慕而效之。其繡面也,猶中州之笄也。女年及笄,置酒會親舊女伴,自施針筆,為極細花卉、飛蛾之形,絢之以遍地淡粟紋。有晰白而繡文翠青,花紋曉了,工致極佳者。[28]
實際上,不管黎族文身的年齡、部位或圖案有多少差異,其寄意基本一致。黎族文身圖案的意義主要反映在臉頰線紋的寓意上,即所謂“福魂”上。據相關研究表明,文于上唇寄意“吉利”;文于下唇寄意“多福”;文于腿部寄意“護身平安”;文于背部寄意“福氣上身”;文于手指上的圈紋寄意“多財”等,反映了黎族生產力低下、經濟貧困,希望借助于文身圖騰的力量改變現實的美好愿望[29]。這是應對落后、貧窮的經濟狀況所做出的一種文化選擇,具有深刻的人文環境根源。
此外,人文環境也是一個歷史范疇,有時間序列。不同年齡段的黎族女子其文身部位也有差異。據20世紀30年代劉咸的調查結果:“如十二三歲時先涅面部,十六七歲時已出嫁者,則涅胸部。”[30]即女子到了十二三歲身體發育年齡時,在臉、脖頸部位施紋,十六七歲結婚后,才在胸部施紋。而《黎岐紀聞》則記載黎族女子在出嫁前才開始文面:“女將嫁,面上刺花紋,涅以靛,其花或直或曲,各隨其俗。蓋夫家以花樣予之,照樣刺面上以為記,以示有配而不二也。”[31]并且通過服飾、色彩的變化,反映人生不同階段的開始,這也是一種文化調適,與文身意義相類似。黎族婦女“婚禮上的盛裝沒有什么特別,只是在花紋上非常繁復、顏色看起來比較鮮亮。參加喪禮時要穿得素一些,由于黎族的筒裙都是有花紋的,所以素的標準就只能是相對顏色和圖案沒有那么顯眼”[32]。這說明文身和服飾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整體,并相互感應和相互影響,但這種文化的基礎仍然是黎族所在的地理環境。
結 語
海南黎族文身是一個很古老的話題,就其產生的根源而言,則眾說紛紜,各有其道理,都可為解答這一歷史懸案提供某種參考。本文主要是從人與地理環境不可分割關系的立場出發,認為黎族的文身,一方面是繼承原居濱海古越人的文化傳統,從沿海傳播到內陸山區;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是在海南山區熱帶雨林條件下,為有效地適應新的地理環境,保護族群安全和方便生產生活,而創造并發展了文身的方式。在文身采取動植物圖案、文身色彩、部位選擇等方面注入新內涵,得以適應新的地理環境,并生存和發展至今。黎族這種調適與環境關系,具有生態文化的內涵,而有其合理性成分,簡單地全盤否定和肯定都不是科學和務實的態度。但最關鍵的一點,是文身首先應歸結為特定地理環境的產物,是適應海南熱帶山區環境的結果,也是一種生態文化形式。其作為一種歷史文化遺產,應予認真研究,從中總結科學、合理的成分和經驗,為海南社會經濟發展和文化建設服務,當前尤應為建設海南自由貿易港提供可開發利用的風俗文化旅游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