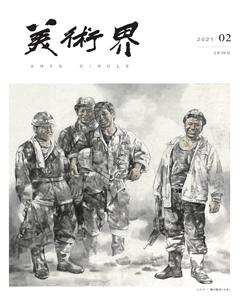準確而無正確

《碰巧的杰作》中講一個女藝術家杰伊·德費奧的故事。開始,她打算在一張長方形大板上,設計一個類似橘子或柚子切面的圖案,從畫板正中心略偏一點向四面輻射開去。在之后很長的一段時間里,她反復地在畫板上堆積顏料,又將其刮去。為了讓圖案輻射點更準確地落在畫板的中心,她又將作品粘在更大的畫板上,并取名為《玫瑰》。之后在很長的歲月里,這幅作品被德費奧每天用顏料堆積、修改,到最后,作品的重量已接近一噸。其中,德費奧與丈夫離婚,即使放在倉庫時也沒有停止過修改,得以展出時已有十一年之久。那么德費奧到底在執著于什么?她告訴朋友說:“開始時腦袋里只有‘一個帶有一個中心的想法。”
一語雙關。十一年尋找的既是“一個中心”的準確,同時也是尋找心中的準確。這個準確無法用直尺與刻度衡量,在于每個人不同的藝術尺度。在這個尺度中,各人有各人的靶心,各自尋找各自的準確。在沒有靶心的情況下,繪畫才會淪落到討論正確與否的境地。
隨著時間的推移,情況在變化,一代一代的人也在變化,但是能從這些藝術家的作品中不斷發掘出新的內涵。
當然,德費奧的《玫瑰》即使在國際上享有一些名譽,但相比馬蒂斯、畢加索或者梵高那樣的畫家是不那么具有代表性的。有一句著名的格言,換一種說法的表達就是,偉大的藝術之所以偉大是因為它們能永葆青春。以上那些藝術家的作品,每十年展出時,都像一個新出現的藝術家一樣:雖然作品早已完成,它的內涵卻在不斷變化,隨著時間的推移,既影響其他藝術作品,又受到其他藝術作品的影響。那么,當我們在欣賞一幅已知的、公認的經典作品時,究竟看到了什么?
這樣的問題,所謂專業者的回答并不會比業余者的更簡單。正如克里希那穆提所說:你明白“局限”這個詞的意思嗎?你接受某種形式的教育。
因此在本質上,一張宋代經典的花鳥小品與徐冰的《天書》并無不同,比如對于細節品質的把控或者形式上對于留白的理解;一張梵高的自畫像與徐渭的葡萄也無不同,比如強烈情緒對于繪畫的作用同時在藝術史上留下了啟迪。能將兩者聯系在一個維度上的,沒有正確,只有一種準確,并因人而異。作品的分類也可以不由古今中外的順序,各個理解維度的不同,作品的意義不同。
《碰巧的杰作》中還有一個關于收藏的故事,有一位艾伯特·C·巴恩斯博士,用消毒藥品弱蛋白發了大財,大量地將塞尚、馬蒂斯的作品和非洲藝術、民間小擺設等匯聚起來,并以與眾不同的方式把它們擺放在一起。比如一幅修拉的名作旁邊,掛上與巴恩斯只有一面之緣的麗茲·克拉克的《賣氣球的人》,原因是他在這些畫中看出了類似三角形或對角線的構圖方案,擺放在一起可以更加凸顯他們的構圖設計。當然這是一個極端的例子,卻是有意思的,如酷愛將八桿子打不著的東西比喻在一起的錢鐘書,兩者之間絕無高下之分,只是抓住了某種表達的準確。
我們不能說古希臘的雕塑是正確的,但準確。也不能說《日出印象》是正確的,但也是準確的。
回過頭來,把一張宋徽宗的《桃鳩圖》放在面前,它的呈現包涵著宋徽宗眼中對于桃鳩的所有表達與詮釋,如春秋時期謬贊東家之子之句: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細節的完美并不意味著全面,而是準確,因此比真的桃與鳩都要多了幾分氣質。當我們提起桃與鳩的時候,口中代之的那個“桃鳩”絕不是這世間千千萬萬的桃鳩,唯獨指的就是這一對。宋徽宗最大的能力在于敏銳地捕捉現實世界中的審美關系,并準確地表達出來,最終升級為中國畫中的范本之一。幸運的是,物象并不具有自己總結自己的能力,將這開放性的命題交給了藝術家。



王華菁
別署花青,生于上海。現定居廣州。2005—2009年就讀于中國美術學院附屬中學;2009—2013年本科畢業于中國美術學院中國畫系;2014—2017年碩士研究生畢業于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系,導師何加林教授;2018年至今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系花鳥專業博士在讀,導師江宏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