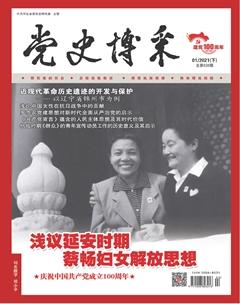孫中山“黨治”監察思想下的實踐與反思
[摘要]在中國政治制度史上,孫中山首開“黨治”先河,其監察思想在“權能分治”理論提出后,由單一的監察院行使監察權,發展為包括“政治系統”和“黨治系統”雙軌并行,“政權”“治權”和“黨權”三方參與的多元立體的監察體系。但在“黨治”下的實踐中,由于一權獨大的“黨權”不斷干擾“治權”和弱化“政權”的監察權力,使孫中山監察思想的內核發生了變異。通過反思孫中山“黨治”監察思想的失效,理清其監察思想中的內在邏輯矛盾,從而揭示政黨的自身建設和接受監督的重要性。
[關鍵詞]“黨治”;“權能分治”;監察思想
[作者簡介]王帥(1994-),男,漢族,河南漯河人,新疆師范大學政法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執政黨建設與當代中國政治研究。
[中圖分類號] D693[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1006-8031(2021)01-0007-03
“權能分治”理論提出前,孫中山監察思想的重點集中于監察院的監察權。隨著“權能分治”理論的成熟和“黨治”的運用,其監察思想形成了多元立體的監察體系,這在中西監察思想史上是一個重大飛躍。隨著國民革命的發展,促使孫中山更加倚重“黨權”實行“黨治”,雖然在“黨治”下孫中山監察思想未能得以有效實行,但其理論價值和失效原因仍值得借鑒和反思。
一、孫中山監察思想的主要內容
在“權能分治”理論提出之前,孫中山強調監察院的監察權獨立,試圖以此糾正西方代議制的不足。“權能分治”理論提出后孫中山監察思想取得了巨大發展,形成了“政權”和“治權”的雙向監督。但革命發展的需要迫使孫中山在監察中引入“黨權”,最終其監察思想發展為包括“政治系統”和“黨治系統”雙軌并行,“政權”“治權”和“黨權”三方參與的監察體系。
(一)“政治系統”中“治權”的內部監督和人民的外部監督
1924年孫中山三民主義的演說標志著“權能分治”理論成熟,其目的是要解決政府和人民之間的沖突。“權能分治”可以概況為:“政權”和“治權”分別由政府和人民掌握。兩者各有職責,互不相擾;人民在“縣自治”和國民大會中使用選舉權、罷免權、創制權和復決權直接管理國家的政治;但人民多是“不知不覺”的,要造就“萬能政府”就要依靠有能力的“專門家”放手使用“治權”;為了避免“專門家”可能侵害“政權”,孫中山強調“專門家”要有道德。因此,“權能分治”事實上形成了“雙向監察機制”,即在“治權”系統內的監察院施行自上而下的監督;在“治權”系統外,人民掌握“政權”施行自下而上的監督。
在“治權”系統內,“五權憲法,分立法、司法、行政、彈劾、考試五權,各個獨立”。在職權上,監察院行使監察權,“是裁判官吏的機關”,“專管監督彈劾的事”。對四院官員的失職行為,監察院可以向國民大會彈劾。為保證監察權裁判官吏的權威,孫中山主張“彈懲一體”,既對各級官員有彈劾權,又對于違法犯罪的官員有懲戒權。孫中山雖然沒有說明是否在地方建立監察院,但按照組織建設的邏輯來說,中央有了監察院,地方也應建立對應的下級機構行使監察權監督地方政治,這樣監察制度才是完整的。
在“治權”系統外,人民對于“治權”的監督主要通過施行“直接民權”的“縣自治”和“間接民權”的國民大會來實現自下而上的監督。孫中山認為歐美政體是由人民選舉產生代議士,人民通過代議士間接管理國家。中國在民國初期也采用了代議政體,但是代議士卻貪贓枉法成了被人民唾棄的“豬仔議員”。鑒于此,孫中山認為人民應該有權直接管理國家,只有這樣才算完全的民權政治。具體起來,就是在作為基層政權的縣,人民有選舉、罷免、創制、復決四個權力直接管理本縣政治。實現自治的縣就可以選舉國民大會的代表組成最高權力機關國民大會,并制定五權憲法建立五院。“五院皆對國民大會負責。……監察院人員失職,則國民大會自行彈劾而罷黜之。國民大會職權,專司憲法之修改,及制裁公仆之失職。”這實際是在五院之上設置了一個最高權力機關進行監督。
(二)并行的“黨治系統”對“治權”的監督
孫中山認為人民大多數是“不知不覺”的阿斗,要實現這樣的四萬萬人都做皇帝就必須由“先知先覺”的革命黨來對他們進行訓導,規定“自革命軍起義之日至憲法頒布之時,名曰革命時期;在此時期之內,一切軍國庶政,悉歸本黨負完全責任”。這客觀上促使孫中山在“政治系統”外建立了一個與其并行的“黨治系統”,進而提出了“黨權”參與監察的需要。
“黨權”參與監察最早可以追溯到“二次革命”失敗后孫中山建立的中華革命黨。孫中山認為革命失敗是因為黨員成分不純導致的革命黨紀律渙散、“黨權”無力,而要提升“黨權”就要加強黨內監察。孫中山在中華革命黨內按照五權憲法模式建立了包括監察院在內的五院,規定黨內監察院負責監察黨務、黨員服務和黨員行為。
但此時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黨依然紀律渙散,真正讓“黨權”參與監察獲得進一步發展的是孫中山決定“以俄為師”。孫中山認為中俄兩國都進行了革命,結果卻是一勝一敗,原因在于布爾什維克黨的黨員有戰斗力,要想革命勝利就必須學習俄國革命的方法。孫中山學習俄國布爾什維克黨的方法就是“以黨治國”,即施行“黨治”。孫中山解釋說“黨治”是要“把黨放在國上”,即革命成功以后由黨來掌握國家政權,黨在國家中具有至高的、強制性的權力地位。
“黨治”不可避免的要黨員參與政權、掌握權力。孫中山雖然強調“黨治”不代表完全用本黨黨員來治國,但是他也強調“本黨黨員若是確為人才,能勝大任的,自當優先任用,以便實行本黨的主義”。事實上,一個政黨為保證本黨的執政地位,往往也會優先任用本黨的黨員參與政權,孫中山設想的“以黨治國”自然不能避免這一問題。他把黨員按照參加革命的先后順序和功勞分為“首義黨員”“協助黨員”和“普通黨員”,并規定在革命勝利后的政權中,首義黨員可以參政、執政,協助黨員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而普通黨員僅有選舉權。為保證黨員的戰斗力,孫中山引進了布爾什維克黨自中央到地方在執行委員會外普遍設置監察委員會的組織模式。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通過決議,從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中央、省、縣和區四級監察委員會,從而構建了一個完整的監察體系對擔任國民政府各級官員的黨員進行監督。
二、孫中山“黨治”監察思想下的實踐表現
孫中山因過早離世,其監察思想的大規模應用,需要繼承孫中山“遺志”的國民政府去實踐。但“黨治”下的“黨權”卻不斷對屬于“治權”的監察權進行干擾,并對屬于“政權”的監察權進行弱化,導致孫中山監察思想在實踐中發生了變異。
(一)“黨權”干擾屬于“治權”的監察權
國民政府以孫中山“遺教”作為“黨治”的根本大法。有學者指出:“研究國民政府的組織和地位的時候,絕對不可忘卻這個‘黨治的事實。”而“黨治”也為“黨權”干擾“治權”的監察權提供了依據。首先,監察院的權力來自于國民政府,而國民政府的權力來自于國民黨。1928年10月頒布的《訓政綱領》則以法律形式對國民政府權力來自于國民黨進行了確認。《訓政綱領》規定訓政期間“政權”由國民黨代行,“治權”由國民政府行使;其次,在“黨治”下國民政府的主要官員,包括國民政府主席、委員、五院院長和正副院長,皆由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選任,而這些“國民政府中樞要員,同時亦即國民黨之干部人物,故國民黨對于國民政府能操縱裕如”。包括監察委員在內的國民政府官吏仍需監察院院長提請國民政府主席任命。此外,在監察院的內部還設置政治宣傳科負責宣傳國民黨黨義及指導各黨員與官吏遵守黨規;再次,“國民黨之政綱與政策,皆由國民黨為之供給,蓋一切政綱政策,由國民黨發源,中政會灌輸,國民政府執行”。國民政府成了貫徹國民黨政綱政策的執行機關,因此國民黨中央和地方的省、市、縣監察委員會對同級政府的施行方針及政績有根據政綱政策進行審核的權力。
自從孫中山“以俄為師”學習布爾什維克黨的“黨治”模式,中國在政治體制上便由單軌制轉向了“黨治系統”和“政治系統”并行的雙軌制,這一轉變不僅因黨政互動而大大增強了政治的控制力,同時也帶來了“政治系統”組織成本的增加。①這極容易使國民黨把“黨權”和“治權”的監察權混為一體。作為國民黨領袖之一的汪精衛對此的態度最具典型性。汪精衛曾表示在訓政時期的一切權力都要向黨集中,“黨治”下沒有任何機關不依靠和服從于黨的。②而黨政監察權混為一體的后果就是使屬于“治權”監察權的完整性遭到破壞。例如,孫中山設想的“治權”內的監察權是“彈懲一體”的,但懲戒權的歸屬在民國時期卻幾經變遷。1925年廣州國民政府初建時,本屬于監察院的懲戒權先后由平級的懲吏院、政審院行使,后因懲吏院、政審院難以建立,懲戒權才最終劃歸監察院,但懲戒范圍仍不涉及刑事案。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的成立,一方面使監察院的建設更加規范,另一方面也使權力進一步集中。1928年10月頒行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雖然規定監察院為國民政府最高監察機關,但其職權僅保留了彈劾權、審計權。監察院的懲戒權則按照懲戒對象歸屬不同的懲戒機關。缺少懲戒權的監察院行使監察的效果自然不盡人意。據統計,從1931年到1937年,被監察院彈劾的有1800名貪官污吏,但只有268人被法院或者其他機構判定有罪,其中214人根本未受任何懲戒,41人僅受到很輕的處罰,只有13人是真的被罷黜。”
(二)“黨權”對屬于“政權”的監察權力的弱化
按照孫中山的設想,國民黨訓導人民就如伊尹訓太甲一般,賢德的國民黨最終會將屬于人民的權力完璧歸趙。這并非是孫中山沒有認識到權力具有侵蝕性,他的解決辦法是要用“德”來化解。他認為在“德”的作用下,“黨權”和“政權”都能良好運行。但國民黨在獲得“政權”和壟斷“治權”以后,并沒有選擇還政于民,而是進一步將權力向“黨權”集中。為避免“政權”制約“黨權”,自然選擇對“政權”的監察權力進行弱化,特別是弱化憲法規定的國民大會權力和人民的自由、權利。
憲法作為保障人民權利的最根本法律,面對“黨權”對屬于“政權”的監察權力的弱化,憲法成了人民能否監督、制衡“黨權”的關鍵。但《中華民國憲法草案》所規定的國民大會和孫中山所設計的國民大會存在一定的出入,規定國民大會的權力包括選舉和罷免總統、副總統、立法院和監察院的正副院長、兩院委員;創制、復決法律和修改憲法的權力;以及憲法賦予的其他權力。國民大會的權力被弱化,特別是國民大會只能復決法律,總統行使有關預算、宣戰、媾和、條約等權力。此外,作為國民大會常設機構的國民大會委員會也被取消,其職權分屬國民大會、五院院長會議和立法監察兩元聯席會議。關于國民大會的代表,《國民大會組織法》和《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法》規定代表人數1200名,年滿20歲的中華民國公民有選舉權,但要經過宣誓。國民黨的中執委和中監委的委員為當然委員,候補中央執監委員等特許人員可以列席,而各選舉人無權推舉候選人,反由國民政府部分或全部指定。③以上都說明了人民試圖通過選舉和借助國民代表大會行使“政權”是極為困難的。
關于人民的自由和權利,《中華民國憲法草案》規定中華民國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擁有包括身體、出版、言論、集會等自由,還有選舉、罷免、創制、復決等權利。為了弱化“政權”的制約,還規定凡人民的自由及權利依據特定的法律可以加以限制。法學家邱漢平對此批評說:“照現時憲草的規定,就是憲法公布之后,中國人的權利保障仍是一個零。”
三、孫中山“黨治”監察思想失效的反思
通過對孫中山“黨治”下監察思想的失效進行反思,發現了其監察思想中的內在邏輯矛盾,認識到黨的自身建設和接受監督的重要性,這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監察制度取得進步的原因。
(一)孫中山“黨治”下監察思想中的內在邏輯矛盾
孫中山設計的監察制度在國民黨的“黨治”下變為了掩飾獨裁專制的“裝飾物”,而根本原因在其監察思想內在邏輯的矛盾。孫中山一生都在追求“主權在民”,強調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但是他又認為這個主人是“不知不覺”的,需要實行“黨治”,一邊代替人民執政,一邊訓導人民。再加上“黨治”的“專門家”多出自黨,這就使得其監察制度能否實行都依賴于黨。
但國民黨在全國執政后的自身建設沒有做好。國民黨1927年的清黨導致自身的組織系統處于癱瘓中,再加上蔣介石重視軍事而輕視黨建,致使國民黨自身的制度化和組織化的重建工作處于放任、停滯甚至退化的狀態。此外,國民黨執政后的黨民關系轉變為控制體制,但卻忽視了權力帶來的腐敗問題。④處于至高地位,又腐化、放任的“黨權”自然不會接受監督,單單依靠“德”去喚醒國民黨進行自我約束,執政為民,這無異于癡人說夢。
(二)進步與成就: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監察制度
中國共產黨作為代表人民利益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認識到要保證黨不腐化就要加強黨的建設和接受監督。中國共產黨在國家治理中同樣重視黨的領導地位,強調黨領導一切。但中國共產黨并沒有將自身排除在監察之外,而是整合各種監察資源形成了黨領導下的、專責國家監察職能的國家監察委員會。國家監察委員會作為國家最高監察機關依照法律獨立行使監察權,不受任何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且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規定的范圍廣泛的公務人員和相關人員進行監督,其中就包括對中國共產黨實行監督。
此外,中國共產黨不斷加強黨的建設,密切與群眾的聯系,讓人民通過制度安排行使權利來監督政治。一方面,不斷堅持和完善作為最高權力機關的人民代表大會和作為其執行機構的常務委員會,保障其職權不受削弱。人民有權選舉代表,并依法行使權力對政治進行監督。另一方面,切實實行基層群眾自治,讓人民廣泛參與到政治中來,做到依靠人民、相信人民,發揮人民對權力監督的主體地位。
四、結語
孫中山監察思想中的“政治系統”和“黨治系統”雙軌并行,“政權”“治權”和“黨權”三方參與的多元立體的監察體系,較同時代的監察制度有了巨大飛躍,有其思想進步性。但由于“黨治”下的國民黨黨建混亂和缺乏監督,其存在的內在邏輯矛盾使孫中山多元立體的監察體系走向失效。通過反思其不足,中國共產黨從中汲取歷史經驗,不斷加強對自身的建設和監督,進而使監察制度發揮了顯著的反腐成效。
[注釋]
①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 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M].北京:華文出版社,2010:226.
②國聞周報[N].1934-11-5.轉引自徐德剛.論訓政初期國民黨黨治下的行政監察機制[J].求索,2012(03):250.
③王世杰,錢端升.比較憲法[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480-481.
④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 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M].北京:華文出版社,2010:141.
[參考文獻]
[1]孫中山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孫中山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3]牛彤.孫中山憲政思想研究[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3.
[4]錢端升等.民國政制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5]龔詠梅.孫中山的監察理論及其實踐[J].蘇州大學學報,1995(04).
[6]王英津.孫中山五權分立思想新探[J].文史哲,2001(04).
[7]劉云虹.論孫中山的監察思想[J].東南文化,2004(05).
[8]牛彤.孫中山“權能區分”理論探析[J].學術界,2005(03).
[9]胡斌.孫中山的監察思想概述[J].湖北教育學院學報,200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