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力分散時(shí)代,沒(méi)人能幸免于“屏幕”
何安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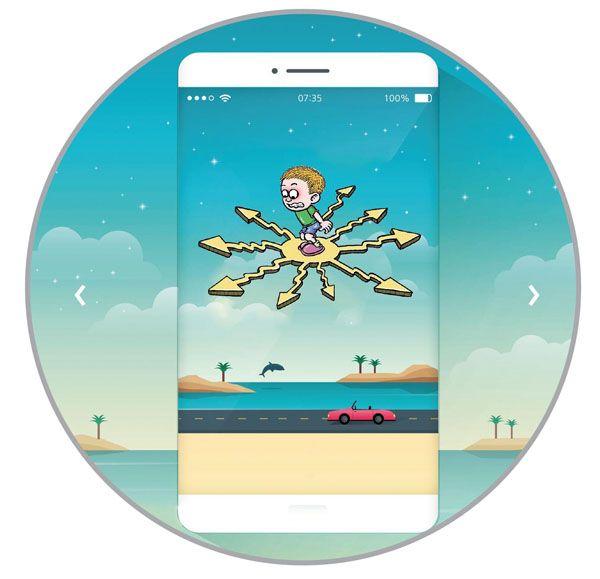


在移動(dòng)互聯(lián)網(wǎng)時(shí)代,保持“隨時(shí)在線”的我們,所有體驗(yàn)可能是比較雷同的,一方面既可以輕松與朋友、家人和同事聯(lián)系,并獲取信息、游戲、音樂(lè)或視頻,另一方面卻可能失去耐心,在社交媒體上紛亂、撕裂的觀點(diǎn)中變得浮躁、焦慮乃至“虛無(wú)”,而這些恰恰構(gòu)成了社交媒體的流量基礎(chǔ)。我們或許認(rèn)為只要能用知識(shí)對(duì)此反思、批判,或重新融入現(xiàn)實(shí)生活,就可以逃離“隨時(shí)在線”。
然而,這并沒(méi)有那么容易。傳播學(xué)家羅伯特·哈桑就認(rèn)為,他作為一位學(xué)者可能有能力反思甚至逃離這一切,實(shí)際上最終卻沒(méi)做到。他轉(zhuǎn)而觀察這一切,在他的《注意力分散時(shí)代:高速網(wǎng)絡(luò)經(jīng)濟(jì)中的閱讀、書(shū)寫(xiě)與政治》一書(shū)中,從哲學(xué)和傳播學(xué)的交又領(lǐng)域?qū)?shù)字生活進(jìn)行反思。在這個(gè)過(guò)程中,他看到,“隨時(shí)在線”讓人集中注意力的能力也在下降,無(wú)法進(jìn)行長(zhǎng)閱讀,無(wú)法深入思考。
沒(méi)有人能幸免于“屏幕”
記者:是什么促使你寫(xiě)下《注意力分散時(shí)代:高速網(wǎng)絡(luò)經(jīng)濟(jì)中的閱讀、書(shū)寫(xiě)與政治》這本書(shū)?
羅伯特·哈桑:我寫(xiě)這本書(shū)的主要目的是針對(duì)我在數(shù)字生活中的處境,進(jìn)行一種環(huán)境療法(或者說(shuō)這至少是一種自我分析和診斷)。作為一名研究數(shù)字媒體進(jìn)程的教師和理論研究者,我一直認(rèn)為,我可以免疫于那些自己向?qū)W生和讀者所描述的網(wǎng)絡(luò)成癮、疏離感、商品化等弊病;作為一名學(xué)者,我曾經(jīng)以為自己可以凌駕于這一切之上——因?yàn)槲抑獣运鼈兌际侨绾芜\(yùn)作的。
但是,從2016年開(kāi)始,我開(kāi)始意識(shí)到自己根本無(wú)法幸免,社交媒體的力量日趨強(qiáng)大和成熟,我也被納入其中。前面我所列舉的種種癥狀,實(shí)際上就是一種日益增長(zhǎng)的“慢性注意力分散”。在針對(duì)注意力分散的研究中,我注意到,數(shù)以百萬(wàn)計(jì)的人們脫離了有血有肉的現(xiàn)實(shí)生活,進(jìn)入了數(shù)字模擬的世界之中,而這也是我正在經(jīng)歷的事情。因此,我希望以自我反省的方式,使自己可以從那些已經(jīng)成為嚴(yán)重困擾的東西之中解脫出來(lái)。
記者:我們應(yīng)該如何理解注意力分散?
羅伯特·哈桑:我們?cè)絹?lái)越理解那些和互聯(lián)網(wǎng)有關(guān)的商業(yè)模式,它們針對(duì)我們的興趣點(diǎn)進(jìn)行了精心設(shè)計(jì),使得我們易于接納。不管是臉書(shū)、微博、谷歌還是百度,它們的商業(yè)模式都是進(jìn)行數(shù)據(jù)收集、數(shù)據(jù)分析,以及將這些數(shù)據(jù)出售給第三方(通常是廣告商)。
不管是你還是我,讓我們盡可能保持在線狀態(tài),對(duì)他們的成功至關(guān)重要。工程學(xué)被提升到了一個(gè)全新的高度,并且吸納了從心理學(xué)、哲學(xué)到生物化學(xué)和神經(jīng)科學(xué)的各種專業(yè)知識(shí)。在尋找利潤(rùn)的過(guò)程中,他們聯(lián)合起來(lái),對(duì)全人類進(jìn)行了一場(chǎng)聲勢(shì)浩大的實(shí)驗(yàn),沒(méi)有人知道這將走向何方。
在線上花費(fèi)越來(lái)越多的時(shí)間,意味著我們與現(xiàn)實(shí)世界的聯(lián)系減少了——而這是在我們進(jìn)入數(shù)字時(shí)代之前,一種更加有意義的生活方式。這個(gè)世界給了我們社會(huì)、文化和政治生活,而這些社會(huì)、文化和政治生活建立在我們身體的基礎(chǔ)之上,建立在物質(zhì)性和連續(xù)性的基礎(chǔ)上,能夠以觸摸、感覺(jué)、嗅覺(jué)和味覺(jué)等無(wú)數(shù)種方式所感知。當(dāng)我們的眼睛盯著一個(gè)玻璃屏幕時(shí),這一切都被封閉起來(lái),我們與原本充實(shí)的生活脫節(jié)了。
如果你心不在焉,你就會(huì)被大數(shù)據(jù)找到
記者:學(xué)者哈特穆特·羅薩所說(shuō)的“加速的社會(huì)”之所以會(huì)出現(xiàn),是因?yàn)楝F(xiàn)在的機(jī)器,尤其是計(jì)算機(jī)比以往任何時(shí)候都奔跑得更快。正如你所說(shuō),“我們認(rèn)為可以使我們更加自由的機(jī)器,卻在時(shí)間上奴役著我們。”同時(shí),赫伯特·西蒙指出,豐富的信息可能會(huì)導(dǎo)致注意力不足。那么,人們應(yīng)該如何面對(duì)“加速的社會(huì)”,又該如何面對(duì)因此導(dǎo)致的“慢性注意力分散”?
羅伯特·哈桑:西蒙說(shuō),從本質(zhì)上講,信息豐富是對(duì)我們有限的認(rèn)知能力的挑戰(zhàn)。我們可以選擇生活在一個(gè)永遠(yuǎn)無(wú)法集中注意力的環(huán)境之中,讓自己被互聯(lián)網(wǎng)及其應(yīng)用程序的設(shè)計(jì)方式所驅(qū)動(dòng);或者我們也可以拒絕這樣做。
我們需要認(rèn)識(shí)并理解在這個(gè)巨大的實(shí)驗(yàn)之中發(fā)生在我們身上的事情,并對(duì)此說(shuō):不。然后,我們需要嘗試控制我們的數(shù)字生活。這可以從抉擇在網(wǎng)上看到、聽(tīng)到、消費(fèi)的東西開(kāi)始,在自己訪問(wèn)的網(wǎng)站、使用的應(yīng)用程序、參與的網(wǎng)絡(luò)社群中找到那些真正重要的內(nèi)容。
抉擇意味著在網(wǎng)絡(luò)的控制下保護(hù)自己,進(jìn)行反擊并奪回控制權(quán)。這并不容易,因?yàn)榫W(wǎng)癮是真實(shí)存在的,而且,在許多方面,我們也離不開(kāi)數(shù)字生活。但不管怎么說(shuō),除非我們想任由數(shù)據(jù)公司擺布,像他們網(wǎng)絡(luò)中的一個(gè)節(jié)點(diǎn)一樣行事,我們都應(yīng)該去嘗試擺脫這種控制。
記者:但更多的人并沒(méi)有認(rèn)識(shí)到這是一種危機(jī)。正如你所說(shuō),這些危機(jī)隱藏在閱讀、寫(xiě)作和認(rèn)知中。
羅伯特·哈桑:有數(shù)以十億計(jì)的人們從未經(jīng)歷過(guò)數(shù)字時(shí)代之前的生活:在數(shù)字時(shí)代到來(lái)之前,西方有著長(zhǎng)達(dá)三百多年的歷史——在中國(guó)則更久,由印刷文化主導(dǎo)著教育、政治、媒體等領(lǐng)域。但這些人不可避免地將會(huì)成為世界上的大多數(shù)。對(duì)他們來(lái)說(shuō),線上生活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信息網(wǎng)絡(luò)的商業(yè)模式:娛樂(lè)、社交網(wǎng)絡(luò)、教育和工作。
這些都是我們可以從網(wǎng)上獲得的。但對(duì)于數(shù)據(jù)公司而言,這些設(shè)計(jì)都是為了收集他們所需要的數(shù)據(jù)而建立的。數(shù)據(jù)公司收集我們的個(gè)人信息,并將這些信息出售給第三方。所以,線上生活是商業(yè)化的,以消費(fèi)化和貨幣化為導(dǎo)向。
十多年前,尼古拉斯·卡爾告訴我們,這樣的數(shù)字生活讓我們變得愚蠢。它讓我們專注于生活中瑣碎的、當(dāng)下的、非本質(zhì)的和非反思的方面。就其本身而言,這些并不是壞事,但它們正在日益主宰我們的行為、生活和思考方式。
記者:既然數(shù)字生活讓我們的思想變得更“膚淺”。那么,是否意味著“持續(xù)在線”的狀態(tài)是一種愚蠢的行為?
羅伯特·哈桑:英國(guó)“野蠻人”樂(lè)隊(duì)的歌曲《保持沉默》中有一句歌詞是這樣的:“我們生活在一個(gè)充滿刺激的時(shí)代。如果你很專注,你會(huì)很難接近。如果你心不在焉,你就可以被找到。”注意力難以集中使得我們很容易被數(shù)據(jù)公司操控,讓我們?yōu)樗麄兎?wù),為他們提供利潤(rùn)。我不知道這是不是愚蠢,但這顯然是一種輕信。我們輕易地把自己的信任放在了并不了解的數(shù)字網(wǎng)絡(luò)進(jìn)程之中——甚至數(shù)據(jù)公司自己也不了解他們?cè)谧鍪裁矗@超出了他們的短期目標(biāo)。
記者:越來(lái)越多的人們開(kāi)始認(rèn)為,看似免費(fèi)的互聯(lián)網(wǎng)世界實(shí)際上讓我們付出了沉重的時(shí)間代價(jià)。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已經(jīng)成為互聯(lián)網(wǎng)的無(wú)薪雇員。全新的“網(wǎng)絡(luò)時(shí)間”已經(jīng)脫離了我們的掌控,我們?cè)趺床拍苡懈嗟倪x擇呢?
羅伯特·哈桑:這個(gè)觀點(diǎn)已經(jīng)成為陳詞濫調(diào),但確實(shí)如此:“你不為產(chǎn)品付費(fèi),那你就是產(chǎn)品。”
如果我們沿著免費(fèi)應(yīng)用程序的道路前進(jìn),這將會(huì)縮小我們擁有的選擇和可能性。商業(yè)互聯(lián)網(wǎng)(或者說(shuō)表層網(wǎng)絡(luò))只是我們每個(gè)人所能訪問(wèn)的信息,以及進(jìn)行通訊的一小部分。如果我們僅僅去簡(jiǎn)單追隨TikTok、臉書(shū)、微博等數(shù)據(jù)公司的商業(yè)趨勢(shì),我們的個(gè)人和社會(huì)視野就會(huì)越來(lái)越小。
沖突、撕裂,是社交媒體賴以生存的基礎(chǔ)
記者:從寫(xiě)作開(kāi)始,科技的發(fā)展讓我們讀寫(xiě)越來(lái)越快,書(shū)寫(xiě)和閱讀的關(guān)系進(jìn)入到一個(gè)全新的、緊張的、充滿焦慮的階段。在加速發(fā)展的世界里,這種媒介節(jié)奏對(duì)我們的認(rèn)知和思維能力顯然是一個(gè)巨大的挑戰(zhàn)。你如何看待這一問(wèn)題?
羅伯特·哈桑:首先你必須要明白,寫(xiě)作和閱讀本身就是一種技術(shù)。我們已經(jīng)習(xí)慣了它作為我們思考和表達(dá)自己的一部分,作為我們思考過(guò)程的一部分,以至于我們忘記了它原本是我們發(fā)明的、我們必須去學(xué)習(xí)的東西。
識(shí)字社會(huì)的文化(即寫(xiě)作社會(huì)),是以印刷品為基礎(chǔ)的文化。它的希望、夢(mèng)想、意識(shí)形態(tài)、宗教、技術(shù)和科學(xué)成就,都是通過(guò)報(bào)紙、書(shū)籍、雜志、期刊、地圖、漫畫(huà)等形式而得以實(shí)現(xiàn)的。這種文化有屬于自己的“時(shí)間”:時(shí)鐘上的時(shí)間,以及印刷媒體生產(chǎn)、發(fā)行和消費(fèi)的時(shí)間。
這一時(shí)期的問(wèn)題是,它是隨著識(shí)字率的提高,以及被稱為“閱讀大腦”或印刷文字大腦的發(fā)展而逐漸形成的。核磁共振掃描顯示,“閱讀大腦”是通過(guò)閱讀紙上印刷的文字以某種方式構(gòu)成的。我們之所以知道這一點(diǎn),是因?yàn)檫@些掃描結(jié)果可以與那些主要在屏幕上閱讀文本的人進(jìn)行比較,后者顯示出了被稱為“數(shù)字大腦”的結(jié)構(gòu)。
這要如何理解呢?“閱讀大腦”是由紙上的印刷品雕刻而成的,它的特點(diǎn)是突觸的形成更加牢固,突觸是讓神經(jīng)元相互傳遞化學(xué)信號(hào)的連接點(diǎn)。這些突觸連接構(gòu)成了深度記憶和長(zhǎng)期專注的能力。換句話來(lái)說(shuō),閱讀紙上的文字可以提高記憶力和注意力。相比之下,數(shù)字屏幕上界面的作用恰恰相反,主要從屏幕上閱讀,實(shí)際上削弱了突觸連接,使大腦在記憶力和注意力集中程度方面發(fā)展不足。因此,“數(shù)字大腦”比“閱讀大腦”更加膚淺,對(duì)任何具有深度或長(zhǎng)度很長(zhǎng)的主題把握能力也較低。這些方面都是壞消息。
幸運(yùn)的是,實(shí)驗(yàn)表明,因?yàn)槠聊婚喿x而削弱的突觸連接可以被逆轉(zhuǎn)。也就是說(shuō),如果一個(gè)基于屏幕進(jìn)行文本閱讀的閱讀者將屏幕切換為印刷品,那么突觸連接,以及他們的記憶力和注意力集中程度可以得到快速提升。不過(guò),我們今天所面臨的問(wèn)題是,數(shù)據(jù)公司迫使我們不斷進(jìn)入數(shù)字世界,我們變成了只擁有短期記憶的“掠奪者”。
記者:在數(shù)字時(shí)代,閱讀、寫(xiě)作和交流之間的新關(guān)系是什么?
羅伯特·哈桑:閱讀和寫(xiě)作已經(jīng)數(shù)字化。我們閱讀到的東西更多了,但是能夠被記住的卻更少了。這是因?yàn)樾畔⒘窟^(guò)大,而且還在源源不斷地增加。我們所依賴的記憶是工作記憶(是一種對(duì)信息進(jìn)行暫時(shí)加工和貯存的容量有限的記憶系統(tǒng)),也就是我們現(xiàn)在消耗和使用的東西,但這種記憶事后很難進(jìn)行回憶。因?yàn)槲覀兊拇竽X中的突觸連接—那些通過(guò)近距離和深度閱讀而增強(qiáng)的突觸連接,在我們通過(guò)屏幕進(jìn)行閱讀后就會(huì)開(kāi)始萎縮。
寫(xiě)作越來(lái)越成為一種具有短信特征的表達(dá),以推特或新浪微博等短格式應(yīng)用為例,這些應(yīng)用程序保持了我們的工作記憶并且缺乏反思能力,而其導(dǎo)致的結(jié)果是交流的退化。正如我們?cè)谏缃黄脚_(tái)上看到的那樣,這種交流會(huì)退化為消極、虛榮的言論,或者謾罵、誹謗以及其他所有可能導(dǎo)致沖突的交流情感——因?yàn)闆_突正是社交媒體賴以生存的根本。
摘編自微信公眾號(hào)“新京報(bào)書(shū)評(píng)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