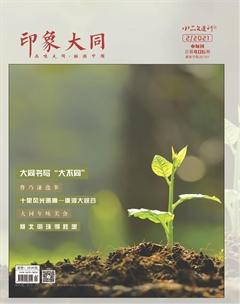年之樂
司響

過年,一個中國獨(dú)有的——一年之中最重要的這一民間習(xí)俗,在逐漸騰飛的現(xiàn)代化社會和人們愈加豐富的業(yè)余生活中慢慢地淡化了,它似乎不再是那么地令人期待,盡管有著火紅的燈籠,喜慶的春聯(lián),以及最討小孩子們歡喜的一塊塊麻糖、一個個肉餡餃子,但在平日里就很充裕的物質(zhì)基礎(chǔ)上,這也僅僅成為了一個民俗,而似乎只有老人家們,還在堅守著,那一份企盼和羈絆。
往昔,雖擁有了和平,可是各種生活上的壓力化作了人們內(nèi)心最深處的痛楚。饑荒,瘟疫,多子,多難,化作一位歲月的匠人,在老一輩人的臉上,雕刻出了風(fēng)霜的痕跡,使他們的面龐,失去了光彩,倒像是個風(fēng)干的橘子。以前,我并不理解這些深奧的問題,可是通過姥姥姥爺,我逐漸明白了。
那時,正是“文革”時期,再加上家境的窘迫,剛讀完高中的姥姥放棄了繼續(xù)完成學(xué)業(yè)的選擇,回到了家鄉(xiāng),認(rèn)識了姥爺,姥爺是在城里當(dāng)兵的,姥姥便做了會計,由于姥姥姥爺?shù)碾p親都是農(nóng)戶,根本沒有固定的收入,只能依靠姥姥姥爺。后來又有了媽媽、姨媽,這些來自家庭的開銷迫使他們省吃儉用,以微薄的薪水來養(yǎng)活這個家。
苦盡甘來,媽媽和姨媽終于長大了,物質(zhì)條件逐漸豐富起來,姥姥姥爺卻在該享福的時候,仍然抱有那種難以割舍的態(tài)度。早年清苦的生活使姥姥和姥爺養(yǎng)成了“能省就省”的作風(fēng),從姥爺用了數(shù)十年的眼鏡盒,到姥姥晚上為了省電而從不開燈炒菜的習(xí)慣,他們注重生活中每一處他人難以察覺的細(xì)節(jié),同時謝絕來自子女的一份份孝心,卻又一味地為子女付出著,他們互相牽絆,時刻警醒著對方和自己,仿佛“不能享清福”這一概念已成為了刻在心底里的條約。可每當(dāng)假期來臨,抑或逢年過節(jié),我和媽媽去姥姥家住的時候,姥姥便會破例,無論早、中、晚,姥姥姥爺都會烹飪魚肉和最拿手的飯菜,像招呼客人般似的盛情款待。我理所當(dāng)然地享受著這一切,直到和姥姥的一次談話,點(diǎn)醒了我。
那次只是偶然談起了個人愛好,姥姥說她,最喜歡過年,因為這樣,就可以見到我們,最愛吃的食物——是餃子。我在驚訝姥姥喜歡這平常我們已經(jīng)吃膩的餃子之余,更多的,是疑惑不解。逢年過節(jié),家家戶戶都是要吃餃子的,每回姥姥都會包葷素兩餡的餃子,所以會剩下很多,姥姥卻像預(yù)算好似的,挨個打包,分塞在姨媽和媽媽的手中,說拿回去吃。但那是姥姥最愛吃的東西啊!為什么這樣,無私地奉獻(xiàn)給后人?我沒有再繼續(xù)追問這看似深奧,實(shí)則簡單,卻又蘊(yùn)含著深刻內(nèi)涵的問題,答案,已然在我心底。其實(shí),我們都早已厭倦了吃餃子,可這是一件多么重要的社會活動,讓一家人,相聚在了一起。那份蘊(yùn)含在年味中哪怕是對于我來說隔了一代的親情,依然擁有火熱的溫度,這不正是父母對子女愛的體現(xiàn)嗎?我頓悟了。世間,便是這樣構(gòu)成的。客觀的外界社會所帶來的影響也好,主觀上這種精神的傳承也好,又或許老一輩的人都是這樣,但又有誰能不被這種精神打動呢?
又要過年了,我一定要抓緊完成學(xué)習(xí)任務(wù),多去拜訪幾次姥姥姥爺,送去幾份祝福,破上幾次例,包上幾頓餃子。他們自己,也就能多吃上些少有享受的東西,大家,都很快樂。
自此,我明白了老人為什么會期待過年。過年本身,并不值得期待,而是它被賦予了濃濃的親情,濃濃的愛啊!
我同老人,一齊期待著過年。
學(xué)校:大同市博盛中學(xu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