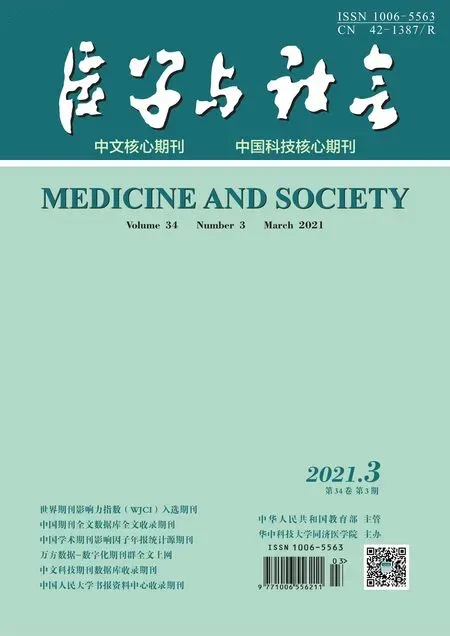基于醫學人類學思考的女性身體四重空間與產科實踐
安姍姍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北京,100084
過去30年間,中國住院分娩率逐年上升,與此同時,醫院內產科技術的成熟導致我國剖腹產率也隨之上升,中國分娩環境已經全面步入了現代產科階段。雖然剖腹產在中國有一定的市場,但由于世界衛生組織的持續警告及國際社會對分娩醫學化的不斷批判,2010年國家政策開始干預被醫學化的分娩環境,提出了促進自然分娩、降低剖腹產率的口號。中國各大醫院積極響應國家政策的號召,嚴格控制剖腹產的手術指征,且紛紛設立了可進行自由體位、家屬陪產的醫院內家庭式分娩中心。2015年以后中國剖腹產率開始呈現出下降趨勢。但值得注意的是,城市剖腹產率已大幅下降,且部分精英女性不再依賴主流住院分娩體系,自主選擇并實踐居家分娩模式,與之相對,農村剖腹產率卻在逐年遞增[1]。顯然,針對同一生理功能——分娩,女性對圍繞著身體構建的分娩環境和孕產行為有著不同的認知和理解[2]。中國孕產行為具有后現代、現代和前現代并存的特點[3],多時代并存而非過渡是中國不同于歐美及日本最大的特征。見表1。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了中國女性對孕產行為呈現出不同理解和認知呢?既有研究并沒有給出確定答案,因為女性特殊經驗在人類和歷史的大部分話語中都是缺席的[4],日常生活中的身體話題在社會科學領域也總是不在場。本研究以中國女性的分娩體驗為焦點,從醫學人類學視角切入,總結中國女性身體多重空間及其互動,這樣的互動將便于我們理解中國孕產行為認知體系為何呈現多時代并存的特點。

表1 分娩環境在各個時代所呈現的特點[2]
1 身體空間的界定
自現代產科模式確立及普及以來,圍繞孕產身體的研究集中在自然科學領域。相比于自然科學領域,社會文化領域的研究起步較晚,且集中于從哲學視角探討身心邊界,從社會學視角分析社會制度變遷、權力關系等宏觀敘事,缺乏對日常生活中的個體體驗作細微描述與分析[5]。醫學人類學透過對分娩實踐的詳細記錄,刻畫出身體在不同文化語境下的象征、隱喻和符號作用,孕產行為的社會功能,及人們建立在不同的身體觀上選擇且實踐的孕產期診療行為[6]。舍佩爾·休斯和瑪格麗特·洛克從醫學人類學視角切入,基于日常生活中生物性身體提出了身體三重空間理論,他們認為身體是在多種話語中被構建出來的個體或者有共性的群體,并對笛卡爾提出的身心二元理論進行了反駁,提出人的身體和精神是一體兩面,身體既是自然的,也是社會文化的產物,同時又被固定在特定的歷史時刻和話語中。具體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個體化身體,即現象學中所表述的獨立于其他個體而存在的自我經歷的身體;第二,社會化身體,即遵循象征和結構主義中對身體的表述,帶有“健康”或“疾病”標簽的社會為理解身體提供了另一種模型;第三,政治化身體,即國家或機構在生殖和性、工作和休閑、疾病和其他越軌行為等方面,對身體的管制、監督和控制[7]。身體三重空間理論主要用來分析處于“健康-疾病”之間的身體,“健康-疾病”不再被視為身體機能勞損的偶然事件,而是與個人經歷、生活方式、社會關系等緊密相關,并象征著某種特定社會秩序、規范體系,身體是否健康或疾病不再僅考慮其肉體狀態,而是將自我感知、社會關系等納入視野。
隨著分娩現代化和醫學化的推進,分娩場所、分娩行為及女性身體都被納入醫學話語中,從普通產檢到唐篩、大小排畸,從孕期到產后,產婦身體一直游走于“健康與疾病”“正常與異常”之間。 簡而言之,以身體為載體存在的肉體與精神,乃至以此延伸出的生物與符號、個體與社會并非二元對立,而是一元整體或二元互補。身體三重空間理論打破了肉體與精神、個體與社會之間的明顯邊界,為挖掘“懷孕”這個特定場域中身體所折射出的不同分娩認知體系提供了多元視角。
然而,孕產身體區別于疾病身體,它不是需要被預防或治療的實體,而是現代化過程中被貼上“疾病”“異常”標簽的,被信息化后的物理身體。分娩正是通過被標簽化、被信息化的生物性身體得以實踐,成為一種醫源性疾病。產婦對分娩的認知很大程度上也是取決于被標簽化、被信息化的生物性身體,而非純粹的物理身體,但是標簽化的生物性身體與物理身體之間差異并不一定會被一般產婦所察覺,因為中國人身體并非是與精神完全割裂的肉體[8]。一方面,孕產身體作為一種現象,適用于身心分析框架;另一方面孕產身體作為深受標簽信息塑造的活生生實體,超越了身心分析框架。三重空間理論主要針對身心二元,強調身心一元主張下情感、精神、經驗的重要作用,卻沒有深入研究擁有歷史深度與社會深度的身體概念[9]。
該研究沿用身心一體基本主張,基于高度可變的生物性身體屬性,在身體三重空間基礎上延伸出第四空間,即具有情境性、地方性及辯證的生物性身體。但從方法論上講,即使身體研究擺脫了身心二元對立的古典哲學,圍繞著身體展開的社會科學依然很難擺脫對個體與社會、自然與文化、本質主義與建構主義等基本關系的探討,只不過有的是在二元范疇內進行,有的則是打破二元而達到某種逾越。該研究焦點是通過關注分娩這一生理過程中的女性身體,探討第四空間辯證生物性與個人化身體、社會化身體、政治化身體發生了怎樣的互動。
2 圍產期女性身體四重空間的互動
本研究采用了人類學參與觀察和深度訪談的研究方法。從2012年到2017年的5年時間里,筆者在X省的5所公立醫院和1所私立醫院,Y省的2所公立醫院和1所私立醫院,作為醫院志愿者進行了參與觀察和資料收集,并對38名女性進行了一對一的深度訪談,訪談的地點為醫院、咖啡廳或調查對象的家中,對其中5名女性(在這5年中有二胎分娩經驗)進行了第二次跟蹤訪談。
基于對田野資料的分析,本研究將從以下三個方面探討身體是如何在特定情境中發生了獨有變化,并形成辯證的生物性身體。
2.1 分娩到底有多痛:生理性陣痛與個體化身體
分娩過程經常伴隨著一個關鍵詞——陣痛。醫學上講陣痛是指為了推動胎兒從子宮頸下降,子宮不斷收縮而發生的正常生理疼痛。一些研究表明中國剖腹產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就是中國女性忍受不了劇烈陣痛[10]。調查發現,一方面女性均表示分娩是疼痛無比的過程,但女性口中無法忍受疼痛不僅僅指宮縮引起的生理性陣痛,還受到以下三方面的影響:①對醫院環境的認知和感悟;②與丈夫或婆婆的關系;③與其他產婦對比的鏡像情緒。三方中任何一方面的突出都會牽動女性身體的疼痛。而相反女性敘述中可以忍受的疼痛恰恰是基于完全個體化體驗。
受訪者U_19這樣形容她的陣痛,“等到8分鐘的時候,我特別疼,我就趕緊和老公說去醫院,到了醫院5點鐘醫生給我內檢,說剛展平,我不懂什么意思,就問她什么意思,她就說要么你去病房、要么去待產室、要么就去做個彩超吧,我當時稀里糊涂的,我不知道自己該去哪里,可是我想去病房的話可能給我打點滴(縮宮素),于是就去做彩超了,彩超結果預測孩子的體重8斤2兩,醫生說孩子有點大,可能會側切,一聽到這個消息我就有點害怕,突然覺得自己下面變得很痛,我媽有過不好經歷至今也沒有很好恢復,幾個好朋友都是被側切了以后留下了病根,我問醫生可以不側切嗎?醫生就瞟了我一眼然后語氣特別不好地說,那得問你的主治醫生。”
U_19不能忍受的疼痛包括以下4個層面:①對縮宮素的畏懼;②受到母親、朋友分娩經歷的負面影響,對由側切帶來的諸多副作用產生了恐懼及抗拒心理;③面對生產方式可能給身體帶來的傷害卻不知道如何是好的無助和沮喪;④醫務人員使用的專業術語讓她無從了解自身身體狀況,而其冷淡態度使她感到委屈和落寞。這些來自于觀念、記憶、行為、認知的不同情緒全部都轉化為女性口中的疼痛,而疼痛并沒有被醫務人員和家庭成員分類處理,反而簡單被歸納為身體上陣痛,個體疼痛均轉化為分娩本來就很痛這樣一個事實。換而言之,女性描述生理性陣痛其實是一種或多種要素的總和,既包括宮縮疼痛,也包括心理上不滿和不安、行動上不便、溝通交流不暢與家庭關系不和諧等諸多要素,但是女性的訴求并沒有得到相應回應,我們可想而知所有的描述都被聚焦在宮縮這個點上時,女性的生理性陣痛到底有多痛呢?每位女性的分娩身體本應該都是個體的,都要經歷不和其它任何人雷同的經驗,但其中成為共性的無法忍受之痛恰恰反映出現代產科模式忽視了女性的個體化,這樣的分娩體驗讓女性失去了自信及生孩子的成就感。正如U_18所述:“我覺得是他們讓我生,而不是自己要生。”
與之相對,有受訪者表示陣痛沒有想象中的那么疼,或者認為是可以忍受的疼痛。在私立醫院分娩的U_16說道:“晚上我真的是疼了一個晚上,幸虧在醫院里,助產士時不時就來看看我,過來教給我呼吸的方法,然后給我按摩,說也奇怪她一把手放在我肚子上我就感覺特別舒服,老公也一直為我忙前忙后的,我覺得陣痛是痛,但是可以忍受的,而且最痛的時候就那么一小會,而且我沒有側切,現在每當我和朋友們聊起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就覺得自己的身子很爭氣,感到特別自豪。”U_16的分娩過程和其它女性一樣是由宮縮陣痛開始的,但她的敘述中沒有出現任何負面情緒和消極認知,她認為痛是正常的、可以忍耐的,甚至是短暫的,在陣痛開始到分娩結束的十幾個小時當中,她的身體被家屬和醫務人員所包圍,個體化身體得到了充分的重視和照顧,甚至到最后她會為自己的身體而感到自豪,在她的描述里沒有出現治療,而是出現了照顧,不管是助產士的按摩,還是丈夫的忙前忙后,都是緊緊圍繞著如何使身體處于更加輕松的狀態。
綜上所述,女性敘述的陣痛并不僅僅由宮縮引起,而是集心靈、經歷、精神、認知、溝通等多要素的融合的個體體驗。疼痛就是多要素復合的身體表達,是焦慮和壓力釋放的重要途徑,是自我認知與社會關系的直接表現,也是有必要和醫務人員進行有效溝通的重要感受。正是通過對疼痛的表達,個人、醫院、社會、國家開始聚焦女性身體、孕產行為,陣痛也成為解讀女性真實分娩經歷和感受的切入口。
2.2 分娩之痛如何緩解:生物性鎮痛與社會化身體
近代醫學未進入生育領域之前,孕產一直都是社會文化的產物。分娩被認為是通過儀禮展現出在各個社會中的象征和其背后的社會秩序,女性通過分娩完成身份的轉變,完成和周圍人關系的重新構建,而處于分娩的身體象征該社會的不同符號。例如在傳統社會,分娩中的身體象征著污穢和禁忌,在主要居室和正堂生育有可能玷污祖先神靈,引來災禍,所以女性的分娩場所只能選擇和眾人分離的偏室[11]。費孝通認為:“生育是損己利人的事情,孕婦的痛苦,臨盆的危險,哺乳的麻煩看上去都是損害個人利益的,但是人類為了追求不同于低級動物的生活,需要供給新的社會分子,組成社會進行分工形成社會的新陳代謝。”[12]顯然,自古以來,分娩就是苦難的代言詞,疼痛讓產婦陷入水深火熱中,刻畫出產婦受控于父權制而失去自我的負面形象。調查發現,中國產科實踐中,孕產身體仍然是社會文化的隱喻,并在緩解陣痛中由生物化、個體化逐步進入了社會化。
U_19這樣敘述她的選擇:“7月16日晚上我舅舅和他朋友來我家,他認識道教協會的會長,那個會長說‘7月17日是好日子,18、19連著兩天都不好,而且9點-11點是巳時,今年是巳蛇嘛,孩子如果生在這個時辰也特別好’,當時我想著隨便吧,能順產就順產吧,但是現在一想到要側切就有點退縮。當時我一抬頭正好看到墻上的表,顯示8點18分,我想這都快9點了,就問家里人能不能剖腹產,他們都說尊重我的意見,我又問麻醉科大夫老公如果剖腹產的話,能在11點之前出來嗎?他說一般來說沒問題,于是我就決定剖腹產,(中略)我想懷孕就是人為計算的,那生孩子如果也可以人為計算的話,就計算到底吧,正好老公是醫院醫生,我想反正都得來一刀,還不如給孩子一個好時辰。”通過案例可知,剖腹產與熟人關系兩者有效結合作為一劑鎮痛藥,不僅使U_19避免被側切或者被使用縮宮素,不用經歷時間長短不一的宮縮痛,脫離了醫務人員為自己選擇而并非自己本意的分娩經歷,實現其自我選擇、自我決定的分娩樣式,而且給孩子帶來具有強壯健康隱喻的生命歷程。在中國社會,孩子的生辰八字對于其以后的成長有著重要的引導和隱喻作用,一個孩子如果可以生在黃道吉日良辰,那么今后的人生,即生老病死、求學、就業、財富、婚姻、家庭、工作等皆會一帆風順,因此為了能讓孩子在吉日良辰內誕生,剖腹產成為了可控有效的手段。其次,占主導地位觀念認為十年看婆,十年看媳,尤其前十年內的孕產行為是測量婆媳關系親疏程度,判斷后十年相處模式的工具與指向標。在媳婦最困難的孕產期間,夫家的尊重、支持與照顧不僅反映家庭關系的和諧度,也折射出產婦本人話語的輕重,因此,為了衡量與夫家關系,她會主動選擇使身心免于痛苦的剖腹產。無醫學指征剖腹產塑造一種正常的、流行的、人工的、自主的身體,無痛的身體象征著和諧、解放、先進,代表著有主體意識、經濟實力、家庭地位的新女性形象,而經歷疼痛的順產和身體則象征著沖突、束縛和落后。然而,剖腹產的選擇和實踐并不是僅靠主體意識就能實現的,它還需要“熟人關系”這個重要載體。剖腹產原本是為了解救產婦難產而出現的產科手術,具有一定的手術風險,如果分娩過程中產婦沒有出現并發癥、胎位不正、羊水過少等需要進行手術的手術指征,那么一般不允許自主選擇剖腹產,但是熟人關系介入下,醫學與非醫學、主觀與客觀、主體與客體、生物與文化等關于身體各屬性間的界限被打破,生物性身體被重新塑造和管理。調查發現,38位女性中有24位女性選擇了有熟人關系的醫院,熟人關系建構了被解放后的女性身體,使其可以擺脫醫學話語的束縛,并且讓自己的主體性得到了進一步的確認,原本被產科模式以統一醫學標準管理的女性的身體,因為熟人關系的介入,醫學標準發生了傾斜,部分女性的身體獲得了優先權和自主選擇權,處于熟人關系中的身體象征著和諧、解放、優先、主動和自我,而非熟人關系的身體則表現出了沖突、焦慮、受控、被動與他者化,這樣的社會話語本質上體現出分娩不是疾病,產婦不是患者,孕產身體也不是病體,女性目的是為了獲取社會化身體,強調與一般婦女不同的個體經歷。
由此可見,圍產期女性的身體既是個體化產婦,更是社會化產物,社會和文化規定了我們對分娩的看法,并且塑造了完全不同于他人的分娩實踐。面對同樣的產科模式,社會和文化仍會塑造出不同的分娩體驗,中國的產科實踐并非照搬西方產科模式,醫學技術剖腹產成為一種具有隱喻的生物性鎮痛法,女性對分娩認知和選擇不僅基于生物性身體,更重要取決于圍繞分娩而產生的文化事件,來源于生育文化、生育信仰、親屬關系、熟人網絡、市場關系等,并通過文化性身體為生物性身體找到了高度可變的方式。
2.3 產痛環境的變化:生物性標準和政治化身體
在上文中看到,女性的身體受到了來自于個體經驗、醫學及社會文化的制約,但正如范燕燕和林曉珊所述:“切莫以為只有產婦個體和現代醫療體系才是幕后推手,實際上,在邁向現代化的進程中,國家人口制度早已與醫療話語體系形成共謀,它們對生育的控制共同主宰著產婦的命運。”[13]建國初期,國家通過舊產婆改造和建立大量的產院等政策,把農村地區女性的健康和婦女解放運動結合在一起[14]。1980年以后,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和國際地位的不斷提高,降低母嬰的死亡率、提高出生人口素質成為了關系國家和民族前途的大事,于是國家積極普及住院分娩,并通過法律條文規定了助產醫院的等級及助產人員的工作場所和助產資格[15]。住院分娩為難產產婦提供了救治的機會,大大強化了產婦對醫院的依賴。2012年調查的10位女性這樣敘述分娩經歷:“寶寶當時臍帶繞頸一圈,我去醫院檢查,醫院說羊水少,而且胎心有時候會到180,醫生建議剖腹產。”2012年的案例中,縮宮素、人工破水、側切已經成為了順產常用的醫學技術,而剖腹產更是一天就可以做幾例的被頻繁使用的手術方式,臀位、臍帶繞頸、羊水變少和胎心過高等問題都能成為進行剖腹產的原因。表面上看是醫學技術的進步救治了更多難產產婦,實際上也可以說國家政策推動的住院分娩讓更多的女性只可以選擇在醫療環境中分娩,從而變成了假定的難產產婦。住院分娩政策的普及強化了女性對醫院的信任,剖腹產的盛行強化了女性對醫生的信任,女性對自己的身體產生了不安和懷疑,認為只有醫學技術才是為母子的平安保駕護航的正常的分娩渠道,而無任何醫學介入的順產只適合條件特別好的個別產婦。分娩變成了一件可怕的事情,女性的身體具有生育功能但是又不能自行完成該過程,失去了自我的能動性。從婦幼保健的角度來看,住院分娩及助產人員專業化等政策的實施使難產的產婦得到了救治,從而導致母嬰死亡率降低,但是從生育個體化和多元化的角度來看,由于分娩場所、接生人員全部都囊括在國家統一管理的公共衛生體系中,家屬以攜帶病菌為由被擋在產房門外,女性的身體也從個體領域隨之進入了公共衛生體系中,包括生幾個、在哪生、由誰接生、怎么生等等,國家政策已經規定好了女性在整個分娩過程需要扮演的角色。
然而2016年調查中,女性身體扮演的角色發生了一些轉變,因為國家政策發生了變化,女性的分娩體驗也發生了變化。如U_14所述:“晚上8點鐘我就破水了,9點鐘往醫院走,可是進了醫院一晚上都沒動靜,也不痛,宮口也沒開,就等到第二天早上10點鐘打了無痛,11點鐘停的,12點50多就把他生了,可快呢,我上產床5分鐘就把他生了,(中略)現在醫院都不給側切也不給隨便剖,我媽(在醫院工作)說醫院得完成上面定的指標,要是超了就不能評級了。”
調查發現,國家早已開始控制剖腹產率及順產中的側切率,Y省一家三級甲等醫院的剖腹產率從2012年的70%下降到2016年的45%,側切率從99%下降到16%。國家為了降低高剖腹產率帶來的負面影響,通過法律條文和行政手段干預各醫院的剖腹產率和側切率,通過醫院的醫務人員去推廣順產并強調自然分娩的好處。醫務人員對促進自然分娩的意識明顯增強了,她們告訴產婦順產也可以不側切,胎兒臀位或臍帶繞頸也可以順產了,分娩形式不再拘泥于橫躺在產床上,可以選擇臥、走、立、坐、跪、趴、蹲等各種姿勢。如果說處于分娩中的身體是基于生物醫學,那么面對同樣的難產問題(臀位、臍帶繞頸、胎心上升等)應采取同樣的手段,但是實際上即使是同樣的問題,解決問題的方法隨著不同年代國家政策及當地文化而變化。
值得注意的是,與低剖腹產率及側切率相比,無痛這個概念持續出現在女性的敘述中,硬膜外麻醉成為自然分娩方式中不可缺少且不可替代的一環,也成為深受女性歡迎和信任的一種醫學技術。我們對無痛分娩的認知一般是緩解產程中由宮縮引起的生理性疼痛,但是無痛分娩并不僅僅是一個醫學概念,而是塑造了與技術、政治交織的身體。一方面,國家積極倡導自然分娩,醫院、醫務人員均以提高自然分娩率、降低剖腹產率為首要任務,但兩者均沒明確與自然分娩配套的個體化、社會化人文關懷;另一方面,女性借助熟人關系、消費關系等平臺,尋求生理身體的出口和個體化的分娩體驗,彌補制度化醫院的人文缺失,這樣的雙重話語致使女性既要個體體驗,還必須同時與醫院方針、醫學指標不存在明顯分歧。無痛分娩則成為融合兩者的紐帶,無痛分娩以文化名義過濾了各種疼痛隱喻,同時又可以滿足高自然分娩率、低婦幼死亡率、剖腹產率、側切率等展現婦幼健康衡量現代化國家形象等諸多標準的實現。
福柯指出:“國家的現代權力不再是由上而下的統治形式,更多運用自愿的方法維持社會秩序,包括個人追求、道德價值和政治措施及生物醫學形成社會規訓。”國家現代化進程中,國家穩定富強與少量優質且健康的人口緊密相連,使得國家與人口學、優生學、生物醫學產生共通關系,并形成國家的權力技術[16]。在孕產方面,國家關注如何掌控健康優質人口以達到現代化國家標準實現國家富強,其政策與生物醫學有效結合,以母嬰健康為由,其婦幼政策及措施更嚴密監控產婦個體身體,有效規范群體孕產行為,正當化國家權力變革后的孕產習俗和社會關系,這種與技術并軌的規訓方式,讓國家擁有生命權力管理個體和群體生命,并透過社會無形網絡接入整個孕產中[15]。但當權力技術形成嚴密體系,這種規訓會引起眾多抵抗,一部分女性開始積極推進無醫學介入的自然分娩,實踐居家分娩模式。她們認為分娩疼痛源于對產科實踐的恐懼與無知,倡導要堅信自己的分娩本能,感受疼痛帶來的愉悅,正確認知分娩對于女性身體的社會文化意義。
3 結論
中國產科實踐呈現出前現代、現代和后現代并存的特點,主要表現在助產人員多元化、分娩主導話語多樣化、分娩姿勢自由化、女性扮演角色多重化及對難產認知的主體化,這種蘊藏在現代產科模式下豐富多樣的產科實踐正是通過產婦身體四重空間形成的。分娩對于女性來說是個體化經驗,對國家來說是公共衛生的一環,對醫院來說是生物醫學的結果,對家人來說是共同體內迎接新生命、其成員得到新身份的文化事件,但是由于分娩主體女性的話語很少出現在公共領域中,所以呈現在我們面前的產科實踐變成了統一化、標準化的現代產科模式。現代產科模式強調分娩作為疾病時的肉體,然而中國產科實踐卻呈現出高度可變的生物性身體,這樣的生物性身體是自然與文化長期交織后形成的人工產物,是隨女性個體需求、社會文化規范、醫學技術、國家政策的不同而變動可塑的存在,是具有技術性、歸順性、消費性、生產性、行為性與反抗性等特點的復合體,更是身體四重空間所代表不同方法論與認識論在實踐中的表現形式。身體四重空間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包括女性在內的社會成員對分娩的認識和理解,共同構建出前現代、現代與后現代特點并存的產科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