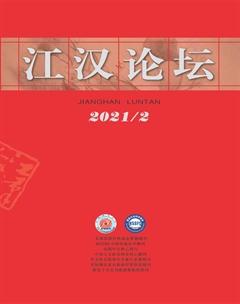蘇軾對《維摩詰經》的接受研究
摘要:蘇軾接受《維摩詰經》有四個特點:一是采用思辨的態度對待《維摩詰經》,提出了“靜故了群動,空故納萬境”的創作論;二是他毫無門戶之見,呈現出“融三教于一爐”的特色;三是接受此經時,側重于接受其風趣幽默、游戲神通的方面;四是經中“火中生蓮花”的思想使其面對人生磨難時極為達觀,從而磨煉了蘇軾的偉大精神品格。
關鍵詞:蘇軾;《維摩詰經》;接受
中圖分類號:I206.5? ? 文獻標識碼:A? ? 文章編號:1003-854X(2021)02-0061-05
蘇軾在慘罹“烏臺詩案”后,謫居湖北黃州四年余,寫下不少千古傳誦名篇。清錢謙益認為:“子瞻之文,黃州已前得之于莊,黃州已后得之于釋。”并贊曰:“文之通釋教者,以子瞻為極則。”① 蘇轍《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銘》載:蘇軾謫居于黃州時,曾一度閉門深居,揮灑翰墨,其文驟變,竟如川流而至,使轍“瞠然不能及矣。后讀釋氏書,深悟實相,參之孔老,博辯無礙,浩然不見其涯也。”② 作為深切了解兄長的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蘇轍,他的看法有著極重分量。蘇軾居黃州期間,不能簽署公文,經常去黃州安國寺焚香默坐,對自己過往的人生進行了深切的反思,并以佛法進行自我修養。同時,沒有經濟來源,因生計所迫,蘇軾親率家人,不分晝夜,躬耕于東坡之上,是以自號“東坡居士”。蕭麗華統計蘇軾引用佛經的情況,排前三位的是《景德傳燈錄》144次、《楞嚴經》113次、《維摩詰經》78次。③ 蘇軾詩文頻繁引述《維摩詰經》相關內容,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關注。
一、理性思辨——“靜故了群動,空故納萬境”
宋詩與唐詩的興味玲瓏、情景交融的風格迥異。宋代由于印刷術的迅猛發展,書本較易得到,士大夫文化修養普遍較高,這可能促進了宋人的理性思維的發展。若說唐詩以情取勝,宋詩則以理趣取勝。時代思潮所及,蘇軾雖有意氣風發之作,然其詩之理性與思辨特點,極為明顯。如“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題西林壁》),“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惠崇春江晚景》),都是眾所周知的述理詩名作。
這種特點也表現在他對《維摩詰經》的接受之中,如:“我觀眾工工一師,人持一藥療一病”,“我觀石子一處士,麻鞋破帽露兩肘。能使筆端出維摩,神力又過維摩詰”,“佛子若見維摩像,當作此觀為正觀”(《石恪畫維摩贊》)④。此詩前部分都是從《維摩詰經》的內容中化出。前五句與《問疾品》《不二門品》相關,贊維摩詰大神通,末一段落則是贊畫師石恪,雖然“麻鞋破帽露兩肘”,但是卻能夠用筆畫出維摩詰,那么畫師的神力則超過維摩詰。此詩中,完全看不到蘇軾對維摩詰的頂禮膜拜,詩歌口吻恰如談身邊的朋友一樣輕松熟悉。可見蘇軾接受佛經之時,并非當作“圣書”對待,而是視作普通的書籍。換言之,對蘇軾而言,佛經雖值得賞讀,但并非為了“成佛”的信仰,他也未曾神化維摩詰。
蘇軾寫有《朝云詩并引》,“阿奴絡秀不同老,天女維摩總解禪”,“天女維摩”當指侍妾王朝云與蘇東坡自己。再讀“白發蒼顏,正是維摩境界。空方丈、散花何礙。朱唇箸點,更髻鬟生彩。……明朝端午,待學紉蘭為佩。尋一首好詩,要書裙帶”⑤ 諸句,便可得知個中情愫。“白發蒼顏,正是維摩境界”,應是夫子自道。“空方丈,散花何礙”,則指《維摩詰經》中“天女散花”一事,亦隱指朝云為“天女”。結合《朝云詩并引》,我們可以看出蘇軾與朝云的關系到了晚年,乃是同道、知己的關系。
“上人學苦空,百念已灰冷。劍頭惟一吷,焦谷無新穎。……頗怪浮屠人,視身如丘井。欲令詩語妙,無厭空且靜。靜故了群動,空故納萬境。閱世走人間,觀身臥云嶺。……詩法不相妨,此語更當請。”⑥ 這首詩也是蘇軾的名作,廣為傳誦。美學家宗白華先生在他的《論文藝的空靈與充實》一文中說:“藝術心靈的誕生,在人生忘我的一剎那,即美學上所謂‘靜照。……蘇東坡詩云:‘靜故了群動,空故納萬境。”⑦ 宗白華以此詩論創作之要點,堪稱解人。而此詩直接引述《維摩詰經》的頻率高達三次。“劍頭惟一吷,焦谷無新穎”,此其一也。焦谷,指炒焦的谷子,語出《維摩詰經》:“如焦谷芽,如石兒女”⑧。“頗怪浮屠人,視身如丘井”,此其二也。語出《維摩詰經》“視身如丘井,為老所逼”⑨。“閱世走人間,觀身臥云嶺”,此其三也。語出《維摩詰經》“自觀身實相”⑩ 一語。“靜故了群動,空故納萬境”一句,從字面看來,未見直接引用《維摩詰經》,然而,此經《問疾品》載,其時長者維摩詰,“即以神力空其室內,除去所有及諸侍者,唯置一床,以疾而臥。”《示現不可思議解脫品》亦載:于是,“長者維摩詰即現神通力。即時彼佛遣三萬二千獅子座,高廣嚴凈,來入維摩詰室……其室廣博,悉包容三萬二千獅子座,無所妨礙。”前后兩段講述的是,維摩詰知道了文殊菩薩率領大眾一起前來問疾之后,用神通使室內一切人、物都消失不見,只剩一張病床。后眾菩薩來到維摩詰空室問疾之后,與文殊同來的舍利弗心想我們坐哪兒,屋內空無一座。維摩詰以神通知他念頭,又在室內變出三萬二千極高大的獅子座來,并且毫不狹窄。結合前三次的直接引述,“空故納萬境”一句實與《維摩詰經》的啟發有關。《維摩詰經》中的“空”是室內無物之空,而蘇軾將之引申為心境之空明、悟性之空靈。此句與《老子》中的“滌除玄覽”有相互發明之處。
此詩先抑后揚,先是“頗怪浮屠人”,后言“細思乃不然,真巧非幻影”,贊其巧妙,妙在何處?“欲令詩語妙,無厭空且靜”,倘若想將詩寫好,必須達到“空靈”“寧靜”之心境。這是蘇軾直接論述佛教空靜與創作關系的詩歌。作為一代文豪,這自然也是他的創作心得。然此均與《維摩詰經》有密不可分的關系。誠如袁行霈所言:“詩和禪的溝通,表面看來似乎是雙向的,其實,主要是禪對詩的單向滲透。”{11} 若說蘇軾的《送參寥師》是對自身創作的總結,那么我們可以從中看出,蘇軾創作之成功也得益于他對佛經的主動接受。
蘇軾曾說,佛書舊時亦嘗看,并以自洗濯,像農夫去草,旋去旋生,雖若無益,但終治而不去也:“公之所談,譬之飲食龍肉也,而仆之所學,豬肉也……學佛老者,本期于靜而達,靜似懶,達似放……仆常以此自疑,故亦以為獻。”(《答畢仲舉》){12} 從這段話中,我們可以看出蘇軾閱讀佛經時,不為“出生死、超三乘、作佛”,而是將佛經與老莊同看,目的是去掉精神上的“草”,達到“靜而達”的境界。但是他又擔心學者將之與懶、放混淆,因而蘇軾對此還自疑,不斷地進行反思。
這種夫子自道式的闡釋與思考,更從側面說明他接受佛典《維摩詰經》是出于理性的思辨,目的是為我所用,以期達到精神上的超脫與寧靜,而非狂熱的信仰,這是蘇軾接受《維摩詰經》的第一個特點。
二、三教融一 ——“乃知至人外生死,此身變化浮云隨”
梁銀林認為,蘇軾最早以《維摩詰經》為題材的詩,應是他于鳳翔之時所作《維摩像唐楊惠之塑在天柱寺》一詩:“昔者子輿病且死,其友子祀往問之。跰鮮鑒井自嘆息,造物將安以我為。今觀古塑維摩像,病骨磊嵬如枯龜。乃知至人外生死,此身變化浮云隨。……誰能與結無言師。”{13} 蘇軾將維摩詰視作具有老莊思想的“至人”,“至人”能將人之生死置之度外。故此,蘇軾對于維摩居士的認知,是以《莊子》思想來達成的。
誠然,早期佛教融入中國,的確是依附于《老子》,甚至出現了《老子化胡經》這樣的“偽經”,而這種現象是佛教傳入中國的初始階段。佛教發展到唐代,五祖惠能創立了中國本土的禪宗,佛教也不必隱藏自己的真實面目而依附于《老子》。從更深層次看,儒佛道很多方面有融通之處,并非井水與河水的關系。高延在《大一統論》一書中指出:“‘三教不過是從一個共同‘主干上生長的三個‘分枝,而‘主干早在史前時代就存在了。‘主干即‘天地萬物之宗教,這一宗教有其基本構成要素與外在表征。囊括天地萬物在內的‘大一統論就是中國的‘一教。”{14} 也就是說,中國儒釋道均有一個共同的主干,這個主干使得儒釋道三教在多層面、多維度有著相互融合與相互補充之處。
基于這一觀點來觀察蘇軾詩文及其思想,我們或許能領會更多,也不會認為他早期以莊論釋有“膚淺”之處。事實上,蘇軾不僅早年將釋道融于一詩,而且隨著對社會人生的體悟更加深切,他在晚年創作中,仍將釋道融于一體。如“不似楊枝別樂天,恰如通德伴伶玄。阿奴絡秀不同老,天女維摩總解禪。……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陽云雨仙。”(《朝云詩并引》)其詩前半寫“天女維摩總解禪”,出自佛典《維摩詰經》;后半則言“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陽云雨仙”,這是典型的道家煉丹成仙的意象,而“巫山云雨”,則指楚國神話傳說,其意是巫山神女,興云降雨,后來卻是專指男女情愛。此詩寫于被貶惠州之時,蘇軾已是年過花甲的老人。如果說因為他將佛道融作一詩是“膚淺”或是“初級階段”的話,那么或許蘇軾一生對佛教的認識就不曾深刻過,而這顯然是不符合事實的。但假如我們換一個角度,不將儒釋道視作各自壁壘森嚴的不同思想,而是視為一棵樹上的不同枝椏,則這個問題很好解決:即蘇軾在不同時期、不同人生境遇中,接受三教的側重點有所不同。或許他從一開始就沒有今人這樣清晰的思想分界。《宋史·蘇軾傳》載,蘇軾十歲蘇母即教讀《范滂傳》,希望兒子作一個有社會擔當的儒者。但這與蘇母自己信奉佛教并不抵牾。可見在宋人眼里,儒佛相通相融、相輔相成,并無矛盾。
現代學術受西方文化的影響較為嚴重,因此各學科、各思想之間存在著嚴重的壁壘。而在中國古代,學科邊界相對較模糊,尤其唐宋時期,儒佛道有較深入的融合,因此蘇軾在接受《維摩詰經》時也有著類似的特點。蘇軾與明公長老論佛時說:“是二法者,相反而相為用。儒與釋皆然。”{15} 蘇軾認為,明公雖然身出家,但是心未出家,也并非逃禪。明公曾告之老友蘇軾:“宰官行世間法,沙門行出世間法,世間即出世間,等無有二。”{16} 儒、釋本無矛盾,作為在家的居士蘇東坡,他一邊體驗和吸取佛家的無畏與超脫精神,一邊盡全力為老百姓和國家付出自己能付出的一切。他還說:“孔老異門,儒釋分宮。又于其間,禪律相攻。我見大海,有北南東。江河雖殊,其至則同。”{17} 可見他對這儒釋道三家的異同是深入思考過的,并認為三者恰如江河之異流,最終歸于大海。
從某種意義上說,蘇軾作為宋代士大夫居士中的典范,他對《維摩詰經》的接受有著代表性的意義。佛教在唐代空前繁盛,禪宗的創立標志著佛教真正成為中國本土的宗教,具有本民族文化的特性。佛教的中國化以結出自己的果實——禪宗,作為最終的結局。《維摩詰經》使得中國士人擺脫了“在家出家”的困惑,從而在世俗的生活中建立起超脫與寧靜的棲居之地。宋代士人無論是否信仰佛教,多給自己取“居士”稱號,于此可看出此經對宋代士人的影響。即便主張排佛的歐陽修也給自己取“六一居士”的雅號,則更可以說明其影響之深遠。
從統治者的角度來看,宋代君主多認為儒佛道三教并行于社會治理有益,一方面予以提倡,另一方面也限制其發展,同時還采用儒佛道相互制衡的方式予以調節。從士大夫的角度來看,三教合流雖有論爭,但士大夫多能按自身的需求吸取佛教中的有益部分,為我所用。
蘇軾在接受《維摩詰經》時,保持冷靜而理性的態度,將儒家的社會擔當與佛教的“眾生病故我病”的無私無畏相結合,一方面在坎坷的仕途中尋找心靈的寧靜與寄托,另一方面于儒道之外用佛眼透視人生世相,從而得到超脫。三教合一,并行不悖,使得蘇軾的人生躍升至新的境界。
蘇軾的晚年進入了李常生所稱述的人生“第五重境界”。“參橫斗轉欲三更,苦雨終風也解晴。云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這是蘇軾《六月二十日夜渡海》的詩句。此詩一二句,可與以下二詩同讀。其一是寫于黃州的《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而另一詩是十幾年之后,在儋州寫作的《獨覺》:“回首向來蕭瑟處,也無風雨也無晴。”李常生認為,晚年的蘇軾實已領悟“平淡灑脫的無我之境”{18}。進入無我之境的蘇軾,于名利紛爭、得失計較毫不掛懷,故對于傷害過自己的政敵章惇等人不僅予以包容,而且將自己被貶期間的保身藥方悉數交托,并囑其保養身體。這無疑是“一切眾生病即我病,一切眾生病愈則我病愈”的維摩精神,但這種精神與儒家的“四海之內皆兄弟”的仁愛精神并無二致。因此,我們可以認為,作為天才的文學家、畫家、書法家,作為宋代佛教居士的典型,作為久經患難而不改其樂的蘇軾,他身上所體現的居士精神,實得益于三教融一的接受與思考,而這也是蘇軾接受《維摩詰經》的第二個特點。
三、幽默趣味——“不須天女來相試,總把空花眼里看”
“蘇軾是不可救藥的樂天派。”這是林語堂先生在《蘇軾傳》中的評價。蘇軾性格樂觀、幽默。晚年貶到海南時,他已是六十多歲的老人了。在這樣一個窮苦的地方,蘇軾的境遇如何呢?食之無肉,病了無藥,居住無屋,出行無友,冬來無火炭,夏來無涼泉,概而言之:“大率皆無耳!”這是蘇軾寫信給朋友時所說的。就在這樣一個“大率皆無”之地,蘇軾卻在某一天吃海南當地漁民送來的蠔時,覺得十分美味,寫信給兒子說:“恐北方君子聞之,爭欲東坡所為,求謫海南,分我此美。”{19} 在一個窮得什么都沒有的地方,得了點蠔,卻跟兒子說要保密,不然北方官員們聽說了,都爭著要貶到海南來,這真是黑色幽默。蘇軾就是這樣,很擅長在生活中發現樂趣、享受生活。或許正因為這樣的性格特點,他在接受這部《維摩詰經》時,也深得此經意趣。
法國學者保羅·戴密微說《維摩詰經》是藝術作品,有巧妙的戲劇安排,“其中有精彩的天女散花一節,佛聲聞弟子舍利弗盡力不能去花,忽而變成女身,真是詼諧詭趣,獨運匠心。”{20} 《維摩詰經》的趣味性直接影響了中國士大夫們接受此經的態度。
《維摩詰經》的趣味性與蘇軾的幽默性格之所以能產生某種程度的共鳴,其間自有道理,如“白足高僧解達觀,安排春事滿幽欄。不須天女來相試,總把空花眼里看”(《贈江州景德長老》),此詩前兩句容易理解,而細細品味后兩句,卻極有意思。傳載這位“天女”,應指《維摩詰經》所述方丈室里的那位天女。文殊師利率眾前來問疾時,天女本來隱身,靜聽維摩說法,甚是歡喜,不知不覺之間,竟然現其身,后來散花于眾。溯其源,此詩從唐代皎然“天女來相試,將花欲染衣。禪心竟不起,還捧舊花歸”(《答李季蘭》)詩中化用來的。皎然贈答詩是因唐代女詩人李治而起。李治字季蘭,她欣賞皎然才氣,向皎然寫詩示好,以表愛慕之意,皎然寫此詩婉拒。蘇軾用在此處,作為贈景德長老的詩句,妙趣橫生。我們也可以從中看到宋人在接受《維摩詰經》的同時,還有對唐人詩句的傳承與化用。
不妨再看:“示病維摩元不病,在家靈運已忘家。何須魏帝一丸藥,且盡盧仝七碗茶。”(《游諸佛舍,一日飲釅茶七盞,戲書勤師壁》)詩之首句,源自“從癡有愛,則我病生;以一切眾生病,是故我病。”{21} 詩之次句,源于“鳥窠禪師曰:‘汝若了凈智妙圓體自空寂,即真出家……如謝靈運之儔也。”{22} 可見魏晉時期的謝靈運,因為接受《維摩詰經》,寫了不少與《維摩詰經》有關的詩,被后人視為在家居士。第三句出自魏文帝《折楊柳行》。詩之末句,寫喝茶之妙,出自盧仝《謝孟諫議寄新茶》。全詩讀來,對仗工整,用典豐富,意趣橫生,標題用“戲書”二字,與全詩的輕松格調相應,堪稱宋詩以才學為詩的典型之作。
蘇軾性格幽默風趣,所以接受《維摩詰經》時,反復使用天女散花這一有趣的意象。據筆者統計,蘇軾詩詞中有11處運用了這一意象,如“結習已空從著袂,不須天女問云何”(《再和楊公門濟梅花十絕(其一)》,“結習漸消留不住,卻須還與散花開”(《座上賦戴花得天字》),“精誠貫山石為裂,天女下試顏如蓮”(《游徑山》)等,恕不贅列。
由以上分析可知,蘇軾幽默達觀,故而接受《維摩詰經》之時,極為注重佛典的風趣之處。此經的趣味性與蘇軾的性格特點產生了極大的共鳴,這可說是蘇軾接受《維摩詰經》的第三個特點。
四、苦難淬煉——“淤泥生蓮花,糞壤出菌芝”
《維摩詰經》載,維摩詰問文殊師利什么是如來種時,文殊說一切煩惱皆是佛種。維摩詰問這是什么意思呢?文殊答曰:“若見無為入正位者……譬如高原陸地不生蓮華,卑濕淤泥,乃生此華……又如植種于空,終不得生;糞壤之地,乃能滋茂。……一切煩惱,為如來種,譬如不下巨海,不能得無價寶珠;如是不入煩惱大海,則不能得一切智寶。”佛經用富有詩意的語言說明煩惱中生菩提,恰如淤泥中生蓮花。這段話也讓蘇軾深有領悟,以這一意象入詩的有數處。且看《陸蓮庵》:“何妨紅粉唱迎仙,來伴山僧到處禪。陸地生花安足怪,而今更有火中蓮。”這里的“紅粉”是指蓮花,以禪眼觀之,郁郁黃花、青青翠竹無不是禪,紅粉蓮花自然也是。《維摩詰經》詩又云:“火中生蓮華,是可謂希有;在欲而行禪,希有亦如是。”這是化用佛經之意象入詩。蘇軾《韓退之〈孟郊墓銘〉云:以昌其詩,舉此問王定國,當昌其身耶?抑昌其詩也?來詩下語未契,作此答之》云:“慎勿怨謗讒,乃我得道資。淤泥生蓮花,糞壤出菌芝。賴此善知識,使我枯生荑。”此處說“怨謗饞”是“得道之資”后,尤嫌不足,又再補充道“淤泥生蓮花,糞壤出菌芝”。聯系韓愈《送孟東野序》中云“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之言,可見蘇軾深知苦難中方有智慧與心性的淬煉。
蘇軾一生宦海沉浮,屢遭家人亡故。蘇軾49歲時與朝云所生幼子早夭,寫了兩首哭兒詩,其中有句“歸來懷抱空,老淚如泄水。”另一首曰:“母哭不可聞,欲與汝俱亡。故衣尚懸架,漲乳已流床。感此欲忘生,一臥終日僵。”老年喪子痛不堪言。然過不多久,蘇軾好友滕達道寫信勸慰,蘇軾回復云:“喪子之戚,尋已忘之矣。此身如電泡,況其余乎?”{23} 好友蔡景繁女兒病逝,蘇軾在黃州寫信安慰說:“驚聞愛女遽棄左右,竊惟悲悼之切,痛割難堪,奈何!奈何!……區區,愿公深照,一付維摩、莊周令處置為佳也。”{24} 蘇軾勸友人如是,自己亦以佛教的空觀來消解人生之苦痛。他在幫助埋葬了“無主暴骨數百軀”之后,寫下《葬枯骨疏》云:“沐浴法水,悟罪性之本空……以戒、定、慧,滅貪、嗔、癡。勿眷戀于殘軀,共逍遙于凈土。”蘇軾愈經歷人世的磨難,佛教的智慧便愈能使他照見五蘊皆空,從而獲得寧靜與解脫。《和陶飲酒二十首其一》云:“芙蓉在秋水,時節自闔開。不如玉井蓮,結根天池泥。感此每自慰,吾事幸不諧。”詩中內容與莊子寧做曳尾于途中的烏龜類似,寧可做華山峰頂上的蓮花,不被采折,可以“結根天地泥”,成其天然。一想到這里,他便覺得很安慰,“吾事幸不諧”。“不諧”意指不好辦、不順利。蘇軾一生顛沛流離,屢失親人,但在佛教智慧的觀照之下,竟然是“吾事幸不諧”!這真是“淤泥生蓮花,糞壤出菌芝”。蘇軾云“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越是苦難之地、污濁之境,越能淬煉出蘇軾高潔、通透、強健、豐富而又純粹的魂靈。蘇軾在精神世界中達到的高度是今人所難以想象的。而之所以能達到這種境界實與蘇軾對《維摩詰經》的精細閱讀轉而深入領悟密不可分。
蘇軾接受《維摩詰經》的“火中生蓮花”、“煩惱皆佛種”的思想來面對人生的種種磨難,從而超越現實“色相”世界,磨練出偉大的精神品格。
蘇軾詩云:“愛鼠常留飯,憐蛾不點燈”(《次韻定慧欽長老見寄八首》),這種博大的仁愛之心既有“齊物論”思想,更出自佛教的慈悲精神。正是因為這種精神,蘇軾“眼前見天下無一個不好人”。俗眼觀之,萬物自有賢愚高低美丑;佛眼觀之,一切眾生平等皆具佛性。蘇軾熟讀佛經,深知佛法,了悟佛教智慧,故常以佛眼觀世。
綜上,蘇軾接受三教并無門戶之見,取各家精華為我所用。在接受《維摩詰經》時,他將經中“眾生有病,是故我病,眾生病愈,我亦病愈”的大乘佛教思想與儒家仁民愛物相結合,歷盡坎坷而能“也無風雨也無晴”,步入人生精深華妙之境。
《維摩詰經》的幽默風趣,深為蘇軾欣賞,詩詞中常有佛經的回響和余音。在此經的影響下,蘇軾提出了“靜故了群動,空故納萬境”的空、靜創作論。
蘇軾曠達、超脫、樂觀的品性是人類精神所能達到的至高境界。無論身處何境,他始終真摯、莊嚴而不粘滯地生活著,并盡可能地創造人生、奉獻人生,這于現代人而言也具有深刻的啟迪作用。
注釋:
① 錢謙益著、錢曾箋注:《錢牧齋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756頁。
② 蘇轍:《欒城集(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421—1422頁。
③ 蕭麗華:《從王維到蘇軾——詩歌與禪學交會的黃金時代》,天津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207頁。
④{12}{15}{16}{17}{19}{23}{24} 蘇軾:《蘇軾文集》,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584、1671—1672、393、394、1961、2592、1487、1911頁。
⑤⑥ 蘇軾:《蘇軾詩集》,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2073、905頁。
⑦ 宗白華:《論文藝的空靈與充實》,《藝境》,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185頁。
⑧⑨⑩{21} 黃寶生譯注:《梵漢對勘維摩詰所說經》,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94、56、329、144頁。
{11} 袁行霈:《詩與禪》,《文史知識》1986年第10期。
{13} 參見梁銀林:《蘇軾詩與〈維摩經〉》,《文學遺產》2006年第1期。
{14} 參見張云江:《嫁接抑或移植:佛教中國化路徑的比較與反思》,《中國社會科學報》2018年2月13日。
{18} 李常生:《王國維的三種境界說與蘇軾的人生第五境界》,《2018眉山東坡文化國際學術高峰論壇論文集》下冊,第239頁。
{20} 保羅·戴密微:《維摩詰在中國》,劉楚華譯,《中國佛教史論集》,臺北華宇出版社1987年版,第 241頁。
{22} 道元輯、朱俊紅點校:《景德傳燈錄》,海南出版社2011年版,第82頁。
作者簡介:楊瑰瑰,黃岡師范學院文學院副教授,湖北黃岡,438000。
(責任編輯? 劉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