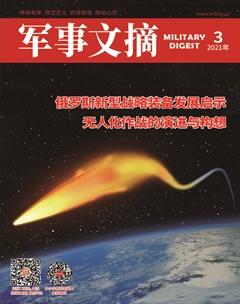只有打得贏,才能談得好
2021-03-16 10:06:38羅援
軍事文摘 2021年3期
羅援
人類歷史一直是在戰爭與和平的交替中曲折前行,而戰爭又是在“打”與“談”的輪回中浴火逢生。戰爭是掃除政治障礙的暴力手段。戰爭的過程就是“打”的過程,戰爭的結束最終是以“談”的形式來實現的,或被全殲而“免談”,或被擊潰而“降談”,或勢均力敵、抑或勢雖盛但為了以小的代價獲取大的利益而“和談”。“和談”是雙方權衡利弊的結果,往往取決于政治的需要,但政治的需要必須以軍事實力和軍事能力為后盾。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和談”也是政治的繼續。當“和談”的障礙不可克服時也只能用戰爭來掃除。
從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來看,如果沒有首戰兩水洞、激戰云山城、會戰清川江、鏖戰長津湖等,就不會有13國的“五步停火提案”;如果沒有隨后的3次、4次、5次戰役,沒有漢江南岸保衛戰,美國就不會再次提出停戰談判;如果沒有志愿軍構筑起銅墻鐵壁般的縱深防御陣地,實施多次進攻戰役,粉碎“絞殺戰”、抵御“細菌戰”;特別是如果沒有血戰鐵原、血戰上甘嶺和金城反擊戰,不可一世的美帝國主義侵略者就不可能在停戰協定上簽字。
實踐證明,和平是打出來的。在戰場上得不到的東西,在談判桌上也絕難得到。
正如毛澤東主席所言:“美帝國主義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講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講理,要是講一點理的話,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
這一點,至今仍然對我們有極大的啟示作用。這就是我們為什么要高舉“能打仗,打勝仗”旗幟的理論和現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