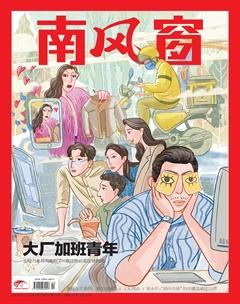理解社會的涌現
鄧耿
布羅代爾曾經有一個非常著名的比喻:在歷史的長河中,短時段的偶發事件就像黑夜中的螢火蟲或者劃亮一根火柴。它可以剎那間照亮周圍的黑暗,但卻無法改變社會變化的整體方向,只有長時段的結構才是左右宏觀歷史前進的重要動力。在很多人看來,新冠疫情就正是這樣的偶發事件,它本身并不那么重要,背后反映出的“深層”規律,才是讓剛剛過去的2020年變得如此關鍵的原因。
探求歷史“深層”規律的沖動早就根植于種種傳統思想之中,從《史記·天官書》的“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到馬克思的五種社會形態演進,為人類歷史進程尋找結構性本質原因的嘗試從未停止過。直到今天,不同價值取向的此類宏大敘事依然在現實政治和社會中持續影響人心和事件。宏大是意義的來源。它既為人們創造新的價值提供了必要的迷思,但同時也將個體價值和意義消弭在壯闊的背景中,甚至引誘人們甘愿為之赴死。在這方面,拼多多的“奮斗”理念和大局觀未嘗不是一個案例。
然而,短時段、中時段和長時段的區分,并非只能導向用長時段的結構來解釋歷史的“宏大史觀”。事實上,在布羅代爾所屬的“年鑒學派”誕生之初。他們所要應對的本來是來自于蘭克史學的還原論思想:重視每一個場景和細節的完美考證,以期復原歷史真相。這種思想其實與那種從宏觀視角給出歷史演進答案的思想,遵循著相似的思維方式:理解和預測社會演化,只有一個唯一的邏輯。但事實并非如此。數量和尺度的改變會造成系統隨之改變,進而產生不同層次上的規律。
有一個常常被人們誤解的詞,可以用來描述這個概念:“涌現”“突現”或者“層展”(emerge)。有人望文生義,以為“突現”便是創造和突變,甚至把它和神創扯上關系。實際上,“涌現”指的是不同層次的規律隨著量變積累造成的演化,這種積累可以是各種時間、空間或數量的積累。在布羅代爾的劃分當中,是時間的積累造成了長時段、中時段和短時段,但這既不意味著長時段的規律能夠完全指導短時段中發生的偶發事件,也不意味著短時段和中時段的規律能夠演繹出長時段的變化方向。正確的情形應該是這三者各有各的規律,彼此存在關聯,但尚未被深刻揭示。
有趣的是,在自然科學領域,“涌現”這一概念也格外重要。197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菲利普·安德森寫過一篇著名的文章,標題就是《多是不同(More is different)》。20世紀以來復雜性科學與非線性科學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就是探究涌現現象的規律,但至今尚沒有令人滿意的結果。有意無意之間,社會理論和自然科學正在探究同一只大象的不同側面。但是大眾顯然尚未接受這種思維,還原論式的本質主義與宏大敘事造成的線性歷史觀依然大行其道。社會輿論在個體與群體、暫時與永恒、眼前與未來的張力當中反復震蕩,每一個極端都以為自己掌握了唯一的真理。更加匆忙的邏輯是用這些未經驗證的事實判斷盲目代替了價值判斷,進而造成更大的錯誤。
理解社會的涌現,要求我們意識到時間與空間尺度為事件和歷史賦予的不同意義,不要輕易用特定層次上的規律處理另外層次上的問題。這并不是說,讓我們放棄對具體事實的仔細甄別和對深層規律的不懈探究,而是讓我們對這些甄別與探究的限度具有更清晰的認知。跨越無數的偶發事件,我們才能看到個體和局部在歷史中的地位,但同時,也不要忽略每一個鮮活的細節應當如何更好地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