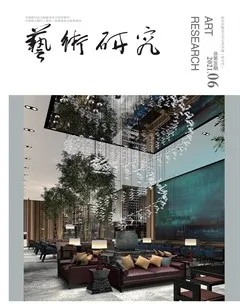從“神思”論看劉勰對陸機藝術想象的繼承與發展
李凡
摘要:《神思》是中國美學巨著《文心雕龍》中的一篇,也是其作者劉勰明確提出了關于藝術想象的美學范疇一“神思”并對其做了專門的論述,這在中國美學史上是具有重要意義的。“神思”論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離不開陸機的《文賦》但是相較于陸機而言,劉勰在藝術想象方面的理論又更為細致,更為深入,也形成了較為完整的理論體系。本文將從三個方面即“神思”的提出、藝術想象中靈感的重要性及獲得條件和藝術想象活動中情感活動的參與進行分析,從而把握劉勰在“神思”論形成過程中對陸機思想的繼承與發展。
關鍵詞:劉勰陸機神思藝術想象
如何理解劉勰所說的“神思”?在《中國美學史大綱》中葉朗先生在解釋“神思”時寫到:“所謂‘神思就是藝術想象活動。郭紹虞先生在其主編的《中國歷代文論選》中也寫到:“‘神思當是一篇完整的藝術想象論。以及,華東師范大學歸青老師在其《“神思”的含義和篇旨的概括一對〈文心雕龍〉“神思”的詞義學解讀》的文章中,從詞義學的角度來把握劉勰的“神思”,他認為:“‘神思中的‘神,指的是神奇;‘神思之‘思,指的是文思,或稱靈感、想象(一定程度上的)。因此,“神思”可以理解為藝術想象活動。而關于想象在藝術創作中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黑格爾在其《美學》中就提到:“真正的創造就是藝術想象的活動”“最杰出的藝術本領就是想象。而在中國古代關于藝術想象的問題早在一兩千年前就被陸機、劉勰等杰出的文藝理論家所認識。在中國美學史上最早將“神思”引入到藝術理論中的文人雖是劉勰,但是對于藝術想象活動的理論完成,并不是他所獨有的,劉勰也是在前人的認識基礎上才得以完成的。而在這些聯系中,其中又以陸機的《文賦》和他的《文心雕龍·神思》篇最為密切。清代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云:“古人論文,惟論文辭而已矣,劉勰氏出,本陸機氏說而倡論文心”。明確地指出陸機同劉勰二者在思想上的淵源關系,《文賦》是中國歷史上第一篇對于藝術創作的相關問題進行探討的專論,在藝術想象活動特征和藝術形象塑造等方面具有突出的貢獻。陸機在進行藝術創作的過程中有所體味到了“神思”進行了一些描述,但并沒有對這種體味做更為深入的理論梳理和探究。而劉勰在此基礎上,不僅提出了“神思”這一美學范疇,更是對藝術想象活動的理論做了更進一步的豐富與發揮。
一、藝術想象活動一“神思”的提出與完善
陸機在《文賦》中關于藝術想象在創作過程中的重要地位已經有所體味,“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鶩八極,心游萬仞。其致也,情曈昽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傾群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浮天淵以安流,濯下泉而潛浸。于是沈辭怫悅,若游魚銜鉤而出重淵之深;浮藻聯翩,若翰鳥纓繳而墜曾云之峻。收百世之闕文,采千載之遺韻。謝朝華于已披,啟夕秀于未振。觀古今于須臾,撫四海于一瞬。陸機主要是通過感性認識的方式,向讀者們展示了藝術創作者在進行藝術想象活動時所展開地廣闊的思維活動圖景,并且對進行藝術想象活動時的精神面貌與狀態進行了較為細致的描述。兩句“精鶩八極,心游萬仞”“觀古今于須臾,撫四海于一瞬”的表述就可以明顯看出劉勰已經認識到了藝術想象活動是具有超越時空限制的特性,但是相較于劉勰而言,陸機對與藝術想象活動的特性只是做了一般性的描述,而劉勰則做了更進一步的論述,將陸機的觀點由感性上升到了理性認識,提出一個明確的概念,即“神思”,并對這一概念做出了自己的定義。他在《神思》的開篇便寫到:“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閩之下,神思之謂也。”之后,他又對“神思”做了更進一步的解釋:“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指出了“神思”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思”,而是“文之思”。接著“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為妙,神與物游。”劉勰也指出了藝術想象活動可以突破時空局限的特性,創作者可以憑借想象活動聯想到千年之前,也可以觀察到萬里之外,超越直接經驗的限制,強調出了主觀精神在藝術創作過程的作用。如同前文所述陸機已經對于藝術想象活動的特性一“形在此而心在彼”雖有所體味,但是他是通過一幅生動的景象而表達出來的,并未上升到理性認識的層面。而在劉勰在面對這個問題時,他不僅向讀者們進行了具象的展示,更是進一步地做了一般性特征歸納和理論總結,并且提出了具有時代特色的美學范疇一“神思”,這對于藝術想象論的認識發展而言是具有進步意義的。
二、藝術想象的靈感一“神思開塞”的規律
1.“神思開塞”的理論探究
“若夫應感之會,通塞之紀,來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滅,行猶響起。方天機之駿利,夫何紛而不理?思風發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齒。紛葳蕤以遝,唯毫素之所擬。文微微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滯,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覽營魄以探賾,頓精爽而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軋軋其若抽。是故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雖茲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戮。故時撫空懷而自惋,吾未識夫開塞之所由也。”陸機根據自己在創作過程中體會到的關于藝術靈感問題的創作經驗,強調出創作者要重視靈感在創作過程中的重要性,要在靈感涌現之際進行創作。但是在面對關于靈感“通塞”問題時,陸機卻露出一絲疑惑寫到“吾未識夫開塞之所由也”。雖然陸機略帶一絲疑惑,但是能夠在他所在的時代,提出關于藝術創作的靈感問題,并強調出靈感在創作過程中的重要作用,不可否認這是具有進步性的,但他并未說出“通塞”即靈感有無問題的關鍵。而劉勰的可貴之處就是在此基礎上對藝術想象活動中的“通塞”問題做了進一步的說明,指出了其“樞機”與“關鍵”。“故思理為妙,神與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氣統其關鍵。物沿耳目,而辭令管其樞機。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關鍵將塞,則神有遁心。”“志氣”是與外物相感的產物,是一種不可抑制的強烈情感,支配著構思活動,成為把內在感知轉化為表達情感語言的“關鍵”。“辭令管其樞機”“樞機”則指文辭能夠恰當傳達創作者的情意,想要做到“物無隱
貌”就要“樞機”暢通。《神思》篇談到:“是以意受于思,言受于意,密則無際,疏則千里,或理在寸方而求之域表,或義在咫尺而思隔山河。”要想達到通暢的狀態,做到文能達意,就須要創作者有較好的文辭表達技巧。因此,劉勰借助對“物”“志氣”(情)“辭令”(文)三者關系的把握,“志氣”是指創作者的感情,感情影響著作品創作的走向。而“辭令”又是表達的媒介,沒有“辭令”“神思”便無法表達,“神”與“物”也無法達到溝通與融合,意象也無法進行創立,劉勰通過對這三者的表述明確了在藝術創作過程中想要達到“通塞”,就要做到思想與外物相稱,創作者的情思能夠被恰當的語言所表述,這便回答了陸機“恒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未識開塞之所由”的問題。
2.“神思開塞”的實踐探究
對于如何獲得“神思開塞”,劉勰和陸機的認識雖有相似之處,但劉勰卻并不贊同陸機“雖茲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戮”的觀點,反對創作靈感的關鍵是在于天機,并非是自己。面對陸機的實踐困境,劉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首先,在陸機“攬營魂以探賾,頓精爽而自求”的理論基礎上明確提出“陶鈞文思,貴在虛靜”,劉勰面對如何把握住“神思”提出了這就需要做到內心的虛靜。關于“虛靜”的理論,二位都有相關的文獻提及,但還是存在一定的差別。陸機在《文賦》開篇即言:“濘中區以玄覽,頤情志于典墳。”“典墳”相傳為我國最早的古籍,陸機借此來進行對前人優秀著作和文章學習的泛指。而“玄覽”出自《老子》“心居玄冥之處,覽知萬物,故謂之玄覽。”老子所言的“玄覽”確實有“洗清雜念而深入觀照”之意。但戚良德先生在《文論巨典:〈文心雕龍〉與中國文化》中認為:“陸機不是論創作的準備,而是描繪創作的發生;不是提出什么要求,而是說創作的沖動是如何產生的。”[8]而此處的“玄覽”陸機主要是想表達在自然界之中,創作者要覽知萬物,然后加以思考,這樣便會產生很多不同的思緒和感觸,而這將會給那些具備藝術創作旦有修養的人引發創作沖動,《文賦》原文也有相應的論述,其云:“遵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于勁秋,喜柔條于芳春;心懷懍以懷霜,志眇眇而臨云。”進而劉勰在《神思》中對“虛靜”說則做了更為明確的說明:“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渝五臟,澡雪精神。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澤辭。”“疏瀹五藏,澡雪精神”,創作者要排除內心的無限雜念,不斷凈化其精神得以舒緩,才能沉浸在無限的遐想之中。其次,創作者在開始進行想象活動之際,僅僅保持虛靜是遠遠不夠的。劉勰又進一步提出:“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怪辭。”除了“虛靜”外,創作者還需要進行“積學”“酌理”“研閱”“馴致”。即要進行有意識的知識積累,明辨事理,除此之外還要留心觀察生活、研究生活,再開闊自己的視野之后而不斷加深對事物的理解,不斷提高自身的感知能力,這樣才能順利進入到構思的環節,也是為靈感的涌現打下堅實的基礎。劉勰“虛靜”觀的研究重點是將放在主體的人格修養上來認識藝術想象,這對于我國古代美學在藝術想象論方面而言是重大發展與進步。
三、藝術想象的情感活動一“情曈昽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到“神與物游”“神用象通”
藝術想象活動的達成不僅僅只依靠“虛靜”的心境,也需要能夠對外物的有所感興。藝術想象活動是創作者精神活動和外在事物的形象貫穿在一起的。想象活動是基于主體的精神活動,受到主體感性活動的影響。“思涉樂其必笑,方言哀而已嘆”“遵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于勁秋,喜柔條于芳春……1慨投篇而援筆,聊宣之乎斯文。”“情曈昽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陸機認識到,在藝術創作的過程中,創作者的感情對于創作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它不僅是藝術構思的過程,也將自己的感情進行表達的過程,在這一過程外物的形象也逐漸清晰。但是陸機對于這種認識始終停留在感性的表達,始終沒有產生理論性的概括與總結。而劉勰卻不同,以其敏銳的理論思辨能力,通過“思理為妙,神與物游”這一命題表達出藝術的想象活動是需要和外在事物緊密相連。以及“神用象通,情變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應。”指出藝術的想象活動要與外部客觀事物相互溝通,思維活動和客觀事物相結合,才能孕育甚至引起情感的變化。“神與物游”表達出主體“神”和客體“物”要有機結合,“神用象通”則是對“神與物游”中主客觀的有機統一做了進一步的說明。另外,在關于形象對靈感啟迪作用方面,劉勰也是有自己的看法,《物色》篇日:“山沓水匝,樹雜云合。目既往還,心亦吐納”。“一葉旦或迎意,蟲聲有足引心。況清風與明月同夜,白日與春林共朝哉!”在中國的文學創作中,關于觸景生情的例子可謂舉不勝舉。正如普希金所說:“靈感是一種敏捷地感受印象的情緒。”藝術的想象活動會伴隨著創作者強烈的情感,由于不同的主體之間,感受有所不同,主觀情感也都有各自的特點,不盡相同。因此,“神思”在每個人身上的表現也是各不相同,繼而所產生的審美情感也不相同。這樣所產生的“審美意象”也就不同。劉勰相較于“天才”論而言,他指出了天才對于創作的影響,但并沒有將創作中出現的靈感等用于天才,而是在此基礎上更為強調后天勤奮的影響。提出了“人之秉才,遲速異分,文之體制,大小殊功”的觀點。在劉勰看來有的人快捷靈敏,文思敏捷;有的人深思熟慮,文思遲緩。但是無論是敏捷,還是遲緩,都可以進行創作。
關于“靈感”論,劉勰的論述是較為全面和系統的。劉勰在陸機有所體會靈感重要性的基礎上總結出了靈感通塞的“樞機”與“關鍵”,也進一步闡明靈感的來源是內心的“虛靜”以及對于客觀現實與知識的積累。正如曹順慶所言:“劉勰不但指出了靈感產生的客觀因素一生活修養與學習修養,而旦看到了靈感產生的主觀因素——虛靜、率志委和與秉才異分,還認識到了藝術靈感之特征一激情之勃發及其與形象思維之融合。”劉勰將藝術想象的理論又向前推進了一步。
結語
不難看出劉勰的《神思》與陸機的《文賦》是一種繼往開來的關系。劉勰的“神思”論是在陸機原有的基礎上又對其有重大的超越,陸機對藝術想象的探究還止于其各個現象的客觀描述,認識還停留在較初步的感性階段,他最大限度地切近了藝術創作的實際情形。他以精美的畫作向讀者描繪了藝術創作這一過程中的美,使讀者在現場感受到這一過程中美產生的真實場景。也正因如此,陸機在《文賦》中的側重點不是藝術創作的基本理論,他大量探討了在進行藝術創作過程中的具體情況。劉勰對于藝術想象問題的探究相對于陸機是系統而全面的,他在陸機的基礎上做了進一步的總結和歸納工作,從而對藝術想象有了更為全面的整體把握,也將這種認識提升到了較為高級的理性階段。他進一步明確了藝術想象活動的理論概念,論述了想象活動的內在情感與外物形象之間的關系以及對于藝術想象靈感的產生及條件,形成一個相對比較完整的藝術想象理論體系。紀昀對于劉勰做了這樣的評論:“自漢以來,論文者罕能及此,彥和以此發端,所見在六朝文士之上。文以載道,明其當然;文原于道,明其本然:識其本乃不逐其末。”劉勰在面對藝術現象時,不僅是“明其本然”,還能夠對其進行理性認識的上升,代表了藝術觀念開始自覺,具有其時代的意義。但陸機在藝術想象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也是不可否認的,沒有陸機《文賦》關于藝術想象理論大廈的地基,也就沒有日后劉勰《文心雕龍·神思》這座牢固而又結構嚴謹的宏美大廈。他們在各自的時代所做出的努力都代表著那個時代共同的特點,也都是中國文學史中的瑰寶。
參考文獻:
[1]葉朗.中國美學史大綱[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郭紹虜.中國歷代文論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3]歸青.“神思 ”的含義和篇旨的概括——對《文心雕龍》“神思”的詞義學
解讀[J].社會科學,2017(3).
[4]黑格爾,朱光潛譯.美學第一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
[5]章學誠.文史通義校注上[M].北京:中華書局,1985.
[6]張松如.老了·說解[M].濟南:齊魯書社,1998.
[7]陳鼓應.老了注譯及評介[M].中華書局,1984.
[8]戚良德.文論巨典:《文心雕龍》與中文化[M].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3.
[9]曹順慶.《文心雕龍》中的靈感論[J].
[10]黃叔琳.文心雕龍輯注[M].北京:中華書局,1957.
[11]戚良德.《文賦》與《文心雕龍》比較研究[J].濟南:魯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9(25).
[12]鄧曾耀.談文學創作中的想象[J].文學評論,1991(6).
[13]李海霞.從《文心雕龍?神思》談審美意象的生成[J].讀與寫雜志,2009(7).
[14]朱志榮.《文心雕龍》的意象創構論[J].江兩社會科學,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