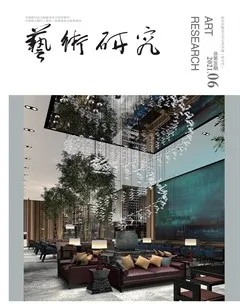山東煙臺棲霞穿花舞的文化形態
秦賀
摘要:棲霞穿花舞是目前煙臺唯一入選山東省級非遺名錄的燈舞類民間舞蹈。穿花舞表演者身著戲裝,左手持燈,在鑼鼓打擊樂的伴奏下,用平穩而輕盈的小碎步勾畫出一幅幅流動的場圖。穿花舞起源于全真教齋醮儀式,經草臺戲班轉化為秧歌戲前后暖場與謝場的手段,至當地民眾農閑時自娛的舞蹈藝術,歷經了由娛神到娛人的精神文化形態演變。穿花舞隱喻的契約精神與教化作用,暗含和諧追求,最終反映農耕文化下守望鄉土鄉情的制度文化形態。
關鍵詞:穿花舞文化形態齋醮儀式草臺戲班小碎步
棲霞穿花舞屬民間燈舞類,又稱戲燈穿花、跑戲燈、跳花燈,流傳于山東煙臺棲霞市的臧家莊鎮泊子村一帶,2013被列入山東省級非遺名錄。棲霞穿花舞擁有約八百余年歷史,發源于宋朝末期全真教的齋醮儀式,明清兩朝開始走向民間并被草臺戲班改編及發展,清末民初一度興盛,新中國成立后逐漸演變成農閑時自娛的民間舞蹈藝術,生動反映出鮮明濃郁的地域文化色彩。文化形態既有具象的物質形態,又有抽象的精神形態,還有物質與精神共育的制度形態,三者之間的關系是辯證的。物質形態離開精神形態便失去價值,精神形態沒有物質形態也無法存在,而使這兩種形態與人發生關系的,就是維持一定群體行為的制度形態。
一、棲霞穿花舞的物質文化形態
棲霞穿花舞一般在春節期間的農閑時節表演,從正月初一到正月十五,有時二月二龍抬頭還會表演。穿花舞最大的表演特色在于由表演者用小碎步按設定路線持燈流動,形成的閃閃發光的各種燈流。尤其在夜晚表演時,似一條舞動的長龍,不斷變化造型,“剪刀股”“四門斗”“龍擺尾”“蛇蛻皮”等為常見的構圖。
1.道具服裝
棲霞穿花舞由身著彩色戲裝的表演者右手持燈表演。穿花舞的道具由全真教法器演變而來,由上下兩部分組成。燈的下部分制作方法:用木條按照方形花盆制作框架,框架口和底均為方形,上大下小呈倒梯形,花盆底部楔入平放的十字架,十字架中間從下向上釘一根細釘子,用來插蠟燭尾部,并在框架上方靠近身體的一側木條中間位置加釘一根突出的短木板,以便表演者手握,框架外再糊上不同顏色的紙張,并繪以吉祥圖案。燈的上部分制作方法:用彩紙人工扎制簇花,花的形象包括荷花、月季花、百合花、迎春花、菊花等,花桿的安裝也在框架上方靠近身體的一側木條中間位置,與起手柄作用的短木板垂直。表演者的服裝有兩種版本。第一種表演者身著不同戲曲行當的服裝,如縣官、捕快、員外、郎中、書生、店小二、豬八戒、地主婆、媒婆、青衣等,人物并不固定。第二種表演者著裝分男女,男子統一為戲曲武生扮相,女子統一為戲曲青衣扮相,此時男女腰部均要系彩色綢子,表演時右手持燈,左手執綢前后擺動。相比較而言,第一種服裝歷史較遠,可觀性更強,戲劇色彩濃,采用度較廣。
2. 表演程序
棲霞穿花舞從明朝至清末民初,在以表演秧歌戲為主的草臺戲班的直接推動下,表演程序逐漸固定下來。穿花舞“在鄉間演出時,一般可分為‘開臺’和‘收臺’兩種形式。”?“開臺”就是在正戲開始前,為了招攬和吸引觀眾,以及活躍氣氛,表演者裝扮好之后,便會來到觀眾席空地表演穿花舞。表演時通常為男12人、女12人,選其中1人為“頭燈”,作用類似于領舞和指揮,其余23人均被視為“燈花兒”。“開臺”結束后,表演者將“燈”懸掛于臨時搭建的舞臺臺口兩側,或舞臺四周的木柱上。正戲結束后,為了表示感謝,草臺戲班班主會帶領表演者到村莊內部表演穿花舞稱為“收臺”。值得注意的是,穿花舞在表演前和后,都會進行一種叫做“謝茶”的禮儀性動作,即“頭燈”站在隊伍最前方,率領全體“燈花兒”將“燈”舉過頭頂后,兩腿交叉同時身體前傾下沉。穿花舞以構圖的流暢多變見長,動作并不復雜,主要目的在于渲染一種紅火而又熱烈的氣氛。棲霞穿花舞動作的突出特點為:在平穩而輕盈的小碎步基礎上,左手隨之前后擺動,右手中的花簇微顫而蠟燭不滅。
3. 音樂伴奏
棲霞穿花舞的音樂伴奏主要有鑼鼓打擊樂和笙胡吹拉樂兩類。穿花舞的純舞蹈部分以鑼鼓打擊樂為主,用來指揮舞蹈的快慢與節奏的急緩;以唱為主、以舞為輔部分以笙、笛子、二胡等器樂伴奏為主,以一男一女邊舞邊對唱的形式表演,唱詞的內容多為當地民間小調。最具代表性的當屬《十二月對花》,②該曲唱詞生動形象典故眾多,歷數十二個月,十二種花,并各配一個故事,具有較高的文學價值和傳播意義。值得注意的是,每一種花對應的月份,恰好是此花盛開的月份,此外還對花的顏色或形態進行了說明,每一個月配有的故事,又和花的顏色或形態密切相關。如“一月一迎春花一人見人愛一梁山伯與祝英臺”“二月一老公子(蒲公英)花一散須彎腰一孔夫子背書”“三月一桃花一滿果園紅色一桃園結義“四月一黃瓜花一搭架攀爬一財神劉海”“五月一小麥花一滿田地黃色一仙姑李三娘”“六月一小栗花一像灑珍珠一酒神杜康”“七月一芝麻花一像柳樹條一楚霸王項羽”“八月一蕎麥花一滿田地白色一尉遲恭訪白袍”“九月一小菊花一滿山坡黃色一快嘴李翠蓮”“十月一眉豆花一長到下霜一孟姜女哭長城”等,而“十一月一小雪花一漫天飄揚一王小摸魚”描繪當地冬日下雪場景,“十二月一蠟燭花一照亮家院一灶王爺”則是臘月點燈燭民俗的反映。穿花舞表現的就是身邊的事,蘊含民眾對生活的認識,這種上層建筑與農業生產息息相關的結果,主要源于當地以農耕為主的經濟方式。
二、棲霞穿花舞的精神文化形態
隨著時間的推移,棲霞穿花舞經歷了全真教齋醮儀式穿花舞、草臺戲班穿花舞、農閑自娛穿花舞三個階段,實現了由娛神舞蹈向娛人舞蹈性質上的轉化。當下,節慶、集會、展演上特色民間技藝表演是穿花舞呈現與發展的重要平臺,穿花舞已成為棲霞傳統民間舞蹈藝術的代表之一。
1. 仙道人文
棲霞穿花舞最初是全真教齋醮儀式的組成部分。膠東半島(地理概念,指膠萊河以東的山東半島地區,包括今煙臺、威海、青島所轄縣市區。)歷史悠久的仙道文化,為全真教在當地的興盛提供了豐厚的人文滋養。《山海經》中的“蓬萊山”和《史記》載的三神山(蓬萊、方丈、瀛洲)傳說就發生在膠東半島北部的渤海、黃海一帶。戰國時期齊國盛行的八神主崇拜,膠東半島占五位。秦始皇三次到煙臺尋求長生不老藥,并派齊人徐福率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仙。漢武帝九次到膠東半島尋仙求藥,公元前133年東巡時,見海中有蓬萊仙山,追而不得,便下令在海邊修筑蓬萊城,這是今煙臺蓬萊最早的建城記錄。“全真道雖由王重陽發籾于關中,但關中地區并沒有適宜全真道生長的土壤,膠東半島才是全真道真正的發祥地,膠東地區誕生并滋養了全真道的領袖群體一全真七子。”③王重陽在陜西傳道不暢,便來到膠東,丘處機在全真七子中第一個拜王重陽為師。丘處機在金章宗三年(公元1203年)接任全真教掌教,五年后,名滿全國,全真教逐漸進入歷史上的最鼎盛時期,金章宗為了籠絡教徒,賜丘處機在家鄉棲霞修建的道觀(公元1191年)名為“太虛觀”。在棲霞期間,丘處機“開化鄰里,立觀度人,時常往返于膠東各宮觀之間,主持齋醮等活動。”?齋醮少不了舞樂配合,“在齋醮儀式中,全體道士表演的群舞一般統稱為‘穿花舞⑤
2. 草臺戲班
當地草臺戲班推動了棲霞穿花舞的第一次性質轉化,即由神壇開始走向民間。齋醮儀式上的穿花舞,目的在于引導神靈降臨、慶祝神靈賜福、表現信徒喜悅。在丘處機的大力傳播及種種善行下,全真教已深入當地人心。同時,伴隨民眾的不斷參與,作為齋醮儀式手段的穿花舞逐漸走向神壇,開始走向當地民眾。最先規模化轉化應用的當屬當地草臺戲班,戲班以演秧歌戲為主,秧歌戲稱為正戲,常演的劇目有《武家坡》《鋸大缸》《打漁殺家》等,內容以勸人向善、和睦鄰里、孝順父母、兄友弟恭、勤儉持家等為主。限于信息手段制約,舊戲班不能向現今一樣鋪天蓋地事先宣傳,也沒有多少像樣的東西回贈鄉民,因此便出現了前文中提到的“開臺”與“收臺”表演。舊時草臺戲班在遇到有道觀或祠堂的村莊,還經常在表演穿花舞之前去祭拜,以表示尊重和祈禱。草臺戲班表演者的半職業化,加上走村竄莊的表演特點,穿花舞得以大范圍的發展與傳播,這一階段是穿花舞快速發展的黃金時期。與太虛宮齋醮儀式時道士表演的穿花舞相比,草臺戲班可與普通民眾面對面接觸,少了許多宗教神秘感,娛樂欣賞性反而占據上風。
3.農閑自娛
時代的發展進步促成了棲霞穿花舞第二次性質上的轉化,實現了由娛神到娛人的徹底改變。當下,穿花舞已不再是宗教和戲班的手段,而演變成了民眾農閑時自娛的民間舞蹈藝術,這是人們宗教認知水平提升與娛樂思維觀念轉化的結果。除了正月表演穿花舞之外,各種節慶、集會、展演等正在成為穿花舞表演的主陣地,如“中國·山東棲霞蘋果藝術節”“棲霞市燕九節廟會”“棲霞市龍王節廟會”“棲霞市秧歌比賽”等。據當地研究人士考察,輝煌時期的穿花舞在泊子村,“全村幾百戶人家,幾乎家家都有會跳穿花的人。”?值得注意的是,當下的廟會,多是政府組織,文化搭臺經濟唱戲,展示的是當地的傳統特色民間文化,把廟會看作神圣祭神儀式的已寥寥無幾。以棲霞市燕九節廟會為例,燕九節名義上是在農歷正月十九(丘處機生日)祭祀丘處機的活動,實際上又有多少當代人真的相信丘處機會下凡來保佑自己。趕廟會,無非是看光景、瞧熱鬧,了解民俗,甚至是品嘗美食而已。廟會中的穿花舞,雖然掛了祭祀丘處機的名,實際上行的卻是向外地人展示當地存在一種民間舞蹈的事,民眾所關注的,一層是祖輩傳下來的穿花舞不能消失,這是文化基因的符號;主要的另一層則是通過穿花舞,可以慰藉勞作之苦,滿足精神之需。
三、棲霞穿花舞的制度文化形態
制度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所形成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體系,具有群體性與服從性的特征。“制度文化形態是在群體認知基礎上建構的,是一定群體認知基礎上的情感使然。沒有群體的認知和熱情參與支持,制度文化則無法形成。”?棲霞穿花舞是農耕文化的真實寫照,是鄉俗的寫照,鄉情的描繪,鄉土的文化。
1.契約效力
棲霞穿花舞折射出的不成文的民間契約約束著當地民眾的部分觀念與行為。“高度同質化的社會意識,猶如強大的機械力將社會成員固定在相對恒定的位置,維持著社會的穩定……進一步講,在鄉土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相互的權利和義務雖然不見于成文法律,只存在于習俗之中,但為雙方熟知,具有法律效力。”⑧中國傳統農耕文化強調集體觀念,個體要服從于大多數個體的意志,個性也必須在共性中張揚,宗族家長制曾長期存在于廣大農村社會,隱性文化基因的傳承,會有意無意、有形無形的滲透到民眾行為中,包括藝術。“民間舞蹈往往作為鄉俗禮儀的一部分體現著民眾活動最本真的生命內蘊,具有生活和文化密不可分的特質。”⑨穿花舞在一定程度上可看作當地民眾思想意識和審美追求的物質化代言,鄉間約定影響著穿花舞的呈現,穿花舞24名表演者趨向統一的舞蹈動作就是最好的證明。從表演時間來看,民眾不約而同的知道要欣賞穿花舞,就要選擇在節慶、集會、展演的時候,不僅觀看要擇時,組織排練也是民眾提前約定時間而進行的。表演的場所一般固定在廣場,表演的人員也是約定好了旦經過專門訓練的,契約精神在穿花舞的完整表演程序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2. 教化作用
棲霞穿花舞促使行為習慣養成作用的發揮在于耳濡目染。學者張華用象數結構來解釋以秧歌為代表的漢族舞蹈的文化特征:“浩若煙海的秧歌場圖中,其最大的部分顯然與中國民間莊戶日常生活的事象物象,有著極密切的關系,象形表義,更配上泥土氣濃郁的名字……還有一個更值得注意的東西一構造一個場圖的菠花(山東叫法,指表演者行進路線的轉角處產生的一種自然的小圓圈流轉)的‘數'菠花的‘數’與菠花連接的不同方式所造之‘象'共同構成了秧歌場圖內在的象數結構。?”透過舞蹈內容和角色設置,如蛇蛻皮、龍擺尾、剪刀股等構圖,可以看出穿花舞的象,就是民眾日常生活所能接觸到的人、物、事,蛇、龍、剪刀等充滿生活氣息,都是穿花舞象形的來源。穿花舞的數,從1:23(燈頭與燈花兒)、1:11(1對與11對)、12:12(男與女)等數量設計,通過一幅幅流暢變化的構圖,如剪刀股2個菠花、四門斗4個菠花等,托物寓意,暗含社會秩序的行為守則。象數結構隱喻的是寓教于樂,藝術的教化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比語言文字說教更生動形象易于接受,民眾在自然與不自然之間運用著這一道理,通過排練與表演穿花舞,潛移默化的移植規矩、移植禮法,從而教化民眾遵守民間契約,從而維持特定群體在一定時空內穩定運行。
3. 求和價值
棲霞穿花舞的社會意識是揚善良、求和諧。穿花舞建立在民眾日常生活的基礎之上,首先是個體本身的和諧,即內容的真實性。身邊物、身邊事,即使是神仙傳說,也是代代相傳、深入人心的記憶,內心的真情實感,外化成舞蹈動作,所謂“蓋樂心內發,感物而動,不知手足自運,歡之至也。”(《毛詩·序》)善良與丑陋往往同在,穿花舞存在勾白臉的縣官角色,審丑的最終目的也是審美,旦是對比鮮明的凸顯善良美。第二,個體與個體之間的和諧。與人為善作為儒家傳統人際關系主張,深深地影響著民眾,夫妻、兄弟、婆媳等,穿花舞中都存在勸人向善,善惡有報的內容。同時,穿花舞男女對舞,通過一問一答,隱喻的是男女個體之間的陰陽協調的哲思。再次,穿花舞內在引導個體與群體之間的和諧。前文提到的宗族家長制是曾長期存在于廣大農村社會隱性文化基因,穿花舞的表演由公眾推選出燈頭,燈頭便成為表演時的領舞或指揮,燈花兒服從燈頭的舞蹈路線運行規則,說明了集體意識代表者的權威性。最后,不同穿花舞表演隊之間的關系并非功利,而追求的是“各美其美”,最終形成“美美與共”,穿花舞的表演者與欣賞者之間,表演目的與欣賞目的的內在要求的一致性,經濟學上的供需匹配恰好可以說明表演與欣賞之間的和諧關系。
結語
文化作為人類在社會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的總和,既包括物質文化,又包括精神文化,還包括依據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而建構的制度文化,而文化所呈現的形態即人性的外在表現。山東煙臺棲霞穿花舞持燈而舞、依約而動、合情而變,實現了由最初的全真教齋醮儀式的娛神,經作為草臺戲班暖場謝場的手段,到農閑自娛精神寄托的娛人的性質轉化,成為了當地民眾的傳統文化符號之一。同時,流淌千年的農耕文化血液里,穿花舞潛移默化地發揮著民間契約效力與行為教化作用,個體本身,個體與個體,個體與群體,群體與群體,統一于揚善良、求和諧的社會意識。棲霞穿花舞以其鮮明的特征、濃郁的風格,演繹著當地民眾對歷史的回味、對現實的贊美、對未來的期許。
注釋:
① 山東省文化和旅游廳.山東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普及讀本.傳統舞蹈卷.下[M].濟南:濟南出版社,2019.
② 李朝莉,如月.柄霞戲燈穿花:歷經數百年興而不袞[J].走向世界,2019(39).
③ 劉煥陽,陳愛強.膠東文化通論[M].濟南:齊魯書社,2015.
④ 支軍.膠東文化撮要[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6.
⑤程群.道教舞蹈研究[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7.
⑥ 林新忠.穿花舞:民間舞蹈的活化石[J].走向世界,2014(48).
⑦ 衛艷蕾.鼓之舞之:山兩晉南鼓舞的人類學研究[M].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17.
⑧ 劉建,趙鐵春.身份、模態與詁語:當代中國民間舞反思[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
⑨ 劉曉真.走向劇場的鄉土身影——從一個秧歌看當代中國民間舞蹈[M].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2012.
⑩ 于平.“秧歌”的淵藪與漢族民間舞的文化體征[J].南京藝術學院學報(音樂與表演),2019(4).
3465500589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