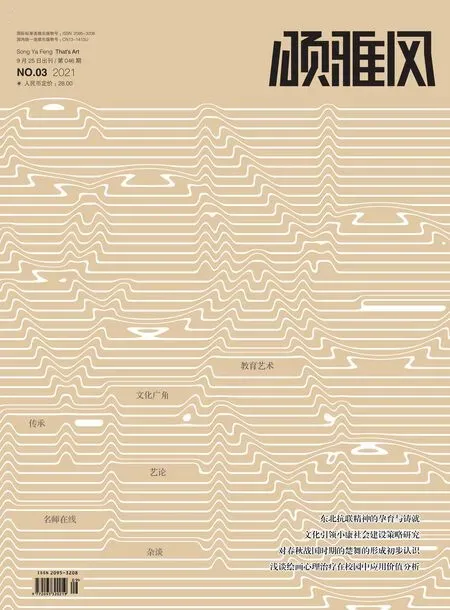淺談《尚書》中“人格天”觀念的政治實踐邏輯
◎籍翔
一、概述
本文中對人格天概念的定義主要基于《尚書》中有關“天”“神”“上帝”等概念的相關提法,而不著眼于傳統中國哲學中天命觀念的形而上解釋。天命觀念在中國哲學中是一個復雜而抽象的形而上概念,在《尚書》成書時期,天命觀尚未被構建成系統的理論體系。如果直接使用天命觀念來進行討論,有可能存在超前解釋與過度解讀的問題。
《尚書》中對“天”“神”等相關概念的描述更類似于停留在人格精神層面的具有主宰性的原始天神觀念。因此本文所探討的“人格天”觀念的相關依據主要來源于《尚書》中對主宰性的“人格天”“人格神”的直觀敘述,并輔之以借鑒有關“天命”觀念的基本理論。
在論述過程中,本文首先探討《尚書》中所敘述的“人格天”的具體內涵與特征、性質,然后將“人格天”在政治行為上的具體體現劃分為四個維度,四個維度分別是:敬德、保民、承祖、敬天。隨后闡釋四個維度之間內在的邏輯關系與其統治者政治行為的影響,從而形成了在“人格天”觀念支配下的政治實踐邏輯。
二、《尚書》中“人格天”觀念的具體內涵及其政治性特征
(一)人格化的“天”
《尚書》中的“天”可以被解釋為一種早期社會之普遍信仰,書中的“天”與人類早期宗教意義上的天神具有極大的相似性。然而先秦時代并沒有典籍對“天”進行系統的理論解釋,而是將“天”“神”與實踐緊密結合起來,通過兩者間的相互作用來詮釋“天”概念。
根據書中內容,“天”具備主宰性。比如《尚書·大誥》中:“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即指天命的絕對正確性,具有絕對的指引作用。
《尚書·大誥》一文中強調百姓安居樂業,社會矛盾消弭是為天意之所向。這種“人格天”可近似為原始社會的“神”,作為人間最高的主宰決定著政權的興亡更替。
然而“天”并不具有類似其他某些宗教的神所具有的創世屬性,《尚書》中從未強調過萬物由“天”所生,而無處不強調“天”與人的相互作用。這一特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古代政治文化中以人的實踐為核心關照的特征。
(二)政治性的“人格天”概念
《尚書》作為官方歷史文獻匯編,其內容主要記述了先秦時代重要政治人物在重大政治事件發生時的所言所行,其內容具有官方性的特征,因而具有十分顯著的政治色彩與明顯的政治宣傳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天”觀念的大量出現主要是在記述商湯伐夏桀這一歷史事件時開始的。
比如《尚書·湯誓》中的:“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又比如《尚書·湯誥》中的:“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
商滅夏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有記載且得到證實的,一個政權通過武力取締另一個政權的歷史事件,其在政治上具有重大意義。新的統治集團取得政權后,其政治合法性必然遭受普遍質疑。與此同時舊有的政治、社會秩序被瓦解而帶來的社會混亂亦需要一個強大的政治權威來重建新的政治秩序,來主持土地等財富、利益的重新劃分。同樣,在后來的武王伐紂中也具有這樣的時代政治需要。因而在古代社會具有強大公信力與主宰力的人格化的“天”就成為了論證這種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支撐。由此可見,《尚書》中的“人格天”絕不僅僅是原始宗教精神意義上的“人格神”,而同時也具有政治層面的結構性特征。天與人在相互的政治層面的作用中互相影響、互為補充。因此,根據現實政治實踐的需要,《尚書》中的“天”具有多樣的表現形式,意蘊精深。
同時,根據《尚書》文本所述,僅有君王擁有與“天”的直接溝通權。《尚書·西伯戡黎》中直言君王為“天子”,即上天之子。這意味君權神授,君王成為了天神之意的唯一持有者。雖說《尚書》中提到了專門負責祭祀事宜的專職人員,而隨著君王權力的擴大與中央集權的發展,天人溝通逐漸成為君主的特權。君王成為了知“天命”、知“天意”的唯一合法者。因而以馬基雅維利式的觀點可以認為,“天”“神”與統治者之間是相互塑造的關系。統治者利用人格化的“天”來獲得統治的合法性,而又因為統治者在建立合法性的過程中又定義了人格化“天”的政治向度,因此形成了“天”觀念下的政治傳統,這反過來又影響、約束了統治者的政治行為與實踐。
由此根據上文分析可知,具有濃厚的政治色彩是《尚書》中“人格天”觀念的重要特征。“人格天”的重要政治功能即為賦予統治集團政治正統性與合法性,由此建構其政治權威,塑造其政治形象。
三、“人格天”觀念在政治層面的四個維度
(一)修身敬德
《尚書》中明確提出,“以德配天”。具有主宰性的“人格天”依據君主的德行來做出相關的反應,并以此來引導統治者作出符合“德”的行為,并且“天”與“德”具有高度統一性。本文將“德”分為“內在的德”與“外在的德”。內在的德即敬德修身,這個維度主要強調統治者需要修養自身的“德”。而外在的德則為施行仁政、敬德保民。筆者認為《尚書》中的內在之“德”首先具有倫理性,進一步而言可以近似于中國哲學中心性論與境界論的雛形。
《尚書·咸有一德》一文中提出了“一德”這一概念。“一德”概念內涵極其豐富也十分復雜,古往今來許多學者都對其有不同的見解。在理學時代,這“一德”這一概念被賦予了更高更深的哲學意蘊,成了具有重要內涵的哲學范疇。本文不具體探討不同時代學術語境下的“德”概念,而將內在之“德”簡單視作人的自身修為與道德品性,而將探討的重點放在“天”“德”與政治正統性三者之間的關系之上。
《尚書·太甲上》提到:“天監厥德,用集大命”。
《尚書·太甲中》提到:“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尚書·咸有一德》中提到:“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
上述文本主要意旨都基本相同,即天僅佑有德之人成就大業、保有政權。《尚書·湯誓》《尚書·泰誓》與《尚書·牧誓》都記錄了新舊王朝更替時,新興統治者對舊統治者罪行的昭示。這種政治行為實為通過對舊統治集團失“德”的政治現狀的刻畫,來宣告“天”剝奪其政治合法性與正統性。而“天”之“德”不可一日失其所在,因而以“德”為載體的“天”之命就轉移到了新興統治者手中。由此,新興統治者便取得了統治的正統與權威。
(二)仁德保民
保民實為敬德的外在表現,并且《尚書》全書最為強調這一層面的“德”。
《尚書·咸有一德》中:“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不保,監于萬方,啟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
《尚書·泰誓中》中:“惟天惠民,惟辟奉天;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這些文段中,“天”與“民”可謂同體同感。統治者如何對待黎民百姓,便近乎于如何對待皇天上帝(即“天”)。又根據著名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出自《尚書·五子之歌》)一句不難得出結論:“天”“民”與統治者的合法性三者之間有著深刻的內在聯系。與上一維度的邏輯相似,“民”是為“天”的承載者,“天”通過“民”來獲知統治者的具體政治行為,又通過“民”來傳達“天”的意志。簡而言之,暴政即違背天道,惹怒“天”,而施行仁政則取悅于“天”,待“民”如何即為待“天”如何。可以說《尚書》中體現出的民本思想是極其強烈的,其甚至將民本思想提升到了宗教性的“人格天”層面,這使得以民為本的政治觀念被賦予了崇高的宗教地位,被統治者賦予了神圣的地位,這在世界政治思想史上是十分罕見的。
(三)承祖 嗣功
承祖與嗣功意為承繼祖上的功績與德行。
“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尚 書·伊訓》
“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尚書·盤庚上》
“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尚書·盤庚下》
“非先王不相我后人,惟王淫戲自絕。”《尚書·西伯戡黎》
“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尚書·大誥》
這些文段主要有兩種含義,一種是詰責當時的統治者不承繼祖宗的功德,肆意妄為;第二種是統治者自己的表白,意在說明其政治行為之目的在于繼承祖上的功德與業績。這一維度同樣與上文中的兩個維度的邏輯相似,“天”以“承祖”這一行為作為載體而賦予統治者以政治正統性與合法性。這實際上論證了政治正統性與合法性被繼承的可能性。這種認識與宗族宗法制度有著緊密的聯系。祖宗在駕鶴西去之后實際上與“天”直接關聯甚至與“天”在某種形式上融為一體,對祖先的崇拜與對“天”的崇拜具有深刻的內在聯系。反而言之,如若當朝統治者不再尊崇祖先,不再在政治行為上傳承祖先的功德與業績,那么就意味著政治正統性的喪失。
(四)敬天 祭天
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尚書·太甲上》
惟天無親,克敬惟親。《尚書·太甲下》
敬天與祭天即行為或精神上對“天”的直接崇拜行為,具體表現在話語和宗教儀式上。這一維度的內涵是十分簡單的,就是指在話語與行為上的敬“天”、畏“天”。是一種宗教層面的儀式程序或是表層的行為與言語準則。
需要注意的是,《尚書》中一些文本體現了《尚書》中對“天”態度與“天”的特征。
四、商紂王:我生不有命在天?《尚書·西伯戡黎》
這段文本主要意在體現商紂王的暴虐不仁,驕奢淫逸。大臣詢問他為何不謹慎行事、恪盡職守、敬德保民,而成就天下大治。商紂王回答說自己的命已被“天”所定,無須主動作為,這一回答有著強烈的宿命論色彩。顯然《尚書》對這種觀點是持否定態度的,這實際上體現出了反對消極宿命論而強調“天”與“人”之間相互作用關系的積極性作為觀念。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尚書·微子》
這段文本意為,在商紂王年間天下大亂,百姓食不果腹。于是人們前去偷盜供奉神祗的供物來充饑。若僅從宗教崇拜的角度而言,偷盜祭品的行為顯然是對“神”大不敬的。而“天”并沒有降罪于民,卻是包容了這種行為。民以食為天,這個文段深刻地體現了《尚書》中的民本觀念。由此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程序上與行為上的祭天與敬天并非最受重視的政治行為,實行善待蒼生百姓的民本政治才是《尚書》所體現的政治核心關照。
五、四個維度之間的內在政治實踐邏輯
“人格天”在政治向度上投射出的四個維度存在著密切的邏輯聯系。
作為邏輯的起點,“天”與“德”的內在體現與外在體現分別是統治者自我內在的德行與外在的仁政、愛民。外在的體現(即仁政)是內在認識與修為(自身的修德)的外部發展。內在的心性修為與外在的施政方針規范了統治者的政治實踐模式,而內在敬德與外在愛民的行為模式又源于對祖先政治遺產的傳承。
對先祖政治遺產的繼承最主要的體現是對祖先政治行為(即內在敬德與外在仁政)的歌頌與效仿,以此來重申家族統治的合法性與正統性,并同時宣告著當前統治者對家族正統性的繼承。對祖先的崇敬與對祖先功績的贊頌與繼承是氏族宗法制度的具體體現,這種行為不僅僅停留在上層統治者層面,也輻射到了古代社會的方方面面。這種對待祖先與家族的態度實際上是對傳統的重視,而對傳統的重視則是農業社會的重要特征。這種理念在政治層面的投射便是對政治穩定性的訴求。
最后,《尚書》中也具體探討了形式層面和具體操作程序層面的敬天。而根據其具體內容,這一層面的行為并非“天”的意志投射在政治層面的邏輯上的根本,反而是在整個邏輯鏈條上最不重要的一環。可以說,一旦完成了前三個維度的政治行為,則這一維度即成為了水到渠成的末流關照。
由此,在實現了內在敬德、外在愛民與承祖嗣功三個維度之后便實現了由“天與德配”出發而產生的“天”對統治者的要求,而實現了這三個維度之后,程序上與形式上的“敬天”則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從而最終實現了“天”的意志作用人的行為之上,再通過“以德配天”而完成了邏輯上的回歸。
六、輿論
本文將《尚書》中有關“天”的論述與具體政治實踐結合起來探討了“人格天”投射在政治層面的實踐邏輯。本文在論述中將書中的“天”“神”“上帝”等詞匯理解為“人格化的天”,并未從“天命”“形上天”等中國哲學的傳統范疇對“天”進行系統的理論性探討。同時,本文沒有借助相關學術成果探討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等有關《尚書》本身內容的相關問題,在對《尚書》內容的選取時并未深究,這可能導致對《尚書》中具體意涵不嚴謹的認識與誤解。并且,對《尚書》中“天”觀念在政治維度投射的劃分相對粗糙,這使得本文探討的內容不夠全面和深刻。
《尚書》之于中國傳統政治的影響可謂極其深遠。根據本文對書中“天”觀念在政治實踐邏輯層面反映的論述可以發現,“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的政治思想在較高的層次上被反復強調。《尚書》將民本政治思想上升到了“天”這一宗教概念之上,可以說這一現象在世界政治思想史上都值得注意。書中通過“人格天”的意志,將“敬德”“愛民”“崇祖”這三個行為指導性概念在邏輯上相互聯系從而實現了統一,而這三個行為又是古代農業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重要訴求,進而被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成為了政治實踐的重要準則。因而可以說,《尚書》中有關敬德保民的思想將仁政愛民提升到了宗教這一極高的層面,這也同時印證了《尚書》中體現出來的原始的敬天愛民的政治思想是中國古代民本政治思想的重要源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