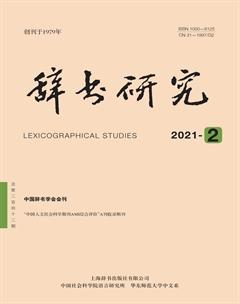融媒體視角下多模態詞典文本的設計構想



摘 要 隨著信息和通信技術的發展以及數字媒體在辭書編纂中的運用,多模態和融媒體詞典成為辭書界熱議的話題。但從發表的文章來看,它們大多模糊了媒體與模態的關系,所涉詞典并不具有真正的多模態特征。文章從紙質辭書的困境與數字化辭書的必然性入手,從三個方面來探討如何在融媒體框架下設計多模態詞典文本,闡釋多模態元素的釋義功能,包括詞典從平面媒體向融媒體的進化、融媒體框架下的媒體與模態的融合、多模態詞典文本的特征與數據結構等。
關鍵詞 融媒體 多媒體詞典 多模態詞典文本 多模態釋義
詞典與新媒體的結合使詞典的查閱終端發生了很大變化,這種詞典表象的變化倒逼詞典文本結構和釋義內容不得不發生改變,因為詞典只有多模態化和數據化才能適應融媒體的技術需要,且其改變程度也決定著詞典滿足數字時代詞典用戶需求的程度。(章宜華2019)本文從融媒體視角探討(外語)語文學習詞典如何進行模態與媒體的融合,并提出多模態釋義構想。
一、 紙質辭書的困境與數字化辭書的必然
詞典的核心問題是釋義,這是國際辭書界的共識。但釋義是一個復雜的問題,盡管詞典編者把主要精力都放在釋義上,但其問題仍是層出不窮。在紙媒時代,詞典學家們為了使釋義準確易懂,把使用了幾千年,但釋義模糊且容易引起循環釋義的同義對釋逐漸轉換成了“解述型”釋義,或以括注的形式對釋義詞進行各種限制,并在學習詞典中推行控制性釋義詞匯(controlled defining vocabulary:2000—3000基本詞匯)。釋義方式經歷了從詞匯對釋到短語釋義(phase definition),從短語釋義到句子釋義(sentence definition),又從句子釋義到情景釋義(situational definition)的過程;但循環釋義、內涵不彰,或釋義龐雜(釋義夾雜各種注釋)、理解困難,以及注釋信息冗余與文化信息欠缺、釋義過度與釋義不足、概念模糊與用法不清等問題同時存在。為此,詞典又增加了文化信息、用法說明和語義辨析等附加內容,百科性詞典和學習型詞典還引入了插圖。
但無論詞典學家如何努力,紙質詞典的“進化”變得越來越困難。譬如,“牛津”“朗文”等系列學習詞典雖然還在不斷修訂,但也僅是注釋方法的微調和注釋項目量的變化,難有大的提升,以致用戶對紙質詞典的興趣逐年下降。作者在多年前的調查發現,在接受型的語言活動中,大學生中使用電子詞典者居多,達52.23%。(章宜華2015)而近些年,隨著新媒體終端的普及,紙質詞典的使用率已經降至“冰點”。據張恒等(2017)118-120,155調查,經常使用紙質詞典的為4%,偶爾使用的占26%,極少使用的占51%,從不使用的有19%之多。而與此相反,91%的學生表示經常使用電子詞典,極少或從不使用的只有3%。這些數據基本符合當時辭書市場的現實;事實上,現在基本100%的學生都使用詞典App,經常使用紙質詞典的人大致占10%。而筆者接觸到的詞典學碩士生許多都沒有紙質學習詞典,需要參考時還要到資料室去借。在這種情況下,數字化就成為辭書發展的必然,也正是在2017年前后,我國專業辭書出版社開始加快數字詞典的研發。
二、 詞典從平面媒體向融媒體的進化
從信息技術角度講,當代詞典的發展要經歷從紙質詞典到電子化,再到數字化的過程;前者指詞典承載方式由物理媒介向電子媒介轉化,后者指將詞典中的圖像、聲音、文字等模擬信號轉換為數字信號,是信息數據化和網絡化的技術保證。從辭書表征的視角講,詞典則由平面媒體向多媒體、多模態和融媒體方向發展,而媒體融合的對象就是詞典的多模態表征。
早在20世紀90年代,紙質詞典電子化和網絡化已經開始。當時,國內市場上出現了一大批光盤詞典,如《康普頓交互式百科全書》《IBM智能詞典》《微軟書架》《韋氏新世界光盤詞典》《美國傳統有聲詞典》等,“牛津”“朗文”也先后推出了光盤和網絡詞典。盡管這些詞典大多是紙質版的電子化,體例結構與傳統詞典并無二致,但有的學者還是捕捉到了多媒體辭書的動向,并認識到多媒體有三個重要特性:用戶友好界面、查閱的交互性、信息的多樣性。(麥志強1994;夏南強2000)國內在90年代中期也推出了網絡詞典(如洪恩在線,1996),《漢語大詞典》光盤版(1997)等。但進入21世紀后,專業辭書出版社在“觸網”方面一直停滯不前,市場上流行的網絡詞典和詞典App大多出自IT公司,《金山詞霸》《有道》《海詞》《百度百科》等占據了在線詞典的主要市場份額。
《金山詞霸》(以下簡稱《詞霸》)是一款比較經典的電子詞典,最大的特點就是全文發音。最初同步發音效果并不理想,2005年引入英語培訓品牌視頻詞庫,用戶可與教師“面對面”學習,練習聽力、發音和語音語調等。2010年后,《詞霸》開始整本內置“牛津”和“柯林斯”等品牌詞典,但多媒體元素并沒有實質性改變,基本不用圖形或視頻,詞典的查詢顯示仍是平面格式,只是在左邊加入一列選擇鏈接(釋義、例句、搭配、辨析等)。《有道》和《海詞》也都宣稱是面向學習者編寫的,但在多媒體方面仍是以“讀音”為主。《有道》的體例和結構與《詞霸》類似,也內置了《柯林斯英漢雙解大詞典》和《牛津詞典》等內容,在少量實物詞條(如anchor、animal、car、leapfrog等)中配有圖片(參見圖1)。《海詞》主要是自編內容,沒有發現“插圖”,但每一詞條都提供了“釋義常用度分布圖”,在“欄目”設置和查詢選擇方面,可以通過選擇“詳盡釋義”“雙語釋義”“英英釋義”提取和顯示不同的釋義內容。
總體來講,上述幾種“學習詞”主要是信息的堆積,并沒有突出的多媒體和多模態特征,且詞典信息項的表述方法和質量都不太適合“學習”的需要。例如,《有道》和《海詞》都不分義項,把不同的意義混淆在一起,例如:《有道》的“leapfrog v.玩跳背游戲;越級提升;超過,超越;跨越(障礙)”,《海詞》的“anchor v. 拋錨;停泊;用錨系住;擔任(廣播電視新聞節目)的主持人”等。此外,釋義和標注錯誤時有發生,如“cheerleader(啦啦隊員)”被釋為“啦啦隊長”,“get on ones nerves(讓人厭煩)”被釋為“令人不安”,及物動詞“consolidate(使加強)”后出現了“合計金額”的名詞性“對等詞”等。《有道》的不少釋義是從網上提取的,錯誤似乎更常見一些,如purple patch本來是“幸運時刻”的意思,卻被釋為“辭藻華麗的段落”;purchase則釋為“……支點;(地產的)年收益;緊握;起重裝置”等;boardroom則釋為:“會議室;交換場所”;更奇怪的是informations被立為詞目[1],釋為“information的復數[2]”。這些詞典的一大特點是例證豐富,并且還做了分類,但大多是從網上抓取的,未經細致的篩選和區分,也無義項針對性,只是重復的堆積,對學習者的作用有限。
在學界,介紹和研究這類詞典的文章也不少,在知網檢索到有關《詞霸》和《有道》的論文分別為107和20篇,但極少有人把它們作為多媒體詞典來研究,批評其編纂質量的卻不少。從媒體性質來講,含有文本、聲音和圖像等內容的就可以叫作多媒體詞典,而上述詞典并沒有系統、平衡地運用這些媒體,所以其多媒體特征不強。
然而,語言教學界對多媒體和多模態詞典的呼聲很高,這是因為:1) 語言的自然習得和日常交流都發生在多模態場景;2) 通信技術的發展使人們的閱讀習慣發生了改變;3) 多元識讀與多模態語境被引入二語教學,對詞典提出了新的要求。近十年來,有關多模態詞典的研究引起學界重視,波蘭學者Lew(2010)提出了多模態詞典學(Multimodal Lexicography),黨軍(2010)也提出了“雙語詞典多模態化”。但他們的研究混淆了“媒體”與“模態”的概念,把復雜的模態簡化為了媒體。之后一些研究(閆美榮2011;羅永勝2012,2015;陳維紅2015)大多也是這個路子,有些則從功能語言學的視角來談詞典的圖文和語義關系(楊信彰2012;張春燕,陳思一葉2016),有的從界面設置或插圖位置來談多模態電子詞典(錢亦斐2016),都沒有涉及多模態元素的性質特征和語義表征機制。
那么,模態與媒體之間是什么樣的關系?模態的實質特征是什么?多模態元素的語義機制和釋義方法是什么呢?我們將在融媒體的框架下來討論這些問題。
三、 融媒體框架下的媒體與模態的融合
多模態源于系統功能語言學的多模態語篇分析,其主旨在于用各種語言和非語言符號來解釋語言的三大元功能:概念功能、人際功能和語篇功能,并指出不同模態可使用不同媒介來的表達。(Kress & van Leeuwen1990/2006;Martinec2005;Royce2007;Matthiessen2007)然而,盡管我們可以從功能的角度來研究詞典學(語篇詞典學),但詞典的語篇畢竟不同于自然語篇,當然也不宜直接用功能語言學中的多模態方法來描述詞典中的模態;因為詞典組織“語篇”的方法與自然語篇有很大不同。前者是“從具體到抽象”,后者則是“由抽象到具體”的認知過程。另一方面,詞典用戶是語言“學習者”,查閱詞典往往是任務驅動,所以必須要結合詞典釋義的實際來談多模態,而不是純粹套用語篇分析的方法。
(一) 多模態的必要性與可行性
多模態語義表征方法比較適用于二語學習詞典,因為成人在學習二語前已經具有比較成熟的母語知識系統,但缺乏或沒有二語的語感,離散的(不系統的)詞匯知識或孤立的解釋往往會受其母語負遷移或目的語規則過度泛化的影響,從而產生中介語偏誤。(章宜華2012)從這個角度講,二語學習者沒有一語自然習得的那種語言環境,這就需要我們在詞典中營造一種學習者缺乏的自然語境,而多模態釋義就是營造這種語境最有效的方法。多元識讀理論(New London Group1994,1996)的提出和多模態教學的實施從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證明了多模態詞典釋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多元識讀就是對多媒體和多模態信息的解讀能力(Williamson2005),已經被證明是一種二語習得的有效的學習方法(吳玲娟2013;張燕2018;高麗華2018),傳統的以讀寫為主的識讀能力在多媒體時代已不夠用了(胡壯麟2007)。
實際上,多模態交際方式普遍存在于我們的日常生活,也就是說,我們的任何交際都是多模態的,所以很容易被識讀和記憶。然而,傳統詞典受限于信息媒介的限制,只能是單媒體語境,查閱和理解有一定難度。進入融媒體時代,信息技術和媒體融合技術為多模態在詞典中的運用創造了條件,使各種模態可以與數字媒體有機結合起來,能大幅提升詞典釋義和使用效果。
(二) 多模態表征與承載形式
在詞典釋義中提供多模態語境或多模態元素有助于二語學習和用戶對詞典釋義的解讀。(楊信彰2012;錢亦斐2016)但模態的形成、承載和傳輸是一個復雜的語言認知和信息處理過程,涉及媒體、多媒體、多模態、融媒體諸多要素。語言認知始于感官(眼、耳、鼻、舌、身),通過光波、聲波、嗅覺傳感器、味覺傳感器和觸感傳感器獲得承載某種信息的圖形、聲音、氣味、口味、感應等意象圖式,這就是模態——一種在大腦中形成的心理實體(mental entity)。如果要表達這些模態信息、讓他人知曉,就需要借助特定的媒體,包括邏輯媒介和物理媒介,前者包括文字、聲音、圖像、圖形、圖表、色彩、結構、動畫、視頻和音頻流等,后者包括紙張、磁盤、光盤、網絡、云平臺、電波,以及各種終端設備(平板電腦、手機、閱讀器等)。從詞典學的角度講,語義模態(詞典信息)需要邏輯媒介來承載,而邏輯媒介則需要物理媒體來承載和傳播。在融媒框架下,這些元素可以得到有效融合(見圖3)。模態因為有媒體承載而具有一定的形式,而媒體則因為承載了模態才具有一定的意義。
(三) 多媒體與多模態的融合
總體來講,多模態首先是一個“感官模態系統”(sensory modalities)。(顧曰國2015)人們通過這些感官與客觀世界互動,并由此產生對應于多個感官的多模態心理意象,然后合成具有語言學意義的模態。具體地講,多模態是詞典用戶感知到的詞典信息與其指稱的實體發生映射而形成的心理意象,并觸發相應的心理空間形成“新”“舊”知識的觸發和聯想,最終形成被釋義詞的概念圖式,以特定的語音、聲音、圖形、顏色、動作、結構等來表達。這個認知融合過程(化學反應)需有兩個條件或“催化劑”:邏輯媒體和物理媒體——媒體是外在形式,模態才是知識內容,兩者需要有機融合(參見圖3)。
具體地講,概念圖式是抽象的、心理的,它需要用文字、聲音、圖像或音樂等來表達,通過網絡、電視、廣播等來傳輸。這就是模態與媒體融合的邏輯機制。這種融合機制可以有效幫助詞典編纂者建立多模態詞典釋義情景,特別是將來擬真模態和VR技術的運用,它可以模擬一切人類所擁有的感知功能,甚至連嗅覺和味覺也可以參與多模態釋義情景的構建,使學習者用戶能有身臨其境的感覺,使詞典的查閱變得“輕松有趣”。
事實上,在多模態環境中,所有的模態都參與意義的構建,(Kress & van Leeuwen1996/2006)因此可以有效提升二語學習者的識讀能力。在詞典查閱過程中,學習者從所指物→意象→圖式概念→文字的感知,要比從文字→意象→圖式概念→所指物的感知容易得多。譬如,一張企鵝在北極冰雪中的照片,或其行走姿態、鳴叫聲音比任何文字釋義的解釋都要清楚得多。中國文化特色詞,如“算盤”“旗袍”“二胡”“古箏”“秧歌舞”等,對于漢語二語學習者或母語初學者來說,語言解釋再配上圖像,或集聲音、姿態于一體的動態演示或演奏視頻,無疑會給用戶鮮明、深刻的印象(見圖4)。
四、 多模態詞典文本的特征與數據結構
釋義是詞典編纂的核心內容。如果我們認可這種觀點,那么我們所做的一切工作(包括語料、信息提取、提煉,以及表述方法和組織形式)都要圍繞釋義這項核心工作來做。概括地講,詞典釋義一是要從語料中提煉出詞義的“不變量”(invariant)(Wierzbicka1996),二是要用多模態來表征語義,因為這種形式可以強化詞典查閱中的語言輸入,增加用戶對詞典信息的注意力和可理解度(intelligibility)。
(一) 詞典釋義中的多模態元素
多模態元素指詞典釋義所涉及的各種模態表征形式,是媒體融合的對象。Bernsen(2008)從信息處理角度來劃分模態,共4類67種。Kress(2009,2010)從多元識讀的角度把模態概括為能夠產生意義的任何符號資源,如文字、圖像、顏色、版式、手勢、音樂、動漫畫等。Lew(2010)從詞典編纂的角度分為文字模態、語音頻模態和非文字模態,后者又分為:非語言音頻、插圖、圖像、圖形和視頻片段。國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現有詞典所用媒體的分析上(見本文第二節)。從詞典釋義的角度講,語義表征所涉及的基本模態有視覺、聽覺和(視)觸覺等模態元素,但這些基本模態各自又包含若干次模態,加之模態往往是以組合的形式出現,因此詞典釋義的模態表征還是很豐富的。例如,從視角上講有文字、符號、動/靜態圖形、動/靜態圖像,以及姿勢、動作、顏色、結構等;從聽覺上講有語音、靜/動態聲音、聲音符號等;從觸覺或視觸覺上講有動/靜態觸覺、視觸覺,包括形態、溫度、質感等其他通過肢體和視線接觸感知或體驗到的事物。
(二) 詞典釋義中的模態融合
需要指出的是,在多模態詞典中,文字釋義在較長一段時間內仍然是釋義的主要內容,但其他模態不再是文字的附加成分,所有的多模態元素都可以充當被釋義詞的意義表征。很可能在將來的某一天,現在的圖解詞典會演化成以非文字模態為主的多模態詞典,多模態與VT技術的融合可能慢慢會“削弱”文字釋義的作用,成為釋義的重要元素。多模態詞典的核心內涵就是多種模態在釋義中的交互融合,能在用戶大腦中產生模態之間的轉換,即一種感覺形態刺激引起另一種感覺形態,產生感官的互通和互補。用戶在解讀和接受釋義時調動的感官越多,事物在心智中形成的意象就更趨于真實,解讀的效果就更好。此外,用戶在查閱中經歷了多種媒體——模態的轉換和輸入,其記憶神經元的刺激就更深刻,其學習興趣就會更加濃厚。
許多電子詞典用了插圖和語音等,但它們之間并沒有必要的模態融合,故最多只能算作是多媒體詞典。嚴格地講,文字與圖形、圖像、色彩等都屬于同一種模態,但這些次模態之間的結合與互動、互補比單一的文字更能幫助用戶解讀語義。例如,由GOOCTO推出的視覺化詞庫(VISUWORDS),就是用思維導圖的方式構成多種次模態的融合,實現了詞匯—語義關系的形象化、可視化(見圖5)。
這是一種在線圖解詞典,輸入單詞便可得到該詞的各種意義以及與其關聯的其他詞類和概念,形成一個可視化詞匯—語義關系網絡。鼠標指向其中任意節點,便可顯示出該節點詞的意義。如圖6所示,名詞borrow有7個義項或有此義的其他詞及詞類,其中與borrow(動詞)/borrower/borrowing等有派生關系;與get/acquired/accept/take等有上下義關系,與lend/loan是反義關系;borrower與recipient/receiver有上下義關系,與lender/loaner是反義關系等。圖6中的方框是鼠標指向borrowing/adoptation節點顯示出的語義解釋。
這種以圖形、線條、形狀和色彩融合形成的“多模態”詞匯—語義網絡圖,既示出了語詞的義項、語義和義項關系,又說明了該詞與相關詞項間的固有關系,為二語學習者提供了一個系統的學習語境。
(三) 多模態元素的釋義功能
1. 文字模態
在融媒體學習詞典中,無論是單語和雙解釋義,還是雙語詞典的譯義仍會將文字作為主要釋義形式,但限制釋義詞匯會使釋義的準確性、辨義能力,以及簡潔性都受到影響,無法揭示出語詞的細微含義;因此,文字與其他模態的結合就顯得尤為必要。如對文字難以表達的內容可提供其他模態的支持,如以粗體字、背景色來凸顯釋義和例句中的核心成分,或與相關詞條的釋義或多模態信息項鏈接,用鼠標指向某一句式或搭配可激活相應的義項和例句等。還可以把釋義與語料庫鏈接起來,從中調取被釋義詞更多的真實用例,以幫助用戶理解和使用。
2. 語音模態
在紙質詞典電子化過程中,語音使用比較廣泛,由初期的詞頭發音發展到全句朗讀和視頻朗讀。手持式電子詞典還設置了一些“聽力練習”“跟讀練習”等動態語音功能,但未做好互動融合。在融媒體詞典中,語音模態表征的對象為詞目詞、例句和人人/機交互。在信息互動方面,詞典可以語音領讀,用戶可以跟讀并錄音,做對比分析、糾正發音。語音還可與視覺模態相結合,在朗讀例句時相應的閱讀部分有圖標或色彩跟隨移動,并與譯文關聯,讓聽覺和視覺模態共同作用于用戶的信息解讀,以“語音—形態”的融合加深記憶。
3. 聲音模態
指語言以外的聲音,是某些詞的主要語義特征之一,如動物、昆蟲、鳥類、禽類、樂器、音樂、音頻信號、警示聲信號,機器和儀器的聲音,以及其他人造物聲音。聽覺模態與視覺模態融合形成視頻,可以表征語義,如“虎嘯”“獅吼”“海豚音”等用文字難以描述,若配上“圖像+聲音”的視頻片段會給用戶深刻印象。像“琵琶、揚琴、古箏、馬頭琴”等樂器,“西皮、二黃、慢板、快板”等京劇唱腔,“火車鳴笛(起動、停車、進站等信號)”,像cackle、clank、clink、buzz等擬聲詞采用多模態融合釋義,不單是文字釋義的重復,更是認知的深化。
4. 圖形模態
指各種非語言符號以及顏色和結構等。視覺模態之于文字,如畫龍點睛,勝過千言萬語。語言伴生符(字體、字號、粗細、顏色)與文字直觀融合,已在學習詞典中廣泛使用,體態符號(動作、手勢、表情、視線、姿態等)往往以(連續)圖片、動圖、動畫和視頻片段來表示,動作性符號、聲音符號、圖形/圖像符號等是真實的模擬,而目視符號(地圖、標識等)則是概括的約定。須指出的是,圖形和圖像的功能和釋義效果是不一樣的,如鳥的照片反映的是其“原型”,但它也源自范疇成員,包括了很多個性細節(屬于意象),無法涵蓋其他范疇示例的特點;而線條畫則是眾多鳥實例的抽象(屬于圖式),其釋義概括性更強(見圖7)。
在視覺模態的組織中,可運用范疇化和格式塔心理學的方法,借助部分與整體關系來凸顯個體特征。例如,《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光盤版)往往把同一范疇的插圖整合在一起,點擊圖中的單詞便可彈出其釋義窗口(見圖8)。這樣,通過同類比較、總體把握與個別凸顯,可以提高用戶解讀的效果。但由于該詞典沒有真正從模態融合的角度考慮,文字與插圖相互獨立,檢索不到flower、bud、stalk等詞條與這個圖組的關聯。
5. 觸覺模態
指靜/動態物理接觸感和視接觸發生的感應模態。前者主要反映在詞典使用終端圖形用戶界面(GUI)上,通過鼠標、手指和聲音來觸發詞典的查詢功能和詞匯—語義之間的鏈接,后者通過視線感知查詢顯示的內容,包括物體狀態、溫度、質感等內容。詞典文本中所有的模態信息都在這個界面上交互和/或融合。因此,圖形用戶界面的構建是詞典發揮多模態效用的關鍵。
(四) 融媒體詞典的特征和數據結構
如果要真正做到媒體融合,多模態詞典就無法像紙質詞典那樣有明確、固定的文本結構,因為各種模態的編碼、存儲和表述方式不一樣,一個詞條的信息內容復雜且信息量巨大,利用平面直觀的方式排列是不現實的。而現在的電子詞典只是載體發生了變化,其信息組織和呈現仍然是平面結構,因此不能算作多模態詞典。下面我們談談基于融媒體技術的多模態詞典的特征和數據結構。
1. 詞典的使用環境基礎
信息化時代,詞典用戶全民化、使用需求標簽化、信息查閱碎片化、查閱路徑網絡化,用戶使用習慣的改變決定了詞典使用終端的電子化和多樣化,以便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用任何數據終端都能查閱,且能快速、準確地獲得任何領域的內容,滿足其不同語言活動的需要。詞典使用終端不再是固定的,而是因時、因地、因人而異的,其載體可以是紙媒,也可以是電腦、平板電腦、手機或電子穿戴用品。
2. 詞典文本構成要素
數字化時代,人們對信息的需求個性化、選擇豐富化。用戶這種需求的改變決定了詞典收詞和文本要素的改變,即收詞要規模化、綜合化、系統化,詞典釋義成分多模態化,詞典信息的組織數據化。各種模態信息須高度融合,能跨媒體或全媒體傳播。轉化的核心就是詞典釋義元素——由單純是文字向多模態轉向,語音、聲音、圖形、圖像、色彩和感應等都作為重要表征形式參與詞目詞的釋義。
3. 詞典文本結構框架
融媒體時代,詞典文本元素和使用終端的多元化決定了詞典信息要集群化、融合化、生態化。集群化指要模糊類型概念,逐步把各類詞典集合在一起,為所有用戶提供個性化使用體驗;融合化指編纂主體融合、詞典資源融合、詞典類型融合、多模態—多媒體融合;生態化指詞典各類用戶可以根據自己的需求準確、快速地獲取所需信息(不需要通篇瀏覽尋找),或與詞典文本或編者進行互動,模態與媒體、用戶與編者相互作用,形成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生態環境。
根據上述特征,融媒體詞典是運用專門的工具,按多模態—多媒體融合和個性化查閱需求對詞典進行數據化處理。具體編纂結構有以下幾個特征:
1) 詞典編纂不再是以詞頭特定順序組織編寫,而是借助計算機輔助編纂系統中的范疇化分類模型來構建任務分配體系,根據語詞的形態、詞族、概念、主題、語用,以及屬性、行為、事件和事物等范疇來組織宏觀結構,運用任務管理平臺按既定分類進行編纂,以及進度和質量監控。
2) 詞典的基本編寫單位不再是完整的詞條,而是詞典微觀信息項中的某一項或幾項數據內容,如形態變化、語音、語法和句法注釋,義項確立、釋義、配例及例句翻譯,各種附加信息、模態信息等。一個編者可負責若干字母,甚至整部詞典全部詞條的某項或多項內容。文字和符號、語音和聲音、圖形和圖像,以及動畫和視頻片段等構成不同的元數據,以便融合處理、組織成多模態語義表征。
3) 詞典信息不再是有限的、類型分明的供給,而是模糊類型、全面提供多模態信息,包括語言屬性、語域屬性、專業屬性及其顯示度,盡力滿足各層次用戶或系統化,或碎片化的信息需求;從視覺、聽覺、觸覺的角度建立文字與聲音、文字與圖形、用戶與文字/圖形/聲音、用戶與編者、用戶與用戶等的互動互補,從而在詞典中構建多模態話語情景。
4) 詞典信息不再是按詞條完整呈現的平面文本結構,而是按關系(SQL)或非關系型數據庫(NoSQL)結構組織和存儲的多模態數據。同一詞條的信息項(如注音、屈折變化、基本注釋、釋義、例證等)要被切分成相對獨立但與詞目詞關聯的數據元,分別與同一詞典中其他詞條的同類數據存儲在相應的數據表格中,并自動進行特征標注。每一個數據化的詞典信息項都被計算機賦予一個或若干個標記,以便為各類用戶提供個性化的精準服務。
25. Martinec R. Topics in Multimodality. ∥Hasan R, Matthiessen C, Webster J.(eds.) Continuing Discourse on Language(Vol.1). London & Oakville:Equinox, 2005:157-181.
26. Matthiessen C.The Multimodal Page:A Systemic Functional Exploration.∥Royce T D, Bowcher W.(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Analysis of Multimodal Discourse. New Jerse & London: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007:1-62.
27. New London Group. A Pedagogy of Multiliteracies:Designing Social Futures.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1996(4):4-75.
28. Royce T. Intersemiotic Complementarity:A Framework for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Royce T, Bowcher W.(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Analysis of Multimodal Discourse. New Jersey & London: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007:62-110.
29. Wierzbicka A. Semantics:Primes and Universal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258-270.
30. Williamson B. What Are Multimodality,Multisemiotics and Multi-Literacies:A Brief Guide to Some Jargon. NESTA Futurelab,2005.(Online. Accessed 23 Oct. 2015. http:∥www.Futurelab.org.uk/viewpoint/art49.htm.)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文科基地/詞典學研究中心 廣州 510420)
(責任編輯 馬 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