摁住樓市“虛火”
◎ 文 《法人》特約撰稿 清和
最近幾個月,房地產調控政策頻出,包括房地產貸款的“兩道紅線”。為抑制樓市“虛火”,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副部長倪虹帶隊赴上海、深圳等地調研督導房地產市場情況。機構統計數據顯示,去年年內累計房地產調控政策次數已達97次。一些人擔心,樓市會陷入越上漲越調控、越調控越上漲的“老怪圈”。
目前,“牛頭熊身”是資產價格分化頗為形象的描述。這些因素,都將對未來房地產短期與長期產生影響,本文將從調控政策、貨幣政策及地方債務三個角度,解讀2021年房地產市場走向。
大熱必調與稍冷必穩
去年,房地產貸款增速放緩:今年伊始,經濟延續了去年“資本通脹,實體通縮”的趨勢,加劇了資產價格的分化。實體低迷下的貨幣沖擊,促使全球金融市場“抱團扎堆”核心資產:美股、港股大幅追高科技類股票;A股追高消費類科技類白馬股;數字貨幣市場追高比特幣;房地產市場追高上廣深核心地段。
繼深圳房價大漲后,廣州、上海、北京樓市亦有“抱團漲價”“暴力拉升”之勢。緊接著,政府出臺了一系列調控:住建部要求穩地價、穩房價、穩預期;廣州傳出限制房地產信貸額度;接著,四大行房貸利率全線漲價;上海出臺“滬十條”,整治假離婚炒房,嚴控消費貸資金進入地產市場;深圳嚴查新房違規打新,嚴格限制購房資格。可以說,每次樓市調控都會引發市場躁動。
目前,我國樓市調控采取“一城一策”,其中關鍵性政策是“限流”。2020年的最后一天,央行和銀保監會發布了《關于建立銀行業金融機構房地產貸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通知》(下稱“通知”),自2021年1月1日起正式實施。根據通知,兩部門將根據銀行資產規模及機構類型,分檔對房地產貸款集中度進行管理,設置了房地產貸款占比上限和個人住房貸款占比上限,此為房地產貸款的“兩道紅線”。其中,房地產貸款占比上限最高為40%,最低為12.5%;個人住房貸款占比上限最高為32.5%,最低為7.5%。
“兩道紅線”的設置,相當于給房地產行業的流動性限量。廣州房貸利率上漲以及個別銀行近期“限貸”,都與這一政策相關。“兩道紅線”發布的4個月前,監管部門曾給房企設置了“三道紅線”,以此約束房企的債務率。此次“兩道紅線”雖未直接針對房企,實際也是間接調控樓市之舉。至此,中國樓市“五道紅線”壓身。
那么,如何理解“兩道紅線”政策以及2021年房地產趨勢?
這一政策本意應該是金融監管部門試圖為金融市場設置一道“防火墻”,謹防房地產風險外溢到金融市場,同時由于“墻不算高”,其影響在貨幣緊縮時才能體現出來。今年3月2日,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在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房地產領域的核心問題還是泡沫比較大,金融化、泡沫化傾向比較強,是金融體系最大“灰犀牛”。

郭樹清強調,很多人買房不是為了居住,而是為了投資投機,這是很危險的。但2020年房地產貸款增速8年來首次低于各項貸款增速,這個成績來之不易,相信房地產問題可以逐步緩解。
2021年,中國房地產調控的態度是“面和水的關系”,即一線城市的調控是“大熱必調與稍冷必穩”,不會改變穩房價的目標。大熱時,北、上、廣,深會出臺一系列針對“炒房”的政策,打擊假離婚、假合同、假證明,嚴控購房資格等等;稍冷時,政策面會適當寬松。另外,貨幣政策也是如此,大熱時,監管部門會督促銀行嚴查實體資金流入房地產。
貨幣轉向與通脹預期
在我國當前土地制度和財政制度下,只有一種調控可能改變房地產趨勢,那就是像新加坡一樣,利用國有土地優勢大規模建設保障性住房。樓市調控只會改變局部短期市場,不構成趨勢。就外部因素而言,影響房地產的最大變量是美聯儲的政策轉向。全球流動性風向標是美聯儲,美聯儲在2021年的緊縮政策(預期)將會對國內房地產產生一定影響。
目前預計,美聯儲將會在觸及2.5%—3%通脹率目標時結束寬松政策,以避免通脹威脅到經濟穩定性。但是,結束寬松政策并不意味著直接進入緊縮政策。因此,2021年的貨幣政策轉向預計相對溫和,與2015年和2016年類似。
雖然美聯儲的溫和轉向不會對國內資本市場造成太大威脅,但壓力仍然存在于兩個方面:一是國內的結構性資產泡沫和債務風險;二是去年開始連續上漲的人民幣匯率。相信中國的貨幣政策會在美聯儲緊縮預期增加時,提前做好緊縮準備。
通常,大量外匯收入會增加外匯占款,從而增加市場流動性。但是,2020年底的外匯占款與外匯收入形成背離。2020年銀行結匯順差10783億元人民幣,但外匯占款減少了1009億元人民幣。
中國人民銀行1月12日公布的數據顯示,2020年12月末,廣義貨幣(M2)余額218.68萬億元,同比增長10.1%。12月,人民幣貸款增加1.26萬億元,同比多增1170億元。2020年末,社會融資規模存量為284.83萬億元,同比增長13.3%。專家表示,2020年12月的金融數據顯示,貨幣政策正在向常態化回歸過程中,增速均有所回落,社會融資規模存量及M2增速等指標向名義GDP增速靠攏的趨勢正在形成。
上述數據說明,政策層面已在為可預期的轉向做準備。在美聯儲政策未轉向前,央行也會保持一定流動性,支持地方盡快消化債務風險,防止貨幣轉向觸發危機。2020年下半年,海外市場大量購入中國商品和證券的同時,國內一些資本意識到流動性溫和拐點的絕佳機會來臨。所以,2021年上半年將處于大進大出的財富洪流時代。
如果下半年美聯儲的政策溫和轉向,全球貨幣政策將跟隨,高泡沫、高債務和高匯率的國家壓力率先凸顯出來。隨著國際經濟復蘇,歐美及東南亞商品供應增加,中國外貿出口會有所回落,國際資本回流美國,人民幣下行壓力預計會增加,持有外債機構還債壓力也會增加。
可以預見,溫和的考驗將從下半年開始,劣質市場與結構性泡沫是可預計的風險。隨著流動性的回落,“兩道紅線”將增加房地產市場的流行性壓力,北、上、廣、深的住房信貸利率可能會上升。
地方債務與金融開放
貨幣是中國房地產的一個支撐,財政是另外一個支撐,而且是更為根本的支撐。長遠來說,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未根本性逆轉前,穩房價的目標不會改變。據統計,2020年全國賣地收入首破8萬億元,同比增長15.9%。
8.4142萬億元,這個數字是自1987年9月8日以來,中國33年土地出讓金收入最高紀錄,可謂“一個新的市場奇跡”。值得一提的是,三分之二賣地收入,主要來源于一二線城市,全國300個城市的土地出讓金總額高達5.9萬億元。
從政府財政數據來看,2020年收入下降,全國財政總收入為18.28萬億元,全國城市賣地收入占全國財政總收入的46%,占地方財政總收入的84%。可見,新冠肺炎疫情加大了土地財政的依賴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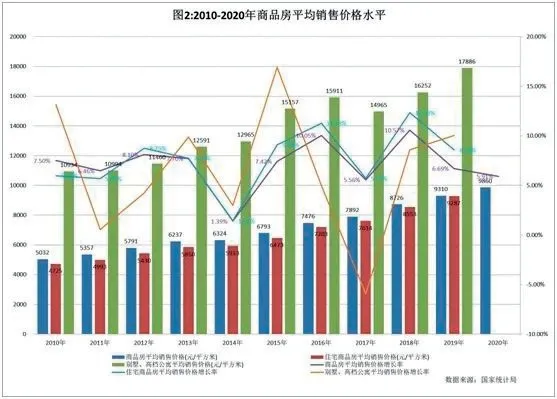
土地財政背后是迅速增加的地方債務。近幾年,中國地方債規模迅速增加,地方債務余額在2017年超過了國債余額。值得注意的是,最近3年,地方債中的一般債券發行規模持續下降,而專項債規模快速增加。2020年,地方一般債券限額只有9800億元,專項債限額達到37500億元。
一般債券是由地方政府稅收來償還,專項債是由地方政府基金收入來償還,主要是賣地收入。專項債的平均周期目前是5年,未來3至5年是地方政府的還債高峰期,這意味著未來幾年,地方政府還得依賴賣地來償還專項債。
去年年底,財政部原部長樓繼偉曾在“新格局下政府債可持續發展研討會”上表示,目前地方政府一般債券(額度)給的太少,而專項債券額度給的太多。“十四五”時期需要優化政府債務結構,提高地方政府一般債務占比,降低專項債務占比。
未來幾年,地方債尤其是大量的專項債,將持續依賴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這決定了未來幾年地方政府的樓市調控基調,即穩房價。
在2020年的樓市分析中,將地方債務視為房價穩定及上漲的底線,將金融開放視為抑制房價上漲的高壓線。在開放性市場中,資本流動會抑制本土房價單邊上漲。
那么,金融系統是否會繼續支持財政系統的土地財政?當全球貨幣溫和轉向時,財政系統的擴張壓力與金融系統的風險壓力會出現一些沖突。在剛性泡沫時代,債務的遠期風險是貨幣擴張,而短期風險是流動性枯竭。如果地方債務風險壓力增加,金融系統不得不施以援手。這兩個系統的博弈,勢必將影響房價走勢。

